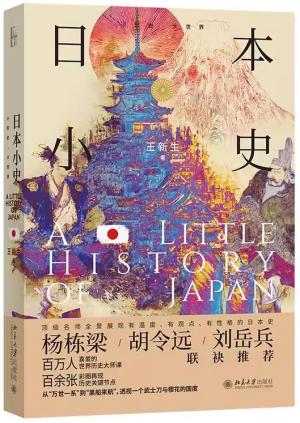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索恩丛书·汉娜·阿伦特:20世纪思想家
》
售價:HK$
75.9

《
“节”与“殉”——八旗制度下的妇女生活与婚姻 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3.6

《
城市群高铁网络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与规划应对
》
售價:HK$
108.9

《
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全两册)
》
售價:HK$
3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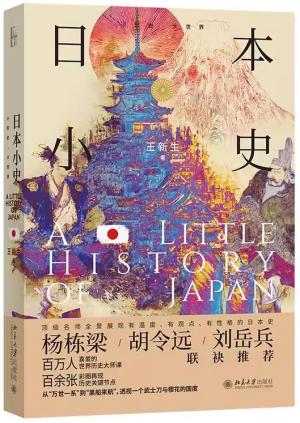
《
(小历史大世界)日本小史
》
售價:HK$
86.9

《
慢慢变成大人 一部颠覆传统教育观的权威指南 驳斥传统育儿观念,直击教育核心 直面儿童成长中的深层议题
》
售價:HK$
75.9

《
口腔临床病例精粹
》
售價:HK$
107.8

《
下潜,潜入夜海
》
售價:HK$
74.8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从拉康派视角介绍了精神分析技术。不同于其他论述拉康的学者,芬克博士通过大量的临床实例详细阐述了他所实践的拉康派的倾听、提问、标点、切分和解释技术,并且使用自己案例中的临床片段,详细地检视了对梦与幻想的工作,以及对转移和反转移的处理。芬克博士不断勾勒出精神分析其他流派和拉康派之间的差异,批评了精神分析中越来越普遍的“正常化”的态度;而且呈现了拉康派治疗神经症技术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以及治疗精神病的全然不同的方法。拉康派强调语言的各个维度,但一直被认为艰涩,本书弥补了这一遗憾,以大量案例展现了拉康派临床的主要方面。
|
| 關於作者: |
布鲁斯·芬克
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及督导分析家,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博士。他曾在法国巴黎的弗洛伊德事业学派(雅克·拉康逝世前不久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受训七年,如今亦是其中一员。1993年到2013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匹兹堡杜肯大学教授,也是匹兹堡精神分析中心理事会成员。芬克博士已将拉康的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包括《著作集:首个英文完整版》《研讨班VI: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VIII:转移》《研讨班XX:再来一次》,他还出版了诸多拉康学派著作,包括《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拉康派精神分析临床导论》《弗洛伊德临床导论》《拉康式主体》、《拉康论爱》《句读拉康》《反理解》(2卷本)等。
张慧强
精神分析家,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行知学派编译组成员,长期致力于精神分析实践与文献翻译工作。
徐雅珺
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硕士,精神分析行知学派成员,艺术项目《一个人的社会》发起人之一,从事临床工作与精神分析和当代中国的研究。
|
| 目錄:
|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倾听和听见
第二章提问
第三章标点
第四章切分(弹性时间会谈)
第五章解释
第六章对梦、白日梦和幻想进行工作
第七章处理转移和反转移
第八章“电话分析”(精神分析设置的变动)
第九章并非旨在使人正常化的分析
第十章治疗精神病
后记
索引
|
| 內容試閱:
|
前言
我所学到的一切都源于我的分析者,包括我对精神分析的了解。
——拉康(Lacan,1976,p. 34)
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分析关乎的并非技术,而是分析家在分析过程中推动分析者所做那类工作。我的推测是,不同的分析家可能会用到很不一样的技术来推动差不多类似的工作。但是我和美国的不同精神分析团体的对话越多,我就越是确信如今在协会与研究所教授的那种技术不仅仅是未能推动我所说的分析工作,而且是在设置障碍。在我看来,当代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已经丢失了弗洛伊德、拉康和其他先驱者们的诸多基本洞见,而且采纳了源自心理学,尤其是发展心理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否认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如无意识、压抑、重复冲动等基本的原则。
因此我斗胆准备了一本技术入门书,旨在牢靠地保留那些基本原则的洞见。在这里我关注的是我所认为的基本技术(尽管这可能和很多临床工作者认为的并不一样),而不是对基本原则的冗长的理论上说明。出于这种考虑,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毫不了解拉康以及大体上对精神分析所知甚少的读者。我希望这本入门书对初学者以及更老练的临床工作者来说都是有用的,虽然是出于不同的缘由。
应该在开头说清楚的是,本书列举的一些技术对我来说很有用——我发现我能够获得我相信是精神分析家
x通过采用这些技术而试图获得的——不过它们不太可能适用于其他人,或者说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有用。我们也得记住,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是对每一个人都行之有效的。然而,基于我十多年来对非常之多的临床工作者(临床心理学毕业生、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家)的督导经历,我有理由相信,那些技术可以帮到很多实践者,常常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相当彻底地转变他们的实践方式。这就是我决定以这种形式呈现这些技术的原因。
这里提到的大多数技术都是用于和神经症患者而非精神病患者的工作。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别,因为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做了很多了(Fink,1995,1997,2005b),但是在我看来处理精神病需要用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技术,这个我会在第十章中简要描述。如我所言,如果压抑应该作为分析家处理神经症的指路明灯的话,那么在精神病中压抑的缺失暗示了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精神病。但是,许多当代分析家似乎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患者并未遭受“神经症水平的问题”带来的痛苦,我想主张说,大多数分析家不再能识别“神经症水平的问题”了,这恰好是因为压抑以及无意识不再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了(另一方面,拉康主张分析家必须听信‘dupes’无意识,这是说他们必须跟随无意识,无论它指向何方,即使这意味着让自己被牵着鼻子走;见拉康[1973-1974,1973.12.13])。这让分析家混淆了神经症和精神病,构想出一种据说适用于所有患者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的诊断似乎是在区分“高功能”个体和不是那么高功能的个体。)我相信,本书中提到的处理神经症的方法适用于如今多数临床工作者见到的绝大多数患者(当然,总有例外),而且读过我在第十章中提到的处理精神病的方法后,实践者也会慢慢同意我的这种观点。
开展精神分析的经验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没人可以面面俱到,即使是终生笔耕不停。我选取的这些主题依据的是在我看来如今分析家和心理治疗师的基础培训中所忽略的东西。我不会做的是,比如说过多讨论情感与反转移(除了第七章以外),因为它们在其他文本中已经着墨够多了——在我看来,是多到需要削减了。我也不会过多描述分析的后期以及最终阶段,
xi
因为本书是一则介绍性文本。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绝不是一本单独的培训手册,那些内容应该由其他读物来补充——可以在参考书目中找到。
我已试图在本书中尽可能地比较和对照我的方法和其他方法,但是我知道采用其他方法的专家们也许会发现我对这些方法所知甚少。正如Mitchell和Black(1995,p. 207)提到的,“在当前很难找到哪个精神分析家能深入精通一种以上的方法(比如,克莱因学派、拉康派、自我心理学、自体心理学)。每个流派的文献都多不胜数,而且每种临床鉴别力都要训练得很出色,这对任何一个试图全部吸收的分析家都是很大的挑战。”我几乎花了整整25年的时间来理解拉康偶尔很折磨人的法语,设法找到方法运用在实践中。直到现在我才开始领略更宽广的精神分析的风采,我想比较以及对照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方法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注定是有些滑稽的。
我在这里讨论的非拉康派的分析家,是那些其作品最易找到且有说服力的分析家,即使我压根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比如说,对于“正常”“投射性认同”等的观点)。既然我的目标不是巨细无遗地呈现其他方法,显然我不用充分展现这些分析家的观点: 我把他们的某些陈述从语境中提取出来,然后进行简化,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细微差别的丧失。然而,我试着避免使用二手资料——即对这些分析家的观点的评论——因为我发现,正如在其他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是的那样,原创者的观点通常更易懂、更有说服力。当我把二手资料当成初始指南时,我惊讶于分析家在阅读以及翻译别人的作品时是多么的漫不经心,即便那部作品相对来说写得很直白;基本上我在别人的评论的基础上对分析家的理论观点得出的每一个初步结论,如果不完全丢弃的话,也得经过极大的修正才行!在开始这项计划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大多数论述拉康作品的英文评论都有严重的缺陷,我把这归因于他写作上的晦涩性,以及此种事实: 讲英语且精通法语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如今在我看来,其他一些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
xii
正如我在副标题中指出的那样,我并没有声称要在这里提供有某种权威性的拉康派方法;拉康著作颇丰且复杂难懂,以至于很难给他的那些迥异(尽管无疑是相互关联的)的方法提供辩护,而且就像有各种不同的拉康派一样,很可能也有种种拉康派方法。毕竟,像别人一样,拉康派分析家也倾向于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改变他们的观点。考虑到在这里我意在提供一种关于技术的介绍性文本,所以我简化了拉康的很多构想;我不打算提供如“解释”(interpretion)和“转移”(tranference)这样的概念在他的早期作品到后期作品中的发展的历史观点,我只会稍加提及或者指涉一些更巧妙且复杂的构想,尤其是那些源自他1970年代作品的脚注中的。(同样的,为了让文本尽可能地易读,我一般会把对其他分析家的评论或批评放在诸多脚注中。)在这里我并不想遵守任何特殊的正统习俗,尤其是在需要调和情况时——这指的是拉康在他后期著作中否定了自己的早期观点的情况。相反,我呈现的是他的那些在我看来最合理且最有用处的论技术的观点;而且我设法用一种或多或少是在实际的分析中所采用的顺序来呈现它们,至少一直到第六章我都是在这么做。
英语世界的人可能相信拉康派分析家是某种边缘群体,因为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他们为数不多。然而,如今趋势可能正好相反: 看看过去几十年来在欧洲以及南美拉康派分析家在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以及英语世界,尤其是在跟IPA沾边的传统培训机构中,新的精神分析家受训者在数量上同等程度的惊人下滑(见Kirsner,2000),事实上,如今可能有更多分析家采用拉康派,而不是其他流派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他们都站在同一条线上——毕竟有许多不同的拉康派——也不是说只有极少数才会同意我在这里说的绝大部分内容。
为了简化我在本书中对代词的使用,我采取了如下惯例: 在奇数章中分析家用“她”代指,分析者用“他”代指;在偶数章中反过来使用。那些没有现成的可查阅的英文版的法语作品,
xiii都是我自己翻译的;当有英文版可引用时,我还是会在很多情况下修改译文,而且经常是非常彻底地修改(对翻译的评论,可见Fink,2005a)。对crits(拉康著作集)的引用,参照的是英文版(2006年版),页面空白处给出的法语编注页码指向的文本。
我想在这里对他们单独说声感谢: 感谢Hélose Fink以及Luz Manríquez对我的鼓励以及在选择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曲集》中的《降A大调赋格曲》乐谱作为本书指英语版。的封面图;感谢Deborah Malmud,Micheal McGandy以及Kristen HoltBrowning在诺顿出版社的愉快共事;感谢Yael Baldwin对手稿早期版本的有帮助的意见,使得本书有了增补和改进。
布鲁斯·芬克
2006年于匹兹堡
弗洛伊德说,有一种类型的言说可能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都是被禁忌(interdited)的——被禁忌(interdited)意味着弦外之音、字里行间。那正是他所谓的被压抑之物。
——拉康(1974—1975,1975.04.08)
精神分析首要的任务是倾听,并且用心倾听。尽管这已经被很多作者强调过了,令人惊讶的是,在心理治疗的世界里只有少数优秀的倾听者。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些主要是个人的,另一些更多是结构上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倾向于听到那些与我们自己相关的东西。当某人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时,我们会想到自己可以反过来告诉他的类似的故事(或者更极端的故事)。我们会开始思考那些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些允许我们“连接”其他人的经历的事情,去“了解”它(那些经历)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至少去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将会如何感受。
换句话说,我们通常倾听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自己类似的生活经历,类似的感受和个人观点。当我们能够确定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观点和其他人相似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和那个人“有了连接”: 我们会说如下的话,“我懂你的意思”“是的”“我听到了”“我感同身受”或者“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或者更少的情况是“我感受到你的喜悦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感受到了对这个似乎和我们相像的人的同感、共情,或者遗憾;我们会说,“对你来说那一定很痛苦(或很棒)”,同时想象着我们自己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会体验到的痛苦(或喜悦)。
当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的经验、感受或观点与另一个人相似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感觉,即我们没有理解到那个人——确实,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如果不是迟钝或不理智的话,也至少是陌生的。
当某人没有以类似于我们的方式操作,或者不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对情况作出反应的话,我们经常会感到挫败、难以置信,甚至是震惊。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试图去纠正另一个人的观点,说服他像我们那样去看待事物,去感受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所感受到的。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如此评判: 我们问自己,怎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事?会有那样感受呢?会那样做呢?
简单地说,我们通常的倾听方式忽视或者拒绝了他人的相异性。我们很少听到,是什么让另一个人讲述的故事对那个人自己来说是独特、特殊的。我们很快把这个故事同化到另一些我们已经听过的、其他人谈及他们自己的故事中去,或者同化到那些我们能够谈及的自己的故事中去,而忽视了正在被讲述的故事和我们已经熟悉的故事之间的区别。我们匆忙地掩盖差异,让这些故事看起来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也至少是相似的。在我们认同他人以及想和他拥有某些共同之处的匆忙之中,我们强行地同等看待这些经常是不相称的故事,根据我们已经知晓的去删减我们正在听到的故事。
这对于大多数形式的认同而言是真实的: 事情或体验的某些方面必须几乎总是被抹掉或忽视,这是为了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同一性。正如凯斯门特(Casement,1991,p. 9)所说,“人们用对待已知事物的方式去对待未知的事物。”我们发现的最难听到的,是那些全新的和不同的东西: 对我们自己,或对我们所知的范围来说相当异样的想法、体验,以及情感。
通常认为,我们人类共享着很多对这个世界的相同感受和反应。这使得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理解彼此,并且构成了我们共享的人性的基础。在一个反对精神分析家作为一个超脱的、冷漠的科学家,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人类的人物类型的尝试中,某些实践者已经建议过,分析家应该有规则地对分析者共情,突显他们共同之处,以便建立一个稳固的治疗同盟。尽管这些实践者有诸多良好的意图(比如,揭露对分析家的客观性的信念),共情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强调分析家和分析者共享的人性,却掩盖或者无视了他们非共有的人性的方面。
弗洛伊德(Freud,1913/1958,pp. 139140)建议分析家要向分析者展示一些“共情性的理解”。然而,他借此并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声称和分析者相像,或者我们应该赞同他或相信他的故事,而是说我们应该显示出我们非常专心,用心地在倾听,而且试着跟随他正在说的东西(他所使用的德语术语Einfühlung,经常被翻译为理解、共情或敏感)。玛格丽特·里特(Margaret Little,1951,p. 35)机敏地宣称,“共情的基础……是认同。”在这儿我的观点是正好和这些人——比如麦克·威廉姆斯(McWilliams,2004,p. 36),他们相信“我们努力去理解那些来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人的主要‘工具’是我们的共情能力”,以及那些如科胡特一样深信分析家的采用“替代性的内省”的能力,“思考和感受自己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在生活的能力”的人——相反。拉康(Lacan,2006,p. 339)暗示,分析家们对共情的调用经常涉及“假装不见”。实际情况是,如果一个分析家要去思考和感受她自己进入了一个分析者的内在生活,她必须忽略所有那些他们不一样的方面,以及他们显然并不相同的一切个性——换句话说,她必须糊弄自己相信他们从根本上是相似的,削去所有差别。但是,A只能在数学的意义上说是等同于A的。
我已经听到五花八门关于什么是共情的自相矛盾的论述(哲学的和精神分析的传统对此提供了大量不同的定义)。我曾经甚至听说,在某种场合中共情的做法会显得像是不共情——例如,当一个患者会把它作为一种家长作风或傲慢的信号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这通常是某些不能预先知道的东西(类似的例子见玛丽·卡迪纳尔(Marie Cardinal)1983年版的《要说的话》(The Words to Say It)一书,特别参见第27—28页)。在我看来似乎是,对于在治疗中使用共情的支持者,在强行用各种概念上的巧妙手法去证明它在各种情况中的适用性。
我认为,我们越仔细地去思考任何两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就越是会被迫意识到,相比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之间有着更巨大的差别——我们和自己倾向于认为的大不相同!
这是我在观念上和一些如麦克·威廉姆斯(McWilliams,2004,p. 148)的人有着根本上的区别的地方之一,他们声称“作为人类,相比于我们的差异,我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尽管她在后来的书中(p. 254)缓和了这种观点。马兰(Malan,1995/2001)也作出了同样的假定,他主张:心理治疗师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中的许多并不来自正式的培训或阅读,而只源于个人经历。在我们自己或那些和我们亲近的人当中,我们其中一些人并没有经历过明显地无知的三角情境中的潜在的危险;或者知道眼泪的使用不仅仅是情绪的释放,也是一种对帮助的请求?(p. 3)事实上,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他提到的事情。在我看来,认同或者试图把我们自己视为和那些不同于我们(种族的、文化的、语言上、宗教上、社会经济上、性别上或者诊断上的不同)的人是相似的,并不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或帮到他们。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被假设需要由分析家这边的共情性回应(比如“那对你来说一定很痛苦”,去回应分析家认为的必定很艰难的生活事件,比如跟一段长期关系说分手)而建立起的同盟,只需要求分析者描述他的经历(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就可以轻易地实现,而后者的优势在于不把话语强加给分析者(见第二章)。在我督导的很多同类型的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中,我发现最经常由分析家作出的评论是共情性的,是想在患者身上培养一种被“理解”的感觉,这通常错过了要点,患者回应道,“不,这并不痛苦。事实上,这比我想的要容易得多——我从没感觉到像这样好过!”屈服于共情性回应的诱惑的分析家经常发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她实际上没有和分析者处于同一频道。
考虑到《韦氏第3版足本新国际英语词典》给出的对于共情的第一条定义:“将一种主观状态(无论是情感的、意向的或是认知的)富有想象力地投射到对象之上,以至于对象好像被注入了这种状态: 在一个对象中读到某个人自己的精神状态或意动”。当分析者描述了一种非常艰难的处境,而分析家要表达共情的话,那么给分析者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神情,或者用一个较平常更温暖的、没有转调成一个疑问句的“嗯”,来表示自己已经听到他正在说的话了,这通常就足够了。
实际上,通过把某人的体验联系于或同化进我们自己的,我们对其个人体验的理解微乎其微。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通过获得更广泛的生活经验,我们能够克服这种问题。毕竟,我们的分析者通常会认为,除非我们看起来年老睿智,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生活经历,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我们自己可能会掉进这个陷阱,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各种各样的分析者,我们只需要打开眼界,远行,了解其他人、语言、宗教、课程和文化。然而,如果获得一个更充分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确实是有帮助的话,这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或其他人是如何真实地生活的理解,而是因为我们不再将每一个人和我们自己对比: 我们的参照框架已经改变了,我们不再依据我们自己看待事情和处事方式去评价其他人了。
在我的精神分析实践的早期,一位50多岁的女人来见我,她含着眼泪告诉我她是如何与同一个男人结婚、离婚以及复婚的故事。我很怀疑,同时想着这类事情只会发生在好莱坞,并且当时一定有一种诧异或困惑的神情浮现在我脸上。不用说,这位女人感觉自己被评判了,并且再也没回来。当然,她是对的: 我当时正试图站在她的角度去想象,而且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通常的倾听方式是高度自恋以及自我中心的,因为我们把其他人告诉我们的一切都与自己联系起来。我们拿自己和他们相比较,我们评估自己是否有比他们更好或更糟的经验,我们评估他们的故事会引起我们什么样的反应,评估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不管他们是好是坏,可爱或可恨。简言之,这就是拉康所谓的想象维度的经验: 分析家作为倾听者,依据反映给她的形象,不断地比较和对照她自己和对方,不断地评估着对方的言说。——无论对方的形象是好是坏,是快是慢,有洞察力还是无用的。想象维度与形象相关——例如,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而不是凭空产生(Lacan,2006,pp. 349350)。
即使拉康和我的观点通常与温尼科特(Winnicott,1949,p. 70)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温尼科特谈到患者时说到,他们“只能在分析家那里看到(他们自己)有能力感受到的东西。就动机而言,强迫症的患者倾向于认为分析家在以一种无用、强迫的方式工作。”他认为对于其他诊断类型的患者而言,也是一样的。对于受训中的分析家以及更有经验的分析家而言,在倾听他们自己的患者时,情况也是一样的。
说来奇怪,即使一些精神动力学治疗师也推荐使用这种自恋的倾听方式,而非鼓励我们以其他的方式倾听。比如说,马兰(Malan,1995/2001,p. 26)建议,治疗师“在认同(患者)的过程中使用对自己的感受的了解;不仅在理论上,也从直觉上明白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甚至宣称,“精神科医生需要让自己认同于患者,试着看自己在同样的处境下会感受到什么”(p. 28)。这种方法和爱伦·坡(Allan Poe)的《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 1847/1938)中所描述的某些东西有着奇妙的类似性,其中一个男孩能在“奇数或偶数”的游戏中击败所有同学,他是通过试着确定他的对手智力水平做到的,试着让他自己的脸上带着与他的对手相对应的同样机智或愚蠢的神情,从而猜测其他人是否会轻易地从偶数改为奇数,或者他是否会做些更复杂的事。这种策略涉及的正是拉康(Lacan,2006,p. 20)所说的纯粹的想象维度的经验。
当在想象层面上的经验中运作的时候,分析家聚焦在她自己的自我形象之上,这个形象是由分析者反映给她的,并且只有在分析者所说的话语反映了她的形象的情况下,她才会听到分析者说了什么。这里她所关心的是分析者的言说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与她的关系是什么。
很多人在一开始都以很相似的方式阅读精神分析文本,当他们阅读理论或者其他人的分析的时候,首先指望着理解他们自己。正如第七章中所提到的,强调对转移进行解释的分析家试图将这种缺陷变成美德。吉尔(Gill,1982)赞许地提到利希腾贝格和司乐平(Lichtenberg & Slap,1997),他们主张:
……在这种分析情境内,分析家总是在“倾听”分析者是如何感受他(分析家)的。换句话说,不管患者的评论或甚至是沉默多么明显地集中在何处,“在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交互影响的过程中,患者对自己的感知的一个或(通常是)多个的方面,总是和他与分析家之间的关系有关。”(p. 72)他在生她的气吗?迷恋她吗?他把她描述为聪明的,值得信任的以及有帮助的,或者描述为愚钝的,不值得信任的以及毫无帮助的?当他表面上正在抱怨他的母亲的时候,分析家怀疑他是否实际上正将他的批判对准她,对准她想被视作好母亲,而不是坏母亲的想法。当他在讨论他的成绩,他的GRE分数或者他的收入的时候,分析家正在心中拿自己的成绩、分数和收入与他做比较。
听这些东西使得分析家在本质上无法听到分析者所说的大量内容——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口误,由于口误经常是无意义的,并不会立即反映出分析家,因此通常会被她忽略。
当分析家主要是在想象的维度或范畴内工作的时候,任何无法轻易地和她自己的经验[她对于自身的感觉——简言之,她的“自我”(ego),我将使用这个术语]相对照的东西都被忽略了,或者经常发生的是干脆没听到。
拉康(Lacan,2006,p. 595)把这称为“二元关系”,他的意思是分析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被构建为不外乎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
我的一个被督导者曾让一个患者在深度抑郁有了轻微的缓解之后中断了治疗。当我问她,为什么她没有试着让他继续治疗,看看他的抑郁是否能够更进一步被消除时,她解释说,对她来说认为生活是令人抑郁的似乎是很有道理的——难道某些抑郁不是一种对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明智回应吗?不管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如何,我向她指出,她似乎假设患者抑郁的原因和她的原因(或者她所认为的她的原因)是一样的,而让他抑郁的原因却很有可能完全不同于她自己的。在比较他抑郁的原因和她自己的原因时,她拒绝或者没有听到他们潜在的不同方面。拉康(Lacan,1990)非常独创性地把悲伤和抑郁视作道德上的失败或弱点,有时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拒绝”(p. 22),在这个文本中这和除权(foreclosure)是同一个意思。(见第十章)既然只有那些多少有意义或可以理解的东西才具有对照性——那么含糊不清、结巴、咕哝、引起误解的言说、首音互换、停顿、口误、模棱两可的措辞、词语误用、双关语等——就被置之度外或被忽略了。凡是不在她的视野和经验范围内的东西,都被忽略或不予理会了。
这实质上意味着,分析家在想象的模式中运作得越多,她能听到的就越少。我们通常的倾听方式——包括作为“普通公民”和作为分析家——主要涉及想象的范畴,这让我们很难去倾听。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那么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