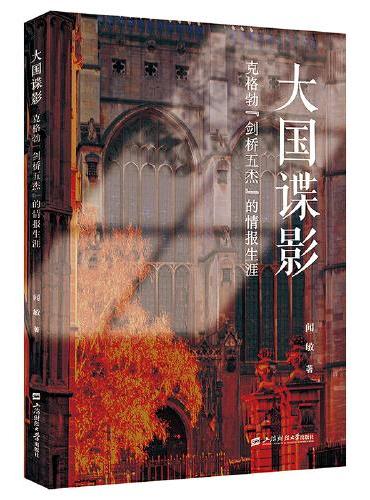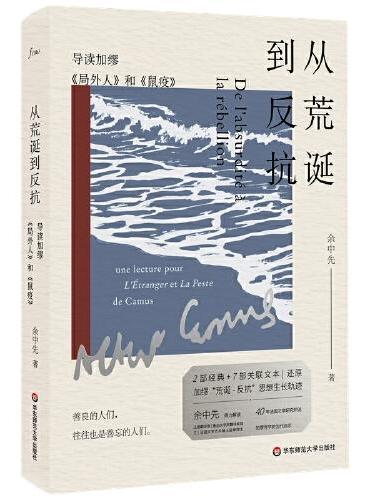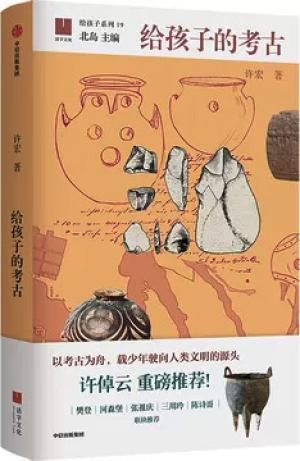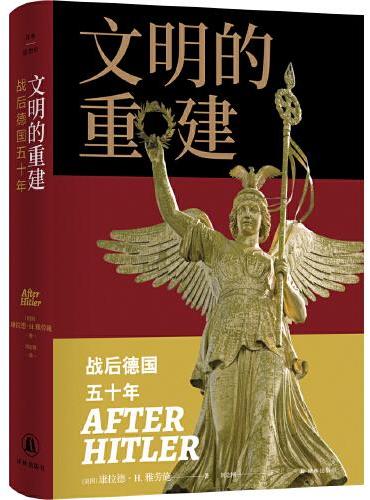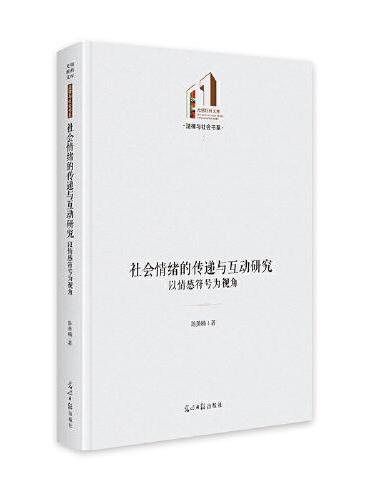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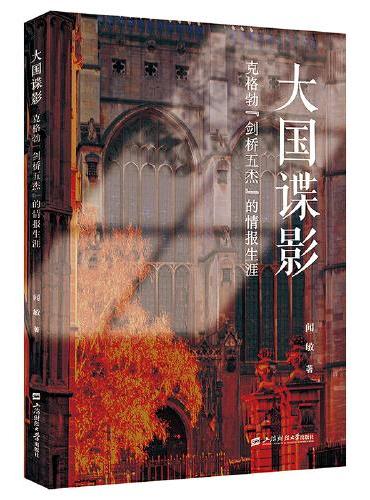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HK$
96.8

《
制造消费者
》
售價:HK$
49.5

《
精简写作:博报堂演讲撰稿人教你写出好文章(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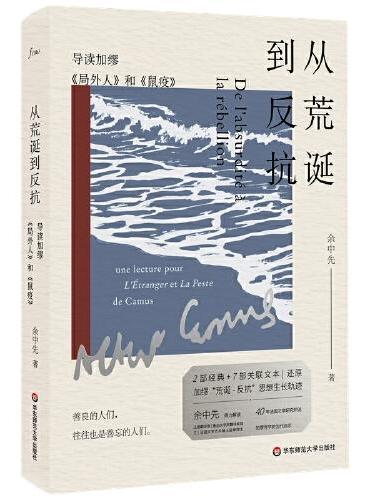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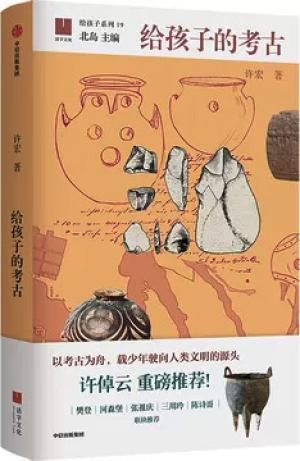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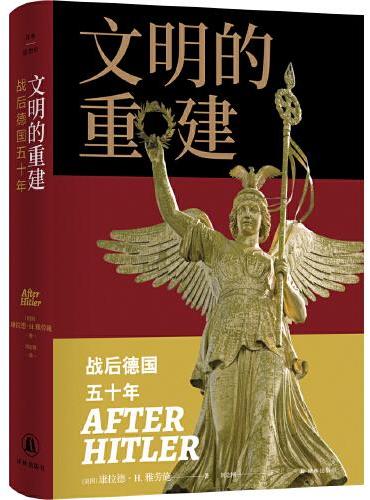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HK$
108.9

《
我以为这辈子完蛋了(经历了那么多以为会完蛋的事,我还是活得好好的!)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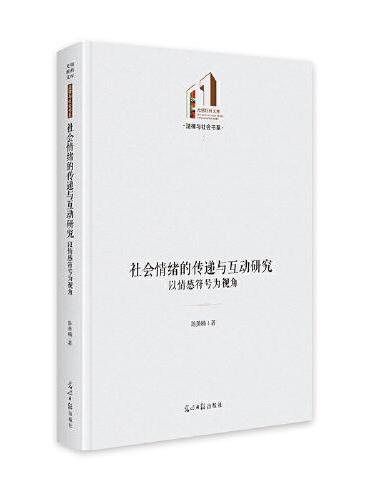
《
社会情绪的传递与互动研究:以情感符号为视角 (光明社科文库·法律与社会)
》
售價:HK$
93.5
|
| 編輯推薦: |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有此一问不是因为我知道,更多是基于我不明白。我们生活中可选择的有那么多,可读报、可上
网、可看电视、可玩摄影、乐器,可远足旅行。没书读的日子里,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其它文娱康乐活动让我们增广见闻,那么,书为何不可不读?而所谓的“读书明
理”,究竟明的是什么“理”?
在《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一书中,梁文道采访了十五个有想法的读书人,这十五个人之间生活上基本没有太多的交集,然而,连结他们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那部分枢纽正是“爱读书”。因为“爱读书”,诗人陈智德喜欢有事没事都去逛旧书店,去淘旧书只为想知多一点想
法,“硏究文史哲的人并没有什么仪器辅助,书就是田野,书就是现场。我们靠着旧书来认识历史,旧书是文史哲知识的载体”。此外,“当你读原版书时,你会觉
得那就是当时的作者或读者所看见的模样,彷佛重返作者新书发布时的面貌”
|
| 內容簡介: |
|
本书著名畅销书作家梁文道的最新力作。梁文道说,这15个人,皆是他感兴趣的人,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独到的想法,能做出非同一般的事业,能开他眼界,让他想到一些他不会去想的事。这15位人物,如一代文章大家董桥,在英美文坛大放异彩的华人作家哈金,在网络上砍出一片历史天空的十年砍柴,以及近年在时评写作上处于风口浪尖的长平,最近风靡大陆的旅行作家舒国治,港台文化传媒界的大手笔詹宏志,思维特出的文化专家赵广超,等等,在梁文道精心的导引下,缕缕细述自己的社会际遇与文化情怀,种种精彩见解和个人感受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可以说《访问》正是一道难得的智识、文化与思想的大餐。
|
| 關於作者: |
|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
| 目錄:
|
序
董桥:读书、文章、做人
赵广超:学问是一种手工艺
王贻兴:终于成了才子
詹宏志:读任何一本书都是为了改变自己
陈智德:我的渡轮终会回航
荣念曾:还有很多事情要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邹颂华@Lonely Planet:鬼马角色扮演
吴俊雄:报答流行文化的奶水
十年砍柴:在网络上砍出一片历史天空
哈金:“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往前走下去”
舒国治:清贫的意义
陈云:解毒中文 替天行道
黎智英:黎智英的另一个脑袋
梁家权:小吃总是旧时好
长平:正义
|
| 內容試閱:
|
◆ 序 梁文道
在我干过的所有文字活里头,我最恨采访。之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调查受访者的资料,构思可能的问题;之后还得费更多的工夫去把录音转成文字,反复修缮其中的空白与缺漏。加上实际访谈的时间,这大概够我写出一整周的专栏有余了。
可是,我还是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替《读书好》做完这一系列的访问。而且在可见的将来,我还会继续做下去。除了有同事帮我记录,省下那最令人害怕的工序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个习惯被采访的人,知道访谈的用处。过去四五年来,我平均每个礼拜要被人采访一次,有时候还真到了口干舌燥心烦意厌的地步。然而,我还是继续受访,能够回答懂得回答的我尽量回答。因为我把它当成了工作,当成了一种表达观点的工具,和我写文章做节目差不多,只是它更轻省更方便。我不需要动手也用不着在镜头前来回走动,只要坐在椅子上等人发问,然后说话。假如对方够诚实够认真,我发现访谈不失为一个代替书写和演说的速食手段。假如对方敏感机智,说不定还能达到理想的对话境界,使我的大脑意外孕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观点和想法。做采访是苦差,但被采访却是份美差。
出于这份替人省事的良善用心,也出于对一些人物的好奇和对自己的挑战,我决定每个月要去采访一个有想法的人。所谓“有想法的人”其实是后来渐渐归纳出来的主题,一开始,我想在《读书好》这份阅读月刊做的是个有关读书的访谈系列,比方说看看人家的藏书,窥视一下他们的隐私。但这个计划一开头就碰上钉子了,首位受访者董桥先生对后辈一向温厚,可他说:“这怎么行呢?这种东西千万不能给人看。”我明白,懂读书的人都晓得私人藏书最能透露自己的隐秘信息。所以近年才会有这么多要求别人打开书房的访问甚至专书,因为我们都很八卦,爱看人家的私生活。
不,这不是我要做的。既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让记者踏进家门,我又凭什么带着摄影师去踩别人家里的地板呢?我真正要做的,是探访一些我感兴趣的人物,这些人还都跟书有关,或者是作者也或者只是读者。并且我相信他们都有想法,能开我眼界,让我想到一些我自己不会想的事,或许还能令读者受益也说不定。“有想法的人”听起来很玄很泛,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人其实不太多,尤其在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真的,我常看坊间杂志的个人专访,记住的真没几个。特别是“成功人士”和“名人饭局”里的名人,他们使我觉得成功成名的前提似乎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要想得太与众不同,于是读者才可以总结出一个通用方程式:“你看,每个成功人士都是这么说的。”继而效法他们,一起成功。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观赏“与CEO对话”之类的节目,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些人说的东西都很相似吗?连最近垮下来的方式都很像。
也许这不是受访者的责任,而是采访者心里早有一番固定的盘算,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能把它们总结成“勤劳”和“掌握机遇”这几大元素。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评论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种访谈文体。在那种文体里面,采访者几乎比受访者还重要,他的目光无处不在,他的感想接连不断;从对方点什么饮料开始,一直到某个最细微最不可察的小动作,全都逃不出“作者”法眼。在这种文体里头,探访者的确成了作者,总是毫不厌倦地要人注意他有多聪明,他的文笔又有多绚丽。因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采访的人就是一篇散文甚或小说里的角色了。
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要最原始最干燥的一问一答,我只要受访者的想法。所以我不记录他们的表情神态和衣着,尽量让他们用自己的言语呈现自己(虽然经过我事后的编整)。这十五人这么有意思,这么不同,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因此,我甚至删去了许多自己当时说过的话,在你看到的文字上伪装出一个倾听者的姿态。假如我存在,那些问题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迹。所以我把本书编辑原来选用的书名《梁文道对话XXX》改成了更单纯更直接的《访问》。Andy
Warhol创办的杂志不也只是叫做Interview吗?纵然它早已失去了草创时期的气息,但这个名字还是利落无匹。
至于书内的十五位受访者,我就不说太多了,也不打算在他们的谈话中勉强拉出一条宏大的主线,大家尽可自己翻看。倒是《读书好》的现任主编邝颖萱必须多谢,在我脱手编辑职务之后,她仍容许我偶尔放肆地刊出一篇万言访谈。大家可别忘记这是份大众读物,这等长度的访问是不少更专门的杂志都收不下的。我最感激的,还是先后帮忙记录访问的编辑,以及几近义务劳动的摄影家;谢谢你们。
(一)访问董桥片段
梁文道: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角度去看。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桥:书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他的遗容很静,一点都不动。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哪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例如杨绛的文章,看多了,我发现真的有斧痕,她的东西一定改过。后来我问她,她果然说有。我想就是这样,再平淡也要有经营。
至于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地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
白先勇也好,可是白先勇的好跟张爱玲不一样。白先勇是一个贵公子,穿着得很整齐,随着月亮出来,然后走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他会很着意在这个亭园里面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亭园这个环境给他什么感觉,他都会写得好。张爱玲不同,她可以到处钻,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成了一个鬼。人家看不到她,她却在整个院子里走来走去,什么都看到了。然后她挑一样东西来写,就像摘一朵花,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文道: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行了。
董桥: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入他人的世界。
但进去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入哪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陆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外文,而且很深入地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伦敦八年,发奋去读的有十几个作家的书,我一本一本地看,Jane
Austen、Charles Dickens……
(二)访问梁家权片段
小吃总是旧时好
人到一定年纪,就要开始回忆幼时吃过的东西,而且很奇怪,这些东西就算现在还在,也一定不如以前的好。要是被人追问下去,你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通常就会祭出最后一招:“总之味道变了。”这个“味道变了”或许可以止住对话纠缠的尴尬,但却止不了别人心里的狐疑。于是饮食的判断变成了单纯的情感怀旧,而怀旧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过去永远美好,怀念永远有理。
梁家权样子年轻,其实已是老资格的传媒人了。干新闻干了大半辈子,这几年却以饮食书写闻名,人称“庶民食家”。他的写作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够平民,喜谈鱼蛋菠萝油多于鲍鱼老虎斑;其二则是怀旧,总在洋溢着个人情感的叙事中述说昔年小吃的温暖可爱。但梁家权之所以成了食家,并不在于他有多念旧,而在于他真真正正说得出为什么以前的东西就是要比现在好,诸般缘由娓娓道来,很令一般怀旧者解气,觉得以后说话的声调都高了点。
这天我们坐在油麻地地标“美都餐室”二楼,俯瞰榕树头一带,难免要从庙街的旧怀起,原来我们两个年龄不同的人,都已经在某个共同的意义上“老”了。
梁家权:我最记得那时还有好莱坞戏院,门前那一档,以前没什么钱,去看《大军阀》,狄娜那一套,只够钱买两只鸡脚食。
梁文道:两只鸡脚啜足全场!看狄娜,啜鸡脚,哈哈哈哈!以前的戏院门口真有很多小吃啊。油麻地有档卖白果、鱼蛋的。
梁家权:以前那些车仔卖“口立湿”,一架车有很多小格的,有酸芥菜又有酸粉葛。
梁文道:以前的香港戏院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饮食传统。现在时代不同了,戏院全变了UA、百老汇那些美式大型连锁戏院,就连食物也跟着变,只可以吃爆米花。我记得第一个这样做的戏院是UA。它规定外面的食物不能带进戏院吃,你只能在里面买它的东西。
梁家权:从前去看戏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我记得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进场前买一堆“口立湿”,看完就盘算去庙街吃煲仔饭或者去吃云吞面,很有计划。去球场看球也是如此,上一趟有朋友请我看南华对曼城,以前我会到大球场看南华对精工。当年大球场里面没东西吃,但我们会在球场外面买杏脯肉、鸡脚、鸡翅进去。但现在大球场内有很多快餐店,卖的不是炸鸡腿就是炸什么的,来来去去也是那些难吃的东西。波已经不好看,现在连吃东西的趣味也没有了!为何要把餐厅全都批给快餐集团做?为何不开放它们?好像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五年前的海洋公园,没什么好吃的,山上山下都是一式一样地卖热狗,有没有搞错?为何不弄鱼蛋?机场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卖猪皮鱼蛋呢?那才是香港特色,如果我是一个过境的旅客,能够吃这些东西多好啊。我真的不明白。人家日本的机场有日本咖哩、拉面和即制的寿司,为何香港机场不做鸡蛋仔和鱼蛋猪皮这些地道的东西?
梁文道:香港饮食文化当中一大隐患,就是我们的庶民饮食出现了很多问题。大陆有很多杂志都说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我反而觉得在香港吃好东西很困难。不论西餐、中菜,你付得起价钱,真的可以吃得很好。但香港饮食上的贫富悬殊真的很夸张,如果你穷,真的没什么好东西吃,没有什么好选择,所有食物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山寨厂做出来。而以前那些小贩,他们卖的东西可能是同类,但因为是亲手制造,做法一定有差别,结果始终是不同的。
梁家权:例如生肠、鸡肾、鸡脚,卤水的制法也各有不同。就算是牛杂,他们会即场放五香粉,不停加水,有时又会放一些不知名的香料。可是现在,那些烧卖鱼蛋,从街头吃到街尾都一样,全是同一家工厂交货。
梁文道:但现在不这样经营又不行,根本负担不来,今天做小贩的成本太高,随时会被封铺会被捉。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用心在家慢慢弄一些好吃的?当然是去工厂拿货合算。所以我说二十年前的庶民在香港会吃得比今天好。
梁家权:我小时候手上只有几元,我要好好想一下怎样花这几元。那时走路和时间根本不算什么,钱才是最重要的。我帮家里送完货去九龙殡仪馆,可以在英京吃一碗碗仔翅。还未吃得够嘛,经过文华戏院,再在那里吃一串鱼蛋和炒螺肉,又站在那里看一会儿唱大戏,买碗鸡粥再走。这样完成一晚的“食程”,却花得不多,十元之内,已经很丰富。那是我的中学时代,就是七十年代。
从前的庙街和上环大笪地,很多人富贵了还是会回去吃;即使是大排档如中环的胜香园,也有人驾名车光顾。有特色的东西,无论贫贱富贵都有人喜欢,平民可以吃富贵的食物,但富贵的人也会向往平民的食物和食制,那为何不尝试多发展这一类东西?自从有了小贩管理队后,首先就是扫了那些街边小吃。
但这也还要看整个社会的潮流,不是说政府让小贩再经营就是改变。其实饮食是一个趋势,是一个潮流来的,说不定人心会被某一种思潮所影响,以某种形式重拾怀旧的饮食。好像我小学时期最喜欢吃的菠萝油,它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直至曾志伟开了一间茶餐厅,就是推介菠萝油的。感谢他令菠萝油再次流行,也掀起了其他饮食怀旧潮。
梁文道:最近几年开始谈保育,香港人才忽然说要集体回忆。但回想一下小贩管理队的出现,那是八十年代的市政局议员常说民意支持他们大力扫荡。他们说收到很多投诉,于是才去封这些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香港人曾有这样一段时期,要急于去扫荡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说在街上吃东西不卫生,我觉得是看你怎样处理而已,日本街头不也有很多拉面档。
梁家权:你看福冈、博多,人家也有很多大排档。我觉得香港人若要生存,就是应该走这条路,而不是把这些食物档一一铲除,将它们全都搬到十分规范化的地方,前店看似很干净,店后却不堪入目,你拿部DV机去后巷看看吧,那儿的情况十分吓人。我觉得可以参考日本大排档的模式,人家虽然在街上,不过可以很洁净,也有店主自己的个人特色。
梁文道:最近有个调查说街上卖的羊肉串,原来有四成是鸭肉,再淋上一些羊尿,让肉串有羊膻味。
梁家权:有一年我在王府井,在大街吃了一口,立即丟掉,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就是烤羊肉串?
梁文道:你真的不要在大陆随便吃羊肉串啊。我在北京认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自己在家煮川菜,煮得很好吃,常在家里摆了几桌,24小时随意让人来吃饭摆流水席。你说上来吃饭,他就会叫你随便坐。你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他喜欢请人吃饭。起初是我们这些文化界的朋友经常上去吃饭,后来消息传了出去以后,很多陌生人也来了。后来这个朋友索性开一间餐厅,家里继续这样宴客,但餐厅也做得很好。他的川菜这样好吃,但他说现在大陆人人都吃川菜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因为中国人的味觉差了,一定要靠味道很浓烈的食物去刺激味觉。第二是因为现在的食材很差。
梁家权:现在大陆也像早年的香港般开了很多私房菜,但很多人根本不懂得煮,就以“私房菜”之名来吸引人。那些食客也是傻的,以为有个很private的地方吃饭很好。香港又有些富豪第二代说想搞一间餐厅让朋友来聚聚,花很多钱在设计上,但最重要应该是食物本身才对吧
三访问长平片段
梁文道: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平: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线上,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轻。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权力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路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什么什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的。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
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什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梁文道: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的效果,那为什么从前没有呢?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平: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风波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首先一批知识分子远离,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
那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屈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活得很难受。于是你看很多人都转过来了,找了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由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信念。
其实整个社会,也在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怎样去面对过去。过去我们是讲正义原则的,其逻辑是全世界我最正义。资本主义很坏,其他人还在落后的状态,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后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改变了。它现在不再试图证明全世界我最正义,它现在要证明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正义。这么多年以来,仿佛就是在传播一种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理论。扩散出去,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喜欢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国品牌也有毒,可见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没有人不自私,我们并不算太过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