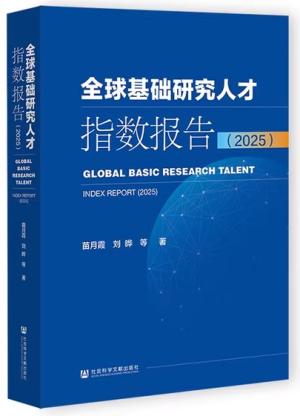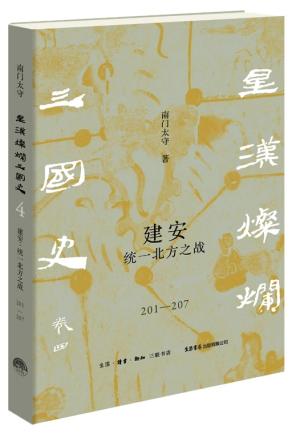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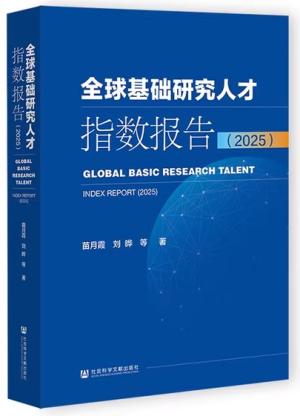
《
全球基础研究人才指数报告(2025)
》
售價:HK$
327.8

《
投资的心法:从传统文化视角看清投资中的规律
》
售價:HK$
75.9

《
如何使孩子爱上阅读:家长和教师能做些什么(基于科学原理,培养孩子阅读水平与内在动机)
》
售價:HK$
54.9

《
博物馆学辞典 博物馆学核心工具书,权威专家联合编纂,理论与实践的指南!
》
售價:HK$
270.6

《
战时的博弈: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理想国译丛075)
》
售價:HK$
162.8

《
明亡清兴 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
》
售價:HK$
74.8

《
北大版康德三大批判
》
售價:HK$
3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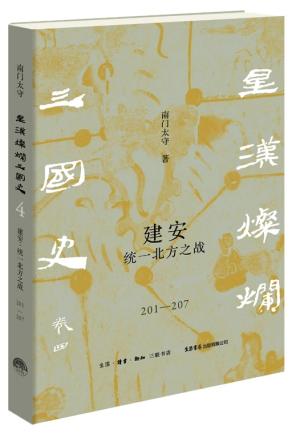
《
建安 统一北方之战(201—207)
》
售價:HK$
53.9
|
| 編輯推薦: |
这是一场基于十四场深度访谈,关于信仰、自由与真实人生的深度对话。
访谈的对象有还俗者、出家人,也有居士和学者。在一次次对话的坦陈与解构中,出家与还俗、出世与入世、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家庭,曾经割裂的事物又汇聚到一起,形成人生的因果。
还俗是一种选择。它未必是一种叛离或者否定,它也可以是一种自洽,一种自我认知改变后的生活实践。
|
| 內容簡介: |
|
《还俗——在伽蓝与尘世之间》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所采访的每个对象都真实存在。本书所撰写的内容均来自现场采访实录和后续整理,当然,出于保护采访对象隐私的考虑,某些人名、地名等使用了化名。另外,本书并不是一部弘法之作,更类似于一份带有社会调查研究性质的报告。作者作为佛教文化的亲历者,之于“还俗”,价值中立,力求在历史背景下,对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客观叙述和有限呈现。
|
| 關於作者: |
|
苏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美学史、佛教美学、建筑美学、生态哲学等。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般项目、中华外译项目共五项,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录播的中国大学慕课“江南古代都会建筑与生态美学”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一流课程)。
|
| 目錄:
|
缘起
甲·还俗者说
蓝智萍:灿烂哥
王如风:自考生
万福明:外部势力
吴小龙:归零
法 鹃:我找老师去了
乙·出家人论
释法也、释可心:论迂回
释宗泽:论宿命
释广弘:论理性的胜利
丙·居士谈
马小迎:寺庙不是养老院
杜维荣:还俗可说
丁·学者言
赵杏根、聂士全、李昌舒:我们要的是解释
王海男:零成本
韩焕忠:僧伽的本义是大众
金易明:七因说
|
| 內容試閱:
|
缘 起
既然此世为僧,又何必还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我用文字把盘桓在佛门内外,影影绰绰的人群的故事记录下来—从还俗开始。
人的社会身份或许有两种,一种是明确的,一种是隐晦的。明确者有标志,例如警服、僧袍、快递小哥的马甲和头盔。标志作为符号,代表制度,制造出一种无须解释的使命感、束缚感。医院里,见到护士服,我会欣然接受,并不在乎给我输液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另一种隐晦的社会身份没有标志,例如路人、小偷、诗人、舞者,以及不愿披露身世的还俗僧人。他们不主动表明身份,消失在人群里,像一个未曾来过的影子,犹豫、飘忽、闪躲,时而构成某种无法预料的给予、伤害、风险或妥协。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可以被归类;从具体的经验上来讲,他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心事。手机丢了,我会猜度:捡到手机的人会不会意外地把手机还给我;不还给我手机之人的人性是怎么形成的。复杂而带有不确定性的人性,更值得记录—我想写下在刹那间摇摆着的尊贵与卑微、偏执与懦弱。
历来,还俗僧人在佛教文化这一大范围里的各类负面人群中,是最晦涩的类型。无论是比丘、比丘尼、住持、方丈、诸山长老、高僧大德,还是信佛、排佛、反佛、灭佛的古代君王、外道、斗士、宵小,还俗僧人不足为外人道的程度起码超过了“马路和尚”“香花和尚”,以及理发店里自己给自己剃度的假和尚。他们既代表着迷茫、迂回和游移,也让人同时产生了对于沉沦和超然、虚伪和忠诚的双向蔑视。他们通常是囊中羞涩却忍辱负重的“包袱”,最容易得到原谅和遭受公开谴责的“背叛”,不留下姓名又在佛门前逗留不去的“倒影”。
还俗不只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还俗看上去是一个“结果”,实则有无穷无尽的“成因”和“宿命”。所以,书写还俗,不能只是誊抄一份还俗僧人的个人简历、口述,而应从不同的社会角度切入并研究这一话题,思考和还原这一话题的深层逻辑。首先,还俗者的“自白”,无疑是认知还俗的“第一手”材料,它直接向我们展示了亲历者如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接下来,与还俗僧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僧团内部仍在出家的僧人。在他们的心里,如何看待身旁这个转身离去的室友、同僚?除此之外,处于僧团外围的居士,又如何面对这一群体?信仰如同涟漪,佛、法、僧构成的内圈并非孤立,它的层次会逐渐蔓延开来,沉淀为居士内心的记忆。最终,佛教文化的研究者,各大高等院校的教授、学者们,又将如何讨论这一话题?只有在立体的维度中才能够真实地解读某一社会现象,内外通透,由表及里。
本书作为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所采访的每一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绝非作者本人杜撰或臆造。本书所撰写的内容均来自现场采访的实录以及后续的整理。为此,本书刻意保留了一篇采访实录的原始版本——《释法也、释可心:论迂回》——呈现给读者。当然,出于保护采访对象隐私的考虑,某些人名、地名,以及寺庙名称使用了化名。另外,本书并不是一部弘法之作,更类似于一份带有社会调查研究性质的总结报告—本人作为佛教文化的亲历者,之于还俗,价值中立,全无褒贬—力求在历史背景下,对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客观叙述和有限呈现。
作为铺垫,有必要指出,还俗并非当代佛教文化的特例,它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仅就中国佛教发展史而言,早在魏晋南北朝,即佛教初入中土时期,就有了僧人还俗的记载。例如,《宋书》中写道:“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时有沙门释休善属文。湛之与之甚厚。孝武命使还俗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大意是,南兖州刺史徐湛之出于游玩的考虑,招募了一批文人,其中就有一位和尚。他后来还俗了,姓汤,做了“扬州从事”。
南朝刘宋的僧人惠琳,是秦郡秦县(陕西)人,俗姓刘,少年出家,住治城寺,是道渊的弟子,学通内外,文章写得好。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左右,他作《白黑论》(又名《均善论》《均圣论》)。文中有一位白学先生,代表儒道;一位黑学先生,代表佛教,相互辩难。“其归以为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伍。”宗旨是佛教的六度与儒家的五教并行,信顺的道与慈悲的佛齐立,并讥讽佛教的来世观。惠琳最终得到了宋文帝的赏识,从此得宠于文帝,参与朝廷机要,权侔宰相。“会稽孔恺常诣之,慨然叹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这样一位僧人的风评如何?世人固然嘲笑他是“黑衣宰相”,“冠履失所”。
在古代,所谓“还俗”并不一定指的是和尚还俗,比如师从诗僧皎然的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约737—784年)在《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中写道:“闻有华阳客,儒裳谒紫微。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还乡见鸥鸟,应愧背船飞。”这首诗是送给吉中孚的。吉中孚也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初为道士,后来还俗,成为宰相元载府上的嘉宾。所以李端揶揄他“儒裳谒紫微”,意思是穿着儒家的衣裳跑到皇宫里去献媚。“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说的是吉中孚为了取媚于上,出卖了自己的药山,但终究不得意,只好化作“孤鹤”回归故乡。无论如何,在这里,“还俗”指的是道士还俗。
在现实生活里,还俗作为普遍的历史事件,通常指古代君王大规模灭佛活动中的一种手段和举措,僧人们实属被迫。任举一例,如唐武宗在位期间(840—846年)的“会昌法难”。“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旧唐书》本纪卷十八 · 武宗)古代的佛教寺院相当于一个庞大而独立的经济组织,不仅屯田而且蓄奴,这些在灭佛期间一律收归国有。还俗是这一取缔行动中非常具体的操作方式。
还俗后的僧人晚景如何?个别的显贵和风光暂且不论,普遍的状况是满目萧然,悲不自胜。杜牧(803—852年)的《还俗老僧》写道:“雪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衲残衣。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此诗中最后一句,“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写尽了眼帘里凄楚的场景。这样一位还俗老僧,人生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无归处。男性尚且如此,女性又当如何?吴融(850—903年)另有一首《还俗尼》:“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三峡却为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空门付与悠悠梦,宝帐迎回暗暗春。寄语江南徐孝克,一生长短托清尘。”这就更惨了。诗中人做不了尼姑,只能重操旧业继续做歌伎。两首诗中,还俗僧与还俗尼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还俗没有“家”的承托,命运里更多的是荒凉。
回到“原点”,是还俗的底层逻辑。《尔雅》曰,“还”,“返”也; 《说文》言,“还”,“复”也。“原点”在哪里?来处,即出家前能够制造出某种“家庭感”的地方。在人们的心中,天下还俗群独占鳌头的“群主”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猪八戒,他心心念念的是高老庄,不是广寒宫。孙悟空更是动不动就回转花果山,而非南赡部洲、五行山,或被自己搅成一锅粥的天庭。为什么?高老庄、花果山才是来处。没有来处,还俗将无路可走。还俗是喜剧还是悲剧,不仅取决于其出于主动还是被迫,同样取决于还俗的僧尼踏上的是回家之路还是身无定处、四处漂泊的不归路。
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一,是以佛、法、僧作为中心主导力量向周边的扩散、过渡和滑落。佛教信仰的族群如同圈层,从僧人到居士再到善男信女的层级落差越来越缓和乃至平均。这意味着,对于还俗僧人来说,还俗的道德焦虑感和精神压迫感正在逐步减弱;僧团内部以及世俗社会,也表现为更能接受这一情有可原的“过错”。其中,太虚大师的态度最典型,他对还俗的态度是“宽许”—凡不宜为僧者尽可退还世俗,退还世俗者也理应获得社会尊重,为他们创办类似于“僧界佛徒还俗会”等组织。既然佛教在人间,禅在生活,还俗的僧人也便不再像是“逃兵”,而更像是“提前下车”的“乘客”。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没有植入作者预先的价值判断标准,保留了各采访对象表述中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位表述者,其话语之间前后左右的抵牾和悖论也同样存在。例如,还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无所谓好不好?还俗究竟是超越还是沉沦?还是无所谓超越与沉沦?僧人需不需要过集体生活?应不应当独居精舍?还俗是年轻人的“专利”吗?是青春期生理反应的必然结果吗?一位僧人理应住在大庙里还是小庙里?什么时候住在大庙里,什么时候住在小庙里?什么叫僧不僧,俗不俗?谁是众生?谁是拯救者?众生需不需要被拯救?笔者的记录不拒绝冲突,甚至更希望能够展现这种种矛盾—生命原本就是鲜活的,命运有不同的版本,因果无常。有放弃就有吝啬,有批判就有矫饰,有虚伪就有真实,有自以为是就有散在天涯。
有一次,一位采访对象警示我,“僧是不可说的”。无论是非好歹,僧的“事”,俗家弟子皆不可说,说了就是罪过,因为佛的企图和用意不可知。按照这一讲法,我正在敲击的不是键盘,而是地狱的门闩,我正在坠落,自取灭亡。
这就是我的处境,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既然我不会对僧人的还俗挑三拣四,又岂敢在文字世界里虚拟出某种至高的道德?
苏州太仓T寺有位居士,是个清癯的小伙子,三十几岁了,有点儿弱不禁风的样子。有一次,同行几个人应邀夜听T寺住持曙提法师吹尺八,下榻T寺。他负责接待,在门口守候指引泊车、分房卡、发小礼品、送水果、凌晨四点半打板子带我们去观摩早课,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全程基本上不怎么说话,远远地站着,总是沉默,穿着义工的马甲。我自己也内向,离别那天下雨,他拿了几把伞来,就与他有过一段雨中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中,了解到,他从上海来,好像是上海财经大学或者同济大学毕业的,记不清了;他已经在T寺做义工做了好几年,碍于家人的拦阻,一直没有剃度而已。写这本书是在2024年春节。春节前,跟他说想采访他,他非常意外,也格外惊喜。当时寺里的事情刚刚忙完,他正在快乐的回家路上,于是约定年初七他回寺后见面访谈。可年初七他发短信来,说王老师,没办法接受采访了。他的母亲知道他要走,在家里坐在床上哭了一整天。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极其难过,有很悲怆的感觉,想他的母亲说是哭了一整天,也许是哭了一整年。我记录的是什么?是镜花水月?还是镜花水月背后那曾经和正在让人撕心裂肺的人生!我拿什么来评价别人的人生?!
所以,我想做的,只是用键盘,把他们和他们的故事转述给你。
★ ★ ★
王耘问:“还俗前后,您对于人群、社会的想法一致吗?”
蓝智萍答:“没想到是这么复杂。”
2020年5月11日,蓝智萍回到老家,迅速步入正轨,赚钱养家,结婚生子。采访他的当天,他的孩子十个月大。父亲并不同意他还俗,因为父亲自己也出家,且已年届花甲,没有了还俗的必要。母亲面对儿子、儿媳、儿孙,尤其是面对儿子与儿媳的口角时感到十分厌倦。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身不由己,这个结局是蓝智萍始料未及的。蓝智萍说:“有时我就觉得,我可以说走就走,随时离开这个家。我对老婆和孩子说,我可以再也不要见到你们!”
业力、命运,是蓝智萍话语“大厦”里最基础的“柱石”。业力到了,就要承担后果。出家是业力所致,还俗也是业力所致。重点在于预设“烦恼即菩提”。人生的词典里,没有“后悔”,但一定有“烦恼”。在庙里的时候,面对佛、面对菩萨,日日跪拜,蓝智萍很快就麻木了,诵经也没什么感觉,见到信徒来祈求也没什么感觉。还俗后,自己好像信徒一样,才知道滚滚红尘中有那么多烦恼。他认为,人并不是因为智慧是对的所以需要智慧,而是因为烦恼多所以需要智慧。烦恼越多,需要的智慧越多。智慧多了,积攒起来了,就成了大智慧。因此人要知命、认命,承认这一切无非是因果。业力的主张并不无奈,只是每个人随着自己的习性、自己的业力前行而已。一切都在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无论如何,蓝智萍所谓的智慧,总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个量化的结果。
与此相参互照的,是始终定格在蓝智萍脑海中的两帧画面。一幅是初入佛门的一幕。寺院离他家近,最多三四十公里,但父母来看他的时候拼命哭。父亲没说什么,他自己有信仰,但也哭。两人往返,是骑摩托车,父亲载着母亲。走的时候,父亲自顾自把车子打着了,坐在前座上一动不动,头别过去,不看佛门这一侧,像被淋成落汤鸡的泥塑。母亲穿着大号雨衣,滑溜溜的,想要爬上后座,腿短,总是爬不上去,费半天劲才爬上去,而父亲始终无动于衷,面无表情。有部很苍凉的电影叫《大话西游》。在一切都已无能为力后,唐僧师徒在漫天黄沙中慢慢朝西边走,消失在烟尘里。《大话西游》的片尾曲是《一生所爱》,歌词里唱道:“苦海泛起爱恨,在世间难逃命运”。那些烟尘一而再,再而三地模糊了蓝智萍的视线。
节选自《蓝智萍:灿烂哥》
★ ★ ★
为什么还俗?王如风的解释是:“佛法就是活法。《坛经》《维摩诘经》强调了,道场不在某个固定场所,而在我们心里,以及在我们心理作用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恰恰回到了世俗社会之后,修行才刚刚开始。一个人,既然能出家,也就能入世。从大乘菩萨道的角度来说,走向圆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更多的经历以及对经历的觉悟来提升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普度众生。”在我看来,这差不多是我所听闻的还俗者关于还俗最无懈可击的解释。
还俗后,王如风的父亲以及姐姐,数年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王如风的出家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俗也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好在这种带有自我进阶意味的过程,没有造成家庭的破裂,没有谁受损伤。常善在H寺常住的时候,他父亲去过,住了两天,并不喜欢,黯然离去。还俗后国庆假期,王如风携妻回家省亲,他父亲内心的磕绊和顺畅,开心与不开心都不在嘴上说,只是把多年酗酒的酒杯藏了起来。
我曾经问过他,是否继续持戒,比如食素。他说:“戒有很多,主要分为菩萨戒和比丘戒,对于在家人来说是沙弥十戒。菩萨戒强调了起心动念,比丘戒针对比丘,而沙弥十戒的对象以沙弥为主,在家信众也可以将此奉为准则。本着最初的戒条来做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于吃素我不太想说。一个是梁武帝,在佛教的领域里瞎折腾,既祸害了出家人,又对不起他的政治。虽然梁武帝表面上做了很多对佛教有意义的事情,但都是别有用心吧。他是最初开始提倡素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近代大德赵朴初提倡僧装、素食、独身的六字方针。吃素非常好,但是不要盲目吃素,劝人吃素,这些要量力而行,要因人而异,要因地域去理解吃素。素的本义是清净,吃素是一件发自内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一种教条主义。但是放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是有它自身的意义的。”
学术界有一个共识,佛学不等于佛教,就像儒学不等于儒教,道家不等于道教。这一点,如果置于原始佛学与大乘佛教之间,区别就更显著。
王如风给我一种感觉,虽然在佛学院里待了将近十年,但他似乎始终是佛学的“自考生”。这也与他出家的发心机缘恰切。他的许多理解往往是基于心灵的感悟,由个人身体力行的实践所积淀完成的,所以才深入,才深刻。
我时常想,如果悬置佛陀的神性位格,将其作为某种人格类型,佛陀大抵上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人。他看到了生老病死,没有沉沦,而在积极地寻觅和传播中道、正道。这就让人觉得,他很年轻,是个青年人。出家与还俗的界限是基于佛教徒的社会身份作出的判断,对于佛教的社会族群来说也许重要 ;但对于佛学体悟,对于信仰者个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
节选自《王如风:自考生》
★ ★ ★
问:“法师,一个还俗者,在您看来,会怎样面对他曾经出家的记忆?”
广弘说:“就修行来说,出家就像是上战场。既然我们上了战场,就意味着要战斗,要跟过去的世俗和烦恼说再见。出家人的出家,在出家人的氛围下,会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坚持,也将坚持到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俗的僧人,大概会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问:“‘把出家人视为战士,出家人是去战斗的’,这句话讲得好之又好!我以前总觉得,出家人要么是一个拯救者,要么是一个凡间的常人,要么站在高处临危不惧,要么站在低处混迹于此。把人生战场化,倒是从来没这么想过。果真如此假设,那么战士会有一种‘降维打击’的落差感吗?起码菩萨不会觉得自己是战士吧?”
广弘说:“其实我讲的战士、战斗主要是要针对自己的烦恼。所以出家人要披甲精进,就像战士要披着铠甲上战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烦恼的力量太强大了。比如对于食物的贪欲,人怎么可能轻易断掉呢?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美食摆在那里,一定会流口水的。你偏要去对治它。可是如果不断掉这个烦恼,那么未来它就会作为某种力量牵引着你,成为投生的引业,你会困于欲界,吃段食以滋生。这种吸附力,会成为你投生于此的一个‘因’,淫欲心也是如此。你这一生,在世俗世界里累积起来的诱惑和烦恼已经够多了,更何况累生累世的累积。所以如果把自己理解为战士的话,我们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欲望。对于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来说,要发菩提心度化众生,回过头来还是要体现到自己身上。烦恼是否已经断除,我们其实是通过度化众生来圆满自己。”
问:“讲得非常好!如果您身边有一位朋友想要还俗,您会对他说什么?”
广弘说:“好好过日子。我觉得其实实在一点更好。你只要审慎思维过了—这是不是一个自己现在不得已、必须为之的理性选择?只要出家是理性的,还俗也是理性的,这就是你的因缘。直面自己,体验生活。”
信仰是什么?是理性的胜利。佛教与其说是让人狂热,不如说是让人清醒。如果说还俗也属于佛教文化的一支,是佛教文化这棵菩提树上的一枝,我想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自己的内心里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白草黄云,驰志伊吾,纵然狼烟四起、马革裹尸,在那些披荆斩棘的日子里,也总还有某种烦恼、欲念、错觉,隐匿于宿世的因缘。直面自己,便是坦然。
节选自《释广弘:论理性的胜利》
★ ★ ★
还俗与学历有关吗?学历越高,还俗的可能性越大。无论是社会学历还是佛教内部学历,学历越高的人,想法越多。对于自发还俗这一现象来说尤其如此。个人能力本来就强,会对教内的一些现象和僧团里的一些情况有不同看法,久而久之道心动摇,以致还俗。
还俗与出家前的职业类型有关吗?有关。僧人主要是过集体生活,所以曾经有过这种集体生活的人,比较容易适应,例如接受过较严格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的。有集体生活经历的人因各种因缘来读佛学院然后出家,有的留下常住,有的毕业了去别的佛学院发展,很多没有还俗。他们的特点是遵守清规戒律,适应集体生活,可能会与室友有小摩擦,但不会起大乱子。
还俗与性别有关吗?比丘尼还俗的概率很小,因为出家的代价本来就很大,基本上不会还俗。佛教对比丘尼出家考察严苛,以规避怀孕、生育,影响僧团声誉的风险。比丘尼入门基本上至少要一年时间,以居士身份跟随僧团集体生活一年。如果受戒人员已经很老了,六七十岁了,出家是没有人给剃度的,也就是出不了家,男女都一样。
还俗与出家人的年龄有关吗?关系密切。能还俗的人基本上都是中青年人—还俗后他们能开启新生活,找个工作,重新组建家庭。出家人一旦超过五十岁,还俗的现象少见。
高龄出家人,在僧团里处境既尴尬又艰难,可能会被随时迁单,清出僧团。僧侣是没有事业单位编制的,且汉地与西藏地区迥异。西藏寺庙里有僧籍,管理相对严格。汉地寺庙里,经常会发现一个人走了,离开了,不知道去哪里了。这种人无归处,相当于被解约,被开除。风烛残年的出家人,对僧团没有多大贡献,其形象也不突出,还要养老,由专人照顾,这着实不大可能。寺院不是养老院。一僧侣年轻时就进入僧团,为僧团付出多,平时相处人缘好,碰巧又遇上一位好当家,或许可以留住。另一僧侣来的时候就平庸,不怎么好相处,安排做事不爽快,手脚慢,很有可能会被清走。清走后,他也就没人管了,只能在外面游荡。来处即去处。
……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采访马小迎,相对而言,理应是最轻松惬意的环节。因为她是我的同事。我们同在H佛学院共事,她的办公室就在研究生班上课的教室的隔壁,甚至采访本身,也是在教室里完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采访结束后的当天,我失魂落魄,以至于郁郁寡欢。
盘桓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句话,“寺庙不是养老院”。我记得中国计量大学的邱高兴教授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有一次在嵊州,开一个关于“唐诗之路”的学术会议。返程时,我们车票时间差不多,就一起在火车站的大厅里候车。那是一个清晨,阳光洒在长椅上。我提起韩焕忠教授的调侃,说等退休了,就去寺庙里轮流住住。邱高兴教授面色沉静,淡淡地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寺院可不给养老。”当时听了,就很伤感,像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信仰不是一条船,足以令我们躺在船舱里、甲板上,饱食终日,百无聊赖地晒太阳。就算是船,船也是纸做的,是纸舢板。人其实是纤夫,是背负纤索,在纤道上拖着铁锚前行的“脚趾”。
节选自《马小迎:寺庙不是养老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