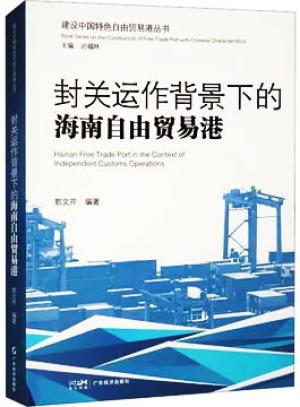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
》
售價:HK$
6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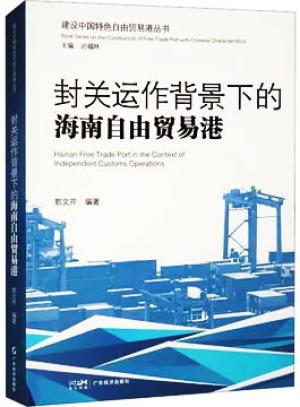
《
封关运作背景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丛书)
》
售價:HK$
85.8

《
滞后情书
》
售價:HK$
47.1

《
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近郊的工薪职员及他们的家庭(看日本系列)
》
售價:HK$
96.8

《
图说航天科学与技术
》
售價:HK$
107.8

《
北派2:西夏梵音(网络原名《北派盗墓笔记》)
》
售價:HK$
52.8

《
当代中国经济讲义
》
售價:HK$
151.8

《
40堂生死课(国内生死学教育先行者、广州大学胡宜安教授25年孜孜讲述,百万人慕名追听的“人生必修课”
》
售價:HK$
63.8
|
| 編輯推薦: |
《高楼》延续鲁迅文学奖得主王祥夫的独特叙事,以细腻笔触聚焦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借主人公大妞的苦难与执着坚守,深挖命运、人性与社会变迁的深层议题。作品生动刻画大妞被母亲跳楼阴影笼罩,却始终以等待被拐儿子小萨为信仰,独自坚守破败旧楼的形象,尽显小人物的坚韧底色。作者以拆迁家属楼为核心场景,串联大妞与邻居的命运交织,在人物坚守与时代变迁的鲜明对比中,织就时代悲剧画卷,于日常描摹中叩问人性,引发读者对命运与时代的深刻深思。
小说卖点在于小开本,便于携带,有效填充大众读者的碎片化时间,机场候车、乘坐地铁等时间段,读者可以抛开手机进行深入阅读。当代作家的最新中篇不仅带有时代性、现实性,而且可以使读者站在小说阅读的最前沿,了解小说这种文学发展的新契机,对阅读时间、场地的要求进一步减少,鼓励大家去阅读,也符合国家全民阅读的号召。
这本书是百花社倾心打造的一款可以成系列的既长销又畅销的中篇小说单行本。依托《小说月报》的号召力,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作者新近刊发的有寓意、有思想、有内涵的中篇小说单行本。
|
| 內容簡介: |
|
《高楼》围绕着主人公大妞及她所生活的即将拆迁的破败家属楼展开,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妞的生活点滴,以及她周围人的故事。大妞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她经历了诸多苦难与伤痛,她母亲跳楼的过往也如阴影般笼罩着她的生活,但却始终顽强地生存,等待被拐走的小萨归来是她活下去的全部信仰。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大妞独自坚守在那栋被时代遗忘的旧楼里,追寻着那渺茫的希望,与周围不断变迁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与邻居老张、小李等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悲剧画卷。
|
| 關於作者: |
|
王祥夫,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五十余部。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以及多种全国年度小说、散文随笔选本选载。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杰出作家奖、《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高晓声文学奖、《雨花》文学奖等奖项。
|
| 內容試閱:
|
一
怎么说呢,你不妨朝西北那边看。
如果有人留意,就会经常看到西北角那栋楼的三楼阳台上总有个女人探出头来朝下看,这女人已经不年轻了,却还梳着两条辫子,因为她梳着辫子,所以又让人觉得她还年轻,这就让人们有些捉摸不定多少觉得有点奇怪,人们看到她的嘴巴在动,却听不到她在上边独自说些什么。
“她在跟谁说话呢?跟谁?”有人问。
“那是个傻子。”有人说。
“她生下来就是个傻子。”停停,这人又说。
怎么说呢,这一带据说马上就要被拆掉了,所以有说不出的乱,到处是拆迁垃圾,不刮风下雨还好些,一旦刮风,垃圾会被吹得到处都是。院子里人们搬家扔出来的垃圾简直是什么都有,瓶瓶罐罐,破沙发烂床,但主要是各种烂塑料袋子,因为这里要拆迁,市政卫生部门就停止了这片拆迁之地的卫生工作,任由它脏乱,其实他们也收拾不过来。垃圾这东西其实是长腿的,会到处跑,今天在东,明天又跑到了西,最可怜的是道两边的树上,挂满了被风吹上去的塑料袋子。这地方肯定要拆了,人们都搬走了。但即使是这样,下边街两边的小饭店、小菜铺、小五金店还有镶牙馆、小按摩店、理发店现在还都继续开着,那些小店老板的想法是能挨一天算一天,就这么,大家都互相观望着,院子里的人家,怎么说呢,现在差不多都已经搬空了,门窗都被拆掉,铝合金、铁合金的窗框子都被拆去换了钱,整栋楼的上面现在是一个又一个的黑洞。说到拆迁,人们一开始还坚持着不搬,因为上边一直在催,一直在催,不停地在催,但没起什么作用,直到后来有了新政策,贴出了告示,上边一条一条说了许多要人不忘初心的大道理,但其实最动人的却只有一条,那就是谁家搬得早谁家就有可能先挑到那边好的楼层,那边是哪里?好像是谁都不会知道,但有消息灵通而又有关系的一些人已经私下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了,一传十十传百,都纷纷跑去看,却原来还是个工地,正在打地基。但位置很好,靠近市中心,又离一所学校不远,西边还有个大超市,大超市过去是家医院。于是人们开始搬了,一家搬,许多家就也跟着搬,有兵败如山倒的味道,很快,院子里整整八栋楼几乎搬空了。但怎么说呢,当人们都纷纷搬走,上边好像又一时不急着拆了,应该是,院子里的人家搬空了,下一步就轮到了小街两边那些大大小小的店铺,但上边下来的人只在街两边的店铺墙上刷了不少很大的“拆”字,用白粉画一个很大的圈把那个“拆”字圈在里边,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刷完这些“拆”字,拆迁工作就停顿了下来,拆还是不拆呢?人们又好像为此十分着急,这是春天时候的事,现在都已经是秋天了,树叶都开始“哗啦哗啦”地飘落了,但还是没有拆的消息,时间停在这里了,好像不再向前去,也不向后退,一时停顿了。但这里人来人往的热闹还是不减,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暂时被安排到了别处,但他们没事还是喜欢回到这里来买米买面或买菜买油,好像东西只有这里的好,或者是找老街坊站在一起说说话,而他们所说的话又左右离不开拆迁。
“怎么还不拆?”有人说话了。
“还不全因为老张那个大妞。”有人答话了。
“她想干啥?”有人又问。
“她想等她的小萨回来,她怕小萨回来找不到家。”
人们说的那个大妞就是那个经常出现在三楼阳台上梳着两条辫子的女人,人们都叫她大妞,别人都搬走了,但大妞却没地方去,你让她去什么地方?她没结过婚,虽然没男人她却生过一个孩子,但那孩子九岁上又丢了,给人贩子拐走了,所以她没地方可去,大妞可真够命苦的。人们说话的时候还会朝西北角那栋楼瞅一眼。有时候就会看到大妞恰好待在上边的阳台上正在呆呆地朝下望,还有,这里的老住户一看到她就会想起大个子老张。
“老张要是还在的话……”有人开口说话了。
但也有不认识老张的人,跟着问了一句:“老张是谁?”
“老张早死了,他要不死他闺女早就有地方去了。”
这人说话的时候又抬起头来朝那边阳台上边
看,别人也都跟上朝上边看,西北角三楼的阳台上边现在没人,但人们能看到阳台上堆满了垃圾,都是大妞捡的,她现在靠捡垃圾过活。人们都能看到她整天背着捡来的垃圾进来出去。
“谁是老张?”那人又问了,想知道个究竟。
“跟你说早死了,老张是个苦命人。”
答话的人是个黄脸老太太,是这个院子里的老住户、最近老年广场舞的明星,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她。关于这个院子里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人们都叫她朱姨,其实她不姓朱,她男人姓朱,人们就都以她男人的姓叫她朱姨。朱姨长了两只小细眼,说话总是神神秘秘,总是把身子凑过来,总是把声音放低,这么一来呢,就像是她要说的话很神秘了。朱姨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男人在农业局当副局长。那一年,她男人把他的老父亲从山东老家接了来,来了就不走了,结果就死在了这里,人们还记着那口大红的棺材,没地方放,就停在他们自家的门口,人们出来进去都要从那口棺材边上过,晚上挺瘆人的。山东人是重礼仪的,那几天好多山东人都从山东那边过来了,来奔这个丧。那时候大妞的母亲还没跳楼,大妞的家就在朱姨家对面的那栋楼,只不过朱姨在一楼,大妞家在三楼,老张女人总是挺着个老大的肚子从三楼下来叫上朱姨一块儿去买菜。
她们买菜总是在下午,这时候的菜便宜。
她们出去了,各自挎着一个竹篮。
“走慢点。”朱姨说。
“我也快不了。”老张女人笑着说。
朱姨对老张女人说:“这回你放心,一定是个小子。”
这么一说呢,老张的女人脸上就有了笑容。老张的女人是个大高个儿,大妞长到后来就随了她,也是个大高个儿。老张女人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她希望自己下一个能生一个儿子。说来也怪,老张家楼下一层的那户姓吕的山东人,女人居然也是一连生了四个姑娘,人们都叫她吕姨,其实她也不姓吕,是她男人姓吕,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随着她们的男人这么叫,男人姓什么就叫她们什么姨,叫到后来人们都不知道她们姓什么了。后来吕姨的肚子又大了,但跟着又一个姑娘生了下来,也就是老五,吕姨看着这个老五是既生气又绝望,她一使劲,把这个孩子就摁在了尿盆子里,等她松了手,那孩子却又从尿盆子里漂了起来并且尖锐地哭出了声。为了她不会生男孩的事,她男人老吕总是半夜打她,吕姨死死咬住牙不让自己叫出声。人们都说老吕的女人也太苦了,是心苦,所以人一天比一天瘦。她工作的单位就在院子东边的商店,从南边出了院子往东一拐就到,所以她把家照顾得有条有理。这天吕姨又在哭了,人们听到了她的哭声,她男人这次没打她,她男人不在家,出差了。她可以放心地哭,把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
“心病,这都是心病。”朱姨对老张女人说。
老张女人没说话,她心里也很难受。
“如果吕姨生个男孩就没心病了。”
朱姨看了看老张女人的脸马上又说:“你这回生的肯定是个小子,你看你这走路。你再迈两步,再迈两步。”
“做女人真麻烦。”老张女人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