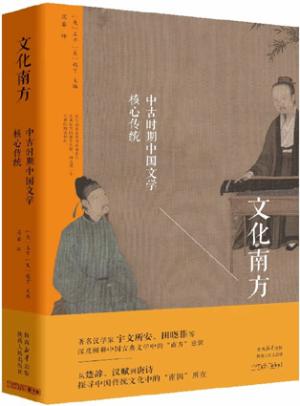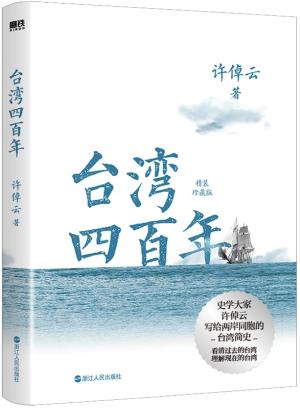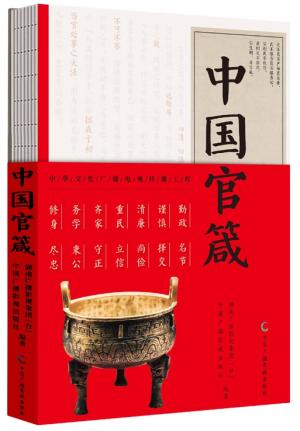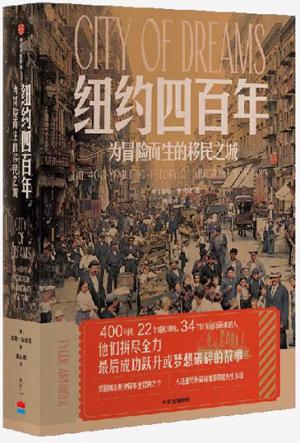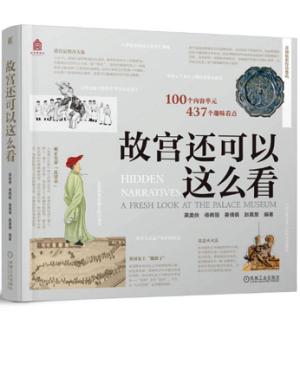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
》
售價:HK$
2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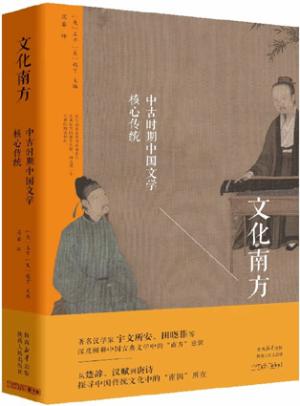
《
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
》
售價:HK$
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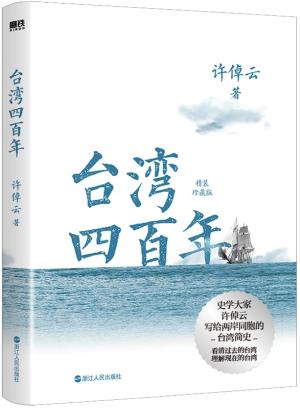
《
台湾四百年:精装珍藏版
》
售價:HK$
59.7

《
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
》
售價:HK$
1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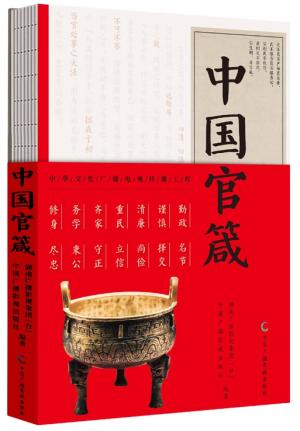
《
中国官箴
》
售價:HK$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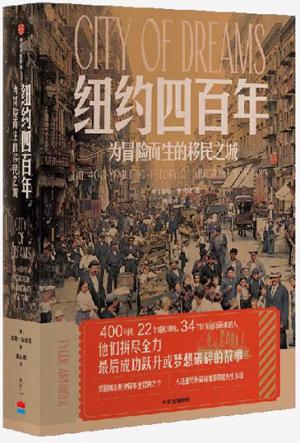
《
纽约四百年:为冒险而生的移民之城
》
售價:HK$
1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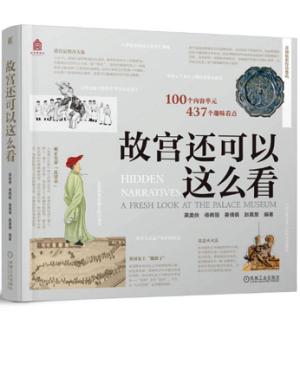
《
故宫还可以这么看
》
售價:HK$
198.2

《
高句丽渤海研究论集
》
售價:HK$
151.0
|
| 編輯推薦: |
相当扎实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基于大量清末档案、文书、日记等史料,勾勒出近代外交体系人员的群像与成长路径,梳理近代外交制度的发展演变,堪称填补学术空白之作。
人与制度并重,始终围绕人来谈制度与体系问题,使原本复杂宏大的政治史研究鲜活、具象、流动起来。
|
| 內容簡介: |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之途,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官这种全新的“职业”的?承担外交职能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使馆脱胎于传统政治体制,它们又是如何建立并运作起来的?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使馆数百名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产生、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并揭开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这一系列晚清外交机构的官员选用、人才培养、权责分配等制度问题。透过人与制度的互动,解释清末民初的外交表现,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重要基础。
|
| 關於作者: |
|
李文杰,1982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外交史与近代边疆的教学研究。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
|
| 目錄:
|
再版序言
导言
上编:总理衙门时期(1861—1901)
第1章 制度的渊源
一 礼部与理藩院
二 总督、巡抚与海关道
三 总理衙门
四 驻外使馆
第2章 总理衙门大臣
一 权责与局限
二 职能
三 选任途径
四 任职缘由
五 日常运作与权力更迭
六 任期与离署
第3章 总理衙门章京
一 权责与职能
二 考试与选拔
三 仕途、生计与保奖
四 升迁与去向
五 任期与身份背景
六 章京个案研究:杨宜治的故事
第4章 总理衙门翻译官与吏员
一 总理衙门的翻译官
二 总理衙门的吏员
附 总理衙门翻译官题名考
第5章 驻外公使(上)
一 庚子前的使才保举与公使选任
二 保举之后各方权力的影响
三 各国使差的内在特点
四 庚子之前使臣的群体分析
五 升迁与去向
第6章 驻外外交人员(上)
一 参赞(上)
附 参赞题名考(上)
二 领事官(上)
三 翻译官
四 随员、供事与学生
下编:外务部时期(1901—1911)
第7章 外务部设置与外交改革
一 改革之议
二 外务部的成立与制度改革
三 外务部制度的完善
四 1907年驻外使馆的改革
第8章 外务部官员
一 外务部大臣
二 丞与参议
三 司员的来源
四 司员的去向
第9章 驻外公使(下)
一 庚子后的保举与选任
二 保举之外的人为因素
三 庚子后使臣群体分析
四 公使成长的个案:以汪大燮为例
第10章 驻外外交人员(下)
一 参赞(下)
附 参赞题名考(下)
二 领事官(下)
三 通译官
四 书记官
结论
|
| 內容試閱:
|
再版序言 从外交官到外交史
在历史学之下众多的专门史领域,外交史应该是最为“保守”甚至“反动”的那一类。史家傅斯年曾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外交史正好有一种“伦理家”的倾向,且伦理意味极强——不但评判外交政策的“好”与“坏”,并且以本国利益得失作为评判依据。这种标准如果被片面强调,就有可能成为孟子所批评的“以邻为壑”。进入20世纪之后,秘密外交的手段逐渐为人们所厌弃,人民主权说深入实践,这使得外交的授权程序被日渐重视。进入21世纪,历史学更是倡导打破国别界限,尝试跨国界、跨区域的文化思考。但是,外交史的研究单位仍是界限分明的民族国家,研究内容仍不离交涉、谈判、条约这些充满着勾心斗角和秘密交易的过程,研究目的仍是从本国立场出发,检讨政府外交政策、外交谈判的利弊得失。
与外交史一样,政治制度史也有相似的属性。政治制度原本属于“经世学问”,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题中最常见的考察内容。张之洞在科举改制之时,建议改变几百年首重《四书》的倾向,将“史论及本朝政法”放在首场,就是看重本朝史事和制度的经世属性。[1]不过,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这种经世属性同样受到质疑。1932年,钱穆计划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有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2]该课程虽然得以开设,但两年之后便停开。现代史学界对于检讨政治制度进而为今所用的经世倾向并不表赞同,或至少不希望予以彰显。
本书涉及的外交制度正好是上述两类专门史的交叉,它们被现代史学质疑或被否定的那些属性,在今天仍有存在的必要。从19世纪中国外交延续下来的遗产,无论在双边关系、多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方面,它所产生的后果、遗留的难题、提出的挑战和形塑的思维,都在影响着现实。只要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外交史、政治制度史作为经世之学就仍有存在的必要。只不过,这些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开出方案,它是在翔实的、尽量减少偏倚地处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和问题分析。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缜密的推断并尽可能得出一些稳妥的结论,为思考现实提供一种视角与素材。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就是本着上述写作目的而作。它的思路比较简单,指向很明确:关注近代的外交人事及其效果,从制度与结构角度检讨外交人事发挥的功能。书中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机构的设计,一是人员的结构。具体而言,机构设计包括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的建制;人员结构包括诸多机构官员的教育背景、来源、考核、升迁、去向。这些要素综合作用于外交人事,决定了外交官的整体特征,并且直接影响了19世纪以来对外交涉的效果与结局。
外交制度研究的脉络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初引起全球瞩目的大事。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不但在全球经济占比中的分量日重,在国际事务和全球秩序上也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日本学者开始重拾几十年前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希望从更长远的历史演进来思考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角色。为此,他们在2003年成立了中国外交(史)研究会。这些学者包括川岛真、冈本隆司等人,关注时段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研究会成员围绕着近代中国的驻外使团、出使日记、公使与领事对外交涉的个案,展开了扎实的研究。
传统的中国外交史习惯进行价值评判,基本思路是“结果导向”。学者们对近代外交总体上持有批判态度——往往将事件结果定性为“丧权辱国”,将作为外交主体的清朝政府定性为“洋人的朝廷”。不过,无论是当年的一线外交官还是今天的学者,尤其是处于对手地位的外方,却往往能看到上世纪以来中国外交近代化和日渐进步的表现,他们会从个案中发现中国外交官的狡黠难缠,甚至让他们“吃亏”的诸多细节。如果向前追溯,这些外交官多源自1875年清朝开始陆续派遣的驻外公使、领事。故而考察晚清以来的驻外使领,成为海外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早期的日本学者坂野正高提出过科举制度下中国近代外交官诞生的问题。近年来,箱田惠子《外交官的诞生——近代中国对外态势的变迁与驻外使馆》[3],考察了清朝驻外使馆的建立、人才培养、人事改革,驻外公使保护海外华人、增设领事馆、进行边界谈判等诸多问题。她认为,清朝驻外使馆有着不同于总理衙门消极作为的政策,早于国内机构接受了当时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清朝的对外体制虽并未改变,但驻外使馆却追求新的外交模式,且因为交涉而造就了一批有外交经验的人才,他们依次递升,甲午战争之前形成规模,在保护华人、界务和外交制度建设上,有积极的作为。辛丑之后,驻外使馆有了正规官制,建立了专业化的制度。
在台湾地区,接受扎实的英国外交史传统训练、长期致力于研读外交档案的唐启华,也对台湾学界中因受“党国史观”影响而被贬低的北洋外交,进行了重新思考。围绕洪宪帝制、巴黎和会前后、1920年代的中俄关系和修约外交展开讨论,重建了弱国状态下中国外交官争取国权的史实,肯定了北洋外交的一些成绩。北洋时期外交官的群体表现,正是源自于晚清外交的培养和训练。
上述学术脉络的梳理,应能有助于安放本书的立意。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形成,源自晚清时期。学者们在讨论晚清外交官的情况时,似遗漏了一个庞大的人群——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官员。这些人包括两类:总理衙门大臣、外务部大臣这些部长级官员,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丞、参议与普通司员。后一群人的数量庞大,约有三百多位,且来源相似,结构上相对固定。他们在外交体制、在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在日常的交涉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通商大臣的体系下,外国公使的交涉对象是由两广或两江总督兼任的钦差大臣。1861年,为应对《天津条约》之后公使驻京的新形势与新挑战,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国公使交涉的对象转移到总理衙门。外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提出诉求,涉及在华的商务、铁路、矿务、借款、界务、教务、觐见君主等各类事务,可以说涵盖中外交涉的大部分内容(此外还有北洋、南洋大臣、各省督抚参与的部分)。总理衙门有作为中枢机构的特征,其上奏能迅速转变为政策执行,更便利地应对列强的诉求。所以晚清外交的重心,并不在“中国驻外公使—各国外交部”一面,而在于“总理衙门/外务部—各国驻华公使”一面。这是由近代中国的特殊性所决定,即列强用条约要求通商、传教、划界,在中国提出诸多诉求,成为其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外交涉的实践中,列强对在华利益强调的分量,远高于清朝对自身海外利益的关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交涉,远多于中国外交官在海外的交涉。这种特殊性使得被称为中国外交史的内容,通常是在内不在外,即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国门之内。
这就造成了一个连带的逻辑:在谈及中国外交官的时候,必须首先考察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官员。由于“天高皇帝远”,信息交流不畅,晚清驻外使领馆在政策执行上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发挥空间,但是从制度运作上来说,稍微重要的决策,都必须商之于总理衙门,或由驻外公使写成奏摺上呈皇帝,再交总理衙门议奏,拿出对策。在决策程序中,晚清驻外公使联络最多、积极进行问策的对象,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日常接待各国驻京公使、与之进行交涉的是总理衙门大臣、章京;起草奏摺这一建策文书,起草往来照会、信函等交涉文书的,都是总理衙门章京。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与驻外使领在人事上有着逐渐紧密的关系:驻大国公使通常在回国后进入总理衙门,如甲午之前的曾纪泽、陈兰彬、张荫桓、洪钧;总理衙门总办章京会出任特使或公使,如与蒲安臣一同出使的志刚和孙家榖、出使俄国的邵友濂、驻德公使吕海寰,部分普通章京还会担任驻外参赞。经过1901年外务部改革,这种“内外互用”的情况更加普遍,直到1907年改革之后,外务部与驻外使领馆互相转任,成为通行惯例。驻外使团成员的任命权,也从公使手中逐渐转移到外务部。
从这个发展线索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总理衙门及此后改组而成的外务部,是外交的中枢,其官员在交涉事务中的重要性,远在驻外使领之上。他们不但应对当时绝大部分的交涉事务,通过文书制定外交政策,也影响着驻外使团的人事制度和关系,还会提出外交制度改革并付诸实施。这些为此前研究注意不够的人群,正是本书要重点论述的对象。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回应科举制度下中国外交官如何形成的问题,将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看作是养成外交官的三个机构,并且将侧重点放在前两者上。根据制度设计,外交官员与科举制度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就当时的社会地位、重要性而言,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堂、司两级官员以正途出身者居多,尤其是数量多达一百多位的总理衙门汉章京,皆来自科举正途(进士、举人、拔贡),完全排斥捐纳人员。[4]这是恭亲王奕?等人出于办事慎重和保密的考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正途出身者在品行上远比杂途受到信任。这种用人特点,与驻外使团的参赞、随员不拘出身,由公使本人“自辟僚属”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国内外交机构的官员,不但在权力和作用上,而且也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都高于驻外使馆。只是到了外务部后期,前者才逐渐与后者合流。科举正途的出身,赋予了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官员包括知识结构、行为方式在内的多种群体特征。
研究思路上,我努力从晚清奏摺、日记、书札、各式题名录中,寻找所有任职于总理衙门、外务部、驻外使馆的人员资料,并为此编制了比较详实的职官表,以此探究上述官员的考选、升迁、去向,在外交体制中的具体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并思考其群体演进过程和结构特征。在详细掌握外交系统每一个个体资料的基础上,对机构建制、官员选用进行分析,从“实事”(用证据充实需要论证的议题)进而尝试“求是”(谨慎推导结论),避免跳过论证、仅凭想象进行宏大叙事。[5]
本书的“剩义”
全书得出的结论比较清晰,已经在书中呈现,这里仅就结论未及之处做一些展开说明。
首先是总理衙门、外务部、驻外使馆的制度影响和意义。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受欧风美雨的持续冲击是一个不争之论。但中国制度变迁所走的路径,不同于日本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制度有着悠久的本土传统,官僚制的整体架构从秦汉以来不断发展并得以完善。其设计除了满足实际的政治需要,在理念上则是融汇了儒家的理想型模式,特别是吸收了《周礼》的设计,形成了六部制度。在遭遇西潮冲击之时,中国制度并非另辟一径,建立新制,而是利用颇具弹性的旧制来适应新的需要。总理衙门、驻外使馆的设置在当时颇有些“创新”的意味,但实际上都只是旧制中的顺势生长,并未对既存体制造成大的冲击。
具体而言,晚清外交制度的变革,并非在既有的架构之外做加法,增添新的机构和人员,而是利用了“使职差遣”的便利。清朝仿行军机处的兼差模式设立总理衙门,使用的关防名为“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中挑选官员兼任大臣,另外从内阁、六部、理藩院挑选司员兼任章京。前者三至十人,后者四十八人。入值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各带原部院的本职、品级与俸禄。与此同时,驻外使团也采用“使职差遣”模式,作为使团负责人的驻外公使,关防名称是“钦命出使大臣”,他们各带三、四品京堂至六部侍郎不等的本职头衔。驻外公使之下的使团参赞、随员、翻译,则各带候补府州县与佐杂官头衔。这样一来,在交涉一线的所有官员——总理衙门堂、司两级,驻外公使及其下属,都在旧的官僚体制占有一席之地。这两个被冠以“钦命”的制度体系,都属于临时的皇命性质,差满即可销差。“钦命”的差使,意味着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官员,而无需对应固定的品级。这使得外交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拘资历被量才任用,同时又不会冲击既存的官僚体制。在财务上,总理衙门经费主要来自洋关三成船钞,驻外使馆经费来自洋关六成洋税,这些都是新的海关税项。它们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来,并未冲击既有的财政结构。
如此看来,旧体制可以根据新产生的需要进行调适,发挥新的功能。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有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总理衙门运转数十年,其负面效应饱受质疑。兼差的制度,让官员在时间和精力上无法专精。19世纪末,出现大量改革总理衙门的声音,建议仿照各国惯例,建立“外部”。这项改革由中国士大夫提出,最后借助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得以落地。
按照《辛丑条约》第十二款规定,总理衙门按“诸大国”意见进行改革。列强驻华公使要求将总理衙门改组为责有攸归的中央部门,由宗支亲王一人管理,另派两人为会办:其一为军机大臣,其一为新部门的尚书,另外须有一位熟悉泰西语言的大臣担任侍郎。与此同时,总理衙门章京改为专任,经过重新甄选,转为外务部司员。一些总理衙门的制度特征也被连带传递给外务部:总理衙门“有官无吏”,不用胥吏而采用司员办事。总理衙门章京转为外务部司员,开去原部院职务专办外交,同样排斥胥吏办事。后续新设中央各部,也以外务部为蓝本。这样,就有可能让胥吏办事的模式从体制中被逐渐消除。
另一方面,在总理衙门司员办事的模式之下,章京通过日常事务积累经验。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从无到有,从单薄到丰富,成为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力,负责与各国驻华使馆人员交涉,处理本部门交涉文书,逐渐成为有着一门专才的外交人员。但在原有的使职差遣体系内,总理衙门章京的升迁依赖于他们在部院衙门的本职,多数人都是六品主事到五品郎中不等。再往上,就需要离京外任道府官员,或者升任在京三四品京堂。无论哪一种,他们都很难升任一般由一二品官员担任的总理衙门大臣,而只能离开此地,另寻发展。因此,原有的在章京任上积累的经验和专才就无法传承。外务部为了安置总理衙门四位总办章京,特意设置了三品的左右丞、四品的左右参议职位,如此一来,五品郎中就可在本部门实现内部升迁,而无需离署、离京去迁就仕途。这一设置有利于外交官职业化的形成。而这个经验,同样传递给此后新成立的中央各部,促成各部门官员的专业化。
最初,驻外使馆方面同样采用“使职差遣”制度,公使出洋时各带本职。这些本职多为三、四品京堂,即那些无需常川到署办事、被看作是“冗官”的职位。公使三年一任,对使团参赞、随员、翻译等外交人员有奏调任用之权。这些使团成员同样属于使职差遣,各带有府州县候补官的头衔。使团有三年一次的保奖,用以奖励成员在外的劳绩,帮助他们仕途的升迁。无论是公使还是参赞、随员,他们进入使团的主要考量,都是借助资历谋求本职晋升。所以驻外使团虽已具备外在的形式,但并不能培养比肩英日等国的外交官。外务部时期的改革,首先将驻外使团各类外交人员变为实职,给予品级,同时让他们与外务部丞、参、司员相互调用,一方面,打通并共享了国内外外交系统的专才及其交涉经验,另一方面,外交改革让内外的外交人员在体系内都有对应的品级和地位,无需借助外官便能完成升迁。这使得外交系统率先实现专业化。
从总理衙门、外务部和驻外使馆发展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们借助清朝固有制度中的使职差遣而宣告成立,利用劳绩保奖的旧制度吸引人才。因实践中遭遇各式问题,清朝对外交制度进行改革,借条约落地建立新的机构,使专业人才久于其任,实现专业化。在清朝最后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但出现了一批经过外交训练的近代外交官,而且因总理衙门、外务部身处外交一线,汇总各类外来知识、技术、方法,也培育出一些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法律人才与西北史地学者。
中国制度原本有内在的逻辑与弹性,可以借此衍生新机构,并承载新的功能。试想一下,如果1860年“庚申之变”后清政府直接模仿欧美,设立平行于六部的外务部,是否能被舆论接受,是否具有可行性?
六部制度当时已存续一千多年,其设置不但反映了传统社会对政府功能的期待,更有着儒家经典的“加持”——它源自寄托儒家理想的《周礼》的设计,吏、户、礼、兵、刑、工与天、地、春、夏、秋、冬的周礼六官契合对应,不容随意更改。“庚申之变”所激发的华夷对立,更是让士人无法因“寇仇”的原因,轻率变更“先王”的设计。就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及其连带的财政支出而言,“原额主义”与轻徭薄赋的理想,也不允许清政府增加大额开支,建立平行于六部的其他中央机构。只有当清朝在交涉实践中逐渐暴露深层次问题,士人深入检讨总理衙门的弊端,从根本上意识到设置新的外交机构的必要性之时,外务部的出现、驻外公使内外互用、原有的使职差遣制度被抛弃,才水到渠成。
这个过程似乎也是近代制度变革的普遍路径:以既存制度为基础,就地取材,利用旧制度的弹性来适应新的功能和需要,先融汇中西制度,再适时进行调整,最终走向更深入的改革。因旧制度存在惯性,故而难允突然间新起炉灶;但旧制度又具有弹性,提供了在既存框架中求变的可能,且能因点滴累积而最终达到质变。近代的制度变革虽讲中体西用,最后却是西用日涨而中体日销。这是一个无法跳跃而去走捷径的过程。
专业化外交官群体的形成、外交体制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事,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熔铸、积累、裁汰,最后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进行确认和加强。新的外交官群体熟稔职业规则,忠实于国家利益,他们的前后传承,突破了政权嬗替的局限。
外交史的新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重点补充了外交官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块——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官员的成长与演进,大致完成了外交官研究的拼图,但是尚有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相关议题。我们不妨从1949年之后外交史的脉络来观察,以便对该书相关议题的研究,做更为全面的把握。
作为专有名词,外交(diplomacy)一词与西方近代国际关系发展密切相关。狭义地讲,它指主权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利益的行为。具体包括遣使、谈判、同盟关系、国际组织、条约与国际法等内容。它是国家达成自身利益的方式,是军事之外的另一手段。在1949年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外交史的上述内容更多地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及与之对应的“中国人民反侵略史”的形式呈现。
帝国主义侵华史所展示的,主要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它在学术上针对的是1949年之前“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辩护,力图掩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的实质”的历史著作,如中国海关洋员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其写作的现实目的,则是帮助“我国人民了解祖国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惨痛历史”,促进“激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6]在该体系之下,有若干双边关系的历史研究,主要是美、英、日、法等国的侵华史。其中,美国并非19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交涉对象,但因为20世纪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向,美国侵华史成为最早写成的国别侵华史。而日本侵华史的议题则集中于甲午战争之后的五十年,尤其是两次中日战争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到了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沙俄侵华史又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多所高校都专门策划该议题的写作,编写了多卷本的沙俄侵华史。
198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逐渐向中外关系史转变。相对于此前研究强调侵略与反抗,中外关系史对于中外交往的关注增加,外交、军事的内容依然明显,但更多地加入了经济、文化关系的内容,且更倾向于呈现近代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接受和利用国际规则的全过程。
2000年之后,近代外交史研究显示出更加深入和多元的特点。在史料利用上,多语种的外交档案得到大规模挖掘。如果说此前的外交史研究较多依赖中文史料和部分被纳入侵华史主题之下的外文档案,包括官方奏摺、大员文集、日记、笔记、中外照会、议会文书以及包含上述类型的各种专题史料集,此时则是大规模利用解密的外交档案。这原本应该是外交史研究的当然之义,但直到21世纪之后才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做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网站开放了大量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以及北洋时期外交部档案,对外交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研究,较多回归到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聚焦于一系列与近代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议题,如历次战争前后的交涉、条约签订与修改、条约文本,条约涉及的口岸开放、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裁厘加税,中国海关税务司、租界与租借地、边界事务、教案与涉外司法、华人华侨事务。这些议题,或者为近代中外交涉的内容,或者是交涉和条约的衍生事务。对它们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是史料积累和学科内部成长综合作用的结果。
伴随对外交史理解的深入,外交史研究也不再局限在狭义的主权国家间的交涉、谈判、战争,而是将与之相关的民间力量、社会舆论、文化交流等都纳入视野。这种更广义层面的理解,与20世纪以来外交与政治实践的变化和发展是相吻合的,即人民主权说被广泛接受,使得作为权力来源的人民在外交实践中有着越来越重的分量,在研究内容上也从秘密外交扩大到大众心理与舆论,从外交精英的谈判、签约交涉延伸为人民的认可与授权,从关注重要政治外交人物到重视普通和具体的人的价值。外交史原有的双边谈判、条约交涉的研究议题,早已逐渐扩大到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民间外交、经济关系、社会文化、思想变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其中,既有对重要人物、关键时刻的重新反思,也有对普通人、日常时刻的多加关注。此外,除了原有的注重单一国别的中外交涉史,学界更多关注背景更为多元、互动更为复杂的多边关系与国际关系史;除了原有的侧重利益博弈的外交史,人们也更多关注含有复杂元素和变量的全球史。可以说,狭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双边交涉为主要内容的外交史的藩篱正在被拆除。
与此同时,国内外交史的发展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及融入世界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人们越来越有兴趣从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以降全球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因应、制度转型与经济和社会变迁,外交史研究不再仅仅作为侵略与反侵略史的附属。如随着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日重,学者们会更有兴趣挖掘周边国家史料,对读中外文的宗藩文书,重建传统宗藩关系的相关史实,进而对宗藩关系作宏观的重新思考。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点——作为清政府交涉对象的驻华使领系统、因通商租地形成的租界这一特殊城市形态以及被帝国主义直接占领的租借地——之外,外国企业与在华商人、作为中国政府组成部分的外籍海关税务司、除教案之外教会的其他活动等更广义的“帝国主义在华存在”,也都是近年研究的热点。有关中外条约的诸多讨论,将条约文本与翻译理论、国际法实践、不同文明间交流结合起来,显示出不同于既往的研究视角。可以说,近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与周边关系、中国在大国博弈中的过往及中国在未来可能发挥的国际影响。以往中国外交史侧重揭露侵略、记录国耻的功用得以大幅拓展。
再回到与本书相关的议题。本书补充了外交官成长的另一半(即与驻外使馆相对应的国内的外交人员),因主题所限,未能对总理衙门与外务部的日常运作进行个案研究。就书中提及的各方面线索而言,至少有以下议题可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是海关道台与交涉使、交涉员的问题。外交活动是一国主权的重要内容,主权不可分割,故而从严格意义而言,有政出多门意味的“地方外交”是不成立的。但在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大臣制度之下,兼任通商大臣的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以钦差的身份,代表清帝与外人交涉。《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根据条约规定,通商口岸领事官可与当地道台同品交涉,而道台作为督抚属官,受督抚节制,自然有本省利益的立场,于是产生了“地方外交”。当重要督抚兼任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或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名时,“地方外交”问题便更加突出。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朝在改制的东三省设立奉天、吉林交涉使司,随后推广至其他各省。交涉使主持一省外交事务,与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并列,受督抚节制并受外务部领导。民国后改为交涉员署,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才陆续收回该派出机构,“道台—交涉使—交涉员”这一系列特殊的外交机构方告结束。这种前后延续约七十年的“地方外交”体系,其涉及的外交事务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体的制度运作、在外交事务上发挥的实际作用,尚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
总理衙门分国别股办事,各股涉及业务,更适合被称为“洋务”而非“外交”。举凡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政之中涉及外洋的内容,都进入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如公使与海关道的选任、海关税收、外债、涉外司法、船舰、铁路、矿务、新式教育。经办这些事务的官员,在各省有督抚、洋务局、通商口岸道台,在京则由总理衙门统筹,因此而产生出一些衍生机构,如船政大臣、路矿大臣、学务大臣,他们多由总理衙门大臣兼任或举荐。到外务部时期,相关洋务机构相继单列,首先是外务部,而后有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各部。各类洋务从总理衙门剥离出来,外务部逐渐转变为专司外交的机构。与此同时,负责通商口岸交涉事务的,也从海关道台、督抚之下的洋务局变为由外务部掌握人事的省交涉使司。我们或可说,“洋务时代”至此过渡到了“外交时代”。这其中的因革历程,外交是如何通过洋务改变人们的认知,改革传统的制度,推动社会的变迁,仍可作进一步探讨。
除了洋务之外,总理衙门因办理界务问题,搜寻并汇总边疆史地信息,推动了一批总理衙门章京或驻外公使、参赞专研边疆史地,提供了展开新学问的资源,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嘉道年间的西北史地,并赋予其新的问题、方法与内涵。因此,近代建制化的机构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外,外交文书的产生、流转也值得注意。在宗藩体系之下,中外行文多使用等级秩序森严的敕谕—表文模式,周边君主行文边疆督抚,则使用平行咨文。《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英交往使用平行照会,此后随着交涉的深入,外交文书体系日渐完善,中西元首之间使用国书,其他平行往来用照会,新体系逐渐覆盖原有的宗藩文书体系。外交文书是双边与多边交涉的载体,记录、承载着诸多中外交涉与制度转型的信息。近年来,学界陆续发掘各国档案馆所藏涉华外交照会、国书、备忘录、国际组织档案,一些双边与多边交涉的史料得以被深入利用。文书所揭示的礼仪及其背后的外交体制转型、重大历史事件细节,都有希望借此得到进一步解释。
以上是借本书重版所说的一些未尽的杂语。此次重版,主要是删除了初版中较为冗余拉杂的内容,增加了部分新出的史料,纠正了初版以来热心读者和同行朋友们指出的诸多讹误。本书涉及的群体庞大,文中的论述,只能采用部分列举和归纳论述的方式。更为详尽的外交官年表,有待在进一步完善后呈现给大家。
李文杰
2025年4月28日于樱桃河畔
[1] 《清史稿》卷437《张之洞传》,第12379页。
[2] 钱穆:《师友杂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3] 箱田惠子:《外交官の誕生——近代中国の対外態勢の変容と在外公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年。
[4] 《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摺》(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6页。
[5] “实事求是”一词,来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意是讲对待古之学问的态度:以充足的证据论述字句,求得真解。实事、求是,是两个并列的动宾短语。
[6]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