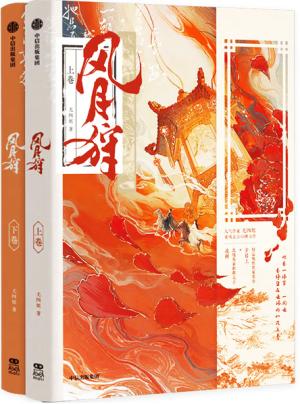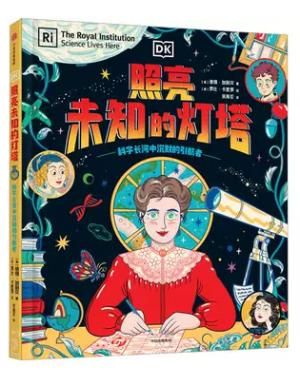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古典与文明·《周官》之制与大一统
》
售價:HK$
86.9

《
海外中国研究·朝贡·海禁·互市:近世东亚的贸易与秩序(一部刷新明清外交与通商认知的典范之作。挑战朝贡
》
售價:HK$
107.8

《
财报防坑指南:20分钟看透企业真实现金流与盈利陷阱
》
售價:HK$
76.8

《
安逸哲学:锦绣天府人生智慧“安逸四川”三部曲第一部 安逸是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的人生智慧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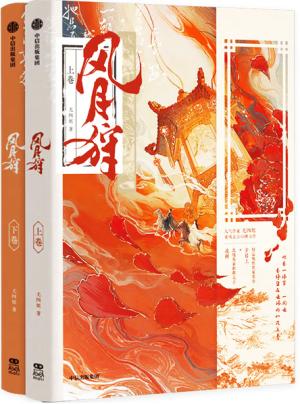
《
风月狩(全二册)
》
售價:HK$
71.5

《
大学问·改过自新:清代以来自首制度的表达与实践(以丰富案例生动还原清代以来自首制度在基层的运行图景,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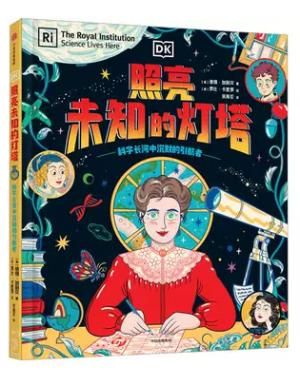
《
DK照亮未知的灯塔
》
售價:HK$
74.8

《
超越高绩效团队教练实战篇(第3版)
》
售價:HK$
153.9
|
| 編輯推薦: |
★六年修订十五万字,全新装帧,“亡命”归来,回首“维新”。
《梁启超:维新1873—1898》不只是《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出版六年后的新修版,更是许知远在《梁启超:亡命1898—1903》后,对梁启超前半生的重新理解与感悟。此番修订,不仅统一了开本、装帧,而且封面选用康梁合影,昭示着梁启超从万木草堂十大弟子到康梁并称的蜕变。五卷本《梁启超》的壮阔已初见端倪。
★从万木草堂十大弟子到戊戌变法康梁并称,百日维新的落幕却衬托出梁启超半生历程的光辉。
许知远说,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梁启超:维新1873—1898》讲述青年时代的梁启超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凭借非凡的才华,主笔上海《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主张兴西学、开民智、变法图强,并最终成为维新者的领袖之一。如果说康有为是理论的缔造者,那么梁启超就是宣传家;但比起康有为的狂傲与野心,梁启超更多的是才情、勤勉、坚定与热血。
★宏大视野,细致笔触,特稿手法,娓娓道来间,重现19世纪末读书人的救国热忱。
在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一筹莫展的时代,以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许知远五卷本传记作品《梁启超》的第一卷,讲述了梁启超从1873年在广东新会茶坑村降生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二十五年人生。梁启超这个来自广东南部一座乡间孤岛的岛民,在清朝稳定的结构中读书、成长、参加科举,又敏锐地察觉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偕同师友作出反应。他拜康有为为师,主笔《时务报》,执教时务学堂,参与戊戌变法,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从新会、广州到上海、北京、长沙,在复原人生轨迹和时代风云的同时,展现了一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本书曾以《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为名于201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出版。此次修订十五万字,特别删去了一些冗余艰涩的文言,统一用公历纪年,表达更为流畅、成熟。
|
| 關於作者: |
|
许知远,作家,媒体人,单向空间创始人,谈话节目《十三邀》主创,个人播客《游荡集》。已出版著作近二十部,包括《梁启超:亡命1898—1903》,随笔集《伯克利的魔山》《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韩等多种语言。
|
| 目錄:
|
引 言 逃亡
第一章 茶坑村
第二章 学海堂
第三章 春闱
第四章 狂生
第五章 战争
第六章 上书
第七章 改革俱乐部
第八章 时务报
第九章 主笔
第十章 海上名士
第十一章 在长沙
第十二章 保国会
第十三章 定国是诏
第十四章 咸与维新
第十五章 密谋
注 释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致 谢
|
| 內容試閱:
|
再版序 莽撞的变法者
修订比想象的更折磨人。
我犹记完成第一卷时的欣喜,它不仅是对梁启超最初岁月的叙述,还试图还原一个时代的色彩、声音与情绪,理解一个士大夫群体的希望与挫败。
重读时,我汗颜不止,意识到自己的雄心与能力间的失衡。我太想把一个时代装入书中,以至于人物常被淹没,还引来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向,似乎个人只是时代精神的映射,其内在动机、独特性反而模糊了。
同样重要的是,我试图描绘一个思想者,却对其思想脉络了解不足。若不能分析学术风气、八股训练对于个人心灵的禁锢,怎能展现出冲破它的勇气与畅快!我也对权力与学术间的纠缠缺少洞察,不管古文今文还是汉学宋学之争,皆与权力合法性直接相关,它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之一。
对于官僚机制的运转,我也缺乏确切感受。这个体制看似严密却充满漏洞。一个小小的、万木草堂式的组织,就能迸发出如此力量,掀起滔天巨浪。
意识到弊端,并不意味着能修正。我似乎能看到八年前自己的莽撞,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很多时刻,全凭直觉来应对繁多材料,建立起某种生硬逻辑。偶尔,你也会惊异于这种直觉的准确性。
事实上,梁启超正是直觉型的思想者。他以二十三岁之龄出任《时务报》主笔,从孔子改制到明治维新,从春秋大义到福尔摩斯,无所不谈,笔触甚至比他的思考更快。他依赖即兴与直觉,头脑中的理念或许庞芜、凌乱,笔下却铿锵有力。他也受惠于上海的印刷革命,它重组了知识体系,催生出新的共同话语,这个年轻的主笔脱颖而出。
这一卷覆盖了梁启超最初的二十五年,从1873年出生于华南的茶坑村,到1898年卷入百日维新。在很大程度上,他以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宣传者的面貌出现。这段时间,他的个人资料并不充分,也因此其时代背景,尤其是康有为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我记得自己对于康有为的摇摆心理。他从一个大名鼎鼎的变法者,似乎变为一个盲目自大者、一个厚颜无耻的自我推销者、一个权力迷恋者,甚至毁掉变法的躁进者。但逐渐地,敬意又重新生出。面对一个恐惧与麻木蔓延的体制,他汇聚了一群维新同仁,带来一股新风,当舞台出现时,他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上。他对青年人的魅力更令人赞叹,他将万木草堂塑造为一台学术生产与政治影响力的机器,学生们聚聚散散,却始终以某种方式联结。这种力量还将延续到海外,造就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商业、文化网络。
这群广东师徒也胆大妄为。他们并非日后宣称的渐进的维新一派,只要时机适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孙文结成同盟,推翻清政府统治。也因此,当维新受挫,围园锢后的计划并不令人意外。
这一版的叙述更为流畅,我尽量将古文白话化,删减了一些烦冗的引用,但一个缺陷仍旧显著。1888年第一次上清帝书以来,康有为在十年间创造了一套政治哲学,从《公羊春秋》到议会民主,杂糅又充满大胆的想象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启超的思想不过是这套理论的阐述与延伸。但如何清晰、生动地描述这套理论,我尚未找到更恰当的笔触。
这一卷的修订,常伴随着威士忌与查克·贝利的歌声,后者常被视作摇滚乐的开创者之一,一首Roll over Beethoven尤得我心。我猜,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如彼时思想界的摇滚乐,带来巨大的感官震撼。查克·贝利令贝多芬翻滚起来,康有为则让孔子摇摆,变为他的变法思想的支持者。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在这一卷中,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
2024年11月11日
第八章 时务报
一
当汪康年从武汉登船,沿江而下时,预料不到自己将面临的混乱与机会。在张之洞眼中,上海强学会迅速滑向令人不安的方向,他要汪尽快接掌这个组织。《强学报》的第一期就在封面上使用孔子纪年,“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并列。两位主笔徐勤、何树龄忠实地贯彻了康有为的理念,宣扬孔子改制考的理论。
身在广东的康有为也期盼汪康年的上海之行,相信他能化解强学会与张之洞之间的矛盾。“此人(汪康年)与卓如、孺博至交,意见亦同”,1896年1月26日,他致信徐勤、何树龄,建议他们“忍辱负重”,与汪康年联合起来,也要找梅溪书院的张经甫多商议。
这期待落空了。汪康年抵达上海后,北京弹劾的风波也波及于此。2月4日,张之洞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关闭只出版了三期的《强学报》。汪康年的上海之行变成了对强学会的接管。《强学报》同人将不满转嫁给了汪康年。学会办事者之一康有仪,也是康有为的堂兄,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语气酸涩又不满,还充满自辩。他仅把三十几两银子、七十多块大洋,还有一些图书、器具转给汪康年,至于余款中的大宗——张之洞资助所剩的七百两银子,康有仪故意绕过汪,托经元善退还给了张之洞。
这小小的波折没有困扰汪康年,反而让他升起更强烈的热忱。三十六岁的汪康年“身躯短小,声音也低,走路极轻,好像有病”,表面“极谨慎小心”,却是“气强在内”。他或许意识到,这是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号“毅伯”,中国文人喜欢用名号代表人生新阶段,他期待自己更为坚毅。过去一年,他试图创办中国公会与译报,都不了了之。如今,他想把关闭的强学会转变成一个新机会,在上海创办一份报纸。这是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拂逆张之洞的意志,后者希望他迅速返回武汉,继续出任两个孙子的家庭教师;他还要在这种肃杀气氛中组建一个新报馆,资金与编辑人员均无着落。
他的好脾气与韧性,让朋友们乐于出谋划策。吴樵劝他与在南京的黄遵宪共商报事。这位广东客家人时年四十九岁,身形消瘦,“瘦到骨立而目光炯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他少年时就以诗才著称,却在科举之路上屡遭失败,直到三十九岁才在顺天乡试中考中举人。对他来说,这一年更重要的事是在烟台结识了李鸿章,李对他印象深刻,认定他是一位“霸才”。这评价与黄遵宪独特的经历相关。早在1870年,他就游览过香港,用“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惊叹。他订阅了《万国公报》,还购买了大量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当他遇到李鸿章时,后者正忙于签署《烟台条约》。这个条约开启了中国对外派驻使节的潮流,黄遵宪被裹挟进这股新潮流,跟随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驻守日本五年后,他成为旧金山的总领事,接着出任驻伦敦参赞与新加坡的总领事。当他1894年回国时,很少有人比他更理解世界与时代潮流。他的日本知识尤其丰富,写了一本《日本国志》,除去历史与文化,更有对明治维新的介绍,笃信它能给中国带来参照。他是最早意识到朝鲜问题的士人之一,建议朝鲜开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应对俄国。
…………
黄遵宪也在寻找同道,以及一项值得投入的事业。与汪康年见面后,他随即成了新计划的热情参与者,不仅个人捐助了一千元,还开始在自己同僚中筹资。在日本时,他就对“新闻纸”印象颇深,相信这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与汪康年一样,他也主张办一份译报。
…………
作为不知疲倦的通信人,汪康年将想法通报给武汉、长沙、南京、北京的朋友们。汪大燮、陈三立、吴德啸、邹代钧都主张先办译报。邹在信中希望“专译西政、西事、西论、西电,并录中国谕旨”,这样才能广泛地研习西学,分门用工,相互切磋。他们还考虑到政治危险,直接评论中国的时政令人不安,转译则安全得多,要少发关于时政的议论,“必有忌之者”。
吴樵为报馆人选焦灼。在他心目中,梁启超是个恰当的人选,在康有为一众学生中,“惟此人可与也”,若夏曾佑或汪大燮能与梁启超共事,“必能济之”。
二
5月初,梁启超抵达上海,立刻扎入了忙乱中。再度见到汪康年令人兴奋,甲午年一别,已近两年未见。徐勤与何树龄已返回广州,库房中或许还有一些尚存的《强学报》,但康有为的痕迹早已消散。
他见到了黄遵宪,迅即感受到其独特风格,“一见未及数语,即举茶逐客”。三天后,他差片回拜,仍“神情冷落异常”。黄遵宪相当傲慢,或许出于一考眼前青年的心理,他大谈日本维新,并要求梁启超作出总结。当晚10点,梁离开黄的寓所,翌日清晨,带着四五千字的文章回来。这一次,黄遵宪改变了态度,他被这个青年的概括能力、行文所震惊,尽管相差二十五岁,却开始成为梁最热烈的拥护者。
确立信任之后,一个热烈讨论期到来。报馆的选址、报纸的形态、印刷机器、人员构成、募款、编辑方向,日夜谋议此事。在出版周期上,汪康年想以《循环日报》为榜样,办一份日报,但黄遵宪与梁启超认定旬报更适合。他们还决定采用“时务报”这一报名,昭示它与现实的密切关联。
…………
至于报纸的出版时间,黄遵宪建议等到皇帝对《请推广学校折》批示之后。这份奏折是李端棻在6月12日上奏的,主张京师和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选派游学,还有一条广立报馆——“请于京师及各省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奏折分析了报纸的重要性,“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二者相需而成,缺一不可”。西方国家报馆林立,“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而“上自君后,下至妇孺”,都是阅报之人,“皆足不出户而天下事了然也”。他将此视作富强之源,因为“在上者能措办庶政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
这份奏折很可能是梁启超所拟,北京同人参与修订,以李端棻的名义上奏,为即将创刊的《时务报》寻求更明确的合法性。对这份报纸的未来,人人都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忧虑经常超过期待。危险不仅来自外界压力,也来自内部。一位友人仍警告汪康年:“卓如素未谋面,不知其为人”,黄遵宪“非任事者,相为犄角,恐有损而无益”。
…………
8月5日起,《时务报》连续四天在《申报》刊登告白:“本报定于七月初一出报,石印白纸,慎选精校,每本三十二页,实价一角五分,每月三本。定阅全年每月取回印资四角二分,先付报资者每年收洋四元,本馆按期派人分送不误。”告白还宣称出版译丛:“本报并有新译各书附印报后,如《铁路章程》《造铁路书》《华盛顿传》《西国学校课程》《俄罗斯经营东方本末》等书,皆新出希见之本。”
谁也不知道这份报纸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它与四马路上拥挤的大大小小的报馆又会多么不同。报馆最繁忙的时刻,正是江南梅雨季节,种种设想、讨论,希望与焦灼,都在潮湿中积酿。
三
1896年8月9日,报纸如期出版。封面设计朴素,刊名“时务报”三个大字居中,采魏碑体,右上侧是出版日期“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右下角则是地址“上海四马路石路”。左侧直接标明售价:每册取纸料费一角五分,定(订)阅全年者取费四元五角,先付资者取费四元。
…………
梁启超的两篇论说刊登于最显著的位置。“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以一连串比喻形容贯通之重要,他相信,国家也是如此,上下不通、内外不通正是“中国受侮数十年”的原因。该文章既是发刊词,也是创办哲学,强调报馆正是贯通中国最有力的工具——报馆愈多,其国愈强。
文中列举了中国新闻业的四个弊端:闭门造车,信口以谈,沉醉琐碎与秘辛;记载不实,在战争中,即使战败,却刊登捷报;对人物与时事的评论缺乏标准;语言陈旧,言之无物,断章取义。这些弊端拉低报馆与记者的声誉,“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蟊贼,目报章为妖言”。
他心中理想的报纸是西方大报,议院言论、国家财政、人口统计、地理状况、民业盈绌、学会课程、物产品种、邻国动态、兵力增减、律法改变、物理发现、新制造新技术,一律刊登,它的影响力惊人,“朝登一纸,夕布万邦”。他自我期许是《泰晤士报》主笔式人物——“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主笔本人也是政治领袖,昨为主笔,今日执政,早晨离开政坛,晚上主笔报馆。在文末,他引用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期许报馆之力。
倘读者因这篇论说而激动,这种激动在第二篇还将继续。“昼夜而变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镕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在《变法通议自序》中,他以一连串天文、地理、生物学的例证表明,一切都在变。他把笔锋转到制度与传统,税收、兵制、选官制度,“无时不变,无事不变”。他不无陈词滥调地引用了《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中国需要新的变。他公布了一个庞大的书写计划,将围绕变法,分十二个门类写六十篇相关文章。这是他的典型作风,急于建立一个宏大目标,赋予它独特意义。像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业,这个计划也无疾而终。
这两篇文章气势恢宏,充满来自国内外的例证和比喻、鲜明的否定与肯定以及各种感叹助词,梁启超令人赞叹也饱受诟病的风格,初见端倪。只要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稍有了解,一定可以感到这份杂志在编辑、思想、文风上的尝试。它不囿于宫廷的斗争、琐碎的社会见闻或对外部世界的简单介绍。它代表着新型知识人对于国家变革的严肃观察,一种新叙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还有姿态鲜明的改革话语的讨论。
…………
…………
他的笔端日益直截了当。第九期上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是他迄今最为大胆的论述,矛头直指过重的君权。中国有两种政治理念,前一种出现于三代之治,后一种则支配了秦代以来的两千年历史——“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他甚至将统治者视作“民贼”。他将描述限定为秦朝到明朝,读者自然可以读到现状。清代正是专制文化的高峰时刻,整个统治哲学都是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基础,雍正更是以“一人治天下”为荣。这样的统治哲学造就了“上下隔绝,民气散耎”,“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这种孤立感或许可以防止内部的挑战,但“外患一至,莫能救也”。这种孤立与恐惧让国人陷入了集体无能,对所有新尝试都抱有怀疑,“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在梁启超看来,这种体制以保护君主一人之权为目的,反造就无人负责的状态,“天下有事……天子……让权于部院……(部院)让权于督抚……(督抚)让权于州县……(州县)让权于胥吏”,最终整个国家成为无权之国。
…………
梁启超幸运得多,遇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甲午战争改变了整个社会情绪,同样重要的是,印刷术正在重组中国人的政治与日常生活,公共舆论蔚然兴起。梁启超不再依赖奏章、幕僚式的建议,开始诉诸报刊。不同时代曾孕育出不同的写作风格:阮元推崇“文选”式的写作,借此来打破考据家过分干涩的表达;曾国藩热衷于桐城派,这符合重建一个被摧毁的时代的道德需求。梁启超面对的则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逐渐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应对这潮流,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康有为和谭嗣同也分享了同样的风格,“不是收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
从万木草堂到《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他的知识训练找到了释放之处。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他的思想与写作仍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万木草堂那些汪洋恣意的演说、庞杂斑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孔子改制的设想,都渗透到他的写作中。读到《西学书目表》时,蔡元培觉得梁的分类与评语颇有用,“识语皆质识”“立意本正”,可惜“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
…………
梁启超不仅借言论影响时势,也试图采取行动。与同代读书人不同,万木草堂像一部政治机器在运转,实用的考量常常压过他们的道德困扰。既然变科举视作变法之根本,梁启超准备联络言官,在一个月内上十份奏折,皆要求变革科举。行动有赖于金钱的润滑。言官制度引诱贿赂行为,饱受清贫的御史们很愿意为几百金的报酬上折言事,他们甚至不用亲自撰写。梁启超期待募款三千金,“以百金为一分……分馈台官,乞为入告”。他用胡林翼来自我鼓励,这位中兴名臣用四万金贿赂重臣肃顺,求赏左宗棠四品卿督师,奠定了之后的胜利。他兴冲冲写信给康广仁、徐勤,“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月内可成也”,同时请求同人拟写奏折,他自己如果“独作十篇,恐才尽也”。他想明年春天推行这个计划,陈炽负责在京城运作。
金句:
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在这一卷中,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
他(指梁启超)作为一个温和沟通者、敏锐阐述者的特性,已显露出来。
他(指梁启超)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
这接连上书是清代历史上的创举。这一次,屈辱感战胜了恐惧与谨慎,无疑是对禁忌的成功挑战。他们在圣贤书上读到的崇高的道德理想,突然有了某种表现渠道,这肯定是一种奇妙的新体验。
这些文章都展示出梁启超对民智的信念,若人人都能拥有正确的知识训练,中国定变得强大。
在私下的谈话中,人们指责制度的弊端,将它公布在新闻纸上则是另一回事。
祠堂是为曾国藩所建,是湖南崛起的象征,本城社交生活的中心。
中国一整套宇宙、政治与伦理的价值观正迅速瓦解,昔日训练在现实面前陡然失效,人人感到茫然。
临行前,江标看到唐才常赠予梁启超的一方菊花砚台,还有谭嗣同撰写的铭文……这枚菊花砚代表着维新者之间的情谊,两年后则成了悲剧的象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