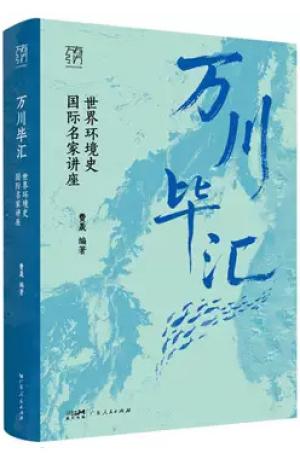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刘心武谈《三言》(冯梦龙文学经典“三言”原著的替代性通俗读本)
》
售價:HK$
74.8

《
边际利润
》
售價:HK$
75.9

《
红帆船
》
售價:HK$
62.5

《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科学的进步,在于人类不断探寻“山的另一侧”的风景)
》
售價:HK$
41.8

《
量价狙击:精准捕捉股市机会(新时代·投资新趋势)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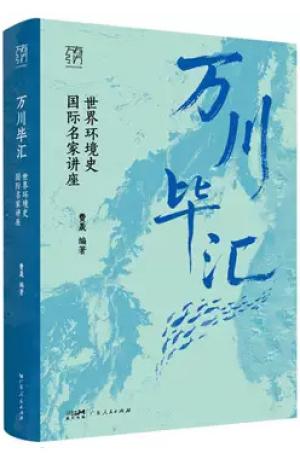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万川毕汇:世界环境史国际名家讲座
》
售價:HK$
96.8

《
企业可持续发展/ESG工作实用手册
》
售價:HK$
50.6

《
HR数智化转型:人机协同与共生
》
售價:HK$
79.2
|
| 編輯推薦: |
1.《史记》专家教大家读懂《史记》。《史记》是“正史之首”,开创纪传一体。不过由于历史与语言原因,普通读者直接入门不易。陈正宏教授作为国内知名文献学家和《史记》研究专家,长期从事经典普及工作,喜马拉雅“《史记》精讲”音频课深受读者喜爱,同时出版《史记》普及读物多种。读《众生》,《史记》不再难懂。
2.从细节中读懂人性,在历史中练就慧眼。列传作为《史记》五体中占篇幅最大的一体,在太史公笔下,既是历史书写中着力细节的部分,也是较能反映特定历史阶段中人性复杂的部分,《众生》对此有颇为细致的呈现与分析。列传又是司马迁借史事和个体命运生发感慨较多的地方,《众生》敏锐地抓住了《史记》的这一特点,从文本入手,前后贯通,抉发太史公更深层次的洞见,无愧于论者所称“太史公的异代知音”。
3.与《时空》《血缘》一起享用风味更佳。《史记》由五部分组成,“陈正宏讲《史记》系列”前两部《时空》与《血缘》已经讲了本纪、世家、表、书四部分,加上这本《众生》所讲的列传,整部《史记》文本的讲解已经完结。《众生》在风格上延续了《时空》《血缘》的特征:既通俗易懂,注重经典故事的传译,又兼顾学术性,介绍文献来源和相关考古发
|
| 內容簡介: |
列传开篇,为什么要主推隐士?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道家的老子,法家的韩非,司马迁因何拉郎配?
刘邦的侄儿,何以成了汉朝的叛徒?
猛将李广,为啥到老都没封侯?
做一个守规矩、有底线的官,难不难?
……
《众生》是“陈正宏讲《史记》系列”第三部,按今本《史记》七十列传的序次,分“先秦的隐士、贤达与刺客”“秦汉的功臣、名流与叛徒”“星空下,换几个角度看众生”三卷,对先秦至西汉前期上演种种历史活剧的各色人等进行充满历史智慧的观照与剖析,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立意,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李陵事件前后,司马迁文献整理与历史编纂两阶段工作重心转移的认识与推考。
|
| 關於作者: |
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史记精读》《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血缘:〈史记〉的世家》《史记百句》《沈周年谱》等,合作主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苏州刻书史》《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沙畹文库汉籍善本图目》等。
在复旦大学多次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史记》导读与精读课程,深受学生好评;2018年在喜马拉雅FM开设线上音频课程“《史记》精讲”,收获近五百万收听量,受到听众由衷喜爱。
|
| 目錄:
|
总序 通读《史记》,让你的视野穿越两千年
本册自序
第六卷 说《列传》(上):先秦的隐士、贤达与刺客
《伯夷列传》(上):列传开卷,为何要主推隐士
《伯夷列传》(下):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老子韩非列传》:拉郎配,有深意
《伍子胥列传》:仇恨是一颗种子
《商君列传》:他的下场,源于刻薄吗
苏秦、张仪二传:两个最著名的说客,司马迁为何不写合传
《孟子荀卿列传》:谈天的驺衍,为何抢了两位名儒的风头
《孟尝君列传》:鸡鸣狗盗的世界
《魏公子列传》:总有一种结局令人感慨
《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家兴亡,尽在此篇
《屈原贾生列传》:真实的三闾大夫,可能比这里写的更强悍
《刺客列传》:一剑出去,改变世界?
第七卷 说《列传》(中):秦汉的功臣、名流与叛徒
《李斯列传》:秦朝强人三部曲
《淮阴侯列传》:功臣的末路悲歌
《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什么投机者也能办大事
《田叔列传》:智者的传记,牵出了司马迁的一位知心朋友
《扁鹊仓公列传》:妙手回春的老中医,是神还是人
《吴王濞列传》:刘邦的侄儿,如何变成了汉朝的叛徒
《魏其武安侯列传》:高层恶斗,有什么好处
《李将军列传》: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第八卷 说《列传》(下):星空下,换几个角度看众生
《匈奴列传》:为敌国写一篇传记,需要怎样的胆识
《南越列传》:天高皇帝远,我要自己干
《朝鲜列传》:反反复复,半岛局势最难猜
《司马相如列传》:浪漫之外,还有文献
《循吏列传》:做一个守规矩、有底线的官,难不难
《汲郑列传》:做人最好是坦荡
《儒林列传》:学者从政,五味杂陈
《酷吏列传》:权够大,心够狠
《游侠列传》:那些昨日的江湖老大
《滑稽列传》:跟您开个玩笑,笑完了您得思考
《货殖列传》:逐利是人的本能
《太史公自序》:为司马氏家族书写传奇
注 释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司马迁在所撰《史记》中,以极具超前意识的模块化结构,将这部叙写历史长度超过三千年、篇章多达一百三十篇的巨著,建构为立体性的史书五体,除了本纪、表、书和世家,位列最后、篇幅最大、以描写众生百态为宗旨的一体,就是列传。
列传的“传”,本义是古人转乘车马的驿站。通过驿站,公文和消息可以迅速传递,以此“传”字又衍生出多种引申的含义,其中在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先泛指记录事件,后特指专述个人事迹的一种文体——传记。
把“列”字加在“传”字的前面而成为“列传”,作为史书中专记古今各式人物的一种体裁,首创者就是司马迁。后人解释说,那是“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意谓太史公写列传,是把一群人的事迹,有头有尾地排成一个序列,跟之前流行的编年体叙写历史,是两回事了。如果允许作一点推论,或许可以说,在司马迁的意识里,历史已不单是事件的时间性推移,同时也是事件主体的个性、志趣和行为,多重要素因缘际会的结果;而在历史中产生过影响的个人,从长时段看,是以集群的面貌出现的。因此,历史的进退,实非一人可以左右。
司马迁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他何以会有如此超前的历史意识?这就得回到西汉前期,看一看太史公当时的现实处境。
在今天西安城郊外的汉未央宫遗址北部,有两个不看标识已猜不出原本功用的土墩,它们是汉代保存图书档案文献的石渠阁和天禄阁遗址。当年,继承父亲遗志的司马迁,曾频繁出入于此,《史记》早期的撰述活动,应该也就是以此两阁所藏为基础渐次展开的。
《史记》七十列传的末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在向我们展示他以及他的家族跟历史文献的几乎是宿命般的关联之后,接着说——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里说的,是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虽然面向政治的学术潮流中,道、法、儒三派轮流坐庄,但从各地征集的书籍文献和历史性的材料,却都是汇聚到太史官署的,而主管这些文书档案的,就是先后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同样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他在父亲去世三年后,继任太史令,做的主要工作,是“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而在李陵事件后转岗担任中书令,回应同僚质疑时,他又特意强调:
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这其中的关键词“掌其官”“纂其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和“整齐其世传”,综合而论,指的恐怕不止是他们父子相继,合作编纂一部《史记》。
已经有学者经过周密的考证,指出《史记》的七十列传中,先秦诸子的列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书列传”,就是就着当时能看到的先秦诸子的各部子书,来写一篇传记。所以有关列传里,像《左传》的诸子故事反而少见引用。(徐建委《因书立传:〈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的立意与取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而如果我们拓宽一下视野,也许可以说,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整个七十列传,大概都是“因书列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都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有关人的文献,除了个人著述,也包括之前的家族谱系素材、个人传记、官员档案和外族史料等。
太史令的职责之中,本就有典守官方档案和各类文献一项,面对愈来愈多的档案文献,司马谈、迁父子应该考虑过后世严肃的目录学家都会考虑的问题——如何把这些文献有序地放置在天禄、石渠二阁的合适位置。
司马氏父子的方案,应该跟后来成型的《史记》五体中的四体,本纪、表、世家、列传有极大的关联。书之所以不归入此类,是因为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
相比之下,个人性的传记资料,是最容易散失的。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摧毁,才把《史记》一百三十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写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
具体而言,每一篇传记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相应的文献或文献群在支撑着它们。太史公是用这一方法,使经过秦火之后非常难得的中国各时代各类名人的史料,得以有一个富于逻辑和历史时间序列的安排。
我们猜测,在太初历的编纂过程中,司马迁作为以天官为主职的太史令被边缘化的那段时间,他并没有闲下来,分管文书档案的兼职,令他把职务行为跟私家著述逐步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他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了虽然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李陵事件虽然使他的这一工作有所中断,但被汉武帝突然提拔做中书令之后,这一工作应该还是继续的。
甚至可以说,未来的兰台秘府收藏格局,其实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打下基础的,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太史公的功劳。扩大而言,《史记》一百三十篇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模块化文献,两者的结合,才是太史公最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史记》成书后司马迁自述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才有一种特别的况味。“副在京师”,意味着《史记》的那个抄本,只是为京师档案图书馆中经过排比的文献,做一个模块指引和提要目录——那当然是烟幕弹——反过来也可以说,脱离了京师文献模块指引功能,具有独立意志的那个“藏之名山”的原本,才是太史公真正的心血之作。我们甚至可以猜想,一如后世那些珍视学问和文采的作者,太史公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那个本子上又添添改改了不少。
当然,从结果上看,原先的工作设计,跟后来的个人著述,在主次上是有一个颠倒的。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之后。他“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报任安书》),背负屈辱依然要从事的,恐怕主要不再是论次金匮石室之书那么表面的事务了,追求个人不朽的名山事业,这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台。像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充满质疑和感慨,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李陵事件后写定的。而本书第三卷“换几个角度看众生”所讨论的大部分篇章,应该也是司马迁在他生命的后期,尤其是担任中书令时期写成的。其中书写族群和类别的群体性汇传特别多,背后显示的,应该是司马迁在对人性有更为透彻的理解后,而改变了书写策略。从另一个视角看,中书令的职位使得他有机会掌握更为全局性的当下文献,为那样一种独特的写作,提供了上佳的条件。
很早就有人把《史记》五体中的十二本纪与七十列传特意提出对举,认为这两体类似《春秋》的经与传,换言之,就是认为七十列传是为十二本纪作解释用的。这样的看法,从纯粹经学的角度说,好像不无道理。不过回到《史记》文本本身,说七十列传为十二本纪这一绵长的历史填充了有血有肉的人,应该没有问题。但认为这些血肉之躯是为帝王世系作脚注,恐怕是既不能服人,更不能让太史公首肯的。
不过,写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其中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个体与群体,却只写了七十篇,涉及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不超过百位数,一定会让读者有一个重大的疑问:列传中有限的人物,是按照怎样的标准被选拔出来的呢?
也是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对列传的选择标准,作过一个扼要的解释,他说: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所谓“扶义俶傥”,就是为人仗义,卓而不群,不同凡响;所谓“不令己失时”,意思是不让自己失去时机,也就是能抓住机遇。因此太史公对七十列传定的入选标准,应该是:第一,为人仗义,品格卓越不凡;第二,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能以一己或一方的作为,在现实世界里留下并不虚妄的名声,那也有资格入传。
而从《史记》文本的实际看,入选标准里的第二个,其实是司马迁更看重的。七十列传中之所以有一些后代看来惊世骇俗的篇章,也唯有从这样的角度,才可以解释得比较清楚。比如刺客,放在今天就是搞国际恐怖主义的,但《史记》里居然专门写一篇《刺客列传》,而《刺客列传》里写得最长的,竟然是一个把谋杀做成生意,又没有顺利完成燕国国君定向委托项目的二流杀手——荆轲。此无他,原因就在于刺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历史走向。
因此就要说到《史记》的七十列传,跟《汉书》及以后纪传体正史里的各传,虽然分类名号几乎完全相同,但背后所支撑的选择理念,具有很大的差异:《汉书》以下正史的列传,大部分主要还是按世俗的地位、名声和道德劝戒的目标选入的。只有《史记》,所选虽然也考虑到德行一面的要素,但太史公更在意的,是那些在长时段历史演变巨流中,曾经(或可能)推动、影响甚至阻碍了历史进程的人,因为只有那些个体和人群,才是雁过留声、人过留痕的真正的历史创造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