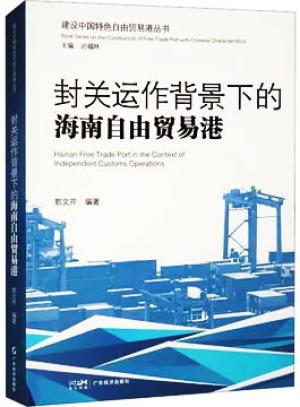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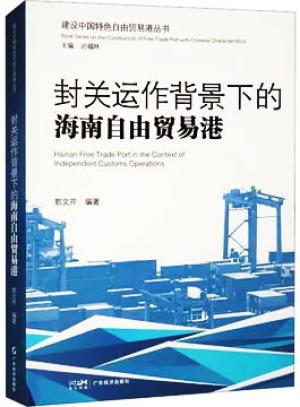
《
封关运作背景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丛书)
》
售價:HK$
85.8

《
滞后情书
》
售價:HK$
47.1

《
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近郊的工薪职员及他们的家庭(看日本系列)
》
售價:HK$
96.8

《
图说航天科学与技术
》
售價:HK$
107.8

《
北派2:西夏梵音(网络原名《北派盗墓笔记》)
》
售價:HK$
52.8

《
当代中国经济讲义
》
售價:HK$
151.8

《
40堂生死课
》
售價:HK$
63.8

《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看日本系列)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以白居易 120 余首节日诗文为线索,串联起元日、上元、重阳等二十余个唐代节日,既是诗人的私人生活史,更是一幅鲜活的唐人岁时风俗画卷,让你在诗行间触摸盛唐烟火气。
★从长安的上元灯海到江州的中秋孤月,从官场宴饮到民间嬉游,书中既有对屠苏酒、五辛盘等节俗细节的考据,也有对诗人在节日里的悲欢离合的细腻描摹,让历史可感、传统可触。
★精选《元日新年图》《上元灯彩图》等传世古画与内容互证,诗、史、画三维交织,带你穿越千年,看白居易如何在宦海浮沉中,把每个节日过成生命的注脚。
★不仅是对唐代节日的还原,更藏着中国人共通的情感密码 —— 团圆的期盼、离别的怅惘、对时光的感慨,读白居易的节日,亦是读我们自己的生活与心灵。
★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杜文玉(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唐史学会理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民俗学系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联袂推荐——这才是打开唐朝的正确方式!
★随书附赠“唐代休假指南”彩蛋手册
★著名书籍设计师周伟伟设计,小开本、特种纸、环保印刷,
|
| 內容簡介: |
|
《白居易的节日:唐诗里的岁时烟火记》以白居易的节日诗文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唐代节俗文化的全景画卷。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循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从宿州避乱的孤灯除夕、长安求仕的元日朝贺,到贬谪江州的湓浦望月、晚归洛阳的千里邈思——在不同的地理节点中,白诗如时光琥珀,封存了元日柏酒、寒食禁火、端午竞渡、中秋玩月等盛世节俗的鲜活细节。下篇则深掘个体与时代的互动——节俗的千年传承、中唐的诗酒风尚、宦海浮沉的身份印记、生命意识的悲欣交集,共同熔铸成其诗中“万人行乐一人愁”的独特节庆美学。
|
| 關於作者: |
张勃
历史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节日节气文化研究,独著、合著、主编《唐代节日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智慧》《清明》等著述20余种,发表文章200余篇。
|
| 目錄:
|
【目录】
引子 白诗中的流光与永恒
上篇 白诗与节日的时空轨迹
第一章 少小辞乡曲:宿州避乱
第二章 喧喧车骑帝王州:长安求仕
第三章 天地自久长:渭南丁忧
第四章 信马江头取次行:贬谪江州
第五章 明年尚作南宾守:擢迁忠州
第六章回马迟迟上乐游:暂归长安
第七章 再把江南新岁酒:外放杭州
第八章 彩绳芳树长如旧:转任苏州
第九章 所思渺千里:晚归洛阳
下篇 影响白居易节日生活的要素
第十章 古节遗风:诗俗风韵映千年
第十一章 诗酒趁年华:中唐风尚与节庆
第十二章 逝水惊鸿:诗行中的生命喟叹
第十三章 宦海浮沉:诗笺里的身份印迹
第十四章 雪泥鸿爪:诗途上的离合悲欢与个体选择
第十五章 节俗之外:非节俗规则对日常的塑造
第十六章 诗由境生:白居易节俗实践中的情境驱动
第十七章 内化与生新:节俗的传承者和变迁者
附录
白居易诗文及节日生活对照表
天时与人事:中国古代的节日休假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引子 白诗中的流光与永恒
节日是以历年为循环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习俗活动的特定时日,由特殊名称、特殊时间、特殊空间、特殊活动、特殊文化内涵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节日是时间的驿站,生活的华章。节日与平常日子互相穿插协调,一弛一张,共同决定着日常生活的节奏。
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节日史。大致而言,先秦时期开始萌芽,秦汉时期初步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已经十分繁荣了。代隋而起的大唐帝国,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号称“海内雄富”,经济空前发展,社会长期安定,城市繁荣昌盛,文化开放包容,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中,经过唐朝人的传承和创造,节日生活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最为绚丽多姿、令人神往的部分,唐代也成为我国节日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新”“老”节日并存。唐朝建立之前,经过长期发展,一个较为完整的节日体系在我国已经形成。根据南朝宗懔(502—565)《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当时流传于荆楚地区的节日已有元日、人日、立春、正月十五、正月未日、正月晦日、二月八日、春分日、社日、寒食、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五月五日、夏至、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秋分、九月九日、十月朔日、冬至日、十二月八日、除夕等。这些从过去走来的“老”节日,大都能在唐代找到它们的踪影。但唐代人并非仅是继承,他们还有许多自己的创造,比如中和节、皇帝诞节、清明节、八月十五、降圣节等诸多“新”节日。另外,一些“老”节日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比如在元日,即新年第一天有“立竹竿、悬幡子”祈求健康长寿的做法,连寺庙也不能免俗,司空图《丙午岁旦》诗云 :“晓催庭火暗,风带寺幡新。”
第二,具有浓厚的娱乐色彩。虽然节日历来都不乏娱乐色彩,但唐代以前,不少节日充满禁忌、迷信、祓禊、禳解等观念及活动,人们过节时常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神灵。比如寒食节时人们不敢用火,害怕引起雹雪之灾。但到唐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唐代人已把节日视为佳节良辰,是追求欢乐的日子,当时的节日诗文中频频出现“佳节”“乐”“欢”等字眼。比如,“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冷朝阳《立春》)说的是立春 ;“佳节上元巳,芳时属暮春”(李适《三日书怀因示百僚》)说的是上巳 ;“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李适《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说的是重阳。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唐代的节日确实成为时人寻欢作乐的时间。几乎在唐代的每个节日里,我们都能看到欢乐的场面。正月十五,“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牛僧孺《玄怪录 · 开元明皇幸广陵》);三月三,“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崔颢《上巳》),人们倾城出游,乐而忘归 ;九月九,“移座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九日登西原宴望(同诸兄弟作)》],人们就在宴饮歌笑中娱乐身心……
第三,节日活动往往在户外进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空间进行,节日活动也不例外。家作为日常生活的中心,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与此相应,户外则是公共空间,是社会可视空间。节日活动在户外进行,就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允许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更多人的“共同在场”,使节日呈现出热闹繁华的盛大场面。在唐代,虽然也有不少节日的活动是在户内举行的,但人们更愿意走出家门,走向大自然。像前面列举的正月十五、三月三、九月九都是如此。寒食清明节,人们郊游踏青,诸多娱乐活动更是在户外举行。“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杜甫《清明》),这些俯拾即是的诗句,展示了寒食清明期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的动人情景。在同一时间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从封闭的场所走向了开放的空间,从自我的后台走到了自我“表演”的前台。“肉既饱,酒既酣……有歌谣者进,有舞蹈者作,皆诚激乎中,章乎形容。”(欧阳詹《鲁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众人的“共在”,使得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观察者。节日的繁华和热闹就在这表演、互动、观察和被观察中形成了。
第四,宗教因素全面渗入岁时节日节俗之中。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在唐朝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节日也深深打上佛、道的烙印。这一方面体现在一些佛、道节日已成为百姓普遍参与的节日,甚至被纳入国家假日体系。比如十二月八日(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四月八日(浴佛节)、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都源于佛教,到了唐代均成为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参与节日的活动中去,和僧众一起营造节日的盛况。唐代宗就曾用奇珍异宝营造万佛山,并于“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唐懿宗也曾于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举行迎佛骨仪式 :“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苏鹗《杜阳杂编》)另一方面,许多世俗节日也出现佛、道色彩的习俗活动。如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在唐代往往被称为上元日,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而它的佛教意味也很浓厚,崔液有诗描写节日的燃灯盛况 :“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上元夜六首(其一)》 [ ] 这里的神灯、佛火、百轮、七宝,无不彰显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另外,受佛、道戒律的影响,唐高祖曾下令:“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宜禁止。”(《唐大诏令集》)后世多位皇帝也不断颁发类似诏令,这深刻影响到很多节日的饮食活动,以至人们过新年(时在正月)、端午(时在五月)、重阳(时在九月)等节日时只能素食,顶多有些腌鱼、肉干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