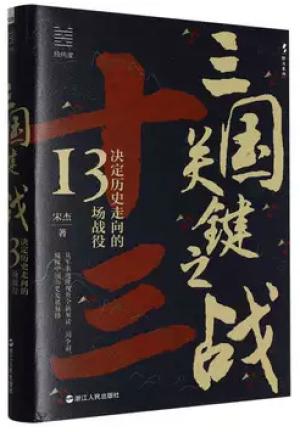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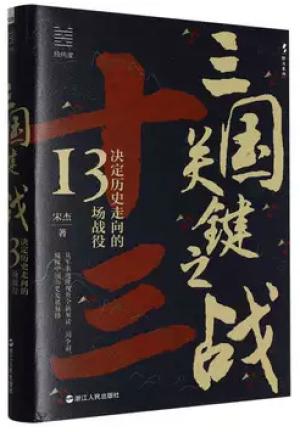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三国关键之战:决定历史走向的13场战役
》
售價:HK$
74.8

《
动物结构与造型图谱 骨骼×肌肉×立体造型×生活百态
》
售價:HK$
98.8

《
救命有术
》
售價:HK$
74.8

《
DK企业运营手册(全彩)
》
售價:HK$
120.8

《
中国历代图书总目·哲学卷(全20册)
》
售價:HK$
2200.0

《
RNA时代(诺奖得主解密RNA分子如何创造生命的新奇迹)
》
售價:HK$
86.9

《
无论在哪儿都是生活(中国好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特别奖得主肖复兴新作)
》
售價:HK$
52.8

《
隋唐与东亚
》
售價:HK$
63.8
|
| 內容簡介: |
|
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追溯到辛亥革命,延伸到解放战争,书写了苏州桃花坞大街方家和黄家两户文人家庭的命运。青年主人公方后乐和黄青梅的成长和感情历程是小说的主线。小说牢牢锁定中国二十世纪风云激荡的五十年,通过一个江南知识青年的成长和命运选择,展现的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心路群像,无论是入世和避世,无论是新文化和旧文化,无论是长期和短期,桃花坞永在血脉中跳荡,而时世动荡中,如何守护桃花坞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丰富而深刻展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知识分子千年而下最深最不可撼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小说写尽温柔细腻,也难掩大气沉厚,其历史感、市井气和思想深度为当代小说创造了新气象。
|
| 關於作者: |
|
王尧,学者,作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等;出版长篇小说《民谣》和《日常的弦歌》等多种散文集;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
| 目錄:
|
目录
引子…………001
卷一…………005
卷二…………043
卷三…………087
卷四…………123
卷五…………157
卷六…………191
卷七…………231
卷八…………257
卷九…………281
卷十…………305
卷十一………333
|
| 內容試閱:
|
桃花坞大街在苏州城北,虽然不比西中市,也是桃花坞一带像样的街道了。
方宅南枕桃花坞河,北面桃花坞大街。临近大街的门厅房,中间是过道,两侧各一间,东侧是厨房,西侧是餐厅。第二进房子临河而起,楼下是客厅和两个房间,楼上两间房,大的做了书房,小的是客房。若是客人多了,就在一楼客厅吃饭。门厅房和第二进房子之间的小庭院,东植石榴,西栽桂树,春天是石榴花,秋天是桂花。方梅初住进来时,石榴很小,一个月后,石榴好像还是那么大,母亲说:这石榴是观赏的。桂花呢,晒干了煮鸡头米。桂花开时,石榴如悬挂的小红灯笼。
两三年间,方梅初跟着母亲从杭州西子湖畔搬到了苏州十全街,再从十全街搬到了桃花坞大街,自己的气息也似乎从南宋到了明清。他不清楚父亲为什么执意要他到苏州念书,母亲对父亲的决定从无异议,他当然更不能问出个所以然。好在,他已经喜欢上这座小城了,桃花坞大街和十全街一样,似乎上百年没有变化过。他走过阊门西街,再从西中市大街走出阊门,这才渐次感受到了现代的光景。
时隐时现的父亲对少年方梅初来说是一个谜。据说父亲的实业做得很大,但在家里父母从来不说这些事。父亲在杭州、上海和苏州之间奔波,有时也去武汉。若是说想专心看几天书,便是待在杭州的意思。若是说有朋友写信来了,便是离开杭州的意思。母亲不问父亲去哪里,根据父亲出行时间长短收拾行李。如果用大行李箱,方梅初知道父亲至少半个月后才能回杭州。逐渐地,他从父亲带回来的特产猜测出父亲的踪迹。父亲说,这是青团子,这是枣泥麻饼,这是松子糖。母亲告诉方梅初,这些是苏州特产。父亲又说,山塘街上的海棠糕好吃,不好带回来,怕馊了。方梅初不知海棠糕的滋味,定胜糕已经让他回味无穷。方梅初在杭州很少尝到带有青草味道的点心,青团子给他的舌尖留下长久的回味。父亲也不清楚青团子的青是什么青,青团子是苏州人清明祭祖的供品。他没有去过苏州,父亲带来的糕团让他尝到了苏州的滋味。在父亲和母亲的闲言碎语中,方梅初知道了苏州的护龙街、阊门、山塘街、观前街,知道了从山塘街走过的白居易,若是再往北走,白居易就到虎丘了。
方家杭州的院子坐落在半山坡上,站在院门口可以看到西湖。这里安静得让方梅初有些惶恐,他时常站在门口东张西望。黄昏时,母亲在厨房做饭,方梅初就站在门前看西湖夕照,余晖尚未从湖面上散去,母亲喊他吃饭了。这个时候,他偶尔也盯着马路上的黄包车,想着有一辆车停下来,父亲挽起长袍下车,再走上山径。他这样的幻想常常落空,等到的是哥哥方竹松。他在仁和念小学,哥哥已经初中毕业了。寄宿学校的方竹松礼拜六回来,这是方梅初和母亲开心的辰光。方竹松颇有大哥的样子,通常上午便带着方梅初走下山坡,在西湖逛荡。午餐在外面吃,这样可以让母亲休息。在白堤西泠桥西侧,方竹松说:“秋瑾之前葬在这里。”方梅初似懂非懂,父亲说起这个名字,好像认识秋瑾。方竹松看着弟弟懵懂的眼神说:“你以后就知道秋瑾了。”随后轻吟道:“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兄弟俩住一个房间,各卧一床。有天夜间方竹松说到自己的打算,钻到了方梅初的被窝。竹松说:“我要去上海念高中。”方梅初想起哥哥回家和母亲聊天时说到了上海,他猜想这可能是大事,不然母亲不会说等父亲回来商量。方竹松说到此事,方梅初不知如何回答,他还没有去过上海,便说:“我去上海找你玩。”
方黎子偶尔带着方梅初出门。1910年3月,方梅初跟着父亲去了西湖金沙港蚕学馆隔壁的唐庄。那是一座已显荒芜的小园子,他们走过曲水短桥,进入一座大房子。父亲和大厅诸位寒暄时,方梅初看见悬额上书“金沙泽远”。父亲落座后,方梅初站在椅子旁边,邻座戴眼镜的先生挑了几粒话梅几颗花生给他。父亲转身看方梅初惶恐,微笑着朝他点点头,他才从先生手中接过了话梅花生,给先生鞠躬。诸位先生说话时,方梅初出了门,走到香雪轩,坐在那里看随风飘荡的翠柳。回程时父亲说:“这次是南社雅集,你知道吧,明代浙江也有南社,现在这个南社是吴江人成立的,操南音不忘本。给你话梅花生的是柳亚子先生,吴江人。”方梅初不知道这些,过了些时日他在父亲书房里看到柳亚子先生的照片,觉得有些面熟,记得先生姓柳,母亲说吴江柳亚子先生。方梅初兴奋地告诉母亲:“柳先生给过我话梅呢,还有花生。”这位小学生美滋滋回味了话梅和花生的味道。
辛亥革命成功后,方梅初才知道父亲是同盟会会员,这让方梅初后来怀疑父亲说是去苏州,其实未必。民国了,父亲并不做官,兴趣和精力仍然在他的实业。1912年暑假,父亲又说从苏州回来,方梅初相信了。父亲对母子俩说:“雪妹,暑假以后,你带梅初到苏州吧,我在葑门租了房子,梅初就在苏州念书,学堂也找好了。”很有意思,父亲把母亲的名字杨凝雪简称为“雪妹”,母亲则喊父亲方黎子“黎子”。母亲说:“好的,黎子。”母亲说了“好”,方梅初不可能说“不”。在这个院子里,他好像从未说过“不”字,对他来说从杭州到苏州只是换一个住的院子。方梅初未问父亲让他们去苏州的理由,他知道父亲肯定有什么考虑。过了些时日,他跟着父母亲先到了上海,再坐火车往苏州。在上海外滩,他和父母亲合影了,留着小平头的他,站在父母亲中间。母亲微笑着,也许是父亲的强大,念过学堂的母亲最终没有成为新女性。他看到旧照片里短发的母亲,记不得母亲什么时候梳髻了。
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是新建的,坐在车厢里,方梅初像坐在新房子里。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开阔的绿色平原和大大小小的湖泊,三三两两的房子散落在田野上,远处的村落似乎都在河边。风景飞速而过,方后乐知道这就是江南水乡了。从吴县站出来,方梅初第一个疑问是,怎么叫吴县站,父亲说:苏州在吴县辖内。他感觉眼前的苏州城是灰色的,这和青团子的青色反差太大。父亲告诉母亲,车站前面护城河的南岸便是桃花坞。母亲点点头,方梅初则想起桃花坞年画,便问父母亲:是桃花坞年画的桃花坞吗?父亲说是。
坐在黄包车上的方梅初由北向南看护龙街两边的房子,觉得苏州城就像县城。或许父亲看出了儿子心中的疑问,在两辆黄包车转到十全街时,方黎子让车子停下,他走到另一辆车旁,对方梅初说:这里向南,是沧浪亭,那里留有林则徐的足迹和题字。路西边是文庙,金圣叹哭庙之处。母亲笑着说:等住下来你再讲古吧。方梅初想起唐庄的细节,他认识的第一位苏州人竟是柳亚子先生:吴江离这里远吗?父亲说:不远,若有时间,我带你去吴江黎里。方梅初明白了,柳亚子先生家在吴江黎里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呢?
方梅初喜欢烟火气的苏州小城,自己的脾气很像这座城市。母亲觉得这座小城安全后,允许方梅初独自出门走走,偶尔也会让女佣陪着他。方梅初常常沿着十全街向西走,临近凤凰街,向南走进一条小巷子,便是网师园。穿过凤凰街向西,靠近乌雀桥时,便到了他就读的草桥国小。若是再向西走,就靠近南北向的护龙街了。护龙街南段西侧是沧浪亭,沧浪亭对面是可园。母亲带他去过带城桥下塘的振华女校,母亲告诉他,这校园是清代织造署旧址。他早上去学堂,街上便有推着车子或担着木桶卖糖粥的。卖糖粥的声音响起,临街楼房二楼便有人应答,一个慵懒的女人打开窗户,用绳子放下竹篮。当盛了糖粥的篮子往上收时,方梅初心跳,担心那根绳子突然断了。秋天的十全街,卖花生的、炒栗子的小摊隔几百步就有。冬天,则有人推着炉子卖烘山芋。街头唯一让方梅初紧张的食物是浑蛋,那种壳里有小鸡雏形的鸡蛋。一只炉子,上面放着砂锅,烧熟的五香酱油味飘逸出来。方梅初禁不住诱惑,买了一只浑蛋,他吞下去后,便感觉一只小鸡在嗓子里上蹿下跳。
他的活动范围很小,几乎就在十全街。他偶尔拐弯走到百步街,那里有一个庭院,东吴大学教员的宿舍。百步街的尽头是东吴大学的南校门,方梅初曾经站在门前的望门桥向里张望。母亲去博习医院就诊,方梅初坐车陪母亲,第一次顺着东吴大学的围墙到了同学说的望星桥。就诊出来后,母亲站在医院门口对方梅初说:东边挨着的就是东吴大学,这地方叫天赐庄。母亲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校园里还有一所学校,景海女塾。天气晴朗时,方梅初常常登上已经凋敝的葑门城楼。向东望去,是朝天湖,那里是每年荷花生日游客的聚集地。向南,是觅渡桥,据说那里是苏州护城河水位最深处。母亲对他唯一的叮嘱是,不要去觅渡桥下游泳。向北望,便可看到东吴大学的钟楼和景海女塾的教室了。方梅初目光所及,在一片粉墙黛瓦的衬托下,东吴大学和景海女塾成了苏州的西洋景。方梅初想,东吴大学南门前面的望门桥,也许是望葑门的意思,站在那里望不到葑门了。
他在黄昏的城楼上或者在夜间会听到笛子悠长婉转的声音。母亲说是昆笛,演奏昆曲的笛子。他循着声音往十全街西门走去,在百步街路口东侧的宅子门口停下。他确定,吹昆笛的是这户人家。母亲看方梅初听昆笛声的眼神,猜测儿子喜欢上了。她托人打听,吹昆笛的是位姓曹的先生。母亲问方梅初:“你确定想学昆笛?”方梅初点点头。中秋节的那天晚上,母亲提着一盒月饼、一袋螃蟹,带着方梅初,轻轻敲开了曹先生家的门。
方黎子在苏州城的一次出行,让方梅初第一次贯穿城南城北,苏州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从护龙街转到了景德路,再往阊胥路。在山塘街,父亲说,再往虎丘走,就是张公祠了,南社第一次雅集之处。父子俩走到了张公祠,方梅初定神看了看关着的大门,父亲问他:你还记得1910年3月,我带你去唐庄吗?那是南社的第二次雅集。方梅初记得,当晚柳亚子先生好像醉酒了,他在另一条船上听到柳先生不时开怀大笑。父亲说,柳先生是喝多了,那天泛舟西湖,醉而有作。方梅初后来知道,父亲说的醉而有作,便是柳亚子先生的《金缕曲》。
他们是坐着黄包车从葑门到七里山塘的。在车上看着不断后退的风光,方梅初再次感觉到了苏州和杭州的不同。山塘街一头连着阊门,一头连着虎丘。近阊门的这段,小贩子的叫卖声倒是婉转,方梅初觉得像是唱戏,父亲说,这就是市井。山塘河过往的船只有摇橹的,有撑竹篙的。方黎子那天心情很好,在山塘街走了一段返回阊门时,他对儿子说,《红楼梦》就是从阊门写起的。方黎子想去唐伯虎的桃花庵旧址,又带着方梅初从阊门去了桃花坞大街。途经桃花桥,方黎子驻足了。方黎子告诉方梅初,西北面就是桃坞中学,沿着桃花坞大街向东不远便是昆曲传习所。曹先生就在这里吹笛子?父亲说是。方梅初问:不去桃花庵了?方黎子说:不去了,以后再去,我们过一会儿看看这一带的房子。
站在桃花桥上,方梅初问方黎子:既然叫桃花坞河,河边怎么没有桃树?方黎子告诉儿子:“你以后去看《烬余录》,唐宋时此地遍植桃花,现在没有了,不知桃花庵里有没有。”方梅初还没有回神,父亲又说:“桃花坞的妙处就在没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
或许就是这次漫步桃花坞大街让方黎子有了在此置房的想法。1915年夏天,方黎子跟着母亲搬到了桃花坞大街,他即将就读的桃坞中学离家只有数百步。方梅初读到南宋《烬余录》了:“入阊门河而东,循能仁寺、章家河而北,过石塘桥出齐门,古皆称桃花坞河。河西北,皆桃坞地,广袤所至,赅大云乡全境。”桃花坞河上有许多桥,从宝城桥向东,依次是桃花桥、新善桥、日晖桥和香花桥,方宅在桃花桥和新善桥之间。新善桥向东,街道渐次宽敞,桃花庵、五亩园都在桃花坞大街的东段,再向东就是护龙街,站在桃花坞大街东头与护龙街交接处,就能看见报恩寺塔。
在桃花坞大街住了一段时间后,一天父子俩又站在桃花桥上,方黎子对儿子说:“你闭上眼睛。”方梅初觉得一片漆黑,然后有一丝光亮,他仿佛听到落英缤纷的声响。方梅初睁开眼,吟诵道:“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方黎子笑笑:“初儿会背白居易的《武丘寺路》了。”
他在桃花坞河的每座桥上看日落,他想看日出,早上起不来。在桥上看落日,但太阳好像落在阊门外面什么地方了。余晖下的桃花坞大街,宁静温馨,在傍晚的嘈杂声中,昏暗的路灯衔接了散去的余晖。这个时候,他看到桃花坞河两岸人家的灯火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