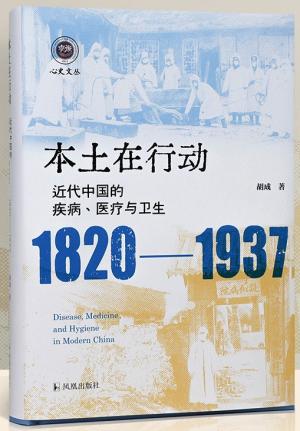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时间的朋友
》
售價:HK$
64.9

《
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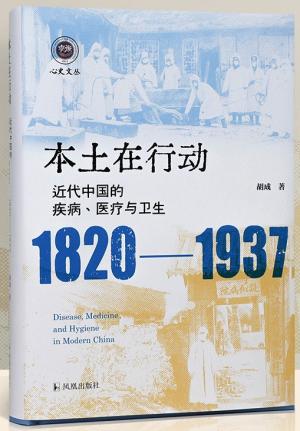
《
本土在行动:近代中国的疾病、医疗与卫生(1820-1937)(学衡心史文丛)
》
售價:HK$
107.8

《
生活中的逻辑学
》
售價:HK$
74.8

《
天下无讼
》
售價:HK$
75.9

《
春台记事 盛晚风
》
售價:HK$
76.8

《
科学与现代世界:现代科学的起源 怀特海全集系列
》
售價:HK$
99.0

《
康有为对“君民共主”宪法概念的建构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本书深入探讨了九个备受争议的中世纪话题:罗马帝国的衰亡、维京人的入侵、十字军东征、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中世纪的性观念、女性在中世纪社会的处境、思想史和环境史、黑死病,以及中世纪的终结。
“中世纪”本身就是史学界中存在争议的焦点,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中世纪的认知始终处于争辩与重构中。约翰·艾伯斯以生动的笔触引入辩题,试图提出每个学生或普通读者在探究中世纪时都会问到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历史爱好者,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理解中世纪的不同角度。这不仅是一部梳理中世纪研究脉络的经典之作,更是一本激发历史思辨的智慧之书。
“我希望自始至终都在可能的范围内展示一些别样的解释,这样解释的历史可以引发争论,乃至改变人生。虽然其中的一些解释肯定会遭到质疑,但把它们发表出来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们正在改变我们看待中世纪世界的方式。”——约翰·艾伯斯
|
| 內容簡介: |
九大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九次历史观念的重新解读,这本“吵得不可开交”的书将为你打开了解中世纪世界的新大门。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外力的催化还是内因的瓦解?维京人入侵,是野蛮的掠夺还是文明间的碰撞?十字军东征,是上帝的旨意还是权力的游戏?
…………
麻风病患者等少数群体和女性是如何生存于世的?黑死病为欧洲带来了哪些致命影响?中世纪的终点在何处?
…………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通过展示不同的历史解释,本书试图打破单一的标准叙事,探索那些被忽视的中世纪史角落。这些解释可能会引发争论,甚至彻底改变你对中世纪史的看法。
现在,请准备好颠覆你的认知,开启一段充满思考的历史之旅吧!
|
| 關於作者: |
|
约翰·艾伯斯(John Aberth)是一位独立学者和中世纪历史学家。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了中世纪历史博士学位,曾在佛蒙特州、纽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他著有大量关于黑死病和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的书。
|
| 目錄:
|
前言 001
地图列表 001
序 001
第一章 如果日耳曼人迁入你所在的帝国,别慌:罗马帝国的衰亡 001
第二章 主啊!请从北方人的蒙昧主义中解救我们吧:维京人入侵 051
第三章 这是上帝的旨意!(至少是教皇的):十字军运动 078
第四章 我是犹太人、异端、麻风病人,切勿见怪:对少数群体的迫害 150
第五章 请不要有性生活,我们这是中世纪:中世纪的性 210
第六章 马利亚和夏娃万岁:中世纪社会的女性 265
第七章 为形式的单一性而自剜双目的人:知识与环境史 328
第八章 尘归尘,土归土,大家一起死:黑死病 353
第九章 总要看看死亡的光明面:中世纪的衰落? 458
结论 485
|
| 內容試閱:
|
前言
这本书最初的构想是要让我写一本中世纪史综述,也就是从大约公元 500年到 1500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当前市场上有许多这样的中世纪历史综述教科书,这本书也要像它们一样,给出一大串年代、名字以及其他有用的事实和信息。显然,我决定不写这种书。原因也很简单: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发现我的学生几乎从来都不读那种教科书。查东西时,它们确实有用,但很难让人全神贯注地读进去。
于是,取而代之的是,我决定写一种别样的书:聚焦于近来关于中世纪历史应该怎样这一激烈争论,而非简单地陈述它是怎样的。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会称我的书为史学史著作,或者叫“书写历史的历史”。本书并没有给出关于这一时期的明确陈述,而是试图提出比它所回答的还要多的问题,希望以此激发深刻的讨论或反思。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提出每个学生或普通读者在研究中世纪时都会问到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或者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的重要性,人们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即使这些争论已近乎尘埃落定,却还是衍生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关学术文献和评论的产业,而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改变。即使我们不是总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们也仍然值得一问,因为它们将历史与我们自身的时代关联了起来;说得再直白一些,这些问题趣味横生,让历史变得“鲜活”。我希望这些问题也能让本书变得足够有趣,让人读得下去。
我是有意带着这样一个目标去写这本书的,那就是使它能够引起争议、颠覆认知、超出常规,有时甚至是异想天开,只需扫一眼章节标题便知。往严肃了说,我们的过去经常被强加上单一的、标准的叙事脉络,一些人已经在这上面开辟了旁侧的窄巷和光线昏暗的过道,而我试图在本书中为它们照亮。我希望自始至终都在可能的范围内展示一些别样的解释,这样解释的历史可以引发争论,乃至改变人生。虽然其中的一些解释肯定会遭到质疑,但把它们发表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正在改变我们看待中世纪世界的方式。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并没有做,那就是猜测如果历史出现了些许偏差会如何。这部分属于所谓的“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流派,我把它留给了另一本书。 1因此,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情景,应该说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不过,对历史的一些修正主义解释甚至改变了对真正事态发展的标准叙述,如果相关史料含糊不清,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我做这一切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作为读者的你思考过去,以及它对当下我们的意义。如果本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它就算是达到了目的。如果你对本书有异议,甚至可能是激烈反对,那么它就更是达到目的了。
第一章 如果日耳曼人迁入你所在的帝国,别慌:罗马帝国的衰亡
那是3月里一个寒冷的黑夜。我在佛蒙特州沉睡的小镇东沃伦(East Warren)的十字路口一筹莫展。我被锁在了车外,而车还在运转(别问我为什么,也别问我怎么搞的)。我敲了敲街角唯一一户人家的门,但无人应答。走投无路的我决定拦住下一辆过路车,碰巧车上是几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游客。
“帮帮我,”我说,“我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一不留神儿把自己锁在车外面了!”
“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历史学教授?”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问道。
“你们随便考我。”
“解释一下罗马帝国的衰亡,限时五分钟!”半小时后,我又回到了十字路口,在一名来自韦茨菲尔德(Waitsfield)的专业锁匠的帮助下撬开了我的车。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朋友把我送到了锁匠那里。
以上是确实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儿,我有时会复述这个故事,以证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实用性。这个故事的结束语是“所以历史真的能救命”。但它也说明了另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人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迷恋经久不衰。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些更加现代的帝国的先导。
罗马,是灭亡了还是转型了?
解释罗马衰亡的尝试,像罗马军团一样众多,像罗马本身一样古老——还请原谅我的俏皮话。其中最著名的依旧是英国古物研究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经典之作,于1776年至1788年分六卷出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不过吉本的盛名完全建立在他的文风上,而他所谓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尚武精神、活力和人员的解释,如今已经几乎被历史学家彻底否定了。自吉本的时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竞争者站出来回答过这个古老的问题。25年前,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在其《罗马的灭亡》(The Fall of Rome)一书中汇编了不少于210种解释,并按照从A到Z的字母顺序排列。其中援引了一些比较愚蠢、离谱,甚至让人觉得很受冒犯(至少就我们现代人的感受而言)的理由,包括:“不再崇拜诸神”“布尔什维克化”“共产主义”“北欧人特性的衰落”“过度自由”“女性解放”“痛风”“同性恋”“高热”“阳痿”“犹太人的影响”“男性尊严的缺失”“铅中毒”“道德败坏”“负选择”“东方化”“卖淫”“公共浴场”“种族退化”“社会主义”“厌世”“差劲儿的饮食”和“庸俗化”。事实上,如果我试图向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救世主们一口气报上所有这210种解释,我十分怀疑自己今天还在不在这里。
但是近些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完全回避了罗马何时灭亡,又为何灭亡的问题,他们怀疑罗马到底有没有灭亡。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谈及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的感受时,会使用“转型”或“缓慢过渡”,普遍回避“灭亡”或“衰落”这样的词,即使用了,也会打上引号,以强调他们对此持保留意见。因此,如今问题不再是罗马为何衰亡,而是罗马事实上真的衰亡了吗?这显然是要在根本上反思讨论的议题。
最先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疑问的历史学家,大概是伟大的比利时中世纪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他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于1935年在他身后出版。在这部影响深远的总结性著作中,皮朗认为,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建立的日耳曼继承王国保留了大量的罗马文化和制度,有很多东西至少延续到了7世纪。然而在那之后,伊斯兰教的崛起切断了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与北方前罗马帝国剩余部分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日耳曼统治者查理曼(768—814年在位)必然只能将帝国重建为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限制在几乎适用至今的地理边界之内,而帝国的重心也自然向北和向西转移了,要沿着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一直走,才能到达终点站罗马。如果说查理曼真的孕育了欧洲,那么担任助产士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在此引用一句或许是皮朗书中最著名的话:“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是无法想象的。”皮朗还声称,直到查理曼时期,与古罗马的决裂才真正出现,中世纪才真正开始,罗马和日耳曼文化的同化才真正发生。
如今,皮朗命题受到了挑战,并且被替代了,这主要是由于考古学的进步。大量这方面的证据似乎表明,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向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的扩张,是罗马帝国崩溃的表现,而非原因。它的崩溃到6世纪末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但皮朗命题有一个有趣的变体,那就是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切断欧洲的国际贸易,反而在查理曼统治时期刺激了国际贸易(尤其是奴隶贸易)的复兴。查理曼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进行贸易往来的证据,就是白银的输入,以及发行了更重的银第纳尔(denarius)或便士作为标准货币。直到查理曼在9世纪去世后,随着帝国的衰落,欧洲的经济停滞才真正开始,而由此催生出的内向型地方分权式封建庄园制,则是宣告了中世纪的开端。最近有证据表明,541年至750年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对人口产生了持续影响(不间断的贸易,尤其是谷物贸易,把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运到各个地方,所以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这也有助于强化上述观点。
尽管皮朗命题不再主宰学术辩论,但其关于古罗马并没有衰亡,而是经过漫长转型步入中世纪早期社会的观点,却被取而代之的“古代晚期”概念全盘接纳了,后者认为欧洲的逐渐演变与同一时间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各自独立的。这一术语最先由 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叫作“Sp?tantike”,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一标签被爱尔兰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在英语中普及开来。布朗通过强调早期基督教会的活力,将通常被定义为从约公元 200年至约公元 800年的古代晚期塑造成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在其最新版的教科书中,布朗强调了“微观基督教世界”(micro-Christendoms)和“象征性商品”(symbolic goods),以说明尽管作为帝国中心的罗马灭亡了,尽管它在贸易和工业领域出现了经济崩溃,但此时的“实用型基督教”(applied Christianity)还在继续茁壮成长。他还强调了基督教机构与新兴“蛮族”王国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以及地中海世界即使在政治经济分裂的情况下也仍然具有的、灵活多变的文化和生态完整性。这一切都是为了反驳吉本的观点。吉本将古罗马晚期描绘成一个堕落的历史阶段,将中世纪早期描绘成一个“原始”时代,或者说是文化衰败、无可救药的“黑暗时代”。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明显看出,在布朗的架构中,宗教和文化上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优先度高于其他一切因素。他的这种方法归根结底是利用了法国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也就是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年鉴学派。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了一个名为“罗马世界的转型”的大型研究项目,这表明,至少在学术界,古代晚期论已经得到了认可。
这就意味着,在当今的历史课程中,通常是这样教学生的:比起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时代,甚至是五贤帝时期的罗马黄金时代(96—180),转型后的罗马帝国已然面目全非,这是一系列长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所致。因此,罗马的衰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需要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暗示,帝国分裂为由“蛮族”,也就是日耳曼部落酋长统治的“继承王国”,是必然的结果,罗马人对此无能为力。这种说法将接管帝国的日耳曼人变成了无伤大雅的占领者,他们并没有入侵或洗劫罗马(他们在410年和 455年确实是这样做的),而是被邀请来的,属于和解程序的一部分。这样做是要制造军事盟友(foederati),因为此时的罗马开始出现人力短缺的情况,非常需要他们。日耳曼人并没有在帝国各地横冲直撞、到处抢掠,而是在迁徙,这通常会显示在地图上,标明每个部落大概的迁徙路线,无论是汪达尔人(Vandals,南下进入北非)、西哥特人(Visigoths)和苏维汇人(Suevi,去往西班牙)、东哥特人(Ostrogoths,意大利)、撒克逊人(Saxons,不列颠),还是勃艮第人(Burgundians)、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Alamanni,法兰西、德意志南部和瑞士)。
不过必须要强调的是,如今的学者们认为,日耳曼人的迁徙和身份认同,远没有这些严重过时的地图和现代的民族形成神话所暗示的那样有条有理,时间上也没有那么死。越过罗马帝国边境蜂拥而至的部落,“是由操不同语言、遵循不同习俗、认同各种各样传统的群体所组成的”,例如哥特人、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的身份认同必然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说“700 年的法兰克人与350年的法兰克人别无二致”是毫无道理的。那些坚持了下来、在5世纪和6世纪成功建立起继承国的部落,例如法兰克人,在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方面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文化。
甚至有人认为,日耳曼人在侵占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时,实际上并没有接管罗马人的土地,而只是接管了他们的税收,因为罗马人的市议员(curiales),或者说是城市上层阶级的居民,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去征收了。除强调连续性和渐变性以外,这个现代版的移民论在描绘日耳曼人时,无疑是以一种更加政治正确的方式,没有把他们描绘成眼神狂暴、只会破坏的“野蛮人”。
古代晚期的转型这一主题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因为尽管它可能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发轫,但它确实鼓励我们将一些典型的中世纪制度(比如封建制和庄园制)再往前追溯几百年,到它们最初扎根的时候。例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其《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写于约公元98年)中描述的日耳曼战士首领及其追随者组成的“comitatus”(意为“同伴”或“武装团体”),经过这样一番描绘,最终指向领主与其封臣之间的封建纽带,尤其是在忠诚和兵役方面。富裕的罗马元老和贵族退居庄园和田庄,在那里,他们保护“coloni”(意为“农民”或“耕种者”)免受日耳曼掠夺者和罗马收税员的侵害,代价则是土地和自由。这被视为农奴制或隶农制的前身,这种制度下的中世纪农民要受到各种法律习俗和庄园义务的约束。为了把这些铺垫好,大多数中世纪历史概述都从公元300年前后的戴克里先(284—305)和君士坦丁(312—337)统治时期开始讲起。人们认为这些对于施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确立基督教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在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定义中,上述这两点都是关键特征。然而,我们也应当指出,就中世纪早期贵族和农民的社会结构形成而言,地区差异是相当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