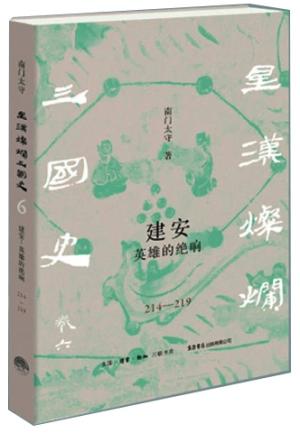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大浪淘沙:从五代到十国 王宏杰五代史三部曲系列 一部生动而富有深度的乱世长卷 一幅反映人性的丰富画卷
》
售價:HK$
105.6

《
第八个侦探
》
售價:HK$
65.8

《
情结(精装)俄狄浦斯情结/该隐情结/自卑情结/救世主情结…… 在诉说与倾听中打开心灵的窗户,探索情结
》
售價:HK$
60.5

《
台湾百科全书历史篇
》
售價:HK$
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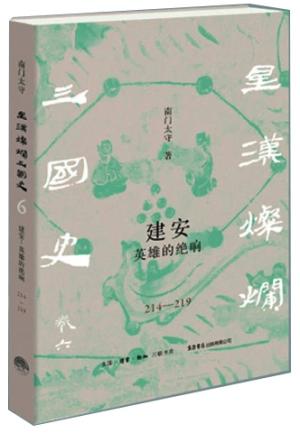
《
建安 英雄的绝响(214—219)
》
售價:HK$
64.9

《
经纬度·何以中国·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
》
售價:HK$
107.8

《
永劫馆超连续杀人事件:魔女决定与X赴死
》
售價:HK$
60.5

《
财富心理学:通向富足人生的50个想法
》
售價:HK$
82.5
|
| 內容簡介: |
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者埃里希·瓦德并非一位单纯的书斋学者。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地缘政治大变局之下,作者借重温施米特这位“新经典作家”,很好地将现实政治处境与政治军事理论相结合,以便更好地理解新的“大地的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自由主义政治语境下人们对施米特的怀疑和攻讦,作者凭借自己长期的国际政治经验和理论,肯定了施米特对政治的定义,即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这一观点在国际关系尤其在安全战略实践中,总是或隐或显地摆在人们面前。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在本书中,作者对施米特的诸多政治军事理论做了综合探讨,并对未来军事发展、国际关系的演变做了展望。通过作者的眼光,我们看到,在旧传统终结、旧框架发生动摇、变革纷起以及新的定位变得必要的时代,施米特的思想范畴和概念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埃里希·瓦德(Erich Vad,1957—),先后在慕尼黑、明斯特、汉堡研读史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在明斯特大学的哈尔维克(W. Hahlweg)教授和特拉维夫大学的瓦拉赫(J.L. Wallach)教授指导下,以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研究取得博士头衔,后投身军旅,继而又在德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担任重要职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瓦德曾任“北约”和西欧联盟国际军事参谋部成员,在此期间,他结合自己的既往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撰写了《施米特与国际战略》一书。
译者简介
温玉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德意志近代早期文学。已出版的编译著作有《启蒙时代的莱辛和他的友人》《论德意志文学及其他》《作为悲剧的世界史——〈蒙特祖玛〉悲剧与史学笔记》《驳马基雅维利》《施特劳斯学述》等。
|
| 目錄:
|
目 录
中译本前言(温玉伟) 1
中文版序 1
德文版序 1
引 言 1
一?安全政策与战略的变量 10
二 对抗与冲突 52
三 权力的优先性与例外状况 88
四 武力与权利:米洛斯对话 98
五 政治性的空间与秩序思想 105
六?扩展的战略概念 120
七 对克劳塞维茨的接受 138
八 游击队理论 156
九 正当性的范式转变 167
十 科技空间革命 179
十一 武力的升级 188
十二 制约大空间中的武力 196
十三 全球维和的矛盾 201
十四 政治与全球权力投射 211
十五 安全政策的秩序与冲突线 228
十六 中间状态 236
十七 欧洲:大空间秩序与国家利益格局之间 243
十八 对和平的定位 255
十九 总结与展望 263
出处与文献 270
??一?说明 270
??二?施米特文章、专著、报告大纲 272
??三?其他文献以及施米特遗产的图书馆资料 280
|
| 內容試閱:
|
中译本前言
温玉伟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余光中
Jeder Name ist eine Nahme[任何命名都是占取] 。
—施米特
在这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挑动全球的神经。按照20世纪政治思想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所理解的“整体战争”概念,中美两国眼下无疑正在敌对,也就是说,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所谓的整体战争扬弃了军人与非军人的区别,除了军事战争之外,也把一种非军事的战争(经济战、宣传战)视为敌对的结果。……战争是在一个全新的、提高了的层次上作为一种不再纯为军事的敌对行动进行的。这里的整体化在于,即使是军事之外的事情(经济、宣传、非军人心理上和伦理上的士气)也被纳入敌对的斗争。超出纯军事领域的一步不仅带来了量的扩展,而且带来了质的提高。因此,它并不意味着敌对的缓和,而是意味着敌对的强化。单是由于对强度的这样一种提高的可能性,朋友与敌人的概念就又自动地变成了政治的,即使是在完全淡化了政治特征的地方,也摆脱了私人用语和心理学用语的领域。(《政治的概念》增补附论,中译本2018版,页115)
这场战争虽然没有刺鼻的硝烟,没有呼啸而过的炮弹,但是,贸易制裁、增加关税等措施的实施,无不影响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贸易战、经济战的打响,不仅直接涉及两国人民,与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密切的世界各国,也无不心惊肉跳。但是这样的“战争”不可避免,因为,
在经济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把握或操纵各种经济关系,面对政治问题和政治决断时就不得不宣布保持中立,从而放弃自己对统治权的要求。(同上,页131)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没有那么健忘,“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应该时时刻刻警醒着被政治自由主义麻痹了神经的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崩溃或者说“和平演变”,除了源于其国内的积弊之外,西方国家(尤其是对峙一方的美国)的信息战、经济封锁、经济战都曾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经历过“一战”的欧洲人民事后常常重复一句话,1914年夏天的欧洲各民族“晕头晕脑地卷入了战争”。经历过“苏东剧变”的苏联人民,嘴边也可能挂着“晕头晕脑地从社会主义梦中惊醒”之类的话吧。
网络时代的我们并没有远离战争,毋宁说与战争—即整体战争—的距离更近了一步。今天,种种迹象表明,大地的法开始奏响了新一轮的三和弦:占取、划分、养育。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对立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谁才具有国际法的定义权。网络时代的占取对象会更为广泛,其占取方式可能会避免直接的暴力。在现代战争中,尤其在整体战争中,与我们日常最为贴近的手机屏幕、电脑屏幕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战场,按照瓦德的说法,
“信息战”和电子战场的非血腥手段,促使科技上势均力敌的国家在对战中,在以传统武力形式交火之前就能分出胜负。倘若信息主导了某个地理空间,那么,它就已被“占领”。(本书页[150])
在施米特看来,即便“真诚的孤独思想家”也无法摆脱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同化。因为,在人们能够通过某种行为弄清问题之前,其观点早已被占领。不难设想,倘若我们的法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们一味强调形形色色的“权利”,而闭口不讲“义务”,倘若我们的年轻人一路追捧好莱坞超人和“韩流”明星,遗忘了本土的神话和侠义恩仇故事,更不用说我们基层的教师、公务员……那么他们也许已经被西方(美式)普世价值的意见所占领。如果我们要规避因为“晕头晕脑”而犯错误,那么,施米特的洞见以及这本研究专著,就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作为一名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学习者,笔者在翻译完这部作品之后关心的是外语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清季,西方耀眼的炮弹和五光十色的主义,将古代中国拉入现代的洪流,中国学人不得不同时面对古今中西之争这样的难题。在内忧外患中,朝廷设立同文馆。不过,外语学习的建制,或者某门外语成为二级学科,还得等到科举的被废、文教体制的彻底西化。不难想见,最初教习的外语不外乎是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国家语言(英、法、俄、德、日)。可以说,自近代以来,我国的外语学习就是地缘政治冲突伴生的产物,而外语学习者的使命自一开始就与国家的危亡兴衰密切相连。即便今日,从国内的外语流行程度也可以看出列强在全球政治中的势力对比关系。作为lingua franca[通用语]的英语(英式、美式),与英国曾经的、美国如今的霸权地位息息相关,而其他与英、美相比实力较弱的国家的语言,只能作为非通用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语种”,出现在我们的二级学科中。
因此,就外语学习者本身而言,他即便不用置身枪林弹雨之中,也已经身处地缘政治纠葛的最前线,甚至自从他一开始接触外语、外国文学,这种处境就已经开始。“一战”后,国联在《凡尔赛和约》的框架内勾销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包括我国山东地区)。20世纪20年代,重新崛起的魏玛民国为了与其他列强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亟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地缘政治策略。1924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在其论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1938年第3版)中强调,德国必须重返太平洋,他建议同胞,
每一本德国书,每个在德国留学的东亚人(当然,不必到处观摩我们最核心的机械)都是我们重返太平洋的先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施行民族心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对人进行最细致的区分。(《太平洋地缘政治学》,页100,译按:此为原书页码,下文引本书亦同)
豪斯霍弗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是因为美国人早前的做法对他有所启示,
尤其是世界大战之后(引按:一战),为了征服西属美洲市场和传播思想,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大量的宣传费用。语言和民族风俗的微妙适应手段也得到了充分运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德国人早些时候具有一定优势。之前,德国为了这个目的有了一整套教科书,里面充满了各种实用的提示。现在,唤醒德国人对太平洋-美洲的地缘政治意识的时刻到了!(同上,页118)
豪斯霍弗从美国人的一份报告得知,美国在太平洋小国推行的语言-文化政策成效显著,
太平洋所有重要民族的五万名儿童在学习美国历史、美国理念、美国政治、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他们都在说美式英语,不再吟唱本民族的旧式英雄歌曲,而是吟唱美国的歌曲,不再穿波利尼西亚人的缀满花环的服装,而是以穿美国式的服装为荣。这在民族合作上是一个卓越的尝试。但是,这同样是一个对下述变化的卓越证明:一个幸福的、自足的岛屿王国变成了一个依赖于制糖业的市场,从一个曾经统治太平洋中部的王国变成了一个珍珠港海军基地的附属物。(同上,页197-198)
豪斯霍弗其实很清楚,早在“一战”前,德国人在中国殖民地就已经实施过类似的政策,而且,在豪斯霍弗看来,德国人在对中国问题的处理上甚至是美国人的老师。只不过“一战”的爆发及其后果,使得德国人不得不放弃亚太地区,无奈地再次退守到欧洲大陆中心。豪斯霍弗提到的文化政治家有来到山东的传教士、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也是中国第一代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的老师;还有在上海活动的德国前海军军医福沙伯(Oscar von Schab,1862—1934),即同济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第二任校长)。凭借这些经验丰富的文化政治家的努力,德国在山东的问题“越来越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或者至少是避免了恶的出现”(同上,页237)。
倘若不是“一战”的爆发及其后果,德国的这一政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效果。因为,
1914年战争的爆发阻止了德国推行这一文化政策,德国文化政策的敌人精心策划,尤其是依照国际法完全站不住脚地驱逐了那些手无寸铁、爱好和平的德国医生、传教士和教师,就连中国人也反对这一驱逐行为。(同上,页237)
很明显,德国文化政治家在当地实施的民族心理学以及对人做的最细微的区分起到了本应起到的作用,因为这种人和人之间心理上的微妙联系,足以产生爱憎分明的情感,一旦“那些手无寸铁、爱好和平的德国医生、传教士和教师”被驱逐,与他们心意相连的中国人也会起来反对。不过,鉴于这种业已建立起来的情感上的联系,豪斯霍弗有理由对德国未来重返亚太(尤其是中国)的可能性保持乐观,
在这种暴力[驱逐] 行为之后仍然存在诸多线索,这些线索是不可摧毁的,它们是通过一种文化感觉编织而成的,这种文化感觉预示着内在的命运亲缘(innere Schicksalsverwandtschaft)。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使德国与太平洋更新关系的要点,同时也是取得经济联系的要点。(同上,页238)
笔者在赞叹豪斯霍弗敏锐的地缘政治眼光的同时,却又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当年豪斯霍弗的苦心孤诣,在21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候),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德两国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已然成为令人瞩目的现实,中国的土地上也不再缺少他所要求的“先锋”!—笔者清楚记得在上海读书时的一天,一位教授对着课堂上一群将来可能走上讲堂的青年学子,吹捧了一番德国制造举世无双之后,不无得意地说:
学习德语嘛,就是要培养亲德派……
笔者当时的疑惑是,我们学习一门外语难道必须成为亲某某国家派吗?比如Germanophilie[亲德派] 、Frankophilie/Gallophilie[亲法派] 、Japanophilie[亲日派] ……可是,无论莱辛的例子、歌德的例子,甚至是而立之年仍立心学习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对话的门德尔松的例子,都值得我们再次反思:之所以学习外语,难道不是要借助它与这个民族的优秀头脑、高尚灵魂交流和对话?难道不是要借助它来倾听最伟大灵魂之间的交谈?难道不是要借助它来研读记录了这些对话的伟大著作?
此时,笔者更加好奇的是,当年的同窗如果已经走上教学岗位,为人师表,他们是否也在将充满稚气的学生们培养成“先锋”?
这部书稿本来由徐戬博士承译,后来笔者中途受命,硬着头皮“啃”完了似乎与自己专业不相干的一本书。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徐戬博士之前翻译的第八章内容,在此表示感谢。
2019年春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