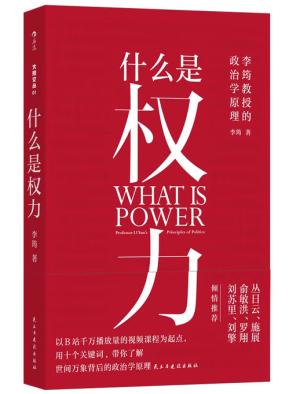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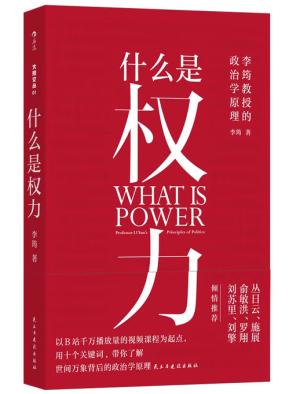
《
什么是权力(一本讲透权力逻辑的政治学入门佳作,一次从学术到生活的认知升级)
》
售價:HK$
66.0

《
债务自由:远离债务困境
》
售價:HK$
86.9

《
清代满汉关系史:全三册
》
售價:HK$
547.8

《
卢浮宫馆藏中国陶瓷
》
售價:HK$
217.8

《
建安 决战赤壁(208—213)
》
售價:HK$
60.5

《
亨利·贝尔坦的“中国阁”
》
售價:HK$
74.8

《
超越高绩效团队教练(第4版)
》
售價:HK$
153.9

《
四旋翼无人机轨迹规划与跟踪控制算法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作者在三联中读开设的同名课程获得了读者大量好评,列举评论如下:
▎格局开阔,语言铿锵有力,是学者中不多见的能用优美语言阐述历史的人。拉出一条西方政治线索,这是具有大历史眼光和大地理格局的做学问方式。
▎这一年来与教授学到了不少知识,那些曾经晦涩难懂的书在教授的一一解刨下,得以彰显其特有的魅力。准备开始按着教授的书单开始阅读,在遇到不懂的地方还会返回这个课堂再次聆听。
▎讲得好,把古希腊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及见解介绍得十分清楚,从而也就可以看出那些先贤的政治智慧是怎样的精深而卓越,甚至他们的失误也成为今天的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我们从上述介绍里却也感到,由于缺少这样一笔博大精深的遗产,我们的改革之路也势将任重而道远。
▎大政治时代,中国人对“西方”“美国”的认知将面临全新的考验。所以,重新认识西方文明传统,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源流,对于当下的中国人理解世界而言至关重要。
本书作者任军锋教授专研西方政治思想史二十余年,是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通识核心课老师之一,他开设的课程均围绕经典文本展开,强调经典文本与现实生活的相互激活:将现实“陌生化”,将文本“生活化”。在他的讲述
|
| 內容簡介: |
思想家不仅在审视自己的时代,更在与先哲对驳辩难。只有将这种对驳辩难的理路呈现出来,思想的场域才能充分打开,读者才有望身临其境,养成权衡取舍的鉴别力和观照现实的判断力。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理解政治,是新世纪压给中国有识之士的精神重担。面对这一重担,轻浮的乐观,抑或轻率的绝望,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理解”政治意味着面对现实的勇气、清晰的判断力以及智性的诚实,进而自觉审视并肩负起这一精神重担。
——任军锋
在中西碰撞、古今相照的“大政治”时代,政治学研究者深觉“理解政治”的紧迫性。“政治”关涉人类生存的核心,“什么是好的政治”与“什么是好的生活”或许在根本上是同一个问题。
本书中,27部核心文本既独立成章,又彼此呼应,以“荷马作为‘希腊的教育者’”为开端,依次解析希罗多德、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普鲁塔克、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里、莎士比亚、霍布斯、洛克、卢梭、帕伯琉斯(麦迪逊)、托克维尔、韦伯和施米特等思想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格局开阔、大开大合,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和思想问题脉络,同时讲解原文不失细腻深刻,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为我们呈现了丰满而有纵深的政治理论图景。
|
| 關於作者: |
任军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与美国宪法。著有《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四论》《民德与民治》等;主编《修昔底德的路标》《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等;译著《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政治科学要义》《寡头统治铁律》等。面向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修昔底德战争史”等通识核心课程,获评2018年“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年度优秀教师”、复旦大学2011届本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
| 目錄:
|
第一章 荷马作为“希腊的教育者”:《荷马史诗》
第二章 国富国穷与帝国兴衰的悖谬逻辑:希罗多德《历史》
第三章 从僭主到哲人的精神成长史: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
第四章 民主帝国的困局和终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第五章 盛世雅典人的迷茫与乡愁:阿里斯托芬《云》
第六章 民主帝国的精神沉沦史:柏拉图《理想国》
第七章 哲人与城邦分道扬镳: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八章 公民哲人苏格拉底: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第九章 斯巴达政制的式微与希腊文明精神的沉沦:色诺芬《斯巴达政制》
第十章 政治学作为立法科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第十一章 政治相对哲学的优先性:西塞罗《论义务》
第十二章 政治民族的肇端与世界帝国的缔造: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第十三章 政治人的“幸福”:普鲁塔克《道德论集》
第十四章 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普鲁塔克《对比列传》
第十五章 重估古典政治: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第十六章 重新勘定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阿奎那《论君主政治》
第十七章 现代卢克丽丝的“德行”:马基雅维里《曼陀罗》
第十八章 僭主的德行与恶行: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第十九章 古代卢克丽丝的德行:莎士比亚《卢克丽丝失贞记》
第二十章 凯撒之死开启了凯撒时代: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第二十一章 现代国家的起源及其特征:霍布斯《利维坦》
第二十二章 政治社会的建立及其维护:洛克《政府论》
第二十三章 人民主权与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卢梭《社会契约论》
第二十四章 美利坚立国的政治理论:帕伯琉斯《联邦论》
第二十五章 “自由帝国”美利坚的崛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第二十六章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分际及各自的使命:韦伯《学术与政治》
第二十七章 从认识“敌人”到理解政治: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
| 內容試閱:
|
自 序
从荷马到施米特,不是思想家们的座次序列,而是思想与思想彼此交锋的场域。思想的历史在形式上贯穿着纵向的时间轴,在内涵上却呈现为横向的问题轴。
思想家不仅在审视自己的时代,更在与先哲对驳辩难:柏拉图在与荷马辩难,修昔底德在与希罗多德辩难,西塞罗在与柏拉图辩难,马基雅维里在与西塞罗辩难,莎士比亚在与奥古斯丁辩难,霍布斯在与亚里士多德辩难,卢梭在与霍布斯、洛克辩难,帕伯琉斯在与孟德斯鸠辩难,托克维尔在与马克思辩难,施米特在与霍布斯辩难。只有将这种对驳辩难的理路呈现出来,思想的场域才能充分打开,读者才有望身临其境,养成权衡取舍的鉴别力和观照现实的判断力。
思想场域的打开幅度取决于将时间轴转化为问题轴的程度。从荷马到施米特,正是通过问题轴而不断打开思想场域的过程:梭伦与克洛伊索斯、西蒙尼德与希耶罗、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柏拉图与狄奥尼修、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维吉尔与奥古斯都、阿奎那与塞浦路斯王、马基雅维里与美第奇、施米特与纳粹—哲人与僭主、哲学与政治、上帝与凯撒、科学与权力之间是否有调和的余地?回答是者,古代有普鲁塔克,现代有科耶夫;回答否者,古代有柏拉图,现代有施特劳斯。
面对这一思想场域,读者不再是思想长廊的游观欣赏者,而是身临其境的理论生活的沉浸式体验者。这种沉浸式思想体验,是一切有效阅读的条件,是任何力图通过阅读获得智性提升的前提,更是思想照进现实的关键。
文本是思想的核心载体,思想通过文本得以结构化赋形。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与文本自身的理论品质,即时空穿透力,密切相关。文本是先哲们为后学精心打磨的透镜,借助它,我们得以审视历史,思考当下,洞烛未来,认识自我。
文本在折射时代,更在模塑时代。理解文本既需要外部视角,又需要内部视角:外部视角需要社会文化史进路,斯金纳、波考克堪为典范;内部视角需要政治哲学史进路,施特劳斯、沃格林堪称翘楚。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他们的卓越贡献。中文学界对相关领域文献的辑译和识读品质,都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在此,笔者谨向政治思想史领域前辈同仁的不懈努力表达由衷的敬意。
本书以荷马开篇,以施米特收尾。前者似无疑义,且在首章中已有论述。而以施米特作结,在于施米特站在大时代的转捩点上。彼时的西方文明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再次被置于分叉路口。不同的选项意味着截然对立的政治决断,双方都为各自的决断付出了空前惨烈的代价。
尽管充满争议,施米特无疑是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的标志性思想人物。其思想与行动高度统一,理论与实践浑然一体。作为思想人物,置身大时代的施米特,其历史关联性是之后的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
施米特之后,“政治思想”进入学院,成为一种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术。思想者不再行动,行动者不再思想,政治学术演化成一种专门的理论科学。政治理论与政治行动的畛域分明,政治理论所关注的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讲述施米特之后更具学院风格的西方政治思想,我们需要探索一种与之匹配的新讲法,符合这种新的思想品格。
中国人研究西方,恰如西方人研究中国,很自然地会有着不同程度的比较视野。然而,百年以降,无论是作为政治社会的 “西方”还是作为思想文化的“西方”,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人文明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我们研究西方,也宿命性地作为认识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政治,是新世纪压给中国有识之士的精神重担。面对这一重担,轻浮的乐观,抑或轻率的绝望,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理解”政治意味着面对现实的勇气、清晰的判断力以及智性的诚实,进而自觉审视并肩负起这一精神重担。
我们业已进入新的“大政治时代”。大政治时代需要“政治的”智识和思维。政治不是经济、社会的附属品或衍生物。政治的原理涉及统治与被治、权威与服从,政治的实践则涉及强权与正义、手段与目的、权力与道德、表层与里层。政治之善在于于国家内部树立秩序,于国家之间缔造和平。
“政治”的动力是权力,不是道德,但“政治”时刻需要面对道德的拷问。对于引领和即将引领社会的人来说,理解政治意味着提升政治智识,涵养政治思维,这是人类凭借理性驾驭政治,而不是被本能驱使的基本要件。
从荷马到施米特,毋宁是一场精神感召。对于其中论及的每一位思想人物,每一部思想文本,本书均力求做到出入其间,游刃有余,同时将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文本解释与阐发。本书涉及的思想人物及其文本,都是笔者在不同阶段教学过程中所聚焦的核心文献。
2002年,即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二年,按照系里的安排,我面向政治学系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专业基础课—“西方政治史”。当时首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讲—如果沿用传统政治史的教法,按历史时段将从古到今的重大政治事件铺排一遍,除开内容庞杂,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教学内容会始终浮于表面。政治事件若无法转化为有意义的理论思考,那么历史只会沦为一大堆凌乱的信息。
课程的前几轮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至于同学们的感觉更是可想而知。几轮过后,我便对教学内容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改成以经典文本为核心,力图以点带面、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比如讲古代政治史,我曾先后以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普鲁塔克、阿庇安、塔西佗、维吉尔、西塞罗、莎士比亚、蒙森、塞姆为核心;讲现代,则先后以马基雅维里、基佐、联邦党人、托克维尔、柏克、麦迪逊、白芝浩、韦伯、施米特、汤因比、施特劳斯、沃格林、亨廷顿、福山等为核心。
为了保证同学们的阅读效果,养成深入阅读的习惯,我刻意减少每学期的阅读量,大多数学期我只布置一到两个文本,聚焦某一位思想人物,整个学期的教学就是带领学生集中研读文本。同学们课前预读,课堂上要报告,并有随机提问与讨论。我对同学的要求是,将全部注意力聚焦原始文本,在对原始文本形成基本轮廓之前,不必涉猎任何二手研究文献,否则在不具备基本鉴别力和判断力的情况下,浏览二手研究只是浪费时间,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收获。
我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备课过程中尽可能吸收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并将其融入讲解文本的过程中。本书每章末尾所附“延伸阅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每学期,会依据现实情境和我自己的现实感更换新的文本,这就使“西方政治史”这门老课每学期对我来说俨然一门新课。每轮选课的同学就如同开盲盒,而我自己也能够保持新鲜感。这种教学方式是开启新的学习之旅的重要契机,既然乐在其中,也就乐此不疲。
我始终认为,所谓教学相长,首先意味着教师通过教学不断自我提升,教学本身为教师在学术上持续成长提供了某种“压力场”,课堂上同学们的注视和反应,对教师构成一种无形的鞭策力量。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水平,才能在这种“压力场”中做到自适其任,进而游刃有余。
我自己的体会是,讲课本身是教师将自己的研究条理化和系统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教师学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头表达会在不经意间激发教师的学术想象力和拓展力,同时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和视野的局限。为此,每次课前,我都会提前一天“入静”,尽可能避免任何额外干扰,集中备课,想象教学过程中的种种可能性,并做好各种预案。而每轮教学从来没有令我失望,时常有意外发现的惊喜,我自然对课堂满心期待。
我的教学既然聚焦传世文本的阅读,而文本本身必然承载着著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精神教诲,这就决定了我的研究领域往往处在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之间。这些年我比较自觉的方法论上的努力,正是力图沟通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借助经典文本所提供的理论视野,统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时段,同时将著作家的理论洞见化用为观照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见识。
为此,我反复提醒同学们,阅读文本切忌置身事外,仅将文本作为某种知识对象。真正的阅读是“介入式”的,需要阅读者的思想穿越感、经验现场感。阅读不是将文本作为知识或观念教条,而是与文本作者对驳辩难,在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往返穿梭,将时间性的历史文本创造性地翻转为空间性的理论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在经典与经验、古代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发现精神的共在性,体会底层逻辑的共通性。
在教学之外,从2017年开始,我连续组织了六届“复旦—政治思想史年会”,主题大多围绕关键思想人物展开,它们是:“修昔底德:历史与理论”“托克维尔: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罗马:旧共和与新君政”“韦伯:现代政治与文明危机”“施米特:现代政治秩序的危机”“沃格林:历史意识与政治秩序”。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也不同程度得益于研讨会上的深入交流,感谢历届与会的学界同人的启发。
二十年弹指一挥,如今回想起来,我的教学和研究路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复旦一批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其间成员换了好几波,但二十年来读书会可谓雷打不动,每周坚持一起读书讨论。我们先后共读的文本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奥古斯丁。之后读书会又转向中国古典文本,包括《春秋》三传、《毛诗》、《庄子》、杜诗、《周易》、《中庸》、《论语》。通过读书,我们建立友谊,砥砺思想,观照现实,涵养心性,保持智性上的谦卑和持续的学习状态。可以说,二十年的读书会成为我个人学术成长的关键助力。本书献给曾经和正在一起读书的学友们。
对于每一章的撰写,笔者均以专题论文的标准自我要求,行文力求要言不烦,稳健精到。为了阅读的流畅性,我在行文中尽可能减少引注,讲述文本与解释文本彼此交叉。一般读者读了相关章节后基本可以省却再去求证原始文本的额外负担。初入门径者不妨以相关章节为起点,循着章末所附“延伸阅读”的指引,自行探索登堂入室的门径。专业研究者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行文中的具体所指,与相关研究者方法旨趣的异同,择善而从便可。
本书部分章节相继在《中国政治学》《复旦政治学评论》《思想史研究辑刊》《思想与社会》《政治与法律评论》《文化纵横》《云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特此致谢!
最后,感谢“三联中读”俞力莎女士及其团队,“如何理解政治”音频课的催更节奏保证了我的写作节律。感谢三联书店的冯金红女士,本书从选题论证到写作成稿,均得益于金红的鼎力相助。责任编辑宋林鞠女士是全书的第一位读者,从形式到内容,林鞠贡献了许多极具针对性的改进意见。作为读书人和写作者,遇见她们,何其有幸!
▎《联邦论》文本导览
18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着重大政治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盛,平民势力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以贵族为基础、王权为轴心的传统政治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由于贵族—王权体系未能有效吸纳新兴平民阶层的诉求,革命成为这一时期难以遏制的浪潮。一旦革命的永动机开启,它便迅速形成了自我运转的动力机制。18世纪末,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场“姊妹革命”前后相继,彼此呼应,共同勾勒出西方现代政治史的独特景象。这两场革命不仅是陷入全面危机的基督教世界破旧立新的关键事件,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事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整个20 世纪世界政治史的走向,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它们的余波,其理论意义也格外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革命者之后需要立法者,革命者志在破坏,而立法者意在建设。推翻旧制度后,如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是树立麦迪逊式的代议共和秩序,还是卢梭式的人民共和秩序?是建立自由的代议共和制国家,还是平等的人民共和制国家?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为托克维尔提供了反思旧制度和探索新秩序的历史素材与理论灵感。贵族社会渐趋没落,民主社会继之而起,社会结构日趋被抹平。托克维尔在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的共和立国实践中看到了基督教国家建立新的自由共和秩序的可能途径,并洞悉了新兴的美利坚国家的崛起势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兰西民族长期陷入革命式的内讧旋涡中无法自拔,曾经的大法兰西帝国至托克维尔时代已风光不再,日渐衰落。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在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新教伦理”。这种伦理集中表现为入世的禁欲主义修行和作为平衡财富欲求过度膨胀的精神杠杆。而这一杠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失落,正是韦伯所洞见的新一轮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危机的根源。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美利坚国家乘势崛起,最终成长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可以说,美利坚国家的未来,直接牵动着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兴衰浮沉。18世纪的美利坚立国,是整个西方精神传统的集大成“作品”,古希腊哲学、罗马政治理论、基督教神学、启蒙主义,在美利坚人的立国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系统发扬。美利坚国家在新世纪的兴衰,不仅可以作为我们透视西方政治文明传统内在张力的窗口,也自然成为我们中国人审视中华文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参照。
《联邦论》(The Federalist)是一部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共同撰写的政治论文集,共85篇,从一开始即作为一种统一的政治行动和完整的政治理论著作筹划,最初一致以笔名“Publius”(帕伯琉斯)发表。在中文翻译上,程逢如先生主持翻译的中译本(《联邦党人文集》)标题采“文集” 字样,给人留下多篇论文结集的直观印象。若对照原书标准版标题The Federalist,其中并无许多流行版本标题常有的“Papers”(文集)。尹宣先生的中译本标题采用《联邦论》,这是为了将三位作者与后来美国政治史上的“联邦党”区别开来。台湾地区的谢叔斐译本也去掉“文集”字样,以突出文本的整体感。
“帕伯琉斯”,这一笔名取自罗马共和国父普布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Publicola 字面意为“人民敬爱之人”。公元前 509年,普布利科拉参与了推翻王政的共和革命,与布鲁图斯一道担任罗马共和政府的同僚执政官,并先后四次当选执政官。普布利科拉以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罗马共和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在《对比列传》中,普鲁塔克对普布利科拉的勋业推崇备至,将其与雅典立法家梭伦对比列传。有关普布利科拉的行迹,本书前文关于普鲁塔克《对比列传》的章节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借用罗马史上著名人物的名字为笔名,这在美利坚立国一代中并不罕见。支持新宪法的“联邦党人”采用“帕伯琉斯”作为集体笔名,与此同时,与联邦党人展开笔仗,质疑甚至反对新宪法的“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则采用了“布鲁图斯”(Brutus)、“加图”(Cato)、“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多那图斯”(Denatus)、“阿格里帕”(Agrippa)等。可见,罗马政治史是美利坚立国者现实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对新生的美利坚国家所承载的文明使命的自我期许。
《联邦论》本身的文本结构是:第1篇作为“序言”,阐述了通过新宪法草案实现北美十三邦“合众为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作者们的写作动机。第2至第51篇聚焦政府组织的一般原理。第52至第84篇分别讨论了联邦国会的众议院(52—61)、参议院(62—66)、合众国总统(67—77)、最高法院(78—83),并回应了反联邦党人主张的《权利法案》(即后来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是否必要等问题(84)。第85篇作为“结论”,与“序言”呼应,重申批准新宪法的必要性,强调新宪法尽管依然存在不足,但不妨在实践和经验中扬长补短,不断检验和改进。
▎《联邦论》的两种历史语境
要深入阅读《联邦论》,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两种历史语境中:一是西方2500年的文明史,二是从《五月花号公约》到南北战争的200年美利坚建国史。《联邦论》是一部凝聚了西方2500年理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集大成作品,它融汇了西方古今政治史(经验)和政治思想史(理论)。85篇文章中有10篇直接探讨了古今缔造政治秩序的正反经验。从古希腊政治哲学、古罗马混合政体理论,到近代自然法、基督教神学和契约国家论等启蒙思想,都在美利坚的缔造过程中得到系统总结和充分发挥,政治科学与立法技艺在《联邦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整合。
公民德行、立法者的技艺、“新罗马”、“新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自然法和自然神祇、山巅之城、特选民等概念,构成了美利坚人自我认知的核心。罗马主神殿的卡皮托山(Capitol Hill)被挪作国会山的官方名称,而参议院(Senate)则脱胎于古罗马元老院(Senatus)。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能否摆脱罗马共和国的盛衰循环,成为一个“永久联邦”(perpetual Union)?美国国父们视自己肩负着“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希望在美国最终完成罗马人未竟的事业。
美国国徽背面两则拉丁铭文“ANNUIT COEPTIS”(神佑吾人基业)、“NOVUS ORDO SECLORUM”(新秩序重开纪元),分别脱胎自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IX-625)、《农事诗》(I-40)和《牧歌》(IV-5)中的诗句。正面铭文“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取自一首托名维吉尔的诗《大拌菜》(“Moretum”)。《五月花号公约》(1620)通过“圣约”(covenant)建立了公民政治体(civil Body Politick),蕴含着“圣约神学”。《独立宣言》开篇即诉诸“自然法则和自然上帝”,将洛克式的自然权利观念宣示为北美独立于宗主国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彼此组建政府,统治者统治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治者的同意。”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笔下分崩离析、内耗不断的希腊,马基雅维里笔下城邦与城邦之间虎视眈眈、战乱不已的意大利,以及古代雅典的群众式广场民主导致的混乱和党争,这些都成为《联邦论》反思的历史镜鉴。而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吕库古、罗马的罗慕路斯和努玛,被“帕伯琉斯”奉为开国创基的立法家典范。可以说,美利坚作为政治民族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但作为文化民族,它代表了整个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别开生面的新产物。
1607年,第一批英国移民在北美建立了詹姆斯敦定居点。1620 年,“五月花号”移民船上的清教徒在登岸前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建立普列茅斯殖民地。之后,马萨诸塞(1628)、马里兰(1632)、纽约(1664)、卡罗莱纳(1669)、宾夕法尼亚(1682)、新泽西(1702)、南卡罗莱纳(1720)等殖民地相继成立,它们通过特许状享有对本地事务的高度自治权。这些殖民地星罗棋布,互不相属,俨然各自为政的小共和国。而在宣布独立后,各邦纷纷制定本邦共和宪法。到制宪会议前夕,北美已有十三部宪法,俨然共和政体的“试验场”。正是之前各殖民地长达150年的相似的治理经验,使英属十三殖民地能联合起来,发动针对宗主国的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百余年所积累的共和宪法实践及理论,为 1787年费城制宪者们设计新的联邦共和宪法提供了基本素材和经验蓝本。
《独立宣言》宣布切断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一切政治联系,从此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独立战争又迫使北美十三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趋向联合,《邦联条例》作为将十三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共同宪章,确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联盟的正式名称,以及作为联盟协议机构的国会。邦联国会实行一院制,由各邦派代表组成,各邦在联盟事务中拥有一票表决权。邦联国会休会期间,日常事务委托给“各邦事务委员会”,重大事务必须有至少九个邦的一致同意。
《邦联条款》虽宣称联盟永世长存,但由于联盟中央缺乏独立的财政和军队,以及独立的行政,所有事务均要依赖同盟各邦的意志,使整个联盟的权力结构失衡,联盟所掌握的权力根本无法确保联盟一致行动的目标。
1786年,由经济萧条引发的马萨诸塞自耕农起义(即谢斯起义)正是对《邦联条例》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巨大挑战。邦联国会在这次“压力测试”面前的笨拙表现,成为1787年费城制宪的重要契机。最初,制宪会议从邦联国会得到的授权仅是修改《邦联条例》。然而,由来自各地的55名代表组成的修例大会在费城经过近四个月的闭门讨论后,最终拿出的是一部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宪法草案要正式生效,必须得到至少九个邦的专门批宪大会的批准。面对反对新宪法此起彼伏的声音,汉密尔顿动员麦迪逊和杰伊加盟,先后在纽约邦的四家报纸上发表85篇专论,对新宪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措置做了系统的解释说明,同时极力说服舆论支持拟议中的宪法草案。尽管已无法确切衡量这85篇论辩文章在纽约邦最终批准新宪法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推动作用,但《联邦论》作为一部指向实践的政治理论著作,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恒久的生命力。
新的《合众国宪法》通过一整套精巧细密的设计,在大邦与小邦、南方蓄奴邦与北方自由邦之间暂时达成了某种权力平衡。然而随着西部拓殖地的开发,新州不断加入联邦,围绕蓄奴问题以及国会席位分配的南北争执渐趋白热化,美利坚国家面临新一轮更严峻的宪制危机,最终酿成了一场空前血腥的内战。经过长达四年的内战,以及战后对南部社会经济伤筋动骨的“重建”,现代美利坚国家的缔造才算最终完成。从开国至内战,美利坚国家的建立过程持续百余年。
在《联邦论》开篇,帕伯琉斯提出了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设问:“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强力,建立政治制度?”[2]揆诸历史,在美利坚国家的缔造过程中,理性并未最终取代强力,法制背后离不开刀剑的支撑。面对针对现代人造国家(即利维坦)的颠覆力量,武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最后保障。帕伯琉斯的 “笔杆子”将“枪杆子”暂时搁置了70年,但现代美利坚国家的诞生依然未能摆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铁律。林肯成为继华盛顿之后再造美利坚共和的“第二国父”,乃实至名归。如果将1787至1788年联邦论者与反联邦论者之间的政治论辩与1858年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对观,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利坚国家的基本特质和内在矛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