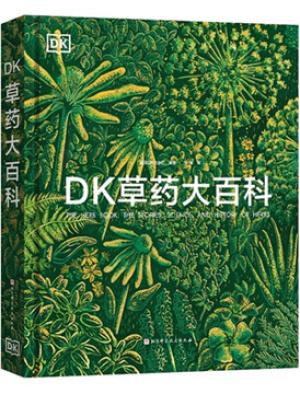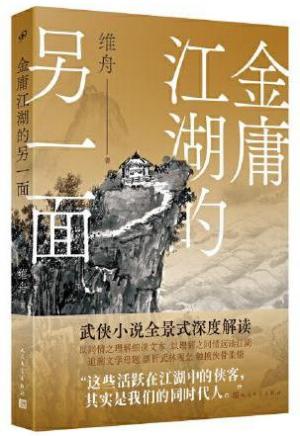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朱子的穷理工夫论 | 香江哲学丛书
》
售價:HK$
104.5

《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一部政治思想史力作,反思传统时代的王朝周期)
》
售價:HK$
86.9

《
甲骨文丛书·英国人在印度:三百年社会史
》
售價:HK$
1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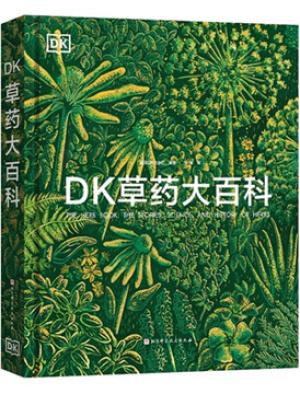
《
DK草药大百科
》
售價:HK$
294.8

《
以远见超越未见:当今时代的教育、文化与未来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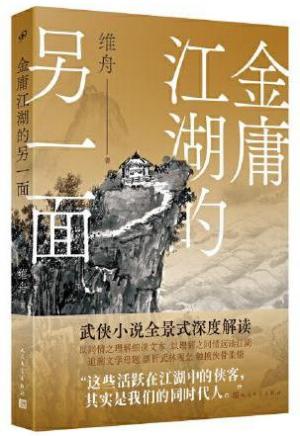
《
金庸江湖的另一面
》
售價:HK$
64.9

《
乘风而上(美依礼芽中文自传)
》
售價:HK$
85.8

《
索恩丛书·帝国计划:英国世界体系的兴衰(1830~1970)
》
售價:HK$
185.9
|
| 編輯推薦: |
★“故事圣手”毛姆晚年重要作品,诠释生命真谛 ★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原著小说
★马尔克斯、莫言、村上春树、张爱玲一致推崇,无删减全译本
|
| 內容簡介: |
|
《刀锋》是英国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小说写一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为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拉里开始了他令人匪夷所思的转变。经历了长达两年的休息,他决定去欧洲寻求人生的意义。为解心中疑惑,他放弃如花美眷,醉心茫茫书海,遍历世界。为传播真理,他解人病痛之苦,除人之世俗恐惧,拯救堕落的灵魂,在散尽钱财后,投身茫茫红尘之中。《刀锋》是毛姆充满哲学深思之作,毛姆以亲身经历写作,把真实的自己写入小说中,其语言犀利、笔触幽默、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书中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通篇哲学笔墨不多,却处处尽显哲学思辨之精华,是一篇思考人生意义、具有浓厚哲学意蕴的小说,一部关于终极价值的书。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对人生意义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
|
| 關於作者: |
|
毛姆,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曾先后就读于坎特伯雷的国王学校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后到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并取得外科医师资格。他的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于1897年发表。代表著作有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人生的枷锁》《刀锋》《寻欢作乐》《面纱》,旅行札记《在中国屏风上》,及各种散文、短篇小说集等。毛姆被公认为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之一,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1952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54年,英王授予他“荣誉侍从”的称号。
|
| 內容試閱:
|
正当我洗脸刷牙、准备出发去艾略特邀请我参加的午餐时,前台打来电话说艾略特在楼下。我有点吃惊,但是我一收拾好就立马下楼了。
“我想我来接你会比较保险,”我们握手时,他说,“我不知道你对芝加哥是否熟悉。”
他和很多常年旅居国外的美国人一样,总感觉美国是一个麻烦甚至危险的地方,让欧洲人自己找路很不安全。
“现在还早,我们可以走一段路。”他建议道。
空气中有丝丝寒意,但是天空万里无云,活动一下腿脚还是很惬意的。
“我觉得在你和我姐姐见面之前,最好先向你介绍一下她的情况,”我们走路时,艾略特说,“她来巴黎和我住过一两次,但是你那时应该不在。今天不是什么大聚会,只有我姐姐和她女儿伊莎贝尔,还有格里高利·布拉巴宗。”
“那个装潢设计师?”我问。
“是的。我姐姐的家布置得太难看了,伊莎贝尔和我想让她重新装修。我碰巧听说格里高利也在芝加哥,所以我让姐姐邀请他今天来吃午餐。他算不上真正的绅士,这是自然,但是他有品位。他为玛丽·奥利芬特设计了雷尼城堡的室内装潢,还有圣·埃尔斯的圣克莱门·塔尔伯特府,公爵夫人对他很满意。你将亲眼看到路易莎的房子。她怎么能在那屋子里住这么多年,我永远都理解不了。说起这个,她怎么能一直在芝加哥生活,我也永远无法理解。”
我得知布拉德利太太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寡妇,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两个儿子要大得多,都已经成家了。一个被政府派去菲律宾,另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他父亲当年一样从事外交工作。布拉德利太太的丈夫曾在全球很多地方工作过,在罗马担任了几年一等秘书之后,他被任命为公使,派去南美洲西海岸的一个共和国,在那里去世。
“他去世后,我想让路易莎卖掉芝加哥的房子,”艾略特接着说,“但是她对这座房子有感情。布拉德利家族很早就拥有这处房产了。他们是伊利诺伊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一八三九年,他们从弗吉尼亚搬来这里,占了大约六十英里的地,就位于现在的芝加哥市。他们至今仍拥有这块地。”艾略特迟疑了一下,瞄了我一眼,看我是否相信,“最先来这里落脚的那位布拉德利,我猜你可以称之为‘农民’。我不确定你是否知道,在上个世纪中期,中西部刚开发时,很多弗吉尼亚人,你知道,那些来自殷实家庭的小伙子,被未知的诱惑吸引,离开了老家的安乐窝。我姐夫的父亲,切斯特·布拉德利,认为芝加哥很有前景,加入了这里的一家律所。不管怎样,他赚了足够多的钱,给他儿子留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话虽如此,但艾略特的神态却在暗示,对于已经过世的切斯特·布拉德利来说,为了进入城里的律所而放弃了自己继承的深宅大院和广阔农田,实非明智之举,不过他攒下了一笔财富的事实多少也算是补偿。后来布拉德利太太给我展示了几张快照,照片里是艾略特宣称的他们在乡下的“故里”,艾略特似乎对她这一行为并不太赞成。从照片中,我看到一座朴素的木屋,一个漂亮的小花园,一步之遥外就是谷仓、牛棚和猪圈,它们的四周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我不由得想,当切斯特·布拉德利先生放弃这些去城里奔前程的时候,他应该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会儿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载着我们一路下行,停在一座褐石房子前。房子又窄又高,你得爬上一段陡峭的台阶,才能抵达前门。这幢房子是一排房子的其中一座,其所在的街道与湖滨大道相接。即便在那个明媚的秋日,它仍然显得死气沉沉,以至于你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对这样的房子充满感情。一个又高又壮、满头白发的黑人男管家开了门,将我们引至客厅。当我们走进来时,布拉德利太太从她的椅子上起身,艾略特向她介绍了我。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儿,尽管五官尺寸略大,但很标致,眼睛尤其漂亮。但是她那张极度缺乏妆饰的黄脸已经松弛,而且不难看出,在与中年发福的斗争中,她早已败下阵来。我猜她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因为她落座时,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坐得笔直,她那件无情的束腰铠甲无疑令她感到这比坐软垫椅子更舒服。她身穿一件蓝色重工礼服,鲸骨撑起的领子僵硬地立着。她一头光泽的银发烫了卷儿,紧紧地贴着头皮,梳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发型。另一位客人还没到,我们一边等他,一边东拉西扯地闲谈。
“艾略特告诉我你经南边路线过来,”布拉德利太太说,“你经停罗马了吗?”
“是的,我在那里待了一周。”
“亲爱的玛格丽特王后还好吗?”
她的问题令我略感意外,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噢,你没去看她吗?这么和善的女士。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她很照顾我们。布拉德利先生在那里做过一等秘书。为什么你没去看她?你又不像艾略特,因为太黑去不了奎里纳尔宫?”
“不是因为这个,”我笑了笑,“说实话,我不认识她。”
“你不认识?”布拉德利太太说道,仿佛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不认识?”
“实不相瞒,作家们有个共识,就是不和皇亲国戚交往过密。”
“可她是多么亲切的女士呀,”布拉德利太太劝诫我道,好像不认识这位皇室成员显得我非常傲慢无礼,“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就在这当口,门开了,管家将格里高利·布拉巴宗引了进来。
格里高利·布拉巴宗的名字起得潇洒,人却一点都不风流倜傥。他矮小臃肿,秃顶活像颗鸡蛋,只有耳边和脖子后面有一圈黑卷发,一张红彤彤、光溜溜的脸,仿佛下一秒就要冒得满脸是汗,一双灵活的灰色眼睛,一张厚厚的嘴唇,还有一个肥硕的下巴。他是英国人,我在伦敦的波希米亚派对上见过他几次。他快活、精力旺盛、大笑连连,但是你无须独具慧眼,就能看出他这吵吵嚷嚷的友善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精明的生意人的内心。他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伦敦最成功的装潢设计师。他声如洪钟,一双小胖手极富表达力。靠着善于传情达意的手势,以及一连串滔滔不绝、激动人心的话语,他能令所有半信半疑的顾客产生错觉,误以为订单是他好心帮忙,从而难以拒绝。
管家又走进来,端进来一托盘鸡尾酒。
“我们不用等伊莎贝尔。”布拉德利太太拿起一杯酒,说道。
“她去哪儿了?”艾略特问道。
“她去和拉里打高尔夫了。她说她可能会迟到。”
艾略特扭头对我说:“拉里叫劳伦斯·达伦尔。伊莎贝尔和这小子订婚了。”
“我不知道你还喝鸡尾酒,艾略特。”我说。
“我不喝,”他一边啜了一口他手中的鸡尾酒,一边义正词严地回答,“但是在这片野蛮的禁酒之地,人还能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在巴黎的一些府邸,人们也开始提供鸡尾酒了。交往不善,败坏礼仪。”
“一派胡言,艾略特。”布拉德利太太说。
她的语气十分温和,但又很坚决,可见她也是位颇有个性的女性。从她看艾略特那愉悦而犀利的眼神推断,她一定对艾略特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好奇她是如何看待格里高利·布拉巴宗的。我注意到他进门后非常职业地打量了房间一番,并且不自觉地扬起了浓密的眉毛。这房间的确惊人。墙纸,以及窗帘和软垫家具所使用的印花棉布都是同一个花色;墙上挂着用大金框裱起来的油画,明显是他们在罗马的时候买的:拉斐尔流派的圣母像、圭多·雷尼流派的圣母像、祖卡雷利流派的风景画、帕尼尼流派的废墟画。有他们在北京居住时期的纪念品:雕刻繁复的黑色木桌、硕大的景泰蓝花瓶;还有他们在智利或秘鲁购买的物件:坚硬石头雕刻的肥硕人像,以及陶制花瓶。房间里还有一张齐彭代尔写字台,以及一架细工镶嵌的玻璃橱柜。白色丝绸的灯罩上,某个没头脑的画家画上了身着华托式华服的牧羊人和牧羊女。整个房间令人瞠目结舌,但不知为何,又令人感到舒适。它充满了家的气息,一种生活过的气息,你感到那难以置信的混乱不可或缺。这些不协调的物件又和谐统一,因为它们都是布拉德利太太的人生片段。
我们喝完鸡尾酒,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孩。
“我们迟到了吗?”她问,“我把拉里带回来了。有什么东西能给他吃吗?”
“我想有的。”布拉德利太太笑着说,“摇下铃,告诉尤金再加个座位。”
“他给我俩开的门。我已经告诉他了。”
“这是我的女儿伊莎贝尔,”布拉德利太太扭头对我说,“这是劳伦斯·达伦尔。”
伊莎贝尔和我匆匆握了握手,便急不可耐地向格里高利·布拉巴宗转过身。
“您是布拉巴宗先生吗?我想见您都快想疯了!我特别喜欢您给克莱门特·多马做的设计。这房间糟透了,不是吗?我已经努力了好多年,试图说服她做点改变。你可算来芝加哥了,我们的机会来了。坦白告诉我,您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
我知道这是布拉巴宗最不可能做的事。他飞快地瞄了布拉德利太太一眼,但是她脸上毫无表情,没有给他透露任何信息。他认定伊莎贝尔是主事的那个人,因此爆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
“我相信这房间一定很舒适,”他说,“但是如果你非要问我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房间的确很糟糕。”
P12-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