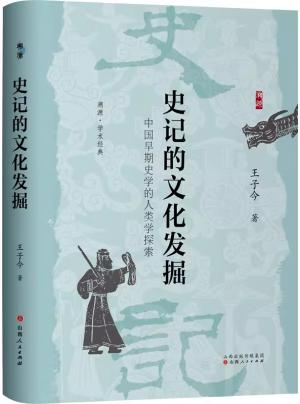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砂与海之歌纪念画集
》
售價:HK$
107.8

《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看日本系列)
》
售價:HK$
61.6

《
当代中国经济讲义
》
售價:HK$
151.8

《
北派2:西夏梵音(网络原名《北派盗墓笔记》)
》
售價:HK$
52.8

《
滞后情书
》
售價:HK$
47.1

《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
》
售價:HK$
68.4

《
风起红楼:百年讹缘探秘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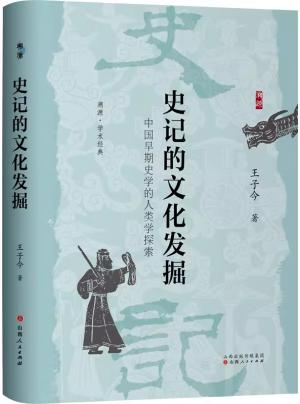
《
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
》
售價:HK$
199.4
|
| 編輯推薦: |
?揭秘洗衣工业化的隐秘战争
一部技术可行性(机械革新)与社会文化需求(性别分工、清洁观念)激烈博弈的辩证史,揭示行业兴衰的深层逻辑。
? 跨越英美两国的工业命运图谱
首次以跨大西洋比较视角,解析技术传播(美→英)与改革理念(英→美)的双向流动,突破国别史局限,展现地区差异的塑造力。
?女工、业主、主妇、改革者的多声部叙事
聚焦多元主体(雇主、工人、消费者、改革者)的互动博弈,在技术选择、行业协会斗争与监管拉锯中,重现蒸汽时代的劳动现场与社会图景。
|
| 內容簡介: |
|
洗衣房曾一度遍布英美城市街头——它们与钢铁厂、铁路一样,都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产物。然而不同于那些更为人熟知的工业化象征,这些“清洁工厂”女始终与家庭领域紧密相连。在本书中,莫恩通过这一独特视角,探讨了性别如何塑造日常劳动分工、劳动力构成及劳动价值评估等更深层的社会议题。英美两国的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文化传统、监管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如何使这个看似地域性极强的行业,最终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跨大西洋特征。
|
| 關於作者: |
作者:[美]阿尔文·P. 莫恩(Arwen P. Mohun),美国特拉华大学亨利·克莱·里德历史学讲席教授,致力于技术史、资本主义史与性别史研究。出版作品包括《美国帝国主义者:非洲争夺战中的残酷与后果》《他和她:性别、消费和技术》等。
译者简介:
孙超,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出版译著包括《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威尔士史》《西方文明史:延续不断的遗产》等。
|
| 目錄:
|
致 谢 i
导 论 001
第一部分
一个行业的起源与成长,1880—1920年
第一章 技术与文化起源 003
第二章 洗衣行业 047
第三章 在洗衣房内 080
第四章 女性工人和洗衣行业 115
第五章 工会化与监管,1888—1914 年 147
第二部分
进入成熟期,1920—1940年
第六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产与消费 191
第七章 “黑白之间”的洗衣房 222
第八章 国家的介入 238
第九章 在关系另一端的服从与执行 266
第十章 妇女、男人与工会 287
第十一章 面临家庭的威胁 330
结论 记住洗衣业 355
注 释 360
参考文献综述 402
|
| 內容試閱:
|
直奔主题
洗衣房是一个没有离我们太远的问题。在许多传统的家庭技艺消失之际,身边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一直是中产阶级经济富裕的象征。对于那些不怎么富裕之人,花点时间在公共洗衣房仍是一种常态。不过,事情也不总是这样。19 世纪时,企业家和机器制造商尝试将洗衣工作从家庭领域移出并让其演变为一种工业化进程。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顾客选择了“蒸汽洗衣房”——这是当时最常见的叫法——而抛弃了洗衣妇(washerwoman)、华人洗衣房、洗衣桶和尖头熨斗(sadiron)。本书所写的就是这一变化在美国和英国的产生,其所呈现的形态,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洗衣工作重新回归家庭后的最终衰落过程。
洗衣业的历史,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所经历的重塑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洗衣房高度机械化,与家庭生活和妇女持续联系在一起。它们的顾客也成了它们的竞争者。洗衣行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女性。洗衣房广泛分布在城市各地,一直规模很小而没有实现集中化发展。这个行业具有特殊之处。人们在分析技术和文化、消费和生产、家庭生活和工业进程时经常拿它说事儿。在诸多方面,洗衣房都是值得谈论的主题。
本书的总体叙述是想详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洗衣工作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实现工业化又回归家庭的。本书认为,这个行业的兴衰以及这个行业在此期间所呈现的形态是一对辩证关系:技术上所可能实现的(既指洗衣房,也包括其竞争者)和文化上所需要的。顾客、业主、工人和改革家在不断的选择中塑造了其发展轨迹。对这个故事进行详细考证后发现,文化观念,特别是清洁、家庭生活、性别角色等观念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能清楚地看到,商业洗衣房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上的限制。只有在没有其他替代品的情况下,那些眼光挑剔的顾客才会接受它。
关注洗衣服务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代表故事的一部分。尽管工人阶级中妇女只是偶尔会将需要洗涤的衣物送到洗衣房,但该行业对她们而言更常扮演着就业来源的角色。她们接触商业洗衣技术并非出于消费选择,而是将其视为谋生手段——一个充斥着高温与危险的环境,她们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于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洗衣房的业主也离不开大量的掌握特定技术知识的妇女,雇用这些妇女所需工资很低。这个阶级以及性别系统所具有的活力跟决定这个行业生存能力有关的技术创新具有完全等价的重要性。
这些工人和他们的辩护者在塑造这个行业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通过工会化和国家管控,他们重塑了洗衣房业主与消费者最终付出的服务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机械化成了一种规避熟练工人诉求的策略,在保护性立法取消了加班和夜班之后,也是一种创造超额产能的方法。国家的介入并非为洗衣房业主所完全排斥。工厂检查和最低工资制度让那些最小型的、最边缘的从业者离开了这个行业,从而带来了某种稳定,也抑制了竞争强度。
雇主、顾客、工人和他们的辩护者(本书中指的是“改革家”)都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所有的这些人都在让衣物变得清洁的技术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群体构建了一种叠合的社群网络,兼具地方性与跨国性双重特征。作为这些人日常互动的场所,个体洗衣房成为这个行业最具体、最亲近的表征。洗衣房融入了社区和城市,它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是人们送去脏衣服、取回干净衣物的场所,是矗立在街头的工业化象征物,也是扰民的雾气和脏水的源头。到 19 世纪末期,人们开始谈论“洗衣行业”(laundry industry)。这种称呼缺乏准确的空间界定,强调的是行业协会和工会会议,改革家的话语,以及监管洗衣房业主商业行为的法律。
许多手段和方法在分析这个行业的诸多面向时是管用的。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性别角色、关系及其意义的动态变化,那么这个故事中的经济和文化的动态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了。性别差异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包括劳动的性别分工、男性洗衣房业主与女性顾客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洗衣过程本身相关的性别化意义。性别化的身份和关系又因种族、族群和阶级因素的加入而变得复杂。比如,洗衣工作和消费,以及(在英国的)管理制度,这些都带有特定的阶级和性别暗示。
在洗衣行业,文化的、技术的、家庭的、工业的因素以一种复杂并且有时候矛盾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为大部分的洗衣房并不生产物质产品,所以洗衣房长久以来被称为服务行业。这种归类有利于说明洗衣房与其顾客之间的关系,但是误读了蒸汽洗衣房根本上的技术和组织逻辑。就洗衣房业主和他们的工人而言,蒸汽洗衣房就是工厂。大西洋两岸的洗衣房业主们努力模仿亨利·福特(Henry Ford),而没有学习那些通常裹挟在“服务业”这类模糊字眼下的银行、保险公司或百货公司。当时的观察家做了一番类比:棉纺织厂代替了棉花纺车,蒸汽洗衣房代替了洗衣妇,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让他们理解了这个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集中化、规模经济、去人工技能、劳动分工、组织化和信息控制都是正处于机械化过程中的洗衣工作的关键性策略。
本书最好被理解为带有强烈比较视野的盎格鲁-美利坚史。一方面,洗衣房在根本上仍旧是地方商业。洗衣房业主们主要在单个的城镇或都市中竞争。地方偏见和地方经济主导着
消费类型。地方劳动力市场也决定着谁能在洗衣房工作以及洗衣房是否能够与洗衣妇和亚洲移民们展开竞争。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个行业也产生一种跨大西洋现象。机械和技术上的持续交流构成了它的历史,其中包括两种跨大西洋对话:一个在英美的洗衣房业主之间,另一个在英美的改革家之间。尽管交流是双向的,但机械和技术知识倾向于从美国流向英国,而改革的观念和实践则是相反的。
所有的这些交流最终导致了技术、劳动分工、企业组织上的某些明显的相似性。不过,这一背景的差异性——基础设施、族群和种族构成以及法律体系上的——又导致了明显的趋异性。最明显的是,英国改革者依托宪政体系,相较美国更早实现了对工业的有效监管。英国的工业在族裔构成上具有相对的同质性;美国的洗衣房则经常在族群上和种族上呈现多元性。在英国,阶级差异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地区差异对这个行业及其监管也具有极大的形塑力。
在它们所处的时代,英国和美国的洗衣房业主们以及为行业期刊写文章的作家们也喜欢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写道,美国人在实现机械化上速度更快,在机械制造上粗制滥造的现象也更多。他们喜欢建造大东西,但又很快加以抛弃。不过,其他的证据表明,在大西洋两岸存在着一种可以被叫作“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的明显的连续性。与那些小型的、地方的竞争者相比,伦敦和芝加哥城市中高度资本化的洗衣房具有更高水平的相似性。这不仅是平行发展的结果,也是跨越大西洋持续的购买、借入和造访后的结果。作为经济实体,洗衣房不像铁路那样。那些自己制造电力或操弄着一辆手摇车的房主要想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竞争是有点可笑,但是同样的情况完全不适用在洗衣房业主的身上。
洗衣房业主的民族主义言论具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功能。这种言论有时候只是为了消遣,但更多时候是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现代化和工业化所产生的一个具有矛盾性的结果是消除了物质生活中的差异,同时又构建了强化民族独特性观念的意识形态。
我在看起来最具现实意义的地方是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强调可能在单一民族的背景下会无意识忽略掉的因素;说明大西洋交流的持续性存在;以及了解文化差异中某些具有模糊性的面向。必要时,我也不再将民族—国家作为比较的基础。特别是在后面的章节中,我意识到了地区性的重要性,尤其是美国南北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洗衣房”这个简便的术语在人口普查档案和行业期刊上随处可见,但又涉及各类不太相同的行业。洗衣房能够(甚至到今日也能够)与一系列机构联系起来:医院、酒店、精神病院、孤儿院,以及衬衫、毛巾等棉制品制造商。这类特定洗衣房的动态超出了我查阅的资料的范畴,因此不在这段历史之中。另一方面,那些以“家庭浣洗”(family wash)或“单身汉衣物送洗包裹”(bachelor bundle)为特色的洗衣房一般很难与亚麻品服务业和制服服务业区分开来:许多洗衣房对这两个行业都有涉足。本书中之所以对这些行业“打包在一起”讨论,部分原因在于我所使用的史料的特点,也是因为它们都很有趣。酒店和餐馆希望以成规模的方式重建家庭的舒适感。它们也是这个工业化时代及其相伴而生的逻辑的发明物。本书只会稍稍涉及所谓的华人洗衣房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亚裔洗衣房业主及其雇员是“他者”——不适合雇用、不受监管,并且也无法为行业协会或工会成员所接受。消费者们却频繁“越界”,为了享受比蒸汽洗衣房更便宜、有时对衣物损伤更小的服务,无视对华人洗衣服务业所制定的种族上的“清规戒律”。
*
在过去的 2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女性主义及其学术作品、妇女史和性别分析,改变了一些学者研究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的方法。本书的部分内容也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产物,即性别在塑造技术和技术在塑造性别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奶瓶和针线活的研究与工程学和钢制大型机械的研究同样重要;女性,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洗衣女工(laundress),都是技术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被动受害者。从外部视角来看,本书研究的是商人和顾客 ;从内部视角来看,本书写的则是妇女和工作。有一批内容丰富的文献对我的整个分析产生了影响。这批文献可以看作关于劳动和妇女的社会史,并且其有意让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性别关系凸显出来。过去有很多的学术作品已经展示了妇女的工作经历与她们作为母亲、家庭主妇和看护人的角色是不可分离的。其他的一些史学家也证明了,性别意识形态塑造了工作技能的概念和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且将妇女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贬值及其对家庭工作的认同联系了起来。改革言论,消费者、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工作场所的空间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
尽管尚未有关于洗衣房的通史问世,但我也不是第一个对其与家庭的特殊联系进行思考的学者。在《为母亲争取更多的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书中,露丝·施瓦茨·考恩
(Ruth Schwartz Cowan)将蒸汽洗衣房描述为技术领域的“未择之路”,并用它们来说明为什么某些替代家庭劳动的技术成功了,而另一些则失败了。考恩对洗衣房现象的解释主要聚焦于其与家庭和家庭劳动的联系。她认为,消费者的选择拒绝了公共的、商业的替代技术可能最好从“大部分人更喜欢私密性和自主性,而不是效率和集体利益”的角度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与考恩的研究相互映照:关注的是工业革命浪潮下家庭的某个面向,而不是家庭中的工业革命。
正如前文所述,本书所构思的对象部分地涉及社会共同体的研究,只是这种社会共同体组织过程围绕着一种特别的技术进程展开。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将社会关系和工业进程结合起来,而二者在其他的分析方法上则是割裂开的。共同体研究对技术史来说一直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把技术放到了背景中来看待。不过,我进一步延伸了共同体概念,让其超越了只关注 19世纪工业乡村的空间限制。甚至在洗衣房这样平淡无奇的世界中,新技术和新社会形态都在延伸着传统的时空边界。
最后,尽管许多不同方向的史学家都在著述关于工业化的各个面向,集大成的任务还是留给了经济史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将社会史、文化史和技术史融入其方法中,质疑并反思那种只关注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叙述方式。我不打算做一番宏大的总结,但是仍想说,书写工业史的某些方法最终还是走向了对宏大故事的重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