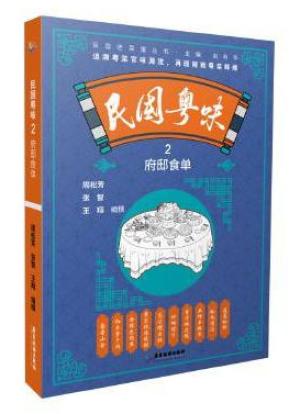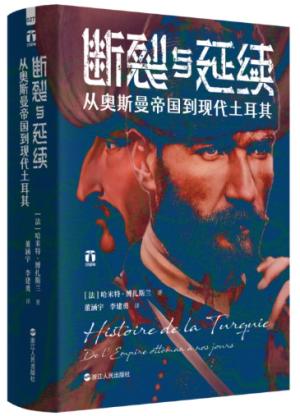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枪与炮:武器百科全书(全2册)
》
售價:HK$
437.8

《
神的人类学:海舍尔的宗教哲学
》
售價:HK$
77.0

《
那些和爱有关的人
》
售價:HK$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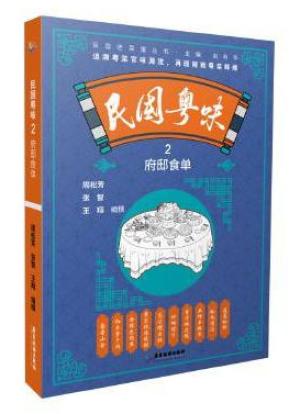
《
民国粤味 2: 府邸食单
》
售價:HK$
63.8

《
今日幼儿教育(第15版)/教育治理与领导力丛书
》
售價:HK$
294.8

《
能量自愈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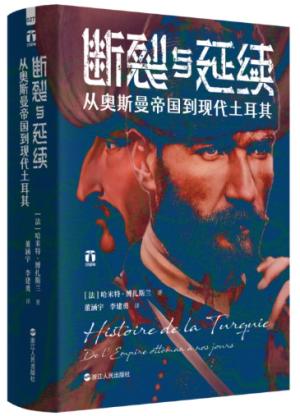
《
好望角系列丛书·断裂与延续: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
》
售價:HK$
151.8

《
中国俗文学史(新校本)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
《百年家事》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以人物侧写的方式,把晚清实业家、水师提督、清华教授、共和国出版人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官场上的宦海沉浮、外交中的刀光剑影、书斋里的理想情怀、激情年代的奇遇人生,都在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不为尊者讳的前提下,纪实呈现。
|
| 內容簡介: |
|
《百年家事》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以人物侧写的方式,把晚清实业家、水师提督、清华教授、共和国出版人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官场上的宦海沉浮、外交中的刀光剑影、书斋里的理想情怀、激情年代的奇遇人生,都在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不为尊者讳的前提下,纪实呈现。纵贯四代人的一百年,横跨三世纪的光影线索,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让读者对时代的离合、家庭的悲欢、命运的跌宕,产生近距离的认识。
|
| 關於作者: |
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县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北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特约出版策划人。
从事编辑工作40余年,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与理念》《今天我们怎样做书》,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做书的故事》《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翻书忆往正思君》,回忆录《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等。
|
| 目錄:
|
序一:直陈磨难,信史可期 郭世佑
序二:家族史与集体记忆 雷颐
自序
我的曾祖父李征庸
第一次广州起义中的李征庸
李准人生中的两个焦点
附录:有关李准的几个疑问
冤家恩公——李准与岑春煊的恩恩怨怨
李准与汪精卫
我的祖母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吊诡人生——我的癌症故事
我的大学梦
|
| 內容試閱:
|
自序
四川省邻水县这个地名,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说是熟悉,因为我从小被父亲告知,在各种履历表“籍贯”一栏,要填上它,我甚至在看不懂地图、不知它的方位时就已经熟知这个名称;说是陌生,因为我对它没有一点感性认知,直到2007年55岁时,我得知这个县城距离重庆只有一百多公里,才借着参加重庆书展的机会,找了一辆便车去了一趟。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里作为我的“籍贯”。我问父亲,这是你的出生地吗?父亲说也不是,他出生在他的伯父、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旧宅里,地点在广州的东园。他说邻水是我祖父的出生地,因而就是我的祖籍。但后来我查了李准自编年谱,得知他说的都不对,我父亲李相崇1914年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准在香港购置的罗便臣道23号寓所,而我祖父李涛1894年出生在我曾祖父李征庸担任知县的广东揭阳县(今揭阳市)县衙内。说起来,邻水只是我曾祖父李征庸和伯祖父李准的出生地。
我们李家本是江宁府(今南京)上元县李家村人,先祖李诣元在康熙年间朝廷拔贡[1]获选为四川顺庆府邻水县教喻[2],从而落业于邻水龙安镇河堰坝,后迁居邻水柑子镇李家坝,至我曾祖父李征庸是第九世,我伯祖父李准和祖父李涛是第十世。曾祖父有两房夫人,育有两儿两女,年龄相差得十分悬殊。李准1871年出生,比1894年出生的弟弟李涛年长23岁。曾祖父李征庸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钦点刑部贵州司主事,第二年因高祖突然病逝,返乡守孝,本应丁忧三年,但他此间在邻水开矿建厂多家,上了操办实业的瘾,八年乐而忘归。后因遭到乡人嫉妒,才返京候命,1887年获选广东河源县(今河源市)知县。此后他将一家人带出了邻水,本人再也不曾回乡。他在广东各地任职,在河源、香山、揭阳、南海等地当过知县,全家人也跟着他四处迁徙。他去世前两年曾被授三品卿衔,任四川矿物商务大臣,准予专折奏事,但他在此任上也没有到过邻水,甚至是否回过四川,都很难说。他1901年病逝于广州,停灵于广州郊外,灵柩直到1905年才被李准护送归葬故里。至于李准,因为就在这一年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也便带着家人(包括我祖父一家)长居广州,辛亥后虽是挂冠而去,却也是定居香港和天津,再没有机会重回四川的。
所以2007年我回邻水寻根,发现五服内的族人,与我同曾祖的已经没有了,同高祖的都不认识、无联系。这些族人带我祭拜了高祖墓,参观了曾祖父当年开设学堂的破旧砖瓦房。族人们很以我曾祖父、伯祖父为荣,因为这是当地李家走出的两位高官,特别是李准,在保卫南海问题上还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说,当地正在打造李准文化品牌,把他和广安地区(邻水县属于广安地区)的另外两位名人一起宣传,我问另外两位名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邓小平和双枪老太婆。我听了很有一些惊讶。
其实也不能说李征庸在邻水绝对没有后人。1887年,有人在山上竹林中捡到一个弃婴交给李准母亲抚养,取名李澂,人称“竹林君”。此时李征庸在外任职不知此事,孩子是夫人私自收养的。不想这孩子生性顽劣,不成器,李准母亲伤透脑筋,总是担心自己教养失职犯了大错。几年后,在她去世之前,把李准叫到面前,嘱咐李准一定要把他调教成才,方才闭眼。此后这位“竹林君”也长期跟随李准,他比我祖父李涛大七岁,根据李家大排行,李准称他七弟,称我祖父八弟,待他亦如手足。1901—1902年,李准曾请在广州番禺中了案首[3]的汪兆铭[4]来给自家的孩子做家教,学生有多人,包括李准的长子李相枚和八弟李涛,也有李澂。1903年汪兆铭赴日本留学,当时李澂16岁,李准把他托付给汪兆铭带到日本。谁知此人一身恶习不改,到了日本即退学,成了流民,李准千呼百唤而不归。直到两年后派人将其送回国内,关在铁屋中。为“收其野心”,李准为其娶妻,后令其返回邻水定居。
李准对这个收养而来的弟弟没有出息深感自责,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感叹:“陷此弟于不肖,我之过也。”当然他也不能信任此人。李澂在邻水,但李准从不提起他。李征庸当年在邻水办实业,是有家族企业的,这些企业由李准继承,但李准宁可托几位侄子管理,也不找李澂。但侄子们也不得力,不过是享受李家企业带来的利益罢了。李准晚年,生活贫困,需要老家经济支持,但这些子侄竟然不肯援手,他在回忆录里多次慨叹:“家中款项亦难接济,屡电催之,亦不应。”“自宅子侄均不可恃。”“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5]至于李澂,其人回乡后即成为恶霸地主,1951年在土改中被镇压。据了解,李氏族人对其人之死并无惋惜和同情。令人遗憾的倒是历史上曾经为邻水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征庸,因与其有养父子关系,土改时被殃及。李征庸的灵柩被挖地三尺刨出,遗体被弃置乡野,可叹。
虽然李准终其一生未能回乡,但我祖父李涛确是动过回邻水养老的念头的。他在天津一直仰仗李准,本人没做过什么官,不过是天津市政府的文秘,工资低微,而他花钱大手大脚,总要依赖李准接济。李涛也有两房夫人,正房是我祖母,姓周,是曾任晚清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周馥的七孙女,两人于1912年在青岛结婚,生下我父亲李相崇和二叔李相璟,又于1916年纳妾卢氏,生下我的三叔李相尹和四叔李相博。祖父一家长期跟随李准生活,四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李准取的。在望子成龙观念下,李准选了四个古代贤相(即姚崇、宋璟、伊尹、文彦博)的名字为他们命名,这也和他自己的名字相对应,因为李准的“准”字来源于寇准。李准在世时,一直是家庭的大家长,万事由他说了算。
李准去世后,李涛失去依靠,坐食山空。1946年,他52岁,要考虑养老了,因为天津消费高,他觉得回乡安居才是上策。但我祖母周氏不同意。祖父在自己的一妻一妾中,历来宠幸卢氏而疏远周氏,此时便决定带着卢氏及其两个儿子,即我的三叔和四叔一同回乡。到底是破落的旧贵族家庭,又变卖了房产,攒够了在农村一辈子吃喝的银钱,他们携带了16只大箱子,千里迢迢回到邻水,颇有衣锦还乡的味道。谁想到,乡间族人眼红之下,将他们带去的财物抢劫一空。做这事的,就是那些李准抱怨的子侄辈人物,据悉李澂也是指使和参与者之一。
祖父自此被驱离邻水,带着一家人流落重庆。他懂英文,曾从香港圣约翰中学毕业,在香港大学也读过一年书,有些文化,很快找到一家中学教书。这样混了两年。待三叔李相尹在黑龙江鹤岗市一间煤矿入职,就把他和一家人都接到鹤岗。新中国成立初期,划定阶级成分时,考虑到他家产被抢后一贫如洗的状况,将他这个旧官僚、破落贵族家庭的公子哥定为“城市贫民”,倒也算因祸得福。他此后在政治上没有挨过整,也没有再享到什么福,1954年因病逝于鹤岗。
祖父离开家乡后,一直到2007年我回乡寻根,60年中,李氏家族中李征庸一脉,再没有人踏足过邻水。邻水对我们这些李家后人,变得极其遥远了。但需要承认,它终归是家族的根脉所在,而李准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为我的祖父、父亲,都是李准抚养长大成人的(曾祖父去世时,祖父才七岁)。我父亲一家直到1936年李准逝世,始终寄居于李准的大家庭内,父亲直到高中毕业的学费,都是李准出资。可以说,李准对我父亲的影响,超过祖父。当然,50年代以后,在阶级论至上的年代,父亲和我们一家对于出身在李准这个封建官僚家庭,是需要表态划清界限的。特别是李准作为前清军队高官,曾多次参与镇压“民变”,其中包括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被认为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这样的家庭“黑历史”令父亲和我们都抬不起头,羞于提起。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海主权问题因为中越西沙之战而升温,李准巡视西沙保卫海疆的事迹又被报刊广为宣传,特别是近些年来他还被誉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父亲和我们作为李准后人,又似乎与有荣焉。总之,无论是褒是贬,李准在我们李家被关注的位置,无可取代。
因此,今天我编选《百年家事》,便是以李准的故事为中心,向上、向下延展。有关李准的文章三篇,前面是关于曾祖父的两篇,后面是关于祖母的一篇,关于父亲的一篇,关于我本人的两篇。每篇文章都是人物侧写,只写人物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的故事。所选的故事,都有一定代表性。我以为,这些文章连缀起来,大体上把邻水李家百年来的经历勾勒出一条线索。遗憾的是关于我祖父着墨不多,只在《我的祖母》一文少有涉及,还有写李准辛亥起义时,提到年仅17岁的他三次被派往香港和同盟会胡汉民谈判(其实说开了,是李准以他作为人质,以表弃暗投明决心),我觉得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多的史料,难以下笔再写什么。当然,我还知道他因为曾在香港读书,很洋派,会跳国标交谊舞,20世纪20年代,就可以在舞厅拉场子、做教练;他也很传统,能和李准一样演练书法,当京剧票友。他京胡拉得不错,是可以上台给张君秋、金月梅等名角伴奏的。这些都是我从别处了解到的。父亲轻易不会谈到他。我没有见过他,甚至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直到最近,我才从四叔的儿子、我的堂弟李放那里找来他的一张半身照,一看吓了一跳:他的相貌与我父亲酷肖,父亲简直就是他的克隆版!但是父亲在感情上似乎排斥他,家庭相册中连他的照片都未保留,这是因为,他1946年遗弃了我祖母。父亲坚定地站在祖母一边,和祖母、二叔一起,与他几乎算是脱离了关系,多年不通音问。50年代中期他去世时三叔曾告知消息,但父亲甚至都没有前往鹤岗奔丧。我想,既然父亲与他如此疏远,那么对他的专文,我只能付之阙如了。
关于这本书,有几点我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我的家族史,即使对于邻水李家中李征庸后人这一支脉来说,它也是极不完整的。我只是写了这个家族中四代人的几位代表人物,而这个家族的后人,据我了解,现在总有上百人吧。其中不少人各有成就,值得被真正的家族史记录。而我这本书作为“史”,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所以我只把这本书叫做家庭纪实文章集。
其次,我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我只想纪实,纪实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不仅要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而且要不为尊者讳。我尊敬自己的前辈,但也需实事求是。我家前辈李征庸、李准,都是功过相兼的历史人物。尽管李征庸曾被孙中山认为有维新思想,在戊戌政变时本能地倾向于主张变法的改良派,尽管李准在辛亥年洞察时局,最终率兵反正起义,使广州未废一枪一弹实现和平光复,但这父子俩终究都是清廷的忠臣,李征庸也参与过镇压1895年同盟会领导的广州起义,李准在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一直到1935和1936年,他还两次到长春觐见已然当了“满洲国”皇帝的溥仪。虽然溥仪留他在长春做官,他以年老体衰婉辞,守住了不当汉奸的底线,但此事终归表明,他对前清的旧君主是有几分愚忠的。这些事实显示李征庸和李准的另一侧面,说明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纪实性作品,只有把这些和盘托出,才可以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同样,书中写祖母、父亲和我本人,我们生活在当代社会的特定阶段,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在每个阶段的规定性和局限性。我想,家庭是奔腾的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它可以出折射时代的晴与阴,光和影。如果本书中的四代人,他们的经历和性格,正好可以透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这100年的时代变迁,那么,我的写作目的就达到了。
再次,这本书不是我的专著,没有经过整体策划,它只是我的家庭纪实文章的结集。由于各篇文章当初都是独立写作、独立发表,需要照顾文章自身叙事的完整性,所以编辑在一起时,涉及李征庸、李准的,乃至我父亲的个别故事时,细节或有少许重复。这一点希望读者谅解。
[1] 即从国子监贡生中选拔人才。
[2] 正八品官员,相当于县教育局长。
[3] 即秀才考试的第一名。
[4] 即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又做了汉奸的汪精卫。
[5]《李准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2页。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第十节(P227-231)
反右运动开始了。按理说,父亲不至于在运动中挨整。他信奉马列主义,真心拥护共产党,一直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虽然有群众说他搞翻译是走“白专”道路,但是他知过就改,这方面的意见已经平息了。他和党员干部相处得也很好,教研室里的党员,对他都很尊重,他也不会像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是因为对个别党员有看法,发牢骚惹祸。他一直在争取入党,主观上希望向党靠拢,哪有那么多意见可提呢?尽管入党始终不能如愿,也是因为自己不够条件,怪不得人的。
他仍然说了错话。并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具体工作问题的是是非非,而是因为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和人较真。
教研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那时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理论依据是,毛主席讲过,知识分子是附在资本主义的“皮”上的“毛”,新中国成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个观点,已经是那几年的流行说法了。当会上有人继续发挥这个观点时,父亲开口了,谈了一点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这个说法可以变一变了,因为经过1949年以后几年的改造,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了。其实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他平时很注意政治学习,清楚地记得,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做了报告,其中谈到,“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许,是他没有直接引述周恩来的原话,而只是说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或许,是他的发挥直接针对了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论断,结果引起一片哗然。当场他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拒绝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不过,这个错误并没有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周恩来说过类似的话。他的问题,没有被扣上政治帽子,只是被定性为认识错误。但是,另外一次讨论,让他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了。
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党内整风依然继续。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仍然主持各种有关整风的会议。一天,教研室的上级主管单位基础课教学部党总支副书记对他说,匈牙利事件中,发生了很多共产党员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的事。现在清华里面,也有别的系在讨论,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如果清华的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会不会亡国亡党?副书记希望他组织开会讨论。父亲照办了。
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好不热闹。很多人在联想,如果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那说明反革命活动很猖獗,被吊起来的肯定不是蒋校长一个人,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当然就要亡国亡党了!这个观点最终成为讨论会的主流看法。
父亲做总结,他是做了冷静思考的。他说:“蒋校长和革命事业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蒋校长上树’和亡国亡党根本联系不起来。”
他没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时散会,大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他们办公楼前,有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场,平时大家都在这空场的四周贴大字报。第二天,父亲去上班时,忽然发现,大字报区的所有大字报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还有人贴出标志,这里叫做“李相崇的西瓜园”。
他顿时就觉得,这件事背后是有人组织的。他落到陷阱里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但是大字报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如果光看大字报,不听他自己解释的话,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制造者,杀气腾腾地要把蒋校长吊在树上!
事后多年,父亲无数次地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说法,是不是有什么失误,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这件事。我大姐夫是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父亲比较信服他的意见。但大姐夫说,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拿出来讨论,是无法回答的。蒋校长被吊在树上,你说没关系肯定不行;但是你说就真的亡国亡党了,恐怕也不对,因为毛主席、周总理毕竟还在呀。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次测试,测试父亲,当然也是测试大家对于蒋校长的忠诚度。
父亲显然没有通过测试。领导上对他失望了。他被大会小会批判了几次。好在此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该戴帽子的右派都戴过了,他没有当上右派,只是被插了“白旗”。
他的群众威信扫地,主任当不下去了。他提出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辞职就会被免职。他的教研室有两位党员副主任,一位名叫马迅,另一位名叫李宗福,都是1949年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力保父亲继续当主任,到上级党委据理力争,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受到批评。
紧接着,学校党委开会,各系各教研室领导参加。主持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谈到近期思想斗争动向,提到父亲的名字,说“李相崇是没戴帽子的右派”。马迅和李宗福都在场,他们当场站起来和这位副书记辩论,批评他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只有戴帽子才是右派,“没戴帽子就不是右派”。弄得副书记一时很尴尬。事后,党委做出组织处理,马迅和李宗福都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他们两个人和父亲,被定性为“三人小集团”。
为了自己的事情,牵连了马、李,父亲一直心存歉疚,但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救人?马、李二人,自知在清华难以翻身,不久之后,两人都相继调出清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