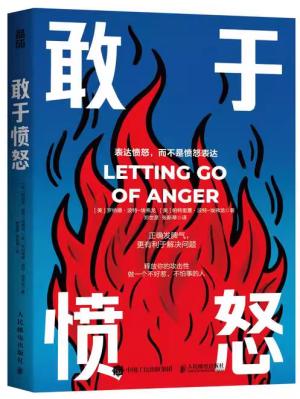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数据资产:从价值评估到价值管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
售價:HK$
74.8

《
时代狂澜与士人心波:晚明传奇中的情与理研究
》
售價:HK$
96.8

《
日本侵华战争及其战后遗留问题和影响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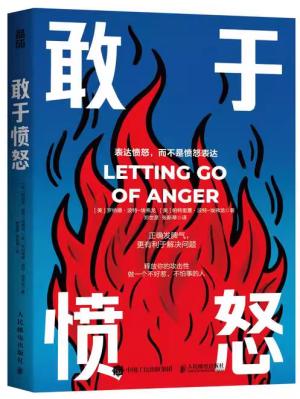
《
敢于愤怒:正确发脾气,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
售價:HK$
65.8

《
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
售價:HK$
162.8

《
面向全球南方——欧盟与新兴经济体战略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HK$
86.9

《
罗马法与欧洲:一种法律文化的历史
》
售價:HK$
68.2

《
英国大历史:时间线上读懂英国3000年,全球化视角下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与动荡
》
售價:HK$
64.9
|
| 編輯推薦: |
★ 郑执小说集2025典藏版升级上市。《森中有林》全新扩写。再版序言回溯创作初衷。
郑执以北方城市为背景,勾勒六个关于命运出逃与回归的故事:幻想在潜艇服役的精神病人、沈阳机场里寂寞的驱鸟员、愤懑中化为异兽的男孩,对父亲的长久告别,三代人命运的游离与挣扎……世纪之交的北方城市里,人物始终处于失落之中。这些故事曾让读者或震撼或感动。在这部典藏版中,作者将《森中有林》一篇扩写,多出近万字的一个全新章节,“在改编同名电影剧本的过程中,逐渐发觉这个故事理应讲得更完整,终将此前一直隐隐觉得‘缺了点什么’的那部分给圆了,大言不惭地讲,它已经是一篇全新的小说了。”全新的再版序言中,郑执回溯创作初衷:“写作大概是最能允许不合时宜的人存息的职业。如果真有命运这回事,我该真心感激它,将我塞给了写作。回敬的方式,当然是继续写,咬着牙写,好时候,坏时候,都要写。”
本次新版由知名设计师陆智昌设计,如同郑执的文字,简洁又充满生机。是值得新老读者“破费”,反复阅读的典藏版本。
★ 21世纪首登《巴黎评论》的中文小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编剧,影像与文学的双重肯定。
《仙症》英译版The Hedgehog 刊
|
| 內容簡介: |
幻想自己曾在潜艇服役的精神病人,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沈阳机场里寂寞的驱鸟员,
愤懑中化为异兽的男孩,
充满黑色幽默的报复,对父亲的长久告别,
三代人命运的游离与挣扎……
世纪之交的北方城市里,人物始终处于失落之中。
作者以锋利而深情的笔触,写尽那些无法被原谅、无法被遗忘的命运。撕开现实的裂缝,让日常生活滑向无法预测的边界。
|
| 關於作者: |
|
郑执,作家,编剧。1987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十九岁写作至今,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
|
| 目錄:
|
再版序 i
仙症 001
蒙地卡罗食人记 037
他心通 069
凯旋门 095
霹雳 119
森中有林 137
后记 241
|
| 內容試閱:
|
两只黄鹂被吕新开从粘鸟网上摘下来,是清明节前一天,也是爹妈忌日。要不是日子赶得寸,他也不至于往深想,他想,这对黄鹂是爹妈化身的,不然咋这么巧是一公一母?铁定是惦记自己了,特意过来瞅一眼,索性对俩小玩意儿叨咕句,上班了,挺好的,放心吧。那只母的竟然应了一声,音儿瘪得能听出来饿不少天了——鲜有人比吕新开更懂鸟——黑枕黄鹂,母的眉羽比公的长,黑亮亮一绺儿朝后挑,像女人描眉哆嗦手了。来机场上班四个月,麻雀、乌鸦、杜鹃、野鸽、山雀、红隼、夜鹰,吕新开摘了个遍,从没如此金贵过谁,下手比绣花都细,生怕折了哪只膀子,愣在网前耗了半个钟头。他后悔犯懒没披大衣出来,给风打个透。四月都出头了,沈阳还刮西北风。
吕新开呵里呵哧地回到办公室,倒是没让两只黄鹂冻着,一边裤兜儿揣一只,掌心搓热当被裹着。已经八点半,大李刚早饭还没吃完,半缸大米粥吸溜儿一早晨了;小李刚不知道搁哪儿弄来根红绳,正往一颗空弹壳屁股上绑,手笨,一直脱扣,嘴里骂骂咧咧。办公室一共就他仨人,俩同名同姓,大李刚三十六,小李刚二十二,长得还连相,都是团团脸,绿豆眼,吕新开刚上班那会儿,以为亲哥俩呢。四个月前,吕新开第一次走进屋,那鼻子霉味儿从此挥之不去—与其称办公室,不如叫储物间,撑死就十平米,还在半地下,刨去一个储物柜,两张桌子,一张行军床,连并排过俩人的地方都匀不出。吕新开双手插兜儿,站在原地转圈儿寻摸。小李刚问,找啥呢?吕新开装听不见,本来就不爱搭理他,这人嘴欠,比自己小两岁,仗着十七岁就上班,在机场也算老人儿了,开玩笑没大没小,上个月俩人差点儿动手,亏大李刚拉架,拽吕新开进走廊劝,别跟小逼崽子一般见识。小李刚又问,卵子落屋里了?吕新开问,昨天分那箱苹果呢?这句是问大李刚的。大李刚说,全烂的,扔了。吕新开问,纸壳箱呢?大李刚说,都搁门口呢。吕新开来到走廊,端起那箱烂苹果,去厕所倒进垃圾桶里,再回来的时候,空纸箱就做了两只黄鹂的新家。他用透明胶带封了箱顶,再拿钥匙捅出两排窟窿眼儿,装修完毕。两只黄鹂对临建房应该是挺满意,几声脆叫打窟窿里传出,底气明显比刚才足不少。小李刚暂停手中活计,啥玩意儿啊?吕新开说,鸟。小李刚说,废话,我问你啥鸟?吕新开眼皮都懒得抬,声更低说,黄鹂。小李刚问,多大?有肉吗?吕新开这才抬头,拿防贼的眼神回瞪,清楚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平时小李刚打的鸟,基本被他带回家吃了,猫头鹰都他妈敢下嘴,炖了锅汤,第二天还把剩的装保温瓶带办公室来,问谁想尝尝。大李刚拣了饭勺里剩的几粒米,来吕新开身边蹲下,顺窟窿眼儿一粒粒塞进去,打算在这儿养?吕新开说,带回家。大李刚说,黄鹂叫得好听,但不好养。吕新开自言自语,两个黄鹂鸣翠柳,下句啥来着?大李刚说,我初中文凭。吕新开说,小学课本里的,说啥想不起来了。小李刚说,两个黄鹂鸣翠柳,我跟你妈交杯酒。——捅完句屁磕儿,自己咯咯乐。吕新开忍无可忍,刚要开骂。大李刚又说,小时候没好好学习,现在后老悔了。说罢碰碰吕新开胳膊,挤了个眼,意思算了。吕新开合计也算了,他不想跟任何人置气,至少今天不想。小李刚没皮没脸,还接话,当初好好学习,现在又能咋的?大李刚说,不咋的,起码分苹果不至于总轮到烂的。小李刚哼了一声,将红绳套进脖子,黄铜色的弹壳在胸前晃晃着——跟个二似的。吕新开心说。
坐单位班车从机场回到大西菜行时是五点。纸壳箱一路被吕新开捧在腿上,两只黄鹂挺懂事,一声没吭,省了麻烦。吕新开主要是嫌跟同事搭话麻烦,平时坐班车,不管困不困他都装睡,没别的,就是懒,懒得记那么多人名。进屋五点多,大勺里有前天炖的豆角,剩个底子,点火热了热,半个凉馒头掰开泡汤,对付一口就出门了。
天开始长了,但冷还是冷。彩塔夜市上个月已经陆续出摊儿,更多的厂子开始不管饭了,夜市反倒更热闹了。把北头第一家是个铁亭炸串,哈喇油爆面包糠的香,还是把吕新开给勾过去了。炸串这玩意儿,吕新开打搬来沈阳那年第一次吃,就上瘾了。小时候在山里跟县城,从没尝过这口。甜酱跟辣酱分装两盘,自己上手刷。吕新开最爱炸鸡排,先滚一圈儿甜酱,再蘸单面辣酱,合他咸淡。俩大鸡排下肚,才算见点儿饱。再往前走,是家游戏厅,偶尔兴起,他也钻进去找人掐两把街霸,今天没工夫,他赶着去再前面一家杂货店,那家关门早,夜市开摆,一家三口就锁门吃饭,因为地摊儿卖的东西更便宜,所以只做白天生意。吕新开家里的锅碗瓢盆不少都是从他家买的,之前去的时候,他记得见过鸟笼子。
赶上老板正要上锁,吕新开进门了。他没记错,指着收银台后面堆在最顶的鸟笼子问,那个多钱?老板说,那个不卖。吕新开说,摆那儿不卖,啥意思呢?老板说,我以前养了只八哥,死好几年了,跟笼子都有感情。吕新开问,八哥咋死的?老板说,话说太多累死的,逮个人进门都得显摆两句,伤元气了。吕新开说,闲着浪费,我要。老板说,五十。吕新开说,二十。老板说,三十。吕新开说,破不锈钢,又不是竹子的,二十五。老板装一脸不情愿,收下钱,鸟笼子交给吕新开,你养的啥鸟?吕新开说,黄鹂。老板问,单蹦儿还是对儿?吕新开说,对儿。老板说,对儿好,不寂寞,黄鹂就得养对儿。吕新开说,两个黄鹂鸣翠柳。老板瞅他一眼,还买别的吗?不买我锁门了。
再回到彩塔街上,天黑利索了。向西的丁字路口,有人烧纸,两团火焰一左一右地蹿动,好像黑夜在对自己眨眼——原本是回家该走的近路,眼见大风卷起烧正旺的黄纸在半空中盘旋,他想起爷爷说过,那是孤魂野鬼在抢钱,突然犯了咯硬,随即掉头,继续往夜市南口走,宁可绕远。出了南口再往东,就是青年大街,也是从市区直通机场的主干道,吕新开每天坐班车来去的必经之路。自打年后开始动迁,整条街一天一个景,全程二十来公里,不是扒房、挖沟、埋管,就是栽树、架灯,没一段囫囵路,报纸上管这叫金廊工程。吕新开提着鸟笼子,沿青年大街慢下脚步,周边的拆迁户也出来摆摊儿了,夜市挤不进去,只能沿南运河排一长溜儿。吕新开有一搭没一搭地转悠,想寻摸俩小盅,回去给鸟盛水跟食儿。眼瞅快逛到头儿了,肚子突然闹起来,一阵阵疼,感觉要窜稀,反思一下,问题不应该出在炸鸡排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估计是给凉馒头拔着了,要不就是早上让风吹着肚脐眼了。他赶紧加快脚步往家拐,还没出几步,拦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坐在地上撒泼,挨了他妈两手锤,说啥就不起来。吕新开路过一瞅,原来是为个玩具气枪走不动道儿了——来复式,一比一,他自己早就想买一杆来练手,说不上为啥,忽就犯起撩闲的心,摊儿主是个大姐,吕新开故意提高嗓门问多钱,大姐张口三十。他急屎,没心思讲价,甩下钱,拎枪要走,被大姐叫住,非送子弹,钢弹跟塑料弹都有,选一个,吕新开抓起一包钢弹蹽了,塑料还玩儿啥意思?他离开时,听身后那孩子快哭抽抽了。
吕新开一路小跑到家,左手鸟笼右手长枪,冲上楼,奔厕所,总算没在最后一刻失守。一泡拉完,才把两只黄鹂搁笼子里安顿好,第二泡又来了,这回肚子疼得他一脑门儿汗,再出来时,腿都快站不住了,直接在沙发上卧倒,盖上毯子,看眼表,快八点了,随后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他又梦见了嘎春河,明闪闪的河水,从两岸的山杨林跟白桦林之间蜿蜒而过,到了夜里还会发光。嘎春河从松花江来,途经新开农场的一段并不深。五岁前,爷爷常领吕新开去河里摸鱼,有时也拎火枪去打野鸭。五岁后,吕新开就敢自己去河边了,不一定非摸鱼,夏天光泡泡脚图个凉快,爷爷也管不过来。那一场山火过后,爷爷比从前更难了,要养活孙子,每天还得坚持进山巡逻。爷爷去世后的这些年里,每次吕新开梦回嘎春河,都是以那场山火收场,梦中的一切都被烧成了红色,连河水都是通红。儿时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从头到脚冒着烟,散落在又高又密的落叶松林中,隔着河水冲他招手,吕新开从不敢越过去,即便他清楚那是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