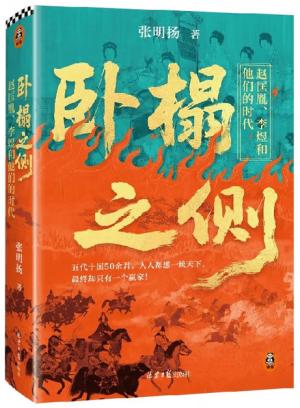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植物圣经(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典藏全彩复刻,跨越400年的科学与艺术瑰宝,一部改写人类植物认知的里
》
售價:HK$
294.8

《
边际利润
》
售價:HK$
75.9

《
红帆船
》
售價:HK$
62.5

《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科学的进步,在于人类不断探寻“山的另一侧”的风景)
》
售價:HK$
41.8

《
量价狙击:精准捕捉股市机会(新时代·投资新趋势)
》
售價:HK$
86.9

《
万有引力书系 万川毕汇:世界环境史国际名家讲座
》
售價:HK$
96.8

《
企业可持续发展/ESG工作实用手册
》
售價:HK$
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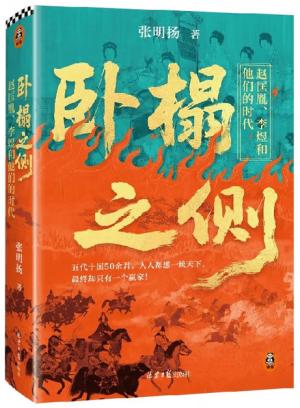
《
卧榻之侧:赵匡胤、李煜和他们的时代
》
售價:HK$
87.9
|
| 編輯推薦: |
|
在这本访谈录中,我们不仅读到了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魅力和人格形象,不仅读到了梁漱溟先生所体验的现代中国思想的演化脉络,而且读到了蕴藏在梁漱溟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精神,她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持续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
| 內容簡介: |
|
1980年,先后有两位美国学者越洋访问梁漱溟先生。林琪即是*位(1980年67月);另一位是艾恺(1980年8月,已成书《这个世界会好吗?》)。这部访谈录广泛与专精并重。基本回顾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讲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对于梁氏特别关心的话题,如乡村建设运动主旨、佛学要义,尤致意再三。这部访谈录遵循口述实录,几无润饰,保持了鲜活的现场感。
|
| 關於作者: |
|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
| 目錄:
|
第一天: 1980.6.19
第二天: 1980.6.20
第三天: 1980.6.22
第四天: 1980.6.23
第五天: 1980.6.24
第六天: 1980.6.25
第七天: 1980.6.26
第八天: 1980.6.27
第九天: 1980.6.28
第十天: 1980.6.29
第十一天: 1980.6.30
第十二天: 1980.7.2
第十三天: 1980.7.5
附录
一九五三年我犯错误的始末: 一九七六年补述梁漱溟
梁培恕致林琪的信
索引
跋: 一点回忆及补充伍贻业
后记: 致谢林琪
|
| 內容試閱:
|
自序
一
本书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当时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博士。我的兴趣主要是上半世纪知识分子对乡下的认识,因而选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及民粹主义的选择在中国(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对梁漱溟先生的著作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他的思想有意义,但没想到我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作研究,更不用说能见到梁先生本人。正好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年,南京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签订互换交流学者的协议。那年秋天,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中国学习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来到南京。
1979年与现在不同,学术界对梁漱溟先生思想并不熟悉,不过大部分学者通过两年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知道毛泽东批评过梁漱溟先生。我们来南京大学的这批美国研究生都被安排了指导教师,而南大历史系教授当中只有伍贻业教授对我的研究题目感兴趣。伍教授有儒学研究背景,又曾在收藏有民国时期材料的档案馆工作过,兴趣和经验比较广,也愿意帮助我学习。我到了南大以后,还不知道是否能去拜访梁漱溟先生。1980年4月中旬,南京大学外办开始联系梁先生的单位中国政协,没有结果。5月底,我直接给梁先生写信。6月8日,梁先生回信,欢迎我到北京去看他。参看《梁漱溟全集》卷八,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二
伍教授和我1980年6月18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去向中国政协办公室的李数女士报到。王芸生先生的追悼大会恰好也是6月19日在政协礼堂前厅举行参看梁漱溟字条,缘虑,1980.6.28 B。,而我们当天临走的时候追悼会正好结束。李数看见梁先生从礼堂出来,介绍我们双方认识。没想到,梁漱溟先生当下很随意地要我们乘坐他的小车随他回家。这样,我们第一次来到梁先生的住地北京木樨地22楼5门9层17号,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我和伍教授再去,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几乎每天早上去梁先生家访谈,一共十三次。
第二天谈话快结束时,我们问梁先生可不可以将每次的谈话内容录音记录下来。梁先生前一天随意地请我们随他回家,此刻又欣然同意录音。当时中国刚开放不久,跟其他中国人正式相处时,我经常会感觉他们有一点犹豫。梁先生一点都不是。恰好相反,和梁先生谈话十分自然,似乎没有不可以问的问题。这样子从第三天开始,每天早上去木樨地录音两个小时左右的访谈。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访问梁先生的外国人,但这不是第一次有外国人访问梁先生。例如,1932年4月4日哈佛大学哲学系的William Hocking教授有一次在北京采访过梁漱溟先生。Hocking留下的笔记描写梁先生说话的声音非常低,以致茶馆的服务员需踮着脚走路。
Hocking, William Ernest. Monday, April 4, 1932. Afternoon. Peiping[礼拜一,1932年,四月,四日。下午。北平]。用打字机打印的梁漱溟访问记。1932年4月4日。 William Ernest Hocking档案,92m71,第49盒,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半世纪以后,梁先生仍然低声说话。结果是录音带有的部分听不清。不过正如Hocking所说,梁先生说话说得很慢,有时会停顿一下,同时也说得非常清楚,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我当时在中国学习还不到九个月,不过听懂梁先生的话不成问题。
Hocking记录梁先生紧跟着他自己的思路,不跟着Hocking转换话题。我们的访问也是这样。我本来告诉梁先生要谈三个大题目: 乡村建设的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谈话基本上都在这大范围以内。梁先生说什么经常好像有所准备,说法不异于其他时间讨论同样的题目。他叙述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事情时喜欢按时间顺序讲。有一个故事给我们讲了两次,第二次的说法与第一次基本上相同。梁先生好像特别愿意讨论佛教。我们也没想到梁先生会主动地要说清楚1953年毛泽东批判他的背景和经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