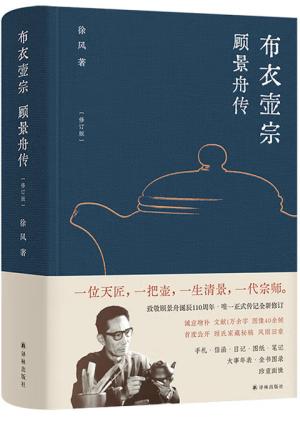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世界中国学:当代发展与未来展望
》
售價:HK$
140.8

《
低空经济蓝皮书:低空经济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217.8

《
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理想国译丛074)
》
售價:HK$
107.8

《
跨越学习曲线:成就非凡的行动指南
》
售價:HK$
64.9

《
财富的秘密:一部瑞士经济发展史
》
售價:HK$
52.8

《
猎头游戏(尤·奈斯博邪恶又疯狂的独立作 当昆汀遇上科恩兄弟 改编电影创造挪威票房奇迹)
》
售價:HK$
54.8

《
全彩速学低压电气电路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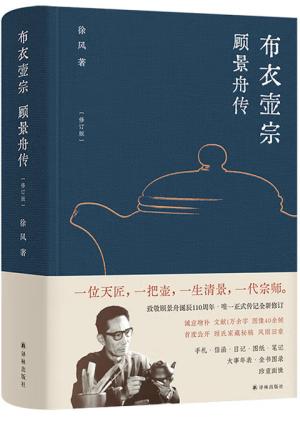
《
布衣壶宗:顾景舟传 一位天匠,一把壶,一生清景,一代宗师。致敬顾景舟诞辰110周年 顾景舟WEI一正
》
售價:HK$
118.8
|
| 編輯推薦: |
作者王湜华是俞平伯挚友王伯祥之子,与俞平伯相识数十载,以俞平伯世侄之视角、更是俞平伯后半生生活的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准确捕捉俞平伯在遭到学术上的坎坷之后、许宝驯夫人逝世之后以及后来又得到正式平反等重要事件的心境。
本书以细腻真挚的笔触详叙俞平伯与许宝驯夫妻坎坷而恩爱的后半生。不论是遭受质疑还是下放劳动的日子,夫人始终陪伴在身边,给予支持,携手共渡难关。后来许宝驯先逝,这对俞平伯是又一大打击。
对于红学的研究,晚年的俞平伯曾有过反思。(我在红学上)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这些都深刻地烙印了俞平伯的后半生,甚至他晚年几乎没有新作,彼时对待红学的心境,更多都是在自我的反思中。
述及俞平伯与挚友王伯祥在特殊时期的交往,感怀郑振铎、朱自清而作文,以及与叶圣陶因《兰陵王》的乒乓球式书信来往。
引用了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其他的诗词文和往来书信等,还原俞平伯作文时的心路历程。
|
| 內容簡介: |
俞平伯先生的白话诗歌、散文妇孺皆知,其文学研究硕果累累,更以红学大家闻名于世。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分析评价了俞平伯的思想、学术、生活等各方面的经历,是一本较好的学术纪实性作品。该书着重从俞平伯的学术生涯出发,展现他的精神世界和学者风采,对俞平伯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俞平伯的影响力,加之王湜华的文学功底,可谓以大师手笔摹写大师。
|
| 關於作者: |
|
王湜华,字正甫,号音谷,江苏吴县人。1935年1 0月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贞观胜慨》、《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元太祖帖木贞元世祖忽必烈》、《俞平伯的后半生》、《弓弦殉情》、《无冕之王》、《努尔哈赤后妃传奇》、《皇太极后妃传奇》、《红学才子俞平伯》、《李叔同的后半生:弘一法师》、《音谷谈往录》、《王伯祥传》等;校点整理古籍若干部。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数十万字;红学类文章论文十数篇,约二十万字。喜爱书法篆刻,亦善作旧体诗联等。
|
| 目錄:
|
目 录
难以忘怀的1954年/1
我们必须战斗/10
写读《随笔》絮语/16
从《随笔》到《简论》/35
交游零落似晨星/45
喜得文孙/50
北京昆曲研习社/53
哀念郑振铎/58
烟卷笔墨/63
从《词选》到《词选释》/67
《寒涧诗存》/73
不可弥补/77
干校生活/82
干校诗怀/86
干校家书/92
感怀挚友/101
发还家珍 兴奋难抑/108
鱼菽曾孙与,苍颜借酒红/116
今日阿谁孚众望/120
地 震/124
晚来非晚借灯明/133
同在一地的两地书/136
重圆花烛/138
重印《古槐书屋词》/154
《学刊》创办前前后后/161
欣慰的1980年/165
《重圆花烛歌》题咏种种/170
感慨弥深,真切弥笃/183
相对苦笑/188
悼 亡/193
拥衾寒暖不关情/202
喜得曾孙/207
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213
《旧时月色》/217
《兰陵王》/225
只有旧醅,却无新酿/241
多背诵,少要框框/245
赴港讲学/248
港游花絮/259
讲学归来的点点滴滴/269
九十大寿/273
四世印汇/277
奖掖抄书/283
翰墨前缘/287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291
《乐知儿语说〈红楼〉》/298
长留遗憾在人间/314
会永远活下去!/317
墓木已拱/319
永恒纪念/322
附录 俞平伯年谱/324
首版后记/374
再版后记/375
|
| 內容試閱:
|
首版后记
俞平伯先生与家父伯祥先生之订交,远在20世纪初,早于我出生十数年,当然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他比家父小十岁,向以长兄视家父,而以弱弟自居。而我之亲炙先生教诲,已在他与家父于文研所同事之后。他的教诲,又每在细小琐事间,而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在均得显现,故得益之深,往往鞭辟入里。凡有求于他,那是必应的,如四代印章之钤拓、抄本上之题识、题诗等。直至家父1975年底谢世之后,先生对我之督励与关怀,更是有增无已鉴于此,我有责任就我之知见与亲炙,来写这部《俞平伯的后半生》。书稿略经周折,最后能在花山文艺出版社,追随《俞平伯全集》
之后得以出版问世,这是深感欣慰的。而责编与美编又提出将《德清俞氏四世印汇》等编印入书,既美化了版面,增加了阅读的兴味,兼有弘扬先德之遗教、敬观前辈之风范等寓意,我当然尊重责编、美编之雅意,更可增补拙笔之不足,多为读者提供一些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既说到也印入了印章,还应多说两句。我的刻章,从年轻时初步接触此道起,亦已逾半个世纪,但始终未得入门。而平伯先生总是鼓励我,有时亦命我为他刻一些名章与闲章。我又喜收集长辈师友的印蜕,当我求拓《德清俞氏四世印汇》时,他重违其意,基本上全让我拓存了。这次印刷出版,连我胡搞的刻印也一并收入了,怎不令人汗颜!姑且不藏拙,以求世人之诲正吧!王湜华记。
2000年8月16日于北京
喜得曾孙
在俞夫人去世后不久,俞平伯做了个梦,梦中得见一块匾额,上书汐净染德四个大字。俞平伯一向有记梦的习惯,这梦见匾额之事,自然记了下来。他越琢磨这四个字,越感到有意思,似有颇深之寓意。于是他又想到了一句诗: 何曾饿死信天翁!他即将汐净染德四字,与诗中之信天翁三字,命笔者为治印。因为在那些最悲痛的日子里。他是辍笔不再为人作书的,命我作印时,他已购得了蓝印泥,答应印刻好后,就再开笔作书,并将钤用之。
信天翁,乃鸟之后,是种体灰白色,长约二尺,嘴长,翼狭长善飞,脚淡红色无后趾,前三趾间有大蹼,又善于游水的游禽。据《正字通》云:信天翁,鸟名,不捕鱼,俟鱼鹰所得偶坠者。《琅邪代醉编信天缘》云:余按信天缘,一名信天翁。国朝连瑞有诗: 荷钱荇带绿江空,唼鲤含鲨浅草中。波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此说可以讽。诗载《群谈采馀》。清代傅王露,字良木,会稽人。平生好学不倦,优游林下,著述自娱。晚年即自号曰信天翁。俞平伯因梦中见匾而想起了连瑞的诗,决定采用信天翁三字来与匾文合刻对章,并愿钤用之,恢复写字,可见其中之感慨是十分深邃的。汐,晚上的潮水;净,动词,洗净,大浪淘净之意;染字之寓意,乃四字中之关键,并非一般点染、烘染,染色之意,正用得上一个现代词污染。串讲之,晚潮洗淘净了被污染的德行。这四字,正如他叫我刻印时说的,很像是在说他的生平。而他取之又与信天翁来刻成对章,则寓意更为不凡, 何曾饿死信天翁,真是感慨良深的自嘲啊!此时虽还未召开为他平反的会,但社会上正直而有良心的人,早已自有看法。对1954年他被批的若干红学观点,亦开始有人敢站出来说公道话了。所以他的心态已逐渐得到更大的平衡。富幽默感,乃是俞平伯一贯的文风之一。自况为信天翁,来与梦中所见匾额配套,这不是最好的幽默与讽刺吗?!
笔者为俞平伯刻这对章的时间是1982年9月11日至13日。在留印蜕时,曾分别为二印作了小记。汐净染德印的小记云: 此乃平伯丈梦中的所见匾额之文,丈自谓颇肖其生平,乃命余作此,自是之后,丈恢复为人作书,即钤用之。信天翁印的小记云:此印亦丈一并命刻者。为鸟名,乃取何曾饿死信天翁之句意。1982年9月11至13日成此对章。我刻的是一朱一白,汐净染德为白文印,信天翁为朱文印。印实在谈不上好,而俞平伯还颇喜欢,还真的用蓝印泥多次钤用在他的书法作品上。
1983年8月8日,夏历癸亥岁六月三十日,俞平伯喜得曾孙。喜讯传来,老人自然十分高兴,次日即作七绝两首以志喜。在收进《诗全编》时,题为《一九八三癸亥岁六月卅日立秋孙李在天津举一子,喜赋二章》,诗云:
其 一
新得佳儿可象贤,吾家五世尽单传。
不虚仙李蟠根大,六月秋生字丙然。
其 二
东涂西抹漫留痕,弓冶箕裘讵复存。
八十年中春未老,倘延祖德到云昆。
此时俞平伯的心情,与八十四年前俞曲园喜得俞平伯这一曾孙时是完全一样的。寄厚望于曾孙,这是此时心情交感中的核心。从传统观念看,曲园老人这样一位清代大学问家,传到孙子俞陛云,中了戊戌探花还不说,学问著述方面虽不及曲园老人多,但在选学、诗学等方面的成就,犹自成家数。到俞平伯这一代,偏偏他的成名之作是《红楼梦辨》,所以当郑振铎等戏称他为红学家时,他有种被开玩笑的感觉。也可以说,从传统治学的观点来看,已从大道滑到了小道上。又偏偏1954年后他的红学观点受到了批判,这小道本是很有新意的开创,却横遭非议与谴责。其内心之懊丧,还真难用几句话来概括清楚。现在自己跟当年的曲园老人一样,虽亦已届耄耋之年,终究还是见到了曾孙降生。这实在是件堪慰平生的大事。
说起这句吾家五世尽单传,似乎从曲园老人算起,到丙然,不是七世,也应该是六世了。为什么说五世呢?其实是从传到俞李这一代而言的,确实是五世。当然,此后家家都只许生一个,俞李当然不能例外,而且今后还要世世代代单传下去。
在此顺便说一说,近日从友人杜春耕处得见的一些新资料。
大家一般都知道俞平伯上面有两个姊姊,而男孩子只有他一个。而从新资料两首曲园老人自书诗的手迹来看,俞平伯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可惜很早夭折了。这两首诗全文如下:
第二曾孙生志喜
半夜听啼声,床头钟再鸣。
刚逢庚伏尽,喜报坎男生。
容易真如达,排行便是名。
来朝传紫电,报喜到燕京。
曲园叟
悼曾孙庆宝
肌肤玉雪貌丰昌,况又聪明记忆强。
以我耄年犹未死,致儿幼岁便云亡。
笑啼都付三更梦,汤药空添一夕忙。
始信人间医可废,老夫旧论不荒唐。
这两首诗,分别书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绝非赝品,因可作假者不会作这样的诗。从第一首看,曲园老人的喜悦心情不亚于得第一曾孙时。又从第二首诗看,二宝后又名庆宝,夭折时虽不大,但似已脱离襁褓,已能显露其聪明与记性,所以对他的夭亡,老人是十分痛心的。亦正因此,这两首诗不知怎么竟流落在外,或许是老人想把这一段痛苦的经历彻底从记忆中抹去吧!
俞丙然双满月之后,重阳节,被带到北京来见太爷爷俞平伯,太爷爷当然特别高兴。特地步当年曲园老人的原韵,作了一首七律:
过夏晨秋产此儿,而今芳在桂蓉枝。
含英玉蕊生庭日,解笑雏入抱时。
未许研红供描墨,还将衰白惜凝脂。
新来世纪知何似,三益还堪作尔师。
这首诗在收入《诗全编》时题曰:《癸亥九月朔曾孙丙然双满月后重阳来京,为书前和春在堂庚子年诗》。俞平伯生于己亥岁腊八,已交1900年(庚子)。
笔者于1983年11月5日晨去拜望俞平伯,因为我让朋友杨晓航特地为他刻了块天元甲子朱文印,送去以备来年可以钤用。那天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块十分精美的朱红寿山石,当即拿出来,命我为他的曾孙丙然刻一块名章,以示曾祖对曾孙之宝爱与厚望,同时还拿出上面这首诗给我读。我受此重托,回家即精心布局,虽难可意,但确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第三天早晨乘光线好,即奏刀。留印蜕后作小记如下: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晨往谒平伯仁丈,敬赠晓航所作天元甲子白文印一。丈出?近作步曲园老人原韵为得曾孙喜作。今丈得丙然,犹当年老人得平丈然。特检朱红寿山石章命作此印。十一月七日晨刻于小雅音谷之南荣。俞家多世单传,诚当贺焉。
印是哪天去送交俞平伯的,因不记日记,也就难查其确了。正巧得费在山寄来1998年1月3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他的文章,题为《俞平伯无题词释》,一开头的三小段,正好说到此事,可补我失记之憾,诚天意也,现即转录如下:
俞平老与我为忘年交,通信十七年,使我从中得到书本上无法得到的教益。他的第一封来信是1973年7月,而与我见面却要到1983年11月,相隔十年多。那是我第一次进京,出席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住在文兴东街一号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现国谊宾馆)。初到首都,人地两疏,靠王华帮助,联袂去三里河南沙沟拜访神交已久的俞平老。
俞平老知道我要来,当我一踏进门,他就用双手捏住我的手,顷刻间竟说不出话来。我想拍照,但他坚持说勿要拍,我这副样子怎么能拍 一口道地的苏州话。华和我也讲苏州话,彼此感到十分亲切、激动,心一酸,我的泪珠已挂在眼瞠里。
坐定后,俞成大姐为我们泡茶,华把刚刻好的俞丙然印递给俞平老,他高兴得连声说好。
因喜得曾孙,此时俞平伯已不再用蓝印泥。那天送给费在山的一幅字上,所钤之印即我所刻的信天翁,已恢复用红印泥了。由此亦正可见他欣喜之心情。
而此时俞平伯毕竟已年迈体衰,又在老年丧偶之后,所以喜中亦仍难离悲影,更为他夫人之未能亲见曾孙而怅失。再说,天津的儿孙曾来京,固为一乐,一大乐,但亦只是短暂的欢快,从长远看,老人还是被笼罩在孤寂之中。从下面这首《癸亥九月口占》中,即可清楚看出:
长眠犹有待,且作昼眠人。
老去心思慢,推敲一字贫。
这才是俞平伯的那段时间恒常的生活写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