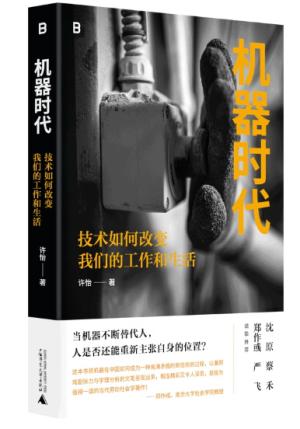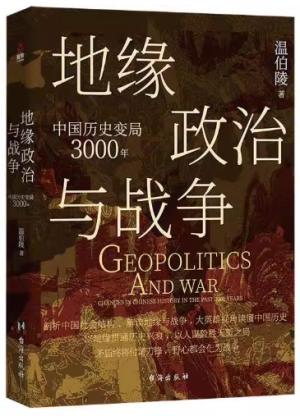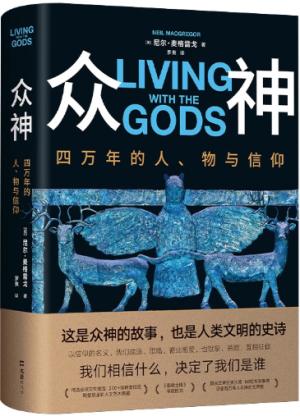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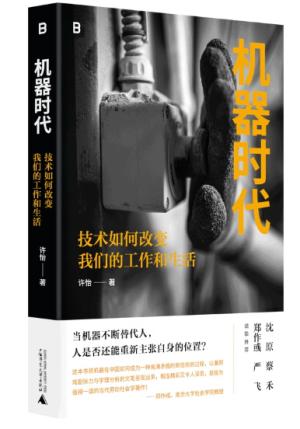
《
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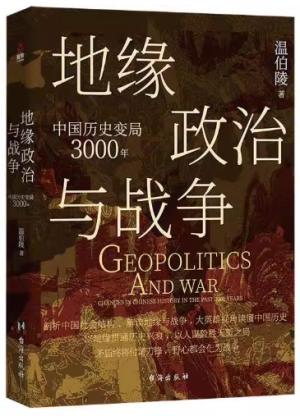
《
地缘政治与战争:中国历史变局3000年
》
售價:HK$
85.8

《
追踪进化论 在游戏中读懂科学史 《龙与地下城》玩家打造 沉浸式体验进化论 附赠精美计分器
》
售價:HK$
86.9

《
消逝的韩光:华丽韩剧背后的血汗与悲鸣
》
售價:HK$
69.3

《
大学问·从“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边墙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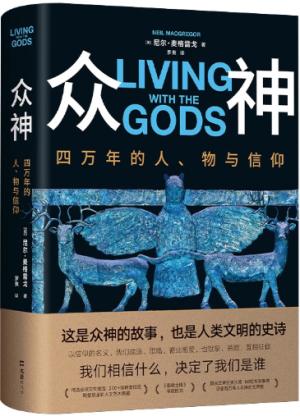
《
众神:四万年的人、物与信仰
》
售價:HK$
184.8

《
汗青堂丛书159·欧洲的熔炉:意大利文艺复兴与西方的崛起
》
售價:HK$
101.2

《
凌空之魂:五十岚大介短篇集 赠猫咪方银卡+鸮女明信片 自然寓言怪谈异色人外兽人都市奇谭漫画
》
售價:HK$
47.1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散文作品精选,也是其毕生的文学精粹,岁月沉淀后的灵魂独白。全书收录了沈从文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经典散文名篇,包括《湘行散记》《云南看云》等。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在沈从文的笔下,一切源于天然,他落眼宽阔、下笔敏感细致,醉心于人性之美,并始终如一地抱有素朴情怀,充斥着湘西山民的热情与生命张力。他的作品,唯有沉心静气细细品读之后,方觉其山光水色,暗香深藏。
|
| 關於作者: |
沈从文(1902—1988)
湖南凤凰人,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无冕之王”,曾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满是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纯粹,同时又不乏对人生的思考。在那个充满焦虑甚至苦难的现实社会中,他笔下的世界给人们的心灵开辟了一方净土。代表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散文《湘行散记》《从文自传》等。
|
| 目錄:
|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遥夜
流光
街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湘行散记
沅陵的人
记蔡威廉女士
潜渊
生命
云南看云
水云
忆北平
怀昆明
一个传奇的本事
不毁灭的背影
天安门前
过节和观灯
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
| 內容試閱:
|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阴郁模样的从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用两只瘦而小的手撑住了下巴,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唉!无意义的人生,——可诅咒的人生”,伤心极了,两个陷了进去的眼孔内,热的泪只是朝外滚。
“再无办法,伙食可开不成了!”——二掌柜的话很使他难堪。但他并不以为二掌柜对于他是侮辱与无理,他知道一个开公寓的人,果像他自己这样住上了三个以上的客人,公寓中受的影响,是能够陷于关门的地位的。他只伤心自己的命运。
“我不能奋斗去生,未必连爽爽快快去结果了自己也不能吧?”一个不良的思绪时时抓着他心头。
生的欲望,似乎是一件美丽东西——也许是未来的美丽的梦,在他面前不住的晃来晃去,他已注了意。于是,他又握起笔来写他的信了。他意思是要在这最后一次决定他的命运。
A先生:
先生,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请原谅我!
一个人,无平白故,向别一个陌生人写出许多无味的话语,妨碍了别人正当事情;在有个时候,还得给人以心上的不愉快,我知道,这是一桩很不对的行为。不过,我为求生,除了这个似乎已无第二个途径了!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嫌依然写了这信。
先生对这事,若是懒于去理会,我觉得并不什么要紧!我希望能够像在夏天大雨中见到一个大水泡为第二个雨点破灭了一般不措意。
我很为难。因为我并不读过什么书,不知道要如何来述明我的为人以及对于先生的愿望。
我是一个失业人——不,我并不失业,我简直是无业人!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的流浪。
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法去做一次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我如今竟又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经验告我是如何不适于徒坐。我便想法去觅相当的工作,我到一些同乡们跟前去陈述我自己的愿望,我到各小工场去询问;我又各处照这个样子写了好多封信去表明我的愿望是如何低而易容。可是,总是失望了。生活她正同弃我而去的女人一样:无论我是如何设法去与她接近,到头终于失败。
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我怀疑:这是我方法的不适当。
人类的同情,是轮不到我头上了。但我并不怨人们给我的刻薄。我知道,在这个扰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一人负有什么应当必然的义务。
生活之绳,看着是要把我扼死了!我竟无法去解除。
我希望在先生面前充一个仆欧。我只要生!我不管如何生活方式都满意!我愿意用我手与脑终日劳作来换每日低限度的生活费。我愿……我请先生为我寻一生活法。
我以为:“能用笔写他心同情于不幸者的人,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小孩子,”这愚陋可笑的见解,增加了我持笔的勇气。
我住处是……倘若先生回复我这小小愿望时。
…………
愿先生康健!
…………
“伙计!——伙计!”他把信这样写就了,叫伙计付邮。
“什么?——有什么事?”在他喊了六七声以后,才听到一个懒惰的应声。从这声中,可以见到一点不理会的轻蔑与骄态。
他生出一点火气来了。但他知道这时发脾气的结果,于事情并不什么利益——简直是有害的;依然按纳着性子,和和气气的“来呀,有事!”
一个青脸庞——二掌柜兼伙计——气呼呼的钝猪一般立在他面前。他把刚写好的封套放了信逬去,“请你,发一下!……本京一分……三个子儿就得了!”
“没得邮花怎么发?……是的,虽然一分也不有!——你不看早上洋火夜里的油,是怎么来的。”
“……”
“一个大不有如何发?——那里借?”
“……”
“谁扯诳?——那无法……并不是。”
“那算了吧。”他实在不能再看二掌柜青色脸给怪样子他看了,打发了他出去。
这时,从窗子外面,送了一个小小冷笑声到他耳朵边来。
他,粗暴的,同疯狂一样:全身战栗,头失了知觉。从桌上取过信来,就势一撕,扯成两半。那两张信纸,轻轻的掉了下地,他并不去注意;只将两个半边信封,叠做一处;又是一撕,向字篓中尽力的掼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