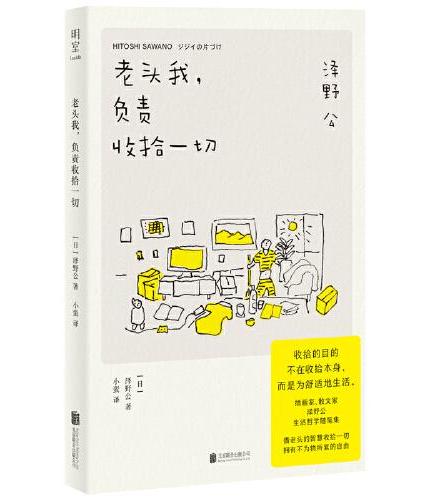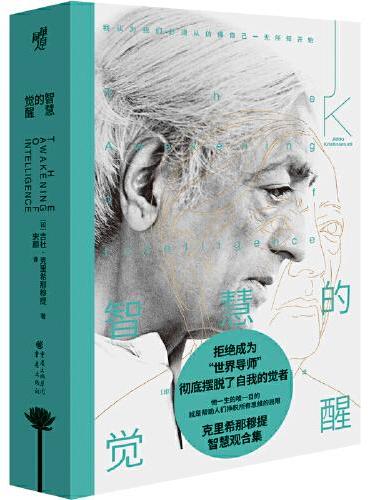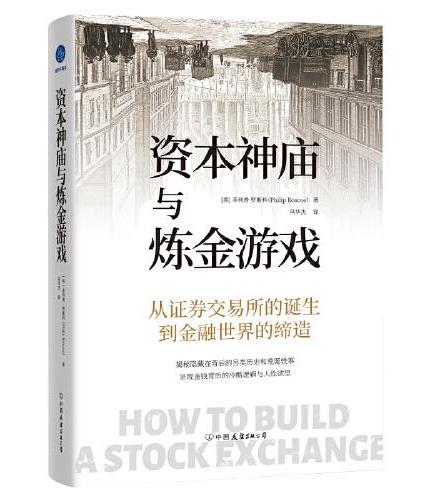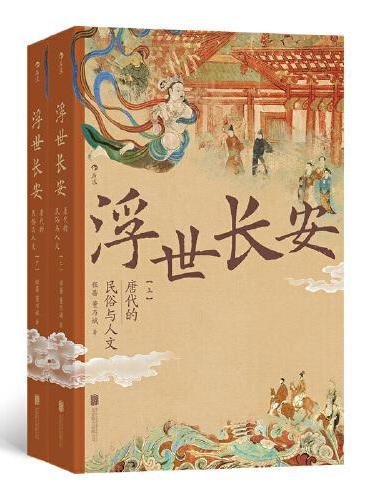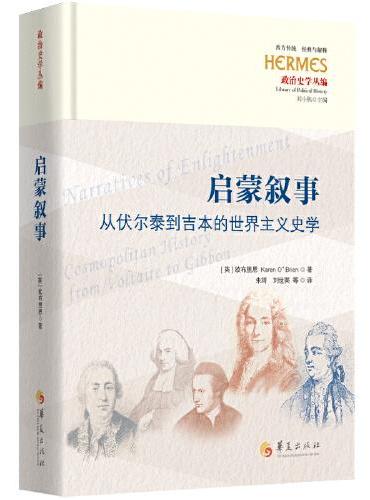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怪谈游戏设计师·泗水公寓
》
售價:HK$
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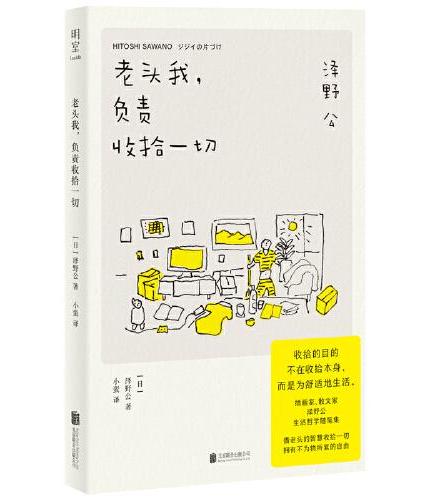
《
老头我,负责收拾一切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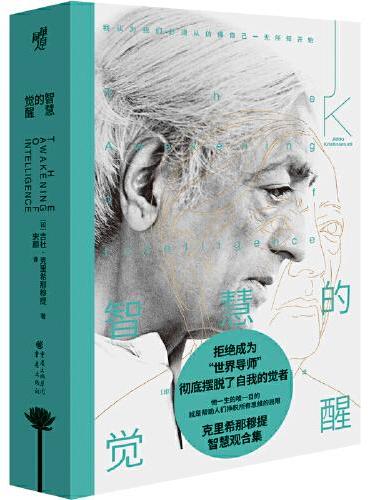
《
智慧的觉醒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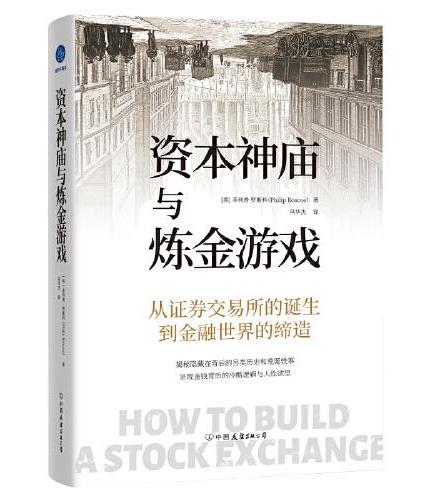
《
资本神庙与炼金游戏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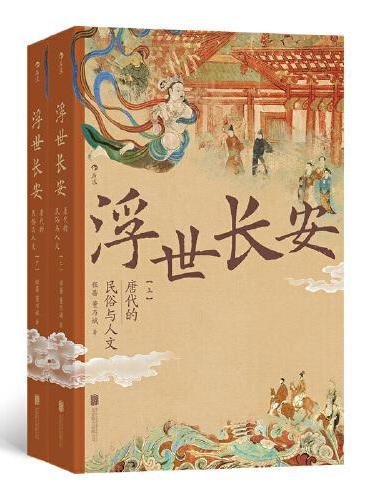
《
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
》
售價:HK$
140.8

《
怀忧终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
》
售價:HK$
53.9

《
生命合伙人Ⅲ:AI时代艺术思维引爆创造力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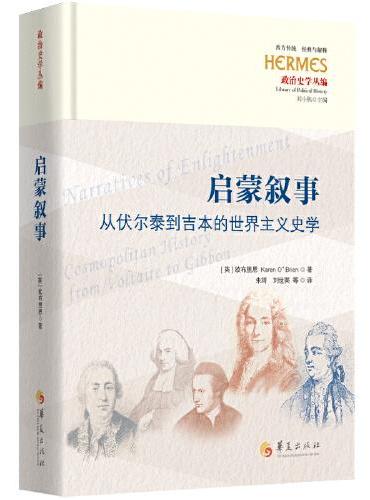
《
启蒙叙事: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
以经典文本阐释为中心,以作家与现象研究为补充,以小见大地建构起关于1949年以来汉语小说的知识谱系和学思理路。
|
| 內容簡介: |
|
作者将手稿、版本、语言、作家论、原典、文本细读等若干关键词,作为一种观照视角、介入方式、研究方法,构成把握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历程及其得失的方法论体系;坚持文献史料与论点的彼此互证、问题发现与阐释的同场生成等原则从事小说研究,并由此展开对中国当代小说重要思潮、现象、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
|
| 關於作者: |
|
张元珂,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传记文学》编辑、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理事、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有《韩东论》、《中国新文学版本研究》,主编《现代作家研究》(共八卷)。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课题、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各一项。
|
| 目錄:
|
编 语言论
讲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问题/003
第二讲 新时期小说元语言论/028
第三讲 新生代小说语言的发生、演进与意义/041
第四讲 图像化、古典化、身体化
——关于新生代小说家语言实践的三种趋向/055
第五讲 中国当代小说引语类型与实践/069
第六讲 新生代小说长句建构的内生逻辑及美学特质/080
第二编 修辞论
第七讲 新生代小说家的元叙述实践/091
第八讲 讲述、展示、综合:新生代小说家的语式实践/103
第九讲 作为小说微观修辞的拼贴/118
第十讲 作为微观修辞的戏仿/130
第三编 小说家论
第十一讲 偏执、耽奇、模式化:阎连科小说论/145
第十二讲 小说艺术家与小说艺术化:韩东论/159
第十三讲 省察人间问苍茫:夏立君论/169
第十四讲 “文学深圳”的建构者:吴君论/189
第十五讲 反类型的青春写作:双雪涛论/203
第十六讲 为“西北藏边”作志:江洋才让论/213
第四编 原典重读
第十七讲 何谓“原典”,怎样“精读”
——中国当代文学原典精读实践情况考察与思考/227
第十八讲 乌兰巴干《草原烽火》的茅盾眉批本及面世价值/241
第十九讲 经典重读:《红日》与《青春之歌》(茅盾眉批本)/265
第二十讲 毕汝谐手抄本《九级浪》发掘与研究/275
第二十一讲 六长篇合论/289
第二十二讲 滕贞甫的《战国红》的小说格调及其示范意义/322
第二十三讲 参与经典化:1990年以来短篇小说精选精读/332
第二十四讲 参与经典化:1990年以来中篇小说精选精读/361
第二十五讲 鲁味小说、传奇体与民间志
——关于尚启元长篇小说的文体实践/375
第五编 现象论
第二十六讲 中共党员在小说名著中的创生、形塑与流变/383
第二十七讲 “红色经典”文本修改中的非作者因素/392
第二十八讲 问题与方法: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若干思考/404
附录
“作品是文学研究核心的要素”
——张元珂访谈/412
主要参考著作/417
|
| 內容試閱:
|
编 语言论
讲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全面推广开的“普通话”,以及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的“毛文体”、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俗潮,不仅决定着或深刻影响着小说家文学观、语言观的生成、演变,也从外到内一次次根本性地改变着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质地、样态、风格。告别工农兵话语、样板戏之后,当代小说语言有六大景观尤其引人瞩目:汪曾祺的古典化、先锋小说家的欧化、寻根小说家的俗野化、新写实小说家的写实化、新生代小说家的肉身化、网络小说家的媒介化。如果说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文化心理分析语言,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上的三大主导形态,那么,以这“六化”为中心和标志,分别上下拓展、纵横勾连,即形成了中国当代小说语言史的基本样貌。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全面、加速推进,文化、文学领域也迎来为中国历史所少见的自由时代,这一切表征于小说创作中,首先就是对小说语言的大解放、大融合。然而,普通话是一种被规范、删减、加工过的由官方指定的通用语,它精致、准确、逻辑性强,但作为小说语言,也有诸多力有不逮之处,比如,若表现“人的神理”(胡适),展现“地域的神味”(刘半农),凸显“语气的神韵”(张爱玲),它不能,也无法替代方言。打破普通话写作大一统局面,或弥补这种语言表现力的缺陷,再次让方言进入小说,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小说语言的再革命,就成了90年代后小说家所必然要努力追寻的实践向度。方言进入小说,从理念到实践,都给中国当代小说观念、文体带来全新可能。
一 方言理念与实践:从边缘到中心
方言是每个人的母语。方言是一种自带性格、自生意蕴、自有美感的地方语言,因而在文学语言中有普通话所无法替代的美学特质、表现功能。方言进入现代小说语言系统,自然备受瞩目。因运用方言并在小说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者,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鲁迅对绍兴方言词汇的采纳,赵树理对晋东南方言语汇的加工,周立波对湖南方言和东北方言的改造,柳青和路遥对陕北方言的大量运用,沙汀和李劼人对川北方言的原生态化移植,李锐、莫言、张炜和阎连科对各自生活区域内的方言土语的采纳,韩少功在《爸爸爸》和《马桥词典》中对方言世界的复活……然而,在百年新文学史上,方言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他者身份被谨慎纳入现代语言中来的。从外部诱因来看,启蒙与革命、民族与国家、阶级与政党,作为一种统一性的有形或无形的支配力量,往往决定着方言是复活还是沉寂的命运。这决定了方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处地位的尴尬和无奈。
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上,方言进入小说并不是自然、自主的,而总是被动的、受压制的。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度关联,特别是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互动,都使得小说家在对待方言时的心态是复杂而暧昧的。那种无可化约的亲和力和被迫舍弃的无奈感,常常在其意识深处并行并存。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生成、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关联,发展到“十七年”时期,更是形成了另一种暧昧、纠缠和离舍。
一方面,老舍、茅盾、周立波、赵树理等从民国步入“新中国”的小说家大都认识到方言的独特魅力和在小说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茅盾说:“我们可以用方言,问题是在怎样用……大凡人物的对话用了方言,可以使人物的面貌更为生动,做到‘如闻其声’。”周立波说:“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地大量地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地大量地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更不会有什么‘发展’。”他这种观点和老舍在40年代的看法如出一辙:“我要恢复我的北平话。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怕别人不懂吗?加注解呀。无论怎么说,地方语言运用得好,总比勉强地用四不像的、毫无精力的、普通官话强得多。”这可说明,关于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优长,以及与小说所结成的互荣关系,在大部分新文学名家看来,已是无须再作论证的命题。在从“现代”向“当代”转型之际,以周立波、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基于地方生活和文学语言特质所得出的观点,就为进入“新中国”的小说家们能否用、怎样用方言土语指明了方向。但是,方言进入小说,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主张禁用或慎用方言者也似乎理由充分、确凿:“‘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不应该使用方言土语来创作的,而应该使用民族共同语来创作。”他们的理由大体可概括为:一、民族共同语需要作家建设并服从,方言不可喧宾夺主。二、方言自身有诸多弊端。比如使用面窄、不好懂、妨碍共同语建设等等。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条。
另一方面,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作为民族通用语的普通话逐渐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隐含等级秩序的“官话”。在此背景下,包括茅盾、老舍、赵树理在内的众多新文学名家不得不转向,至少方言土语已被置于慎用、少用或者不用之列。在此后几十年间,这种秩序愈发坚固,难以撼动。为何出现这种局面?因为普通话规范的制定及其在全国的推广,首先对小说名家提出要求——不但在创作中慎用或不用,而且已出版著作若涉及方言或口语中过于粗鄙化的语词,需按照普通话规范予以删改。所谓“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自然首先要求诸如周立波、老舍、叶圣陶这类新文学名家起模范带头作用。虽然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取缔或消灭方言,但限制或约束方言运用,以打破人与人之间在交流上的隔阂,继而辅助于现代民族国家大一统进程,则是一以贯之的举措。
新时期小说主潮是以欧美为师、以译著为本逐渐生发而来的,表现在小说语言和语法上,“欧陆风”造就的翻译腔及其话语权,又对小说家的方言探索与实践造成另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制。李锐说:“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书面语,它已经成为一种等级化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等的语言,而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在书面语里头,欧化的翻译腔被认为是新的、潮的、先锋的。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用任何一种方言来写小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土得掉渣。”在新时期文学现场,从作为一种语言资源的方言,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泛方言小说”,除在“寻根小说”中一度得到有效展开外,在其他小说主潮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翻译腔”与普通话的双重压制下,方言更是不被看好。即使在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作家的寻根小说中,方言和方言世界一度被置于主体位置,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依然不过是一种借此追溯精神之源、寻觅文化之根的工具。方言及方言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它们能摆脱一切桎梏独自显示自身存在吗?如今看来,20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中的方言及其世界,依然被置入沉重的现代理念中,并在简单的落后与先进、文明与愚昧的对比中,升华为反思、审视、重铸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主观想象和实践。方言在寻根小说中的出场、表现,本身就是现代性烛照、比衬的结果。它的出场短暂而匆忙,仿佛夜空中的彗星一闪而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