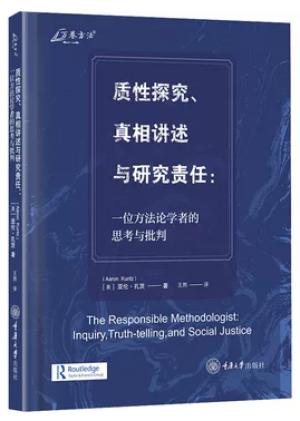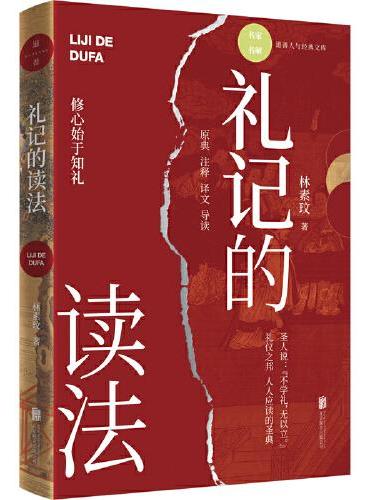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穿着哲学逛街去:时尚现象学
》
售價:HK$
75.9

《
体重管理师培训体系
》
售價:HK$
85.8

《
财之道丛书·未来战争:硅谷与五角大楼的科技革命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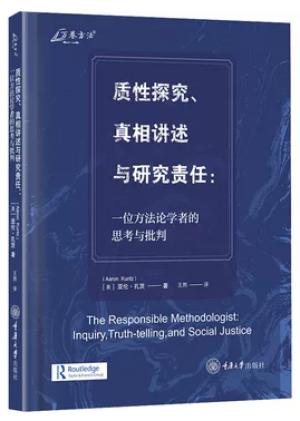
《
质性探究、真相讲述与研究责任:一位方法论学者的思考与批判
》
售價:HK$
49.5

《
从文化史到社会史:战后历史学家的思想轨迹
》
售價:HK$
107.8

《
问对问题赢学习:DeepSeek中小学生使用攻略
》
售價:HK$
65.8

《
目标感:小成果驱动下的价值交付
》
售價:HK$
1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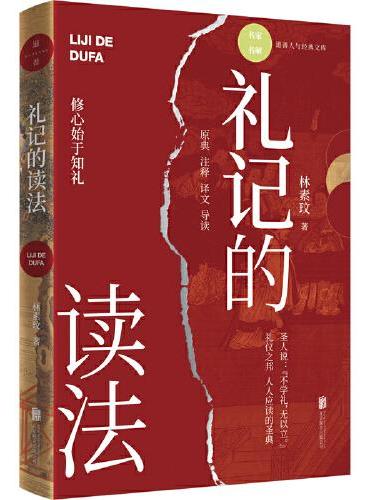
《
礼记的读法
》
售價:HK$
82.5
|
| 編輯推薦: |
“年轻的流亡者,在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了激情与魅力。”
1.不一样的主人公:马丁·埃德尔韦斯
不是纳博科夫式的天才,而是
一个和自我身份疏离的青年,
一个对政治情绪无动于衷的观看者,
一个在社群中出入自由的孤独影像,
一个被激情燃烧直至死亡的干净而纯粹的冒险者。
2.不一样的荣耀:无益无用
不是建功立业,亦非青史留名,
而是一种只为实现个人愿望的
“英勇之举”,“高尚光荣”却“无益无用”,
是彰显个人勇气的荣耀,也是光辉灿烂的殉道者的荣耀。
3.神在纳博科夫式的细节与联觉中
流亡者马丁就像一个氛围驾驶员和影像大师,所到之处氛围感拉满,画面感立现。他将我们带入瑞士绝美的秋天,让我们低头便看见“车辙蒙上了云母色的薄冰”;或者英国剑桥的公共休息室,抬头便望到“满头火焰的女巫从烟囱中蹿向星空”。那些原本转瞬即逝的环境、色彩、声音、心理,被定格在了一帧帧的细节中,被赋予了一种无可挑剔、繁复而迷乱的精确性。
4.著名翻译家石国雄老师由俄语译出,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韵味与美感
与纳博科夫后期的“烧脑神作”相比,《荣耀》情节流畅而富于诗意,是
|
| 內容簡介: |
|
《荣耀》是二十世纪公认的小说大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早期的俄语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为实现儿时梦想,不顾世俗眼光,毅然奔赴险境的故事。主人公马丁本是一个追求浪漫、漫无目的的俄国青年,因俄国革命举家逃离故土。他的亲英派母亲将他送到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在那里,马丁寄宿在一户俄侨家,身心很快被他们家的女儿索尼娅占据。然而,索尼娅性情多变、妖冶轻佻,让马丁可望而不可即。爱而不得的马丁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就会变成索尼娅的影子,将在柏林的人行道上遛来遛去,直至生命的尽头,把他心中日益成熟、重要而庄严的东西白白浪费在感情上。于是,马丁决定离开柏林,在清除旧念的孤独中思考探险计划。那是他儿时的梦想,是他一直想去探索的未知,是童年床头画作中那条密径通往的尽头。凭借一颗殉道者之心,和喷涌战栗、难以抵抗的流浪者的激情,马丁踏上了独属于他的孤勇之旅,谱写他一个人的讣告,直到生命尽头。
|
| 關於作者: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
| 內容試閱:
|
……一九三○年五月,在写完《眼睛》之后,我立即开始着手创作《荣耀》,年底便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孩子,我们在柏林西部卢伊特波尔德大街上一座庞大阴暗的公寓里租了一间客厅和卧室。那公寓是独腿将军冯? 巴德莱本先生的住所,他上了年纪,能做的事便是专心修订家谱。他那宽大的前额有几分纳博科夫家族的特征,事实上,他与著名国际象棋手巴德莱本确实有点血缘关系,后者像我笔下的卢仁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夏的某一天,《当代纪事》的主编伊利亚? 丰达明斯基从巴黎来,要买下我那还处在“生根阶段”(好比是收获之前的庄稼地)的书稿。他是个社会革命党人、犹太人、热情的基督徒和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总之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后来德国人在一座死亡集中营里杀害了他)。交易谈妥后,他兴奋地拍着大腿,从我家暗绿色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画面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本书曾经有过一个相当迷人的书名《浪漫年代》(后来弃之不用是因为我倾心于更精练的词“荣耀”,它意指“英勇的壮举”、“高尚的行动”),我原本想选这个名字,部分原因是我受够了西方记者把当今时代称作“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或诸如此类的呼声,但主要还是出于我写这部小说的意图。这是我一部带有意图的小说,着重揭示了我那年轻的流亡者在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的激情与魅力。
如果由我自己来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那么某些类型的评论家就会无事可做了(特别是其中那些狭隘无知的家伙,我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影响,也许竟会有人以为是我在幕后用催眠术害得他们做出一些无礼举动)。毋庸置疑,在这部小说近乎沦落为虚假的异国情调作品或平淡无奇的生活喜剧后,它提升到了一种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艺术境地,这种文学高度只有在我很久以后写成的《爱达》中才会再次达到。
那些想在书中寻找人道主义内容的人也许会问:《荣耀》的主人公与我其他十四部小说(包括用俄语和英语写的作品)的主人公们有什么联系?
马丁是我笔下所有年轻男性中善良动人的形象,而暗眸无神、黑发粗糙的小索尼娅(从名字来判断,她的父亲带有切列米斯人的血统),任何精通爱情游戏和情场规则的人都会认为,虽然她无疑是个喜怒无常、冷酷无情、卖弄风骚的女人,但她是我笔下所有年轻女性中为异乎寻常地迷人的形象。
如果说马丁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认作是我的远亲(他更讨人喜欢,但也比我幼稚得多),我与他在童年记忆和长大后的个人好恶方面存在某些共同点的话,那么他那对平庸的父母则恰好相反,从任何理性角度看都不像我的双亲。至于马丁在剑桥大学的朋友们—达尔文从头到脚都是虚构的,穆恩也是一样,而“瓦季姆”和“特迪”在我过去读剑桥时确有其人,他们以N. R. 和R. C. 的姓名缩写形式出现在我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一九六六)第十三章的倒数第二段里。济拉诺夫、伊戈列维奇和格鲁济诺夫,他们属于这样一类人—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极左的旧派恐怖主义分子和极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之间,一方面远离君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同样远离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连载《荣耀》的那本杂志的追随者中,我与这类人多有接触,但上述三位都不是以某个真实具体的人物来描摹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本书中为这种政治形态作出适当的描述(对俄罗斯的流亡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俄语作品的主要读者而言,由于他们熟悉这种政治理念,对它有着像对常识那样下意识般的精确感,所以他们马上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有一点事实我仍然无法接受:美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一直以来完全忽视了在俄国侨民中存在着的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九四○年,在纽约,当我说我既不支持苏维埃也不支持君主制时,一位眼光特别狭隘的左翼作家兴致勃勃地问:“这么说,您是个托派分子喽?”)。这一点真值得我每年用放烟火般接连不断的蔑视和讽刺去揭露它,以示庆祝纪念。
然而,《荣耀》的主人公马丁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塑造马丁的魔法师手上的两套主要法宝之一。马丁的命运赋格曲的主题就是实现愿望。他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人,是人中的珍品。但是,实现愿望的过程本身必然贯穿着强烈的怀乡情结。对童年幻想的追忆与对死亡的预期结合在了一起。马丁后去禁地佐尔兰德(与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虚构的国度赞巴拉毫无关系!)时所走的那条危险小径,就是在儿童房墙上的水彩画里那条蜿蜒曲折、带有童话色彩的林间小径的延续,通往一个没有意义的终点。或许,“如愿以偿”这个标题对于本书会更为理想:纳博科夫不可能没注意到,俄语“英勇行为”一词在英语里往往被译成“功绩”,而编纂者在图书目录中采用的正是后者;但是,一旦从中觉察出动词“利用”的含义,那么俄语“英勇行为”的隐含意义—虽然这种行为很高尚很光荣,却无益无用—就立即消失了。因此作者选了“荣耀”作为英语书名,与原俄语书名相比,它离字面意义更远,更间接,却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俄语书名的隐含意义及其在骄阳下伸展开的所有纷繁复杂的自然联想。这就是崇高事业和无私成就的荣耀,是尘世间的荣耀和不完美的世间天堂的荣耀,是彰显个人勇气的荣耀,也是光辉灿烂的殉道者的荣耀。
如今,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已经备受质疑,作者吹着惊讶的口哨回忆起,在尚不遥远的过去,比方说,在一九五九年前(也就是作者为他的英语小说写的七篇前言中的篇问世之前),大家都以为父母离异必然会导致孩子的人格产生分裂。马丁父母的分居对马丁的心灵绝没有这样的影响,把马丁闯回祖国和他的父亲早逝扯在一起,这种做法只有对一个在噩梦般的考试中绝望挣扎的笨蛋来说才算可以原谅。而满腹空欢喜地指出马丁爱上的姑娘和他的母亲有着同一个名字,这同样是十分轻率的。
我的第二套法宝就是:我虽慷慨地赐予了马丁许多天赋,却有意没把才华加进去。要把他塑造成画家或作家,那太容易了。要让他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同时又赐予他通常是从事创作的人才会有的敏锐感官知觉,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不让他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为了逃离现实(只是在不太喧闹的楼层上有一间打扫得较为干净的陋室罢了),而是为了缓解生存的难受感—那又是多么残酷!建立自己小小的、却又光芒万丈的功绩的诱惑占了上风。结果使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设计的一道象棋谜题,它的美妙之处在于自相矛盾的步:白后有四个棋格可走,但在其中每个格子上,对处于四种死局中的一匹白马而言,白后都成了障碍(这么厉害的棋子—却是个“障碍”!)。换句话说,白后成了完全无益的障碍,成了棋盘上的多余棋子,在接下来的棋局中不起任何作用,它不得不自我流放到一个中立的角落里去,待在一个行动迟缓的小卒后面,停在那里不动,无所事事,默默无闻。要想出解决这道难题的一步棋是异常困难的。《荣耀》也是这样。
作者相信,睿智的读者不会热衷于去翻阅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以寻找相同的素材或相似的背景。《荣耀》的趣味在于别的地方,它创造出推动情节的幻象,需要读者从细小事件的彼此呼应和相互联系中,从小说前后的跳跃切换中去搜寻:一个时隔久远的白日梦直接化作抱在胸前的足球带来的幸福,或是书中偶尔出现的场景—马丁母亲在小说勾勒的时间框架外伤心哀恸,而读者只能去猜测这一抽象的未来,甚至在他已经快速翻阅过后七章,看到情节沿着疯狂的曲折轨迹向后发展,所有人物在暴风骤雨般的尾声中粉墨登场,使故事达到高潮之后,终恰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一个潮湿晦暗的日子里,一只鸟儿停在栅门上而已。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七○年十二月八日于蒙特勒
十三
在初留下的剑桥印象背后,不知为什么,让马丁难忘的始终是那个在瑞士刚刚见过的绝美秋天。每逢早晨,柔和的薄雾便遮蔽了阿尔卑斯山。一串残败的花楸果躺在路中央,车辙蒙上了云母色的薄冰。尽管没有风,白桦那鲜黄色的树叶却一天天变得稀少,青色的天空透过树叶沉静而愉快地望着大地。茂盛的蕨类植物呈现出红褐色。纤细的蛛丝在空气中四下飘浮,闪着彩虹般的微光,亨利叔叔把它们称作“圣母的发丝”。有时候马丁会抬起头,以为自己远远听到了迁徙中的鹤发出的唳鸣声,却连一只鹤也没看见。他曾经四下溜达过很多地方,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他骑着一个干粗活的人的破自行车,在沙沙响的小径上穿行,而他的母亲坐在枫树下的条椅上沉思着,一边用手杖尖刺穿褐色土地上潮湿的深红色树叶。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始美景在英国并不存在,英国的大自然好像是在温室里培育出来的,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秋天就这样在几何形的花园里、在细雨蒙蒙的天空下缓缓逝去。但是那些红灰色的墙,在一个难得的晴朗早晨覆满银色白霜的长方形草坪,细细的河流,与倒影合成一个正圆的拱形小石桥—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美。
无论是恶劣的天气,还是卧室里的严寒(学校传统禁止在卧室里生火取暖),都不能改变马丁沉思冥想、充满生活乐趣的精神。自己的小客厅,热烘烘的壁炉,蒙着灰尘的自动钢琴,挂在墙上无伤大雅的石版画,低矮的藤编扶手椅,摆在架子上的廉价瓷器摆设—所有这一
切马丁都由衷地喜爱。深夜里,壁炉中那神圣的火焰奄奄欲熄,他便用火钳将还在阴燃的小火炭扒在一起,放上一些木屑,然后在上面堆起高高的煤块,用风箱“呼呼”地吹火。为了让烟囱通风,他还展开一张宽大的《泰晤士报》挡在炉边。绷紧的报纸开始发热,变得透明起来,正面的字行与反面透过去看得见的字行混在一起,好像是某种晦涩语言的奇怪符号。接着,火猛烈燃烧,发出轰响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红褐色的斑点,渐渐变黑,突然变成了窟窿,整张报纸燃烧了起来。它被风一下子吸进了烟囱,朝上飞去。深夜晚归的路人,穿着礼服的教师,他们透过哥特式暗夜的黑幕可以看见一个满头火焰的女巫从烟囱中蹿向星空。第二天马丁得去交罚款。
马丁天生具有活泼、善交际的秉性,所以他并没有孤独太久。很快他就与住在楼下的达尔文成了朋友,在足球场、俱乐部和公共食堂也结识了一些人。他发现,所有人都认为应该与他谈俄罗斯,应该弄清楚他对革命、武装干涉、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怎么想的,而有些到过俄
罗斯的人则夸赞俄罗斯人的好客,还问他是否碰巧认识莫斯科的某位伊万诺夫先生。马丁厌恶这样的谈话,他从桌上随手拿起一卷普希金的书,开始大声朗诵阿奇博尔德? 穆恩翻译的《秋之韵》:
哦,忧伤的季节,眼睛的陶醉!
我喜欢你那道别的美丽!
我爱大自然豪华的凋零,
森林换上金色和紫色的外衣。
这一举动让周围的人惊诧不已,只有达尔文这个身材魁梧、睡意蒙眬的英国人独自赞许地点着头,他穿着亮黄色的短上衣,摊开手脚坐在扶手椅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嘴里的烟斗发出呼哧声。这个达尔文经常在晚饭后拜访马丁。他向马丁详细地说明了一些历来就有的严格规矩:无论有多冷,大学生上街不应该戴礼帽和穿大衣;对任何熟人,无论是握手问好还是祝早安都不行,即使他是原子大佬汤姆孙②本人,也应该以开朗的微笑和轻快的感叹词来致意;
乘普通的划艇泛舟河上可不好,为此得坐方头平底船和独木舟才行;永远不要重复大学里那些立即就能让新生着迷的老俏皮话。“但是要记住,”达尔文精明地补充说,“遵守这些传统不应该走得太远,有时候为了吓唬一下那些势利小人,上街时不妨戴圆顶礼帽,腋下夹一把
伞,这也是可以的。”马丁有一种感觉: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已经待了很长时间,有好几年了,他是在怜惜他,就像怜惜任何一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一样。他那种懒洋洋的神态、慢腾腾的动作和舒适惬意的样子令马丁惊诧。为了激起对方的忌妒心,马丁冲动地讲述了自己的漫游经历,他下意识地在贝丝身上添油加醋,说了她许多好话,却对这些虚构情节与事实交错混杂的过程浑然不觉。诚然,这些夸大其词是单纯无害的:在克里米亚高原上的两三次野餐变成了他拄着木棍、背着行囊在大草原上的日常漫游;阿拉? 切尔诺斯维托夫变成了一位巡游途中的神秘旅伴,在游艇上陪着他,他们俩的散步变成了在希腊一座岛屿上的长久逗留,而西西里岛的紫色轮廓则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花园和别墅。达尔文望着天花板,赞许地点着头。他的眼睛呈淡蓝色,空虚木然,毫无情感。他喜欢半躺着把双脚舒舒服服地高高搁起,所以总能让人看到结实的鞋底,上面有复杂的橡胶纹路。他身上的一切—从这双脚到他那瘦削的鼻子—全都品质优良,硕大无朋,透出沉着与冷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