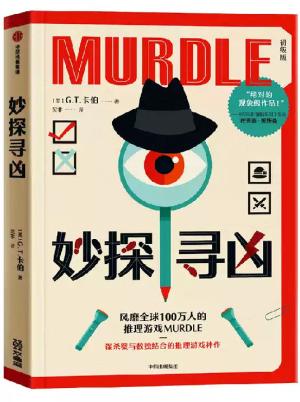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并购手册:整合组织,执行战略和推动新增长的实用指南 乔治·布拉特,杰弗里·普里切特
》
售價:HK$
141.9

《
大学问·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
》
售價:HK$
107.8

《
制度与轮回:从商周至明清的历史运行
》
售價:HK$
64.9

《
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增订本〕
》
售價:HK$
85.8

《
奥斯曼帝国衰亡史:1683—1923
》
售價:HK$
151.8

《
构建和平:缔造欧洲解决方案,1945—1963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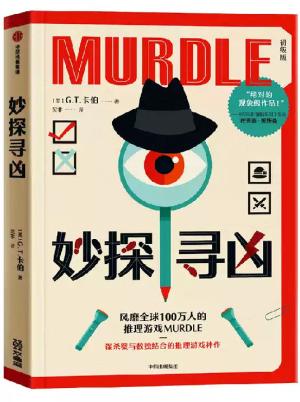
《
妙探寻凶
》
售價:HK$
63.8

《
清代皇宫图鉴(全三册)清宫廷史专家写给大众的皇家生活百科全书
》
售價:HK$
260.7
|
| 編輯推薦: |
|
扎米亚京的一生堪称传奇,他的成就不仅限于在文学领域创作了《我们》这部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的传世之作,同时他还是当时苏联最杰出的船舶制造工程师之一。也许正是因为长期的理科思维使扎米亚京的作品独树一帜,也使得《我们》成为文学史上划分时代的浓重一笔。如今《我们》已经受到了种种赞誉,但是仅此一部作品仍然不足以展现扎米亚京的伟大,或者说扎米亚京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背后的思想和思考方式,时至今日,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
| 內容簡介: |
本书为扎米亚京的小说作品集,包含作家最著名的传世之作《我们》,以及三个早期作品:《僻县》《岛民》《捕人者》。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僻县》是最早为扎米亚京赢得声誉的作品,其中描述的“无视道德而又贪得无厌的动物本性”的形象至今为人称道。《岛民》和《捕人者》两篇小说创作于作家旅居英国的最后两年,因此这两篇小说也极具“英国腔调”。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就像在《僻县》中批判俄罗斯毫无生机的生活那样,无情地鞭笞了所谓西方文明里世界机械式无意义的生活。这几部作品也为后来《我们》的创作打下了根基。《我们》作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为人们所熟知,但是除了反乌托邦元素,小说中还鲜明地论述和剖析了主人公的冒险精神,心理与哲学、爱情与工业也同样是小说的架构性主题。与其说乌托邦或反乌托邦题材的特色催生了扎米亚京的想象力,不如说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作者本人力求摆脱现实引力的结果,也是他又一次检验各种思想正确性的大型艺术化实验。与其说未来世界的法则和科技发展的预期辉煌成就是读者的兴趣点,不如说主人公因心态失衡而造成的矛盾冲突才真正直击人心。也正因如此,这些创作距今已经超过百年的小说,不仅在今天依然毫不过时,甚至为人们带来了更多有益的启示。
|
| 關於作者: |
|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文学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也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不仅文学造诣极高,同时也是苏联早期最优秀的船舶制造工程师之一。因曾在英国学习、生活多年,扎米亚京精通英语,为人极为绅士,早年的作品也颇具“英国腔调”。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作家便多次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在“十月革命”之后,作家没有改变支持革命的初衷,但是对过于严苛的审查制度表示不满,因此引起了当局的排斥。之后他的作品开始遭到封禁,最终作家本人也被迫移居巴黎,并在巴黎渡过余生,但终其一生都保留苏联国籍。作家的传世之作《我们》最初于1924年在英国出版,但直到1988年这部作品才正式在作家的祖国与读者见面,《我们》也被认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扎米亚京以“著名反乌托邦主义作家”闻名于世,但是实际上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是公认的语言大师,更是继承了兼顾思想与文学性的伟大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经典文学大师。
|
| 目錄:
|
目录
我们001
僻县245
岛民343
捕人者425
译后记457
|
| 內容試閱:
|
译后记:
矛盾交织的一生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于1884年出生于坦波夫州(现名利佩茨克州)一个名为列别姜的小县城(据188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列别姜当时的常住居民为6678人)。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娘家姓普拉东诺娃)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古典文学,弹得一手好钢琴。父亲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扎米亚京是一位神甫。扎米亚京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写道:
“你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孤单的小男孩,肚子趴在沙发上,没有同龄的玩伴,一个人埋头读着书。有时候他会躲在钢琴底下,而妈妈则在演奏肖邦。小县城就是这样——家家户户的窗口都摆着天竺葵,马路当中的木桩上拴着一只小猪仔,几只母鸡在尘土中抖着羽毛。……列别姜曾是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笔下最有俄国特色的地方,也极具坦波夫地方特色……四岁时就已经读过果戈理……书籍就是我的童年玩伴。”扎米亚京全身心地热爱故土的风光,痴迷地留恋列别姜“坚不可摧”的俄语方言,怀念热闹喧哗的马市。这些少年时期的记忆,和作家对俄罗斯积重难返的落后与因循守旧的批判态度一样,都是伴随他一生的灵魂烙印。也许自小熟读经典名著的人,都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出鲜明的个性。更或许扎米亚京青年时期经历过太多战乱,所以离经叛道的精神几乎深入他的每一部作品,构筑起世界文学史上一道绕不开的风景。
1893年到1896年,扎米亚京进入列别姜本地一所普通中学,可很快便转学至沃罗涅日[ 俄罗斯地名。]的中学继续学业,直至190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后来,他曾将这枚金质奖章典当,却终其一生未能赎回。典当的金额在当时还是一笔比较可观的数目,足有25卢布。中学毕业后的扎米亚京决定报考圣彼得堡工业学院舰船系。他在自传中解释说:
“在中学里,我的写作成绩一向优异傲人,可数学却并不总是那么尽如人意。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了(我够执着吧)最需要数学的专业——圣彼得堡工业学院舰船系。”
大学求学期间,暑期实习为扎米亚京创造了周游各地的机会。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未来的作家也借此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创作素材。1905年,他在敖德萨亲眼见证了“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当时的见闻后来被他写进短篇小说《三日》(1913)。回到彼得堡后,扎米亚京便投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中,并因此遭到逮捕,在单人牢房里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可高墙内的扎米亚京反而高效率地利用了时间,他不但开始自学英语,还写作了一些诗歌。出狱后,他被流放回列别姜,但年轻的他却找到机会偷偷潜回了圣彼得堡。之后,扎米亚京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自愿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1905—1910),参加了维堡区[ 俄罗斯地名。]战斗兵团,并积极参与革命青年大学生组织的活动。在圣彼得堡工业学院毕业后,他获得了船舶建造工程师的学位,继而在舰船建筑学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在专业技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多年以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此评价自己的成就:“六册散文,六部剧本,六艘破冰船。”
扎米亚京始终认为自己的职业属于“异端”。而在1917年以前,大概只有支持布尔什维克,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异端者”。作为舰船建造工程师,他的才华被广泛认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多次被逮捕,也不止一次被驱逐出圣彼得堡,发配回原籍列别姜。也正是那个时期,他遇到了自己后来的人生伴侣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乌索娃(1883—1965)。妻子几乎比他多活了三十年,死后与他同葬。
1908年的毕业前夕,扎米亚京初次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一个》得以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女孩》两年后才完稿。而真正使扎米亚京名声大噪的是1913年发表在圣彼得堡《训诫》杂志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僻县》,创作于流放拉赫塔[ 俄罗斯地名。]时期。作家在小说中不无心痛地抨击了俄罗斯乡镇冷血而又冥顽不化的兽性,犀利地揭示了这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痼疾”,也向世人展示了痼疾背后的阴暗王国。《僻县》不仅为扎米亚京赢得了声誉,也使他成了同行们口中的语言大师。小说主人公巴雷巴(这个名字对俄罗斯人来说,多少有些奇怪。来源于俄语单词барыга,意为“投机商”“二道贩子”,具有强烈的贬义)也因此而成为“无视道德而又贪得无厌的动物本性”的形象化身。虽然扎米亚京后来远离了偏僻的乡村,投身于更广阔的天地,足迹远涉圣彼得堡、伦敦和杰斯蒙德,但在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他依然会回首故土,以全新的目光再度审视自童年时就熟悉和热爱的俄罗斯文化。
小说发表后即引起了一些知名文学家和作家的重视,其中就包括高尔基。七年后,高尔基在评论扎米亚京时写道:“他一心想成为欧洲绅士那样的作家——优雅、尖锐、讽刺而又充满质疑,可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写出比《僻县》更好的作品。”苏联评论家、历史学家波隆斯基(1886—1932)这样评论扎米亚京:“……他对衣衫褴褛的人,对备受打压的人,甚至是野性难驯的人倒颇有善意,而且他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这种好感……”
1913年,扎米亚京写了中篇小说《穷乡僻壤》。小说讲述了一座位于远东地区小军营的内部生活,而主人公的命运其实不仅仅是服役于“穷乡僻壤”的军官与士兵的命运,也直指当时已然“穷途末路”的俄国国运。为此扎米亚京不但本人被诉诸法庭,被判流放凯姆[ 俄罗斯地名。],就连刊登了小说的那一期《训诫》杂志也受到牵连,被尽数没收。尽管如此,作为一名资深的专业工程师,扎米亚京依然能在俄罗斯各地服务于造船事业。
1916年,扎米亚京受命赴英国进行专业技术交流。在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南希尔兹等各地的造船厂,他参与建造了俄罗斯第一批破冰船。“十月革命”后,扎米亚京担任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破冰船的总设计师之一。旅英期间,扎米亚京由衷地惊叹于英国发达的科技和英国人深厚的文化修养。可说来也很离奇,这个国家似乎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特性,竟让作家时不时联想起俄罗斯偏远的乡村。也许,这种特性表现为对运动、自由和自然天性的恐惧。用扎米亚京的术语描述,就是缺乏“能量”。本质上来说,俄罗斯的痼疾和英国的缺乏能量,对扎米亚京而言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表现方式:固步自封、熵[ 根据热力学定理:越保守的体系,熵的值越大。](entropy)值高,最终都导致死气沉沉。
1917年,扎米亚京回到了圣彼得堡。作为一位享有盛名的语言大师,他不但在工业学院授课,还在“艺术之家”文学演播室为新生作家举办讲座,在赫尔岑教育学院开设“最新文学”课程。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并任职于艺术文学活动家联合会理事会、文学之家委员会。他与高尔基及其他几位著名作家一起,策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向新生代读者、苏维埃读者介绍“古今中外所有名著”。在《世界文学》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为赫伯特·威尔斯写过文章,后者的作品毫无疑问对他写作《我们》产生过影响。
然而作家骨子里离经叛道的精神却始终没有改变,历史乐观主义也从没在他的心中有过生根发芽的机会,他依然对可能破坏文明生活的种种观念抱着愤世嫉俗的质疑和鄙夷态度。“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扎米亚京延续果戈理的风格写作了《龙》(1918)、《洞穴》(1920)和《马迈》(1920)。不过,果戈理的风格似乎不光体现在他的作品里,甚至在生活中也留下了印迹。
圣彼得堡当时已更名为彼得格勒。也许,作为一个外地人,扎米亚京是最先敏锐体察到圣彼得堡魔幻般氛围的。当然,作家是通过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先辈们的传统透视棱镜观察圣彼得堡的。表面看,革命后的圣彼得堡依然如故,可是新生的彼得格勒却似乎已经走向另一个反面。扎米亚京的敏感不无道理,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83),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安娜·阿赫玛托娃(1899—1934),俄罗斯诗人、作家。]、康斯坦丁·瓦吉诺夫[ 康斯坦丁·瓦吉诺夫(1899—1934),俄罗斯诗人、作家。]等,均留下了关于那个时期彼得格勒的记述。在文学家们的眼里,彼得格勒已经变成了一座濒死的城市,是圣彼得堡“可怕一面”的倒映与放大。在短篇小说《马迈》和《洞穴》中,扎米亚京大胆地把军事共产主义比作了史前穴居时期的人类生活方式。短篇小说《龙》反应的也是圣彼得堡与彼得格勒之间的对立。圣彼得堡曾是一个精神世界,多元文化与美妙音乐的天堂,爱情与幸福的温床。而彼得格勒却已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想要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去,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到脚长出毛发来,长出锋利的獠牙,把身上所有的文化印记抹得一干二净。这个彼得大帝眼里的童话世界变成了丛林,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昔日的审美价值体系失去了意义。
然而在同行们眼里,扎米亚京显然过分美化了革命前的圣彼得堡,而只刻意批判革命初期出现的种种弊端。因此作家被毫不留情地归类为尚不稳固的年轻政权的敌人。其实扎米亚京的见解并不单一肤浅,《马迈》就讽刺了圣彼得堡旧时期的文人。扎米亚京的小说里,没有讴歌革命的雕章镂句,而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评议却随处可见,这也同样引起了同行们的反感。
1934年,根据作家本人的请求,斯大林亲自批准其加入苏联作家联合会。1935年,扎米亚京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反法西斯文化保护作家代表大会。可是扎米亚京本来就是个异端的人、一个不安分的反抗者、一个革命者。所以,无论是社会生活、政治、科学技术还是艺术领域出现任何形式的因循守旧,都会遭到他的抗争。君主专制根深蒂固时,他反抗君主专制;苏维埃体制在全国遍地开花时,他反抗体制的弊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苏维埃文学领域的代言人之一,他却是最积极的体制弊端的批判者,可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移民团体则把他看作薪火相传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作家本人而言,这些都还算不上矛盾。他曾说,他的一生都在与保守势力作斗争。用扎米亚京自己的术语来解释,保守势力即所谓的“熵”,不管是沙皇俄国、英国,还是在新生的苏维埃祖国,他都从未放弃过与“熵”的斗争。给斯大林的信中,扎米亚京称自己为“不合时宜”的作家。
如果说扎米亚京在有生之年不合政权的“时宜”,那倒也罢了。可作家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他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我们》,非但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其影响力竟越来越深远,直至他的悲观预言得以实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早已享誉欧洲的扎米亚京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起,终于回归了俄罗斯文学。而那个时候,读者深感兴趣的已经不是扎米亚京的写作技巧与文学成就,而是作家的思想深度。现在,当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都已成过眼云烟,所有的“时宜”都被历史的洪流涤荡殆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修辞大师,一位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家,一位传奇而又多舛的命运的“矛盾体验者”。
对极权社会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最终被作家艺术化地植入了科幻长篇小说《我们》中。小说最初的构思,是为了讽刺“苏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意识形态工作负责人口中的乌托邦社会。“苏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曾大力鼓吹将全世界改造并建设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社会,其建设和治理的主要原则便是“彻底消灭人类的灵魂与爱的情感”。
1921年长篇小说《我们》脱稿,对扎米亚京的同行非议也随即愈演愈烈。尽管《我们》在作家生前并没有被允许发表,可由于扎米亚京在很多公开场合朗读过《我们》的片段,所以听说过这部小说的人绝非少数。但更多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到小说的完整文本,而只能通过诽谤式的批评文章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说《我们》被先后翻译成捷克语、英语和法语。直至1988年,这部小说也只是在西方广为人知。
1930年,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РАПП)为代表的苏联文学界对扎米亚京的攻击达到了顶点。方方面面的打击下,几乎崩溃的扎米亚京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苏联国内已经不太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前途。于是,万般无奈的扎米亚京只好宣布退出作家联合会,并提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恳请移居海外。在信中,他简短明了地陈述了出国的理由:“对于作家而言,丧失写作的机会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而移居海外对作家而言,其实是一个万分痛苦的决定。最后,在高尔基帮助和运作下,扎米亚京于1932年顺利抵达了法国。
关于这段故事的始末,我们可以通过扎米亚京的一封信有所了解: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本人执笔写下此信之际,已被判处最高级别的惩罚,特此恳请您换一种惩罚的方式。
本人的名字想必您是知道的。作为一名作家,对我而言,丧失写作的机会即意味着被判处死刑。如今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再也无法继续工作。年复一年甚嚣尘上的恶意中伤,犹如无法逃脱的天罗地网,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创作都是难以想象的。
我绝非打算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饱受凌辱的无辜者。我知道,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里,我所写的作品里,的确有一些东西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理由。我知道,我有一个很讨人厌的习惯——总是不顾场合说些不合时宜的话,而且自认为说的都是实话。比如,我向来不会掩饰自己对文学上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和刻意粉饰的态度。我以前认为,现在依然固执已见地认为,这么做无异于玷污作家本人,也玷污了革命。当初,我正是因为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在《艺术之家》杂志,1920年第一期),以激烈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令许多人难堪,从而招致报刊杂志对我群起而攻之。从那时起,这种群体式攻击便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持续至今,最后发展到了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造物神话的地步。这就像以前,基督徒为了便于更形象化表现各种罪恶,就编造出一个魔鬼一样,评论界也把我打造成了苏联文学的魔鬼。而唾弃魔鬼,自然是一件善事,因此所有人都尽其所能地唾弃我。我每发表一部作品,就一定会有人想方设法从中挖掘出魔鬼式的构思。
……
苏联法典中,比死刑低一个级别的是强制迁居国外。如果我真的是个罪犯,而且理应接受惩罚,那么在我看来,也不至于是文学死刑那样的重罚。所以恳请把我强制迁出苏联以代之,并保留我妻子与我同行的权利。如果我不是罪犯,那么恳请允许我与妻子暂时出国,哪怕一年也好。这样,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国家在文学领域能为崇高思想服务,而不用再面对小人奴颜媚骨;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国家对语言艺术家的作用的看法哪怕稍微有所改观,我就会毫不迟疑地回来。我相信,这一天已经指日可待。因为物质基础一旦建设成功,建设上层精神建筑,建设真正无愧于革命的文学艺术,必将变成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知道,在国外我也会异常艰难。因为我不可能在那里加入反动阵营,我过去的经历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沙皇时期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还曾为此坐过牢,被两次流放,战争时期因为发表反军国主义中篇小说而遭到诉讼
即扎米亚京的《远在天边》(1914)。沙皇政府书以该小说“丑化俄国军队”为由将作者和发表小说的《箴言》杂志的编辑人员送上了法庭。)。我知道,如果说在国内我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是因为我早已习惯凭良心而非奉命写作,那么在国外,我迟早有一天会因为相同的原因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分子。但是在国外,哪怕条件再艰难,我也不会被判闭嘴,即便不用俄语,我也能够在那里写作并发表作品。
……
我本可以为去国外的请求找一些更合乎常情的理由,而且都并非不重要:为了治愈长期以来的慢性病(结肠炎),我必须去国外治疗;为了使两部已经译成英、意两国文字的剧作顺利上演(即剧本《跳蚤》和《名誉长舌协会》,曾在苏联各大剧院上演),我也必须亲自去一趟国外,此外,这两部拟上演的剧作还能让我不用因为申请外汇而给财政人民委员会添麻烦。这些理由全都彰彰在目,可我并不愿意隐瞒请求批准我与妻子出国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作为一名作家走投无路的现状。在国内,作为一名作家,我已经被判处了死刑,就在我们国内
……
移民期间的扎米亚京算不上高产。他专门为法国报纸写文章,基本以俄罗斯现代散文为主题,有时候也会写一些关于先锋艺术的内容。而在当地的俄罗斯移民群体眼里,扎米亚京始终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外来人士。更为糟糕的是,病痛和对故土的思念逐渐耗去了他的精力。1937年3月17日,作家于巴黎辞世,安葬于巴黎南郊齐约的一座公墓。终其一生都保留了苏联国籍。葬礼上,只有寥寥几位生前好友为他送行。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移民心中,他的死都犹如鸿毛击水,没有惊起任何涟漪。
跨越东西方的《我们》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或许扎米亚京只是长篇小说《我们》的作者。这部小说当然是作家本人常年艺术探索、实验的结晶,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传世珍品。可实际上,扎米亚京留给后世的文学遗产,无论从题材、体裁还是语言风格方面,都是多姿多彩的。简单粗暴地为他贴上“著名反乌托邦作家”的标签,恐怕有失公允。他的作品里,既有俄罗斯与欧洲文化的相遇相容,也有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与冲突。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思想意识层面的矛盾冲突随处可见,也就不足为奇了。扎米亚京在自传中也承认,自己从小就对矛盾事物的体验情有独钟,经常不顾场合地体验矛盾冲突而乐此不疲。
虽然扎米亚京时常自诩为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罗斯作家,以讽刺小说见长。]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写作风格的继承人,但他却不遗余力地呼吁同行们将视线投向西方,向西方作家学习视觉感强烈、引人入胜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作为数学和船舶建造业的专家,扎米亚京始终没有放弃过在文字工作中探索自然基本法则,甚至曾试图推导出某种符合现代艺术形态及发展规律的公式。终其一生,扎米亚京都固执己见地认为,“数学方法”对文学创作而言是颇为有效的捷径。用“数学方法”研究文学艺术,固然不啻为标新立异的创作思路,可是在同时代文人看来,难免会有一厢情愿的“矫情”之嫌,作品也可能会因此而变得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
不管是文学作品风格,还是平日里的言行举止,扎米亚京总给人留下内敛而又稳重的印象,甚至有时候会被人认为过于刻板。难怪勃洛克[ 勃洛克(1880—1921),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诗人。]戏称他为“莫斯科的英国人”。这个雅号也伴随了作家的一生。扎米亚京精通英语,对英国文学尤为兴趣浓厚,也是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的铁杆崇拜者。有意思的是,当年旅英期间,扎米亚京笔下的创作主题依然是俄罗斯;可回国后,他却在作品中屡屡反思和总结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临近人生终点时,扎米亚京以移民身份定居巴黎。那时候的作家坚持只用俄语写作,所以在欧洲人眼里,他一直是个纯而又纯的俄罗斯作家。
1917年和1918年,扎米亚京分别发表了“英腔”十足的中篇小说《岛民》和短篇小说《捕人者》,为其在英国的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继动物本性的代言人巴雷巴之后,两位形象鲜活的主人公杜勒先生和克拉格斯先生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前者热衷于强制同胞们接受救赎;后者则阴险伪善,靠着“捉奸”而赚得盆满钵满。“异端者”扎米亚京就像在《僻县》中批判俄罗斯毫无生机的底层生活那样,无情地鞭笞了所谓西方文明世界机械式无意义的生活。扎米亚京的确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出色地发扬了果戈理的传统,擅长在外表丝毫没有相似之处的人身上,发现内在的共性。而且与果戈理一样,他的叙事风格与诗意的修辞融为了有机的一体。事实上,这种与果戈理“血脉相承”的感觉,一生都在鼓舞作家。而“英腔”小说在扎米亚京的作品中也并非只是“独栋小洋楼”式的存在,它们作为有力的延伸构架,支撑起了日后的传世之作《我们》。
《我们》的创作结构在《岛民》与《捕人者》中便已经初露端倪。比如主人公在“记事”中的诸多议论和大一统国家的科幻描述,显然借鉴了《岛民》中副主教杜勒梦寐以求的机械式理想社会。大一统国家里,人们变得犹如机器,行为规范和准则让人觉得既滑稽而又高不可攀,甚至做爱也被纳入严格的作息安排。可是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曾服从于任何法则,所以就有了爆发。《岛民》中的肯布尔和《我们》中的工程师Д503最终都爆发了,而且爆发的过程都是通过“正统”叙事者的视角加以呈现,而小说中的所谓正统叙事者,最终也都抛弃了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接纳的行为规范,背叛了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尽管与社会传统思潮相比,个人的思想显得渺小而不足道,与宏观宇宙相比,微观个人的行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然而在扎米亚京笔下,社会层面的爆发与个人情感的起伏跌宕就像宏观宇宙与微观个人之间的联系,不仅无法剪断,而且始终平行进展,彼此相融,相互影响。因此,当小人物的命运面临万劫不复的必然毁灭时,读者内心产生的同情与共鸣便有了声振寰宇的效果。
记事20
提纲:放电。思想材料。零度峭壁。
放电是最恰如其分的定义。我现在发现,这和放电简直一模一样。最近几天,我的脉搏变得越来越干燥,跳动愈发频繁,压力也越来越大。就好像阴阳两极靠得越来越近,已经噼啪冒出火花,只要再靠近1毫米,轰地就炸了,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我的心里既平静又空虚,就像这幢楼一样,所有人都离开了,唯独我自己病恹恹地躺着,倾听着思绪清晰而又铿锵的敲打声。
或许,这种“放电”把我治好了,我也终于借此摆脱了烦人的“灵魂”,又变回了和我们大家一样了。至少,我现在想象着O走上立方体的台阶,想象她坐在气钟里,心里没有一丝痛苦的感觉。如果她在手术局里把我供出去,我也不会在乎。这辈子的最后一刻,我定会心存感恩,虔诚地亲吻恩威荣主惩一儆百的手。接受惩罚是我在大一统国家应有的权利,我绝不会把这个权利拱手相让。我们任何一个号码,都不应该也不允许拒绝这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唯一的权利,因此也是最珍贵的权利。
……可是,思绪仍在悄悄地,却又铿锵清晰地敲打。似乎有一架神奇的飞船正把我带往高空,而那里是我喜爱的抽象思维的蓝天。我发现,即便在这空气最为稀薄的纯净空间,我关于“有效权利”的论断,仍像充气轮胎一样,噗的一声轻响,破裂了。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古代荒谬偏见的反刍,是古人关于“权利”想法的再现。
有的思想是黏土捏成的,而有的思想则是用金子或者我们珍贵的玻璃锻造的,生生世世坚固无比。想要鉴定制成思想的材料,只需滴一滴强酸。其中有一种酸叫做彻底还原
原文为拉丁语。
,古人了解这种试剂,他们好像也是这么叫的。可是古人害怕这种有毒试剂,他们更喜欢看到哪怕就是用黏土捏成的天空,宁愿要玩具一样的天空,也不愿要一无所有的清一色湛蓝。可是我们,感谢恩威荣主,我们是成年号码,我们不需要玩具。
这么说吧,如果把强酸滴到“权利”思想上,就能鉴定其本质。即便是古时候,最老练的人也知道,权利的来源就是力量,而权利则是力量衍生出来的功能。就好比有两个砝码盘,一个盘子里是1克,另一个砝码盘里是1吨。前者代表“我”,而后者就代表“我们”,代表大一统国家。这样就一目了然了吧,如果要允许这个“我”在大一统国家享有一些“权利”,或者说允许1克能够和1吨抗衡,这两者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必然就会有这样的分配:把权利交给1吨,而义务则赋予给1克。这也是从微不足道走向千秋伟业的必由之路,必须忘掉自己是1克,必须意识到自己是1吨的百万分之一……
你们这些胖乎乎满面红光的金星人啊,你们这些黑乎乎铁匠一样的天王星人啊!我都能在蓝色的寂静中听见你们在抱怨。你们要明白,一切伟大的都是简单的;你们要懂得,只有算数四则运算才是永恒的金科玉律。只有建立在四则运算基础上的道义,才是伟大的,才会永远正确,流芳百世。这就是终极智慧,也是几百年来,号码们汗流浃背拼命尥蹶子呼哧直喘也要奋力登攀的金字塔顶端。站在这个顶峰往下看,残留在我们内心的祖先原始野蛮本性依然像卑微的蠕虫会蠢蠢欲动。但在这个顶峰面前,每个号码都一样。违法的母亲O也好,杀人犯也好,还有那个胆敢写诗挑战大一统国家的疯子诗人也好,他们全都一样。等待他们的,也是同样的下场——古已有之的死刑判决。这也是住在砖头房子里的古人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绝妙审判。虽然那时的历史才刚起步,古人每天清晨都沐浴在玫瑰般幼稚的朝霞中,可他们的“上帝”同样把毁谤神圣教会的行为,视作与杀人同罪。
天王星人啊,你们长得黝黑且内心残忍。你们和古代西班牙人一样,聪明地学会了用火刑把人烧死。虽然你们不说话,可我觉得,你们和我想的一样。但是我听见,粉红色的金星人似乎对酷刑和死刑议论纷纷,在讨论要回到荒蛮时代。亲爱的金星人们,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不擅长哲学而又数学地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