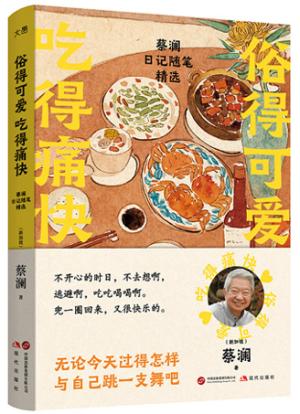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明代郎署官与文学权力
》 售價:HK$
107.8
《
人工智能与影视制作(影视制作全流程AI实战指南,深度结合DeepSeek等AI工具实操)
》 售價:HK$
97.9
《
一人公司:用个人品牌实现自由人生
》 售價:HK$
74.8
《
俗得可爱 吃得痛快:蔡澜日记随笔精选
》 售價:HK$
53.9
《
十一种孤独(理查德·耶茨作品)
》 售價:HK$
85.8
《
玫瑰花园
》 售價:HK$
54.8
《
智能体时代
》 售價:HK$
86.9
《
镇馆之宝 精讲66家博物馆文物珍品 从新石器时代到大清王朝
》 售價:HK$
756.8
編輯推薦:
★ 长达900页的大部头传记,权威、材料丰富,全面彻底地梳理本雅明的生平经历:从家乡柏林的成长求学到精神故乡巴黎的困顿流亡;从谋求学院一席之地失败到积极活跃于报刊、广播,立意成为德语世界的一流批评家;从始终孤独、复杂纠缠的亲密关系到几段同等重要但极为不同的友谊。
內容簡介: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是20世纪上半叶至为重要的思想家,其观点与思想异常迷人,却也捉摸不定,对整个20世纪的人文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本雅明学术兴趣广泛,横跨哲学、文学、艺术、摄影、电影、建筑、翻译等,却从未被限定在某个现代学术领域、某种写作文体和某类思想范式之中。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本雅明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发现某种形式,在其中,一种可与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媲美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能够通过直接动人心魄且让人过目难忘的文采,发出回响”。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目錄
导 言
內容試閱
导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