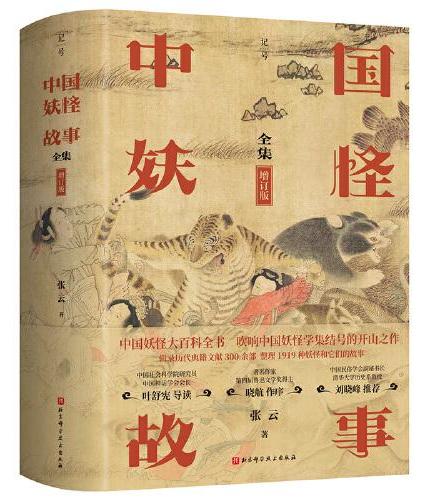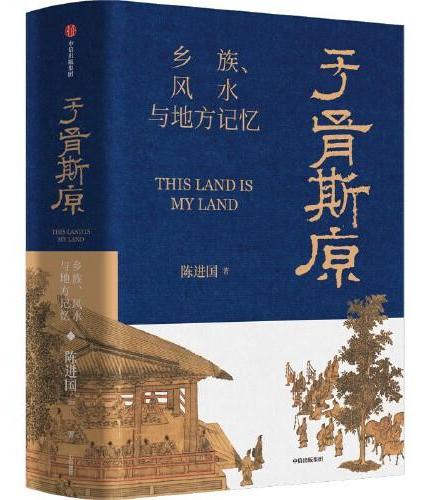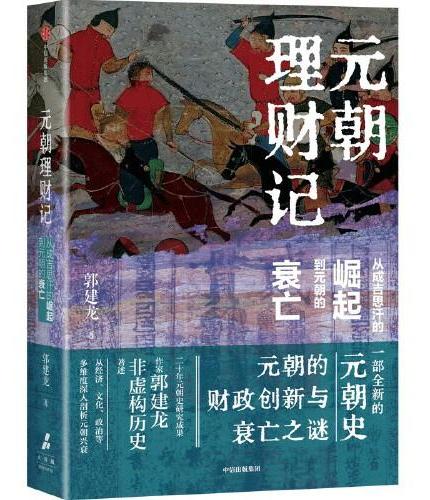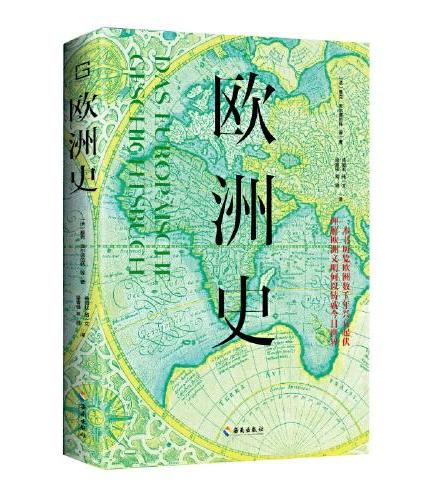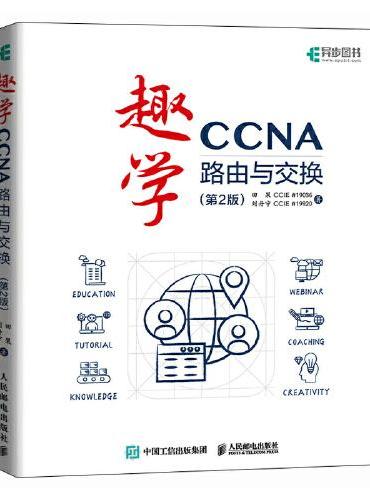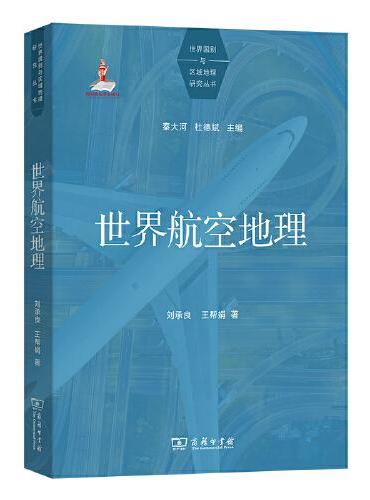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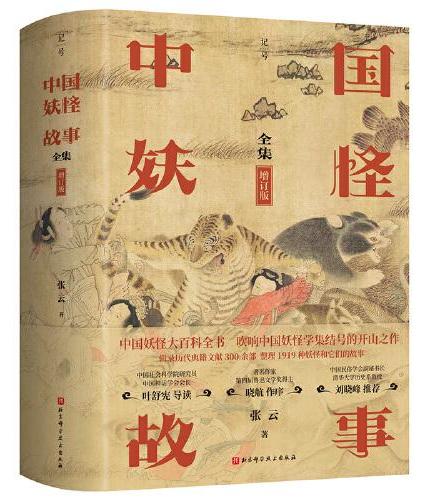
《
中国妖怪故事(全集·增订版)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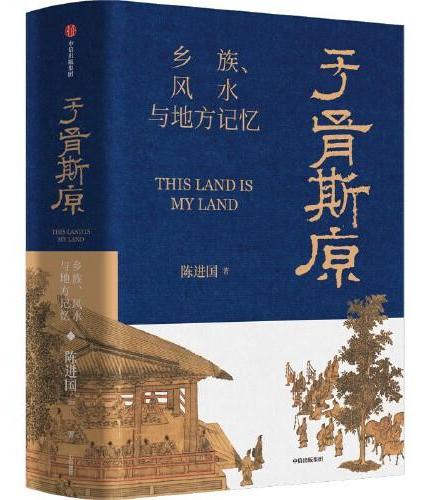
《
于胥斯原 乡族、风水与地方记忆
》
售價:HK$
177.0

《
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
售價:HK$
98.6

《
我真正想要什么?:智慧瑜伽答问/正念系列
》
售價:HK$
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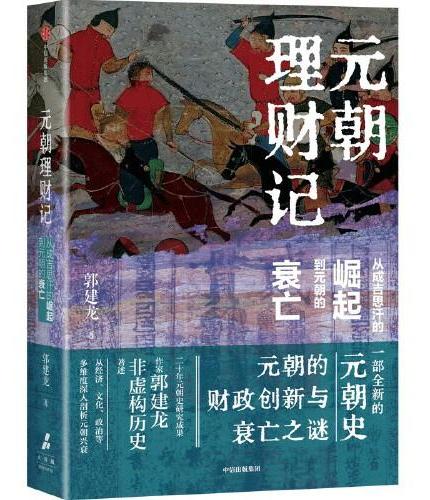
《
元朝理财记 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
》
售價:HK$
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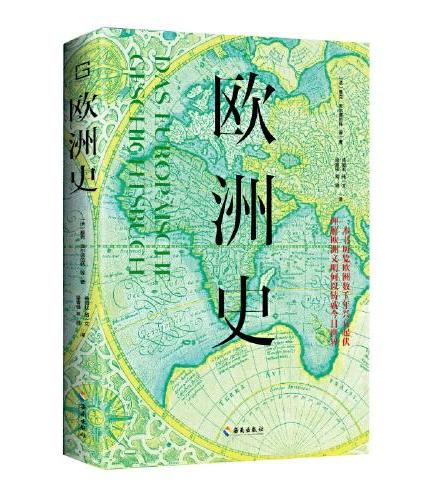
《
欧洲史:一本书历览欧洲数千年兴衰起伏,理解欧洲文明何以铸就今日世界
》
售價:HK$
3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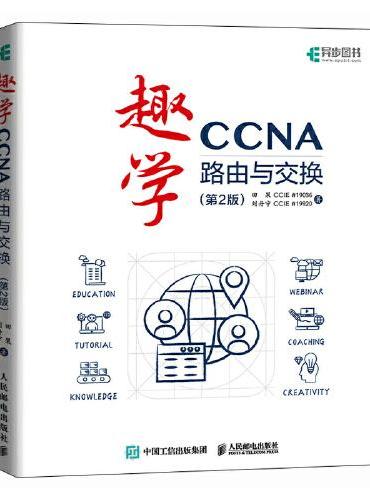
《
趣学CCNA——路由与交换(第2版)
》
售價:HK$
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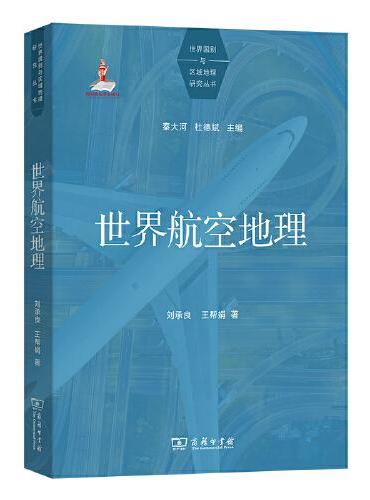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HK$
244.2
|
| 內容簡介: |
《准风月谈》收鲁迅1933年6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1934年12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初版。包括《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中国文与中国人》《难得糊涂》《青年与老子》等。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夜颂》
|
| 關於作者: |
鲁迅(1881—1936)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著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十九种,文学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两种,另有《两地书》《鲁迅书信》《鲁迅日记》行世。
|
| 目錄:
|
目录
前记
一九三三年
夜颂
推
二丑艺术
偶成
谈蝙蝠
“抄靶子”
“吃白相饭”
华德保粹优劣论
华德焚书异同论
我谈“堕民”
序的解放
别一个窃火者
智识过剩
诗和预言
“推”的余谈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踢
“中国文坛的悲观”
秋夜纪游
“揩油”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为翻译辩护
爬和撞
各种捐班
四库全书珍本
新秋杂识
帮闲法发隐
登龙术拾遗
由聋而哑
新秋杂识(二)
男人的进化
同意和解释
文床秋梦
电影的教训
关于翻译(上)
关于翻译(下)
新秋杂识(三)
礼
打听印象
吃教
喝茶
禁用和自造
看变戏法
双十怀古
重三感旧
“感旧”以后(上)
【备考】:《庄子》与《文选》(施蛰存)
“感旧”以后(下)
黄祸
冲
“滑稽”例解
外国也有
扑空
【备考】:推荐者的立场(施蛰存)
【同上】:《扑空》正误(丰之余)
【同上】:突围(施蛰存)
答“兼示”
【备考】:致黎烈文先生书(施蛰存)
中国文与中国人
野兽训练法
反刍
归厚
难得糊涂
古书中寻活字汇
“商定”文豪
青年与老子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