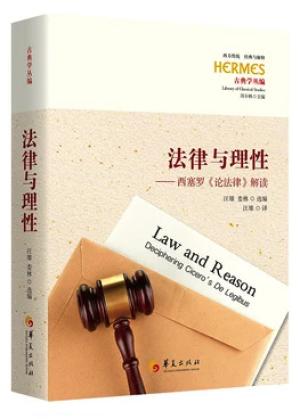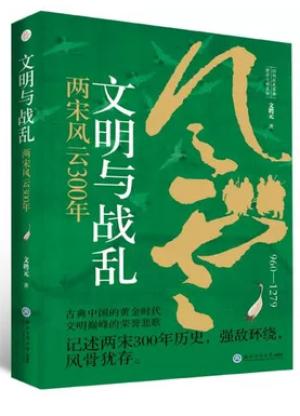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
》
售價:HK$
63.8

《
生而液态:齐格蒙特·鲍曼与年轻人的三场对谈(社会学大家鲍曼的最后一课,给每个现代人应对不确定性的哲学方案)
》
售價:HK$
53.9

《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珍藏本)
》
售價:HK$
6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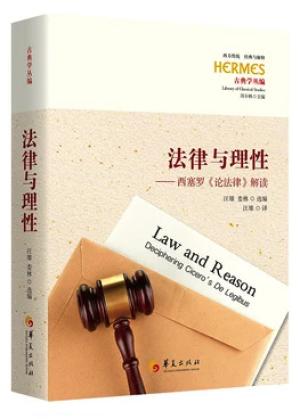
《
法律与理性 : 西塞罗《论法律》解读(刘小枫主编;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
售價:HK$
86.9

《
一个数学家的叹息:如何让孩子好奇、想学习、走进美丽的数学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士严加安、斯坦福大学教授齐斯·德福林等力荐)
》
售價:HK$
47.1

《
DK生物运转百科(全彩)
》
售價:HK$
140.8

《
规则怪谈:无罪的嫌疑人 《规则怪谈》系列小说第三部重磅来袭!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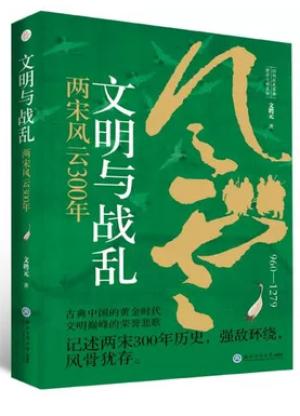
《
文明与战乱:两宋风云300年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寓理于象的小型纪事散文
并非正襟危坐的箴戒,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分享对哲学、历史、人生的感悟,令人读来轻松怡然
阅读经典时一闪而过的思想断片
读书时刻的一个印象、一点情绪、一个意念,以及它们与知识的关联
全球史视角下的文史哲审美观念
古今中外的典籍掌故,经过“再脉络化”的串联,生发出对当下的哲学思考或审美体悟
|
| 內容簡介: |
作者寄形于小品,有意延续先秦以来便存在的文学传统。本书即按照撰写的主题,分为“如是吾闻”“美与忧虑”“时间—空间”等凡十二章。而章下段落如珠错落,篇篇着墨不繁,却微言大义,不失思想性和知识性。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者长期在人文学科中钻研,通晓德、英、日等多种语言,熟稔古今中外人文经典,故在书中随处可见经典的引援——既有大量的历史文人掌故、禅宗公案,描摹了众多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画像;也有词源考据、翻译推敲,分享了作者的治学心得。此外,本书还融入作者个人的生活观察、教学反省、审美体悟,以及哲学思考。片言只语间,耐人寻味。
|
| 關於作者: |
|
李雪涛,江苏徐州人,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德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除专业论著、译著、编著外,出版有《思想断章》(小品文集,2018)、《东西合集》(诗集,2019)等作品。
|
| 目錄:
|
凡 例 ⅰ
前 言 ⅲ
如是吾闻 001
美与忧郁 029
时间—空间 041
四海之内 073
知识分子 093
过眼云烟 135
多层意义 161
自我—他者 275
生死之间 313
历史记忆 331
正法眼藏 343
东野圭吾 359
附 录 385
|
| 內容試閱:
|
前 言
一
我将《思想断章》的文体看作是“小品文”,因此这一本的书名定为《思想小品》,这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这一文体的名称实际上是从汉译佛经而来,在佛经中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起初并无文体的含义。例如鸠摩罗什在姚秦弘始五至六年(403—404)译出的二十七卷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被称作《大品般若经》;而于弘始十年(408)从梵本《八千颂般若经》译出的十卷本、仅相当于《大般若经》第四分被称作《小品般若经》。一直到了晚明才有诸如陈继儒(1558—1639)《晚香堂小品》、陈仁锡(1581—1636)《无梦园小品》这样的书名出现,在文学史上我们才知道此类的文体是“小品文”。实际上,此类短小精悍、富于理趣的文章,从先秦以来就存在,一直到今天。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当时执文坛牛耳的会稽二兄弟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也是以小品文著称:鲁迅擅长写作犀利的抨击时政的杂文,而周作人的大部分作品则都是知识性、思想性的散文。
我将上一本的《思想断章》拿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看, 他说我写的是Aphorismen(箴言集)。实际上,Aphorismen 与小品文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主要的是小品文中并非都是正襟危坐的箴戒,很多是纪事的小型散文,即便是箴言的话,也会有一个场景。我从来不认为存在所有时代都通行的真理!不论箴言还是小品都是ad-hoc(特定的、临时的)性质的,不可能是永久的。
尽管小品文的篇幅有限,但却给我以在“人的思绪有时如江河直下,纵横恣肆,一泻千里,有时又三弯九转,隐晦曲折”[1]之时随时截流的便利。
书中有很多的小品文充满着对哲学和审美的思考,但显然并非一本哲学著作,因为我并没有以抽象的文字加以诠释,而常常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讲出,寓理于象,希望在比较轻松怡然的情调中,表现出对历史、人生乃至对审美的领悟。书中大部分的段落着墨不繁,不过是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进行哲学思考或审美的体悟而已。
二
人的很多想法一旦生成,很难改变,有时自己根本意识不到。我写下我的一些观点后,有的时候忘记了,后来会再次写此类的“感想”。在后汇总的时候,发现一些想法是一样的,只是在用词方面稍微有些差别而已。
2004 年我从波恩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北外。之后我到图书馆去借书,竟然发现有几本书是我在1980 年代的时候借过的,上面还有我用铅笔划过的痕迹。看样子,一个人对某一领域的兴趣,也不是很容易改变的。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 在《往事与随想》的序言中写道: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2]
这一本《思想小品》并非像本《思想断章》一样花了几年才完成,它尽管是在两年间完成的,但同样留下了我写作时不同心情的痕迹。
三
对于我的学生们而言,他们这一代人生来便手握鼠标,快速地转换着各种页面。数字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从来不反对数字生活,也享受着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但对我来讲,这远远不是生活的全部。麦当劳、必胜客我有的时候也吃,但往往只是为了充饥,它们绝不能代替一顿真正的珍馐美味。
在一个印刷品泛滥的时代里,如何保持自己的鉴别力和鉴赏力,我觉得不断阅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对我来讲,经典既是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作品,同时也是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知识。
生活之中,常常会有一闪而过的瞬间想法,有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印象,或是一点情绪,或是一个意念,虽然根本不是什么成熟、完整的思想,却会有一段时间萦绕在你的脑海之中,难以忘怀。这些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系统思想的火花。当你真正找到知识间的关联后,很多的知识可以逐渐转化为你的思想了。
在本《思想断章》的前言中,我曾经指出,所谓的“断章”大都是读书思考时想到的,根本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因此谈不上所谓的系统、完整。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旅行者是否会走遍世间的所有角落?一个教师是否可以将他所有的知识都教授给他的弟子们?……更何况每一个人还有其他各种身份。因此,同样这本《思想小品》所展示的也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面向。
知识史永远不是一种静态的发展,而是一个文化间不断调试、碰撞和融合的动态过程。正是由于知识的接纳和排斥往往根植于接受者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知识的传播者——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格外引人瞩目。《思想小品》中的十二章并非可以独立分开的话题,而是以知识与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不断相互激荡、互相交错的内容。
四
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在如此简短的小品文篇幅中,往往需要有机地串联和容纳古今中外的语言和思想,而又要写得自然流畅,曲折有致,确实不容易。因为是短小的文体,所以很多的道理都不可能说透,只能点到为止,更多的是让读者去思考,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互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的这些小品文都是没有完成的,它们的终完成还仰仗着读者的参与。
《思想小品》中引用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书籍,对我来说,不论是禅宗的公案,还是东野圭吾的小说,都是我思考的材料。我从来不把它们看成是完整的东西,而是随时可以予以拆除的部分。德文中的auseinandersetzen 的意思是分解开来进行研究,日文中将这个词翻译成“对决”,我想这些材料都是我进行“对决”的对象。书中一些篇章尽管包含很多源自古代中国、西方和印度的智慧,但经过“再脉络化”的过程后,这些被镶嵌在新的“文脉”(context)中的文字却成为了当下对自由、理性和审美的新探索。
也正因为如此,这本看似很小的书,不是一两天可以轻松对付得了的。如果想要真正理解这些横贯古今中外的文字背后的意义,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人生的阅历,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思想可以等同于直接的词意。我希望,读者读完此书后,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自己思考问题的开始。
几年前我在读《断舍离》一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作者山下英子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士,只是运用佛教的观念和智慧来处理人生当下的问题而已。而今天在中国的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以传统文化和佛教来解释人生的书籍,但大部分作者很少有现代意识,这是的问题。
五
顾炎武(1613—1682)著有《日知录》三十二卷、《日知录之余》四卷。有的时候他在一年的时间内仅能写作数条,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实际上,《日知录》每条文字短则不过几十字,长则有千余字或二千字,但以考据见长的顾炎武,一定要在排比考究、钩稽融会后,才会动笔著述的。有关自己做学问的方法,他在《与人书》中写道: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炎武在这里以铜铸钱作比喻,来说明他并不希望用翻铸旧钱的方式,省时省力来快速完成自己的著作,而是希望从自然界采集原始的原料开始,经过自己的加工,成为崭新的思想。他将那些使用已有旧材料做的学问称作“钝贼”。皎然(730—799)说:“此则有三同。三同之中,偷语为钝贼。”(《诗式·三不同语意势》)因此,在顾炎武看来,“期之以废铜者”就是“偷语”!我读的书一向很杂,其实不论是“废铜”,还是“偷语”,都会成为我借以进行哲学思考的材料。
六
1919 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他们的使命——如何继续中国文化的传统。1958 年元旦,以新儒家的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张君劢(1887—1969)、徐复观(1903—1982)四人的名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其实他们所致力发扬光大的无非是两个方面:道德与审美。这一点从徐复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中国艺术精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3]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在科学上不如西方,但其中的道德和审美两大支柱是无与伦比的。这部著作表面是在考察中国艺术,实际上是借以讨论人性论,特别注重以先秦哲学家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来把握他们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联性。其实现代以来,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将阐发中国文化审美这个方面看作的目标,视为他们的职责所在。这一个方面的发展,我认为也可以避免道德儒学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通过更为宽泛的文史哲中的审美观念,来接续和重构中国文化的传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4]
七
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个人活得再久,也不过百岁而已。但如果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那么他就可以经历多个精彩的人生:他可以与那些优秀的人共同分享过去的美好时光。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读文学和哲学的话,那么他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闲适从容,很少会有高尚的情操。
徐梵澄(1909—2000)先生在室利· 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1872—1950)《周天集》的“译者序”中写道:
即以目前这一小册子而论,皆是一点一滴。譬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此一斑虽小,而全豹之文炳蔚可观了。
这一小册子简便易读,与高文大册不同。谓瑜伽既摄人生之全,则人间之重要事皆所涉及。无论称之为格言、或箴言、或名言、或片言、或寸铁、或散策,一一涵义皆异常丰富……其关于艺术、伦理、性灵、美、爱、乐、自由、和平……诸说,并非一概独创,而是多依傍前修。读者随意掇拾一条,是可供久久玩味的。
《周天集》是我年轻时常常把玩的一本小册子,近日重翻1991 年的这个版本,到处可以看到我当时标注心得的痕迹。
写得完美的文字跟活得精彩的人生一样难得。这样的一本小书是我平时思考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同时也不是完整的。实际上,我一直信奉的一种说法是:“Sensum, non verba spectamus.”[5]意义胜于言词。但这些文字记录了我这两年来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对美的追求。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字只是我个人精神气质的体现。
文字并非多就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有时只言片语往往胜过千言万语。现在回想起我上大学时听过的报告,如果能记得什么的话,一定是对我产生过作用的片言而已。洪应明写道:
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便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片言只语内,便宛然见千古圣贤之心,才是高士的眼界,达人的胸襟。(《菜根谭·闲适》)
常常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使人悟道,而并不一定在呶呶不休之中。“片言只语内,便宛然见千古圣贤之心”,与其说是对作者的要求,更应当说是对读者的期许。我想,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人生深邃的洞察反省,很难对本书中的“片言只语”产生共鸣。
书成了之后,我向我的同事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讨教“思想小品”的拉丁文名称,他告诉我可以译作cogitationes parvulae 或是cogitamenta parva,我选择了后者。感谢我的博士生何玉洁帮我做了索引。
2019 年2 月于北外全球史研究院
[1] 李雪涛著《思想断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前言”,第4 页。
[2] 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往事与随想》(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序言”,第9 页。
[3] 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 年。
[4] 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锦民老师于2018 年5 月26 日在外研书店举办的“历史和当下: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提出以上的观点。
[5] Dig. 34, 4, 3, 9.
放下
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与一群朋友到山中踏青,回来的时候遇到一阵疾风暴雨,由于之前雨具被仆人带走了,同行的人每个都显得惊慌失措,唯有东坡心情放松:不用在意那穿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长啸着,一边悠然地慢慢行走着。竹杖和草鞋轻捷得胜过骑着高头大马,下点雨有什么可怕的呢?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我的一生。“莫听”二字说明了下雨对他来讲是外物,根本不足萦绕于怀。不仅仅是此次郊游偶遇的一场风雨,即便是江湖上的暴风骤雨又奈他如何?这是从生活的磨炼中真正体会到了将一切“放下”的心态。
朋友数的上限
我的微信朋友圈中有一千三百多个“好友”,手机通讯录中有一千六百多个联系人,当然其中大部分的人现在都不经常联系。此外,我的微信朋友圈也很少看,有朋友会因此抱怨我从不给别人点赞,问题是我实在没有时间看朋友圈,自己当然也不发朋友圈。
牛津大学研究认知与进化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 教授在20 世纪90 年代提出“社会脑假说”,认为,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演化策略: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中彼此协助。人类的种群大小是一百四十八人,这是著名的“邓巴数”(Dunbar’s number)。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个部落的平均人数是一百五十人。108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统计出的英格兰村落平均居民数约为一百五十人。邓巴从人类学的角度证实了这样的假设:人的大脑新皮质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一百五十人的稳定人际关系。[1]也就是说,即便我有一千多个“好友”,但真正在实际生活方面的朋友依然是在一百五十人以内。但每个人真正的“好友”可能只是个位数:“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祖堂集》卷十《长生和尚》)
[1] R. I. M. Dunbar, “Coevolution of neocortical size, group size and language in huma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 1993, p. 6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