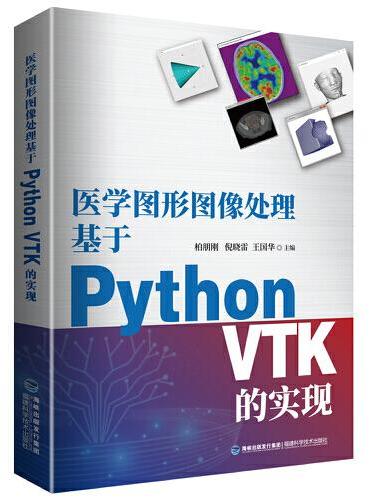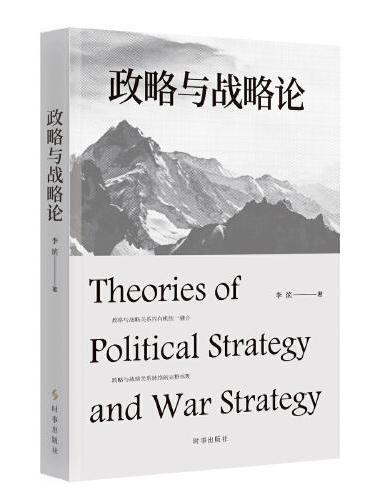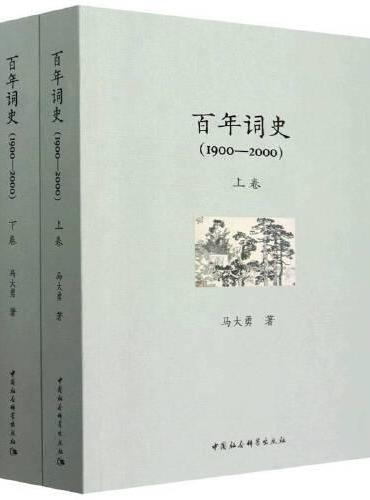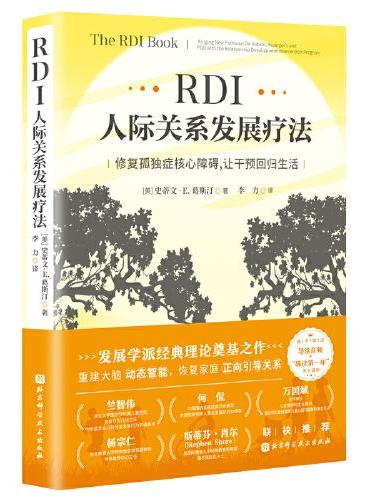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
售價:HK$
103.8

《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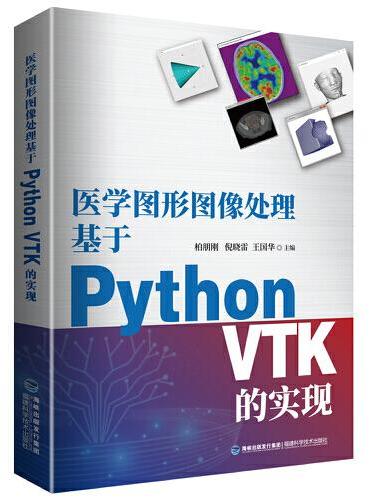
《
医学图形图像处理基于Python VTK的实现
》
售價:HK$
166.9

《
山家清供:小楷插图珍藏本 谦德国学文库系列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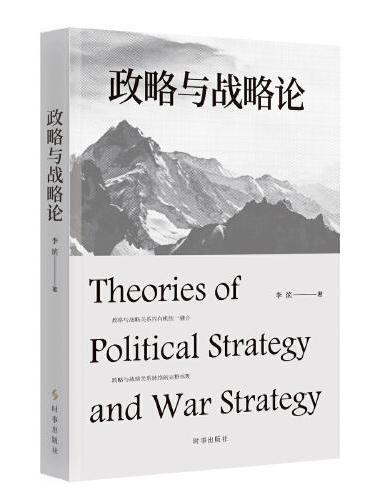
《
政略与战略论
》
售價:HK$
1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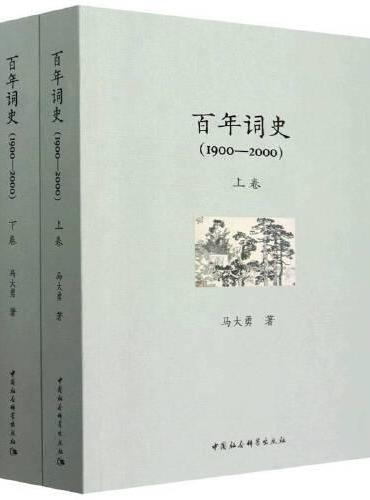
《
百年词史-(1900-2000(全二册))
》
售價:HK$
3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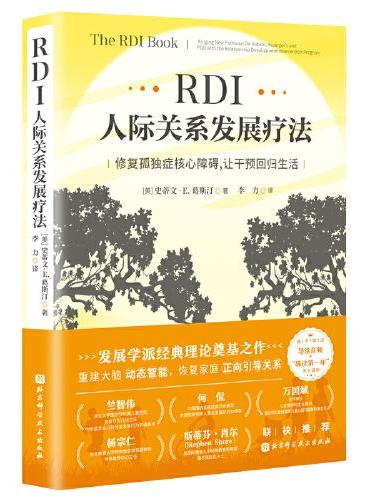
《
RDI人际关系发展疗法:修复孤独症核心障碍,让干预回归生活
》
售價:HK$
99.7

《
金融科技监管的目标、原则和实践:全球视野下加密货币的监管
》
售價:HK$
110.9
|
| 編輯推薦: |
我在米兰,经历
她的罪过、命运与无邪的青春。
在所有当代情爱小说中,只有《情人》《洛丽塔》与《米兰之恋》这三部堪称经典。其中杜拉斯写出了绝望,纳博科夫写出了欲念,而布扎蒂则写出了宿命。
——《纽约时报》
|
| 內容簡介: |
|
《相爱一场》是意大利著名作家迪诺·布扎蒂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一部略带自传色彩的作品。故事背景设置在米兰,男主人公安东尼奥是一位人到中年的单身建筑师,属于这座城市的中产阶层。然而,出身上流社会的他,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比他小三十岁的妓女拉伊德。这段爱情充满猜疑与痛苦,却又透露出爱人与追逐被爱的幸福。作者将爱情中种种纠结的情绪书写得淋漓尽致,从而奠定了本书作为情感小说的经典地位。
|
| 關於作者: |
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1906—1972),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作家,生于北部的贝鲁诺城,幼时移居米兰,1928年毕业于米兰大学法律系,曾担任过战地记者、专栏作家、美术评论家、《消息邮报》主编等职。
1940年完成的《鞑靼人沙漠》,为布扎蒂带来了世界性声誉,他也因此被称为“意大利的卡夫卡”。布扎蒂中长短小说兼擅,著有《魔法外套》《七信使》《史卡拉歌剧院之谜》《那一刻》《垮台的巴利维纳》《魔术演练》等作品,堪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大师比肩。此外,布扎蒂还多才多艺,小说之外亦擅剧作、写诗、绘画。
|
| 內容試閱:
|
第二十九章
他已等了一天。可以肯定,拉伊德会露面。哪怕冒决裂的风险,他也不给她打电话,绝不给她打电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不打电话的含义就等于对她说:你看,我就在这里,你就向我脸上吐口水好了。另外,她肯定读了他开了头之后留在桌上的那封信。当他在场时,拉伊德故意看也不看便把那封信扔到了废纸篓里,但可以想象,他刚一离开,她便跑去拣起打开读起来,因为她并非对那封信不感兴趣。而且这次她可真有那么一点点害怕了,因为她会感到,这次确实是她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他已等了两天。显然,她是在故意气他,好像安东尼奥到她家等她,这是对她的不敬。另外,大家都知道,当自己做错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显出自己受到了伤害的样子。拉伊德依然没有给他打电话,这使他很不安。很清楚,那天只是斗斗嘴,在他的心目中,这就是决裂、就是真正的决裂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冒头,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可是,她会不会把安东尼奥的那封信当了真?她会不会把弦拉得太紧?她会不会认为安东尼奥爱得着魔因而过于软弱,所以只能了结这件事?可是,谁告诉他说拉伊德真的害怕了?也许她对他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不对,她去哪里能找到一个月拿五十万里拉的好事?
他已等了三天。他开始感到不妙。他一直就坚信,她将会露面,还没等她向他请求原谅、没等她表现出悔意,她就会露面了,脸上还是那种傲慢的样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肯定,她会露面。设法让女人来求你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跟她一刀两断,莫过于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是,心里总是感到怪怪的,尽管她手头并不缺钱,那是妈妈留下的一笔五十万里拉的遗产,是妈妈工作的那家公司给的一笔清算费,前几天已经到手。
他已等了四天。办公室的电话铃每响一次,都会使他感到一阵震颤,震颤一直传到他的脊背,而且到处乱窜,直使他喘不上气来。是的,他想,她手上有那么多钱,蛮可以坚持好长时间,更何况她还可以肯定,只要她一下命令,肯定就能再拿到钱。他想,她可能想到了他是多么痛苦,因而在窃笑。夜里,不管什么时候醒来,她都会说:“就在此时此刻,那个家伙一定在想我。”对她来说,这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谁能知道,她在多么高兴地搓着双手讥笑他啊,甚至是同她的女友们一起讥笑他。不,也许不是这样,因为她只有一个女朋友,那就是法乌斯塔,她知道法乌斯塔是个什么样的糊涂虫,是个什么样的怪人。她信任她,但到一定限度为止。
可也许她会搓着手对这个女友说:那个家伙还想气我?现在我教训了他,我至少一个月不给他打电话,反正我现在有钱。到了月底,他会乖乖地爬到我面前,恭恭敬敬,温温顺顺,像条小狗,甚至比从前还要温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教训,难道他会认为,由于给了我那几个小钱,我就得没白天没黑夜地拜倒在他面前?我已经二十岁了,我需要呼吸,我需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惯他,不是吗?因此,我就得让他妒忌,让他妒忌得发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象的,我的那个小叔叔想象我换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因此他脸色苍白,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烟,甚至由于发狂而去找姑娘,希望满足自己的胃口,希望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能够暂时忘掉拉伊德。可是,对他来说,结果反而更坏,这主要是因为周围像拉伊德的人极为少见,而且,即使承认有可能找到比拉伊德漂亮的姑娘,但那绝非易事。正是可能找到的这个姑娘的美貌、脸蛋、小嘴、大腿和乳房会使他想起拉伊德的美貌、脸蛋、小嘴、大腿和乳房,拉伊德的这些东西并非十分漂亮,但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需要的就是她的脸蛋、她的小嘴、她的大腿,虽然所有其他女人的这些东西也可能一样漂亮,但很难找到,会使他感到恶心。
就这样,安东尼奥在设想拉伊德的想法,越想越恨她,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真的,甚至比这还要糟,因为在拉伊德的计谋中,她把自己身体方面的这些资本当作撒手锏,而没有很清楚地考虑到她这样做对于安东尼奥来说意味着什么,她这样说话,这样动她的嘴唇,这样嬉笑,这样嗤之以鼻,这样接吻,以及她那发“尔”音时的奇特方式构成的米兰式口音,对他安东尼奥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已等了五天。依然没有任何音信。已经很清楚,拉伊德想大赌一把,反正她不会有任何损失,而且,即使是一个月之后再露面,她也不会给人以后悔投降的形象,而是相反,依然是仁慈的女王,说到底,是她给了她这个卑微的奴仆好脸色,是她给了他生命和阳光,是她给了他期待已久的恩典。可是,一个月之后,如果她打来电话,他是不是该把电话挂断?一个月之后,他的病是不是会痊愈?一个月之后,对他来说,拉伊德是不是不再是令人不快的记忆?一个月之后,他是不是会找到一个也那么漂亮可人但更温顺、更温柔、在做爱方面更有欲望、更有本领的姑娘?这都是美梦,安东尼奥知道,这都是美梦,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奇迹。对他来说,只能是拉伊德,只有拉伊德才能给他带来安宁,哪怕是再过一年、再过两年也是如此。
他已等了六天。这天早上,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急需知道,至少知道,她是不是在米兰,或者是否并没有同某个男人鬼混。于是,他请一位男同事拨了拉伊德的电话号码,就说要找一个叫罗马尼的律师讲话。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声音是什么样的?”“是个女人的声音。”“年轻吗?”“我想是的。”“是不是发‘尔’这个音时有点特别?”“啊,是的,似乎发‘尔’这个音时是有点特别。”“是个什么样的声音?令人高兴还是令人讨厌?”“不,我觉得,不那么令人感到高兴。”“可准确地说,她讲了些什么?”“没说什么。她说,您拨错号了。你还想让她说些什么?”
就这样,他的笑料越来越多,好像这件事成了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流传得相当广的佳话。他可真成了傻瓜。他在想,拉伊德是不是马上就能猜到这个电话是他打过去的,为的就是试探一番。在她来说,这是多大的胜利啊!她知道,安东尼奥已经忍不住了,依然不敢直接给她打电话,但已到了极限,愤怒、不安和嫉妒使他头昏脑涨。再过两三天,他就会气急败坏地爬到她脚下请求原谅,真是个傻瓜。现在,她仍感到自己极有把握,根本不必急于露面,仍不给他打电话,谁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他已等了七天。他希望知道一些情况,于是前去找埃尔梅里娜太太,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问她,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个能干的姑娘。但那个女人马上便猜了出来,立即向他打听拉伊德的消息。
他回答说:“噢,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您呢?”
“我也没有,从4月以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她同您在一起。我想给她介绍一个般配的先生,她同我约好了时间,但后来却没有露面。于是我也没再坚持。这时,有人告诉我,您对她感兴趣。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退到一边了。”
“是谁告诉您的?”
“我也记不起来了,这样的事传得很快,女朋友们互相……我记不起是弗洛拉还是蒂蒂告诉我的。怎么,您也没有见到她?”
“没什么,她有点太任性。”
“都是这样。您也太娇惯她了,因此她就冲昏了头。都是些傻姑娘,当她们找到好机会时,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机会给溜走。像您这样的人实在难找!我不是在恭维您,不管是什么样的姑娘,即使是比拉伊德还要好的姑娘,也应该把您紧紧抓住不放才对,像您这样的男人,实在难得。您也知道,她并不坏……要我说的话,那我就得说,她是个好姑娘。可是,您知道是怎么闹到这种地步的吗?可能是有那么几个喜欢吃醋的女朋友,正是她们给她出了些馊主意……她很自信,确实,她太自信了……同她在一起,先生,您得……您是不是知道……”
“知道什么?”
“这,就是告诉您,也没什么不好……一天,本来已给她安排好同您见面,那是在你们见过三四次之后,仅仅三四次,不会太多,您走了之后,开始争起来……本来是一件小事……是一套女装,是她从我这里拿走的。不对,我现在想起来了,不是一套女装,而是一件连衣裙,是一件浅褐色针织连衣裙。”
“对,我也想起来了。”
“对,您真是个好样的,这您就知道了,我讲的不是谎话。总之,我还有一万五千里拉没有收回……拉伊德坚持说……算了,这算不上一回事,不是吗?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的嫂子也在场,我嫂子您也认识,为了快点解决那件事,我当时对我嫂子说:‘好了,等安东尼奥先生打电话来时,咱们可以给他安排另外一个姑娘,反正他的口味咱们也都已经知道了……’您知道吗?这时,拉伊德马上举起拳头说:‘安东尼奥先生?你们真让我觉得好笑。那个人我早把他攥在手心里了,我要他干什么他就得给我干什么!’真是太过分了,我们只好……您懂了吧?刚见了三四次面,她就冲昏了头脑!”
“最近几天,她到过您这儿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如果她不是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来过电话的话……但请您放心……这样一个姑娘,要甩掉并不容易……她们这样的人我都了解……她们以为只有天知道她们是什么人。可是,到了她们需要……您可得坚持住,懂吗?给她打电话,这您连想都不要想。您一定要坚持住。您将会看到,她会像一条小爬虫一样返回来爬到您的脚下。”
他已等了八天。突然出现了一线希望。这天上午,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他抓起电话说了一句,电话那头却没有回答,但很清楚,那边的人在听着。后来,那边把电话挂断了。他去问电话接线小姐,刚才找他的那个电话是男的打来的,还是个女的打来的。回答说是个女的打来的。很可能是她。她可能认为他顶不住了,他前天的那次电话试探可能使她认为胜利在握了。两天过去了,她也沉不住气了。
他已等了九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他只要头脑一转,便径直转到拉伊德身上,死死地盯着她,中间没有丝毫的间断。时间越是流转,就越是感到羞辱的残酷。他可是用所有的方式表示了他的爱啊!他越想越恨,简直再也无法像有身份的男人一样行事。元旦那天夜里,快三点了她才回家,那时他为什么没有勇气给她两个耳光?不,不是一般的两个耳光,而是十分响亮的两个耳光,直打得她爬到地上站不起来,然后,她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好了。如果他那天这样教训她一顿,他就会感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即使她从此再不照面也在所不惜。而现在呢?现在失败的是他,如果她再不回来,那他安东尼奥就得年复一年地忍气吞声,她则有权蔑视他,在所有的人面前讥笑他,说他是个四肢发达、自不量力的乡巴佬,需要的时候,这样的乡巴佬只能打家里的贱货两个响亮的耳光。
他已等了十天。他同埃尔梅里娜太太约好,约会定在下午。埃尔梅里娜十分高兴,答应给他介绍一个肤色浅黑的姑娘,这个姑娘将会“像拉伊德的妹妹”。实际上,安东尼奥去见埃尔梅里娜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埃尔梅里娜通过她手下的那些姑娘总是可以掌握大量情况。“拉伊德的妹妹”叫路易塞拉,面色苍白,相当恭顺,也还令人喜欢,但在床上却令人乏味。安东尼奥来到客厅时,埃尔梅里娜太太对他说:
“我了解到,前天晚上拉伊德在2号舞厅,有人告诉我,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了一身红衣服,整个晚上一直在跳舞。她是有一身红衣服吗?”
“是的,是上个月买的。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
“别的没有了……对了,等一下……路易塞拉,路易塞拉!”
“来喽。”那个姑娘在卫生间里回答。不一会儿,她穿戴整齐走了出来。
“路易塞拉,问你一件事,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拉伊德的姑娘?”
“拉伊德?有点黑?长长的头发?”
“对,就是她。是你的朋友吧?”
“怎么可能,我是通过伊里斯才认识她的。”
“就是莫斯科河大街的那个伊里斯?她们把她也拉进去了?”
“是的,就是那个伊里斯。”
“可是,路易塞拉,你这样的人怎么也到伊里斯那里去?她那里可不是人们说的所谓住家。别人对我说过……他们说,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妓院……我敢说,她们把她也拉下水了。”
“我只去过两次,后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只要一看就可以知道。太太,您讲得对,那个地方,真比妓院还糟,人来人往,始终不断。”
“这个拉伊德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了?”
“她一直泡在那里,从下午一点一直泡到晚上。”
“请告诉我,她接待多少人?”
“这我怎么知道?从来来往往的情况看,一天至少十来个。另外还有伊里斯的儿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个没正经的家伙,每天客人来之前,必须伏首听命地让他也开开心,算是开开胃口。她在那里可有事好干……可是,您问我这些干什么?”路易塞拉看着安东尼奥。他面色苍白,对他来说,这些真是可怕的消息。
“那个拉伊德是哪里人?”他问对方,心存一丝希望。
“不知道,也许是那不勒斯的,也许是卡拉布里亚的。”路易塞拉说,“我们都叫她特伦奇娜。”
“噢,幸好是这样。”安东尼奥说,“我觉得,不可能……”
“对,不可能是她。”埃尔梅里娜说,显出她对她的商品了如指掌的样子。“我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是她。另外,我知道,拉伊德不是堕落到那种地步的人。”
他已等了十一天。现在他已表明,他能够坚持住。这时也许可以给她打电话了,这时打电话也许不会丢脸。安东尼奥试着这样想了一下。接着他想清了,越晚越不好,时日过得越多,如果是他首先让步,他的屈服就越是个严重问题,就越是带有灾难性。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之后才到手的成果为什么要丢掉呢?对这些事很在行的埃尔梅里娜太太也向他建议,还是要坚持下去。可是,太可怕了。电话就在那里,就在只有半米远的地方。只要拿起听筒,拨几个号码,那边就会传来她的声音:“喂。”他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那种冷淡、懒散、厌烦、傲慢却又亲切的声音。那是动听的声音,他还能听得到吗?
他已等了十二天。这时,她应该露面了,不为别的,为了钱,她也该露面了。毫无疑问,她找到了另外一个男人,那个人或许也可以给她很多钱,也许那个人不在米兰市,每周来找她一两次,其余时间她完全自由,不然的话无法解释。在近几天里的某一天,可能他将遇到她,她穿得十分高雅,坐在朱丽叶牌跑车方向盘前,她看到了他,可她连个招呼也不肯打。
他已等了十三天。还是没有音信。他又去找埃尔梅里娜太太,他感觉这是最接近前线的地方,这是可以得到第一手信息的地方。埃尔梅里娜太太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乔恰里亚地区的姑娘,长得还算不错,受过训练,但像只野性的动物。那些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大厅里又遇到另外一个姑娘,是刚刚结婚不久的新妇。“是不是有点像拉伊德?”他回答说是,这样回答只是为了让对方高兴,实际上一点也不像。那个女人蜷缩在沙发里,心情很坏,一脸的不高兴,分开两条腿,让人看着她那肥而坚硬的大腿,这两条肥腿同她的身体很不相称。她冷冷地看着他,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她不喜欢这位先生。后来,两个姑娘一起走了。
“请问,太太,后来又听到一些消息没有?”
“关于拉伊德的消息?”
“是的。”
“没有,一点也没有。”
“太太,希望您能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可能,我愿意答应。”
“是这么回事,如果拉伊德来电话,请马上告诉我。”
“看您说到哪里去了,一定马上告诉您。一定。可是,您会看到,她不会打电话来的。”
“能不能安排一次会面,好像我是她的新客人。比如说,我进来时,她已脱了衣服在床上等着,难道她会跳起来?”
“不,这个可不行,这您应该知道。如果拉伊德打电话来,我会立即告诉您,仅此而已。您是我的朋友,出了那件事之后,我不想再让拉伊德到我家来。”
“可是,她是街上遇到的那种人当中的一个,不是吗?”安东尼奥觉得好像受到了伤害,好像被触到了自己的伤疤。
“我不能说不是。同她,同弗洛拉和克里斯蒂娜,我们在去年过得很不错。”
“请告诉我,她最后一次来就是同我一起来的那次,对吧?”
“是这样。”
“就是她出发前往罗马那天?”
“看您记得多清楚啊,确实就是那天。可是,只有老天知道她去没去罗马。”
“是我把她送到火车站的。”
“那么,您想知道她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什么后来?”
“就是您送她到火车站之后。”
“怎么,她没有坐火车走?”
“她把行李寄存到行李寄存处,立即跑到埃尔西莉娅那里,那是我的朋友,您也认识,不是吗?她急急忙忙跑去,像个妓女。”
“您是怎么知道的?”
“是埃尔西莉娅告诉我的,不是吗?好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大约四点,或者四点半,她给我打来电话。我问她,你不是要走吗?她说:‘是的,我今天晚上走,可现在我得到您那里去一趟,请您安排一下,有人陪我去。’我对她说,那你就来吧。那天,我这里没有别人。没过十分钟,她同一个人一起来了,那人可真叫吓人,我可以告诉您,那是个令人作呕的老头子,至少六十岁,肚子有这么大,嘴里没有一颗牙。只有鬼知道她是从哪里把这么一个人找出来的,也许是在丰塔纳广场,就是那个卖杂货的市场。她让我感到真难受,不得不把她拉到一边。我对她说,拉伊德啊拉伊德,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她说:‘我知道,他确实令人作呕,可是,我需要钱,您能让我怎么办。’总之,托尼诺先生,我敢向您发誓,如果有人对我说,这是一百万里拉,你同这个男人上床就是你的了,那我也要发誓说,我绝不干。而她呢,哪怕只有五千里拉,一万里拉,她也肯……”
他已等了十四天。在埃尔梅里娜太太那里听到的可怕消息也没有使安东尼奥丧失对她的兴趣。那都是些很久以前的事,当时他还只是拉伊德普普通通的客人,但是,从那以后,拉伊德再也没有在埃尔梅里娜那里露面,这就说明她同他是真心的。谁知另外有多少姑娘,虽然有一个富人能维持她们的生计,但这些姑娘还是前往妓院;如果有车,晚上她们会开着车到路上转个没完。另外,谁能知道那些故事是不是真的,在编造这些故事方面,女人是真正的能手。也许那是真事,只是并非拉伊德的事,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是很简单的事。从根本上说,埃尔梅里娜的利益完全在于要把他和拉伊德分开,她那种语气就是,想尽办法让他对拉伊德再也不感兴趣。难道拉伊德不是使埃尔梅里娜丢了一个很好的主顾吗?他要信埃尔梅里娜的鬼话就真是个傻瓜了。已经十四天过去了,他难以再继续坚持下去。有时他觉得好像是生活在噩梦之中,好像是在胡思乱想,是稀里糊涂,是妄想,有时又觉得好像拉伊德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好像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今后也永远不会见到她了。可他需要她,没有她,他无法生活;没有她,世界就是空的,就没有意义。他像一个机器人似的来到办公室,只有天知道他今天能不能好好工作。迟早总会有那么一天,人们终究会知道,他确实已经完蛋。他打开门,很怪,里面的灯开着,他看到拉伊德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她在等他。她瞪着圆圆的眼睛在看着他,眼神中含着怯意。她面色苍白,头发蓬乱,无精打采。
“我来了。”她说。
“怎么样?”他这样说,好像已经没有一点力气。
“你想怎么样?糟糕透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