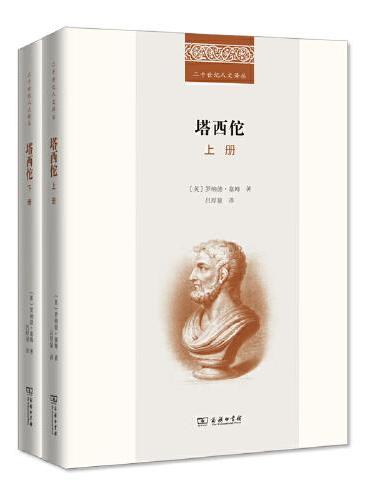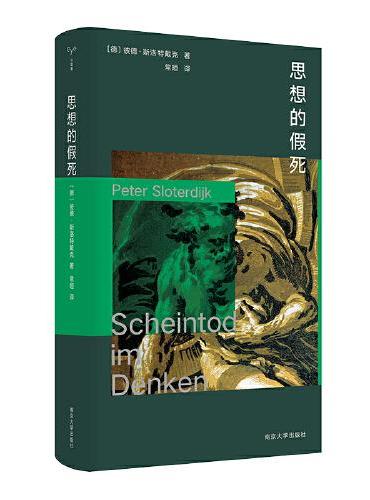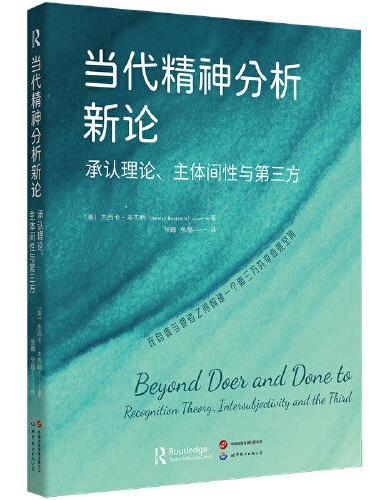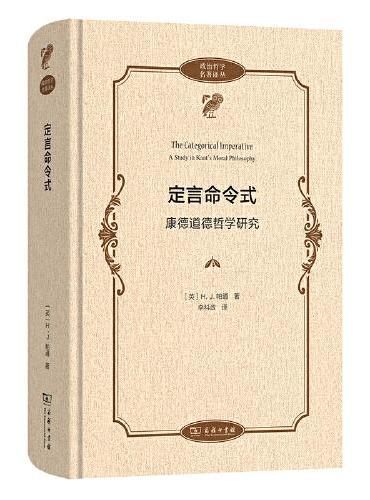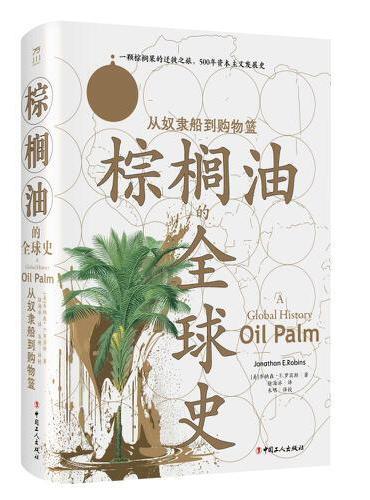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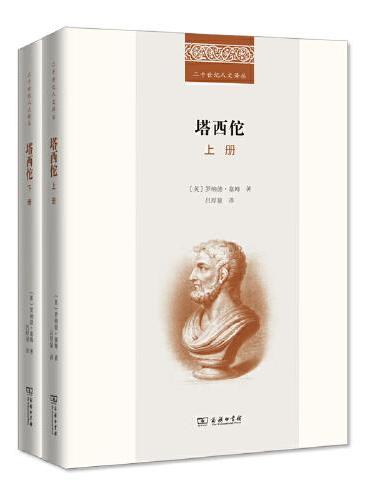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HK$
3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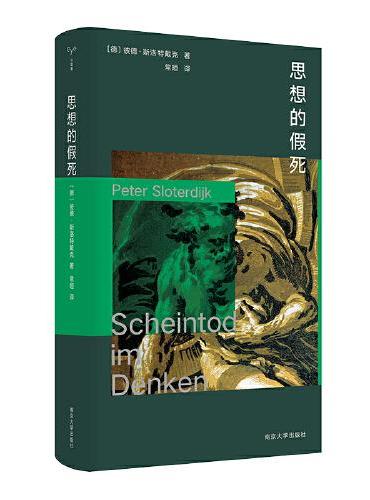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思想的假死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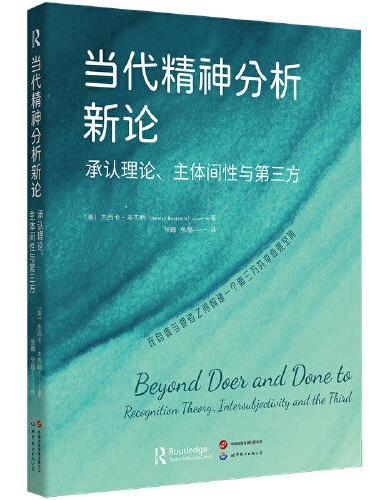
《
当代精神分析新论
》
售價:HK$
94.6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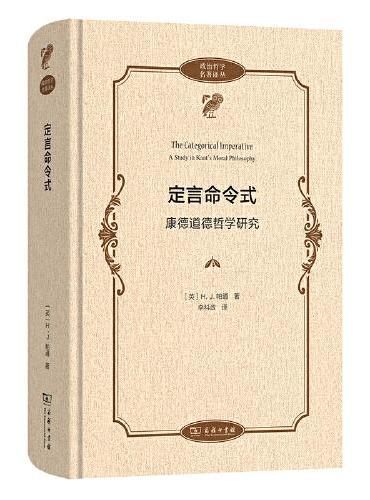
《
定言命令式:康德道德哲学研究(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
售價:HK$
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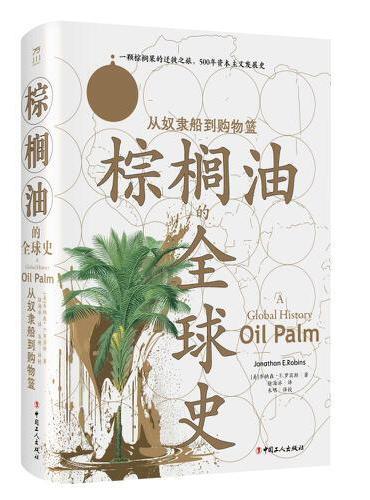
《
棕榈油的全球史 : 从奴隶船到购物篮
》
售價:HK$
96.8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308.0
|
| 編輯推薦: |
|
《上帝之城》是美国当代最具天赋和抱负、最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E.L.多克特罗,回首动荡而苦难的20世纪,对人类精神和历史命运做出的深切探索。多克特罗是美国当代的文学大家,获得过包括美国全国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小说奖、全美书评家协会奖等十几种文学奖项,2011年入选纽约“作家名人堂”,2013年获得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小说家金质奖章。《上帝之城》是他的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对20世纪苦难的真实还原。
|
| 內容簡介: |
这是我们时代的真实记录,也是关于20世纪的躁动而悲伤的多声部叙事。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各种各样的描写:宇宙理论、宗教生活、恋爱事件、哲学观点、流行歌曲、故事梗概、电影场景;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物:科学家、哲学家、大屠杀幸存者、纳粹军官、内阁成员、神学家、电影制片人……这一切就像作者笔下的大都会纽约一样,光怪陆离而又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但作者绝不仅仅是在玩着后现代的“拼盘”游戏:在动荡而苦难的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多克特罗通过展示一位改宗的基督教神父和一位进化派犹太教女拉比的心灵世界,对人类精神生活和历史命运做出了真正的探索。
|
| 關於作者: |
|
E.L.多克特罗(1931— ),美国犹太裔小说家、编剧。1931年出生于纽约市,先后毕业于肯雍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1964—1969年任新美国文库的资深编辑,1969年以后专心从事写作和教学,在纽约大学主持美国文学格拉克斯曼教席,并曾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莎拉劳伦斯学院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等院校任教。多克特罗被公认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有天赋、最有抱负和最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全美书评家协会奖(2次)、笔会福克纳文学奖和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奖章等多项荣誉。
|
| 內容試閱:
|
有理论认为,宇宙是从一个点开始,呈指数级扩展的,从一个单独的时空点、一个时刻 / 一件事、某个初始的粒子事件或偶然的量子事件,直到爆炸这个词所远远不能涵盖的范围——虽然这个理论还是被人们叫做 “大爆炸理论”。我们应该记住的,记在我们心中的,是宇宙并不是爆炸进入事先已经存在的空间,爆炸的是空间本身,它带着所有的事物一起像巨大的花朵一样绽放,一瞬间无声地闪现,宇宙中的所有气体和物质、黑暗和光明同时迸放,宇宙中的虚空迸放成无垠的空间和时间——这样说行吗?
从此宇宙的历史经历了星际物质的演变,经历了尘埃、星云、燃烧、发光、脉动的演变,在最近一百五十亿年左右的时间里,一切从一切身边逃离了。
但是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即初始的单一,或者说单一的初始,在它们亚微观的存在中包含了所有的空间、所有的时间,包含了即将大量地、突然地、壮观地迸发出的我们可以理解和学会的众多概念……说宇宙并不是由空间爆炸而成的(空间本身就是宇宙的属性),而是空间和它所包含的全部事物一起爆炸——这么说意味着什么?说空间是扩展后的、延伸后的、绽放后的东西——这么说又意味着什么?扩展、延伸、绽放成什么了?宇宙现在还在扩展它的星系,星系中有燃烧的恒星、正在老去的恒星、巨大的金属陨石、宇宙尘埃的云团,它们一定是在填充着什么。如果这是扩张,它应有边界,在目前我们远没有能力测量这个边界。宇宙的边缘此时此刻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在它覆没之前,在那个急速变化、势不可挡的变量之外,事情是什么样的?被征服、被充满、被赋予活力、被照亮的是什么?还是没有什么边缘、边界,只有无数个宇宙扩展并相互融合,按无穷无尽的序列进行着,全都在同一个时刻?因此扩展徒劳无功地扩展成自身,无穷回旋的暗物质,可怕的了无生气的无限,没有特性,没有体积,没有光或力或量子的脉动,这些基本的转化能量都没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所发明创造的,我们的意识本身就缺少容量,缺少物理属性,就像我们幻想中的宇宙一样,归根结底是一种无心的、冷漠的、非人的投射。
我想找个天文学家谈谈。我在想人们是如何麻木自己来适应集中营生活的。天文学家也是那样麻木地适应星光闪烁的宇宙的?我是说,把观看宇宙当成一个工作?(不是让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免除观看宇宙之苦,而是费心费力地向我们描述宇宙之广大,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权把宇宙当做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干着其日常工作的普通天文学家,是否能理解在他的研究对象——天体现象——之外,在他测定的辐射线之外,在他对自身职业必须怀有的敬畏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无比令人生畏的真理——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终极背景,哲人先贤总结得出的这个思之令人惊骇的结论——那就是,即使我们转向上帝,也无法减轻如此深广的、灾难性的、令人绝望的无限性所带来的不幸?这就是我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上帝也和这个问题有关,和这些基本的事实、这些显而易见的概念有关,他就太令人畏惧了,以致人们无从祈求上帝的慰藉和安抚,也无法因领悟上帝的奥秘而得到救赎。
——昨天晚餐,代号莫拉。这一两年来我见到她,只和她简单地交谈过,每次内心都有同样的迹象——我渐渐意识到一种强烈的关注,或胸口一瞬间的发紧,奇怪的是,这也许并非与性有关的兴奋。往往,随着一阵失落感,那种感觉也就消失了,然后我瞥见了自己也许已经荒芜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我看见了生活本身倔强的品性,它拒绝像应该实现的那样被实现……我成了她的饭桌伴侣,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人群中继续进行社交生活是值得的。
她没有化妆,也没有戴首饰,来的时候总是很随便地穿着最为简单的衣服,她的头发总是很随意地夹起来,仿佛是在参加晚会前最后一分钟才梳理好的,而那晚会是她丈夫硬要拉她去的,那种男士都打黑领结的正式晚宴。
她安静的风度是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就注意到的——似乎她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似乎在我们优雅的环境中她却身在别处。因为她不要求别人注意她,看上去似乎也没有自己的职业,在周围令人晕眩的女性中间她看上去太平常了。然而她总是她们不太掩饰得住的仰慕的对象。
一个身材苗条、腰身修长的人。纤秀的脸颊,深棕色的眼睛。嘴很大,肤色是均匀的淡褐色,带些苍白,纯净无杂质,似乎有光线照在她脸上。这种斯拉夫式的匀称,特别是她斜夹住的一缕头发下的前额,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我总能在她身上感受到那种仿佛君临一切的冷静。
她点点头,微笑了一下,目光清澈地直视着我,以她特有的安静在桌边坐下,我发现她这种镇定的风度是最吸引我的。
一切进展顺利。让我来款待你……舌尖上蹦出我的台词。她善于回应,以她特有的安静表示欣赏。喝第三杯波尔多红酒时,我想,在周围谈话声的掩护下,我该采取行动了。我的坦白引起了她既欣赏又不置可否的愉悦。但随即她的脸颊就飞上了红晕,她停住笑,看了看她丈夫,他就坐在附近的那张桌子旁。她拿起叉子,垂下眼睛吃她的晚餐。她衬衣上的第一颗扣子照例敞开着,显然里面什么也没穿。但我却发觉很难想像她与人有什么风流韵事,于是我变得忧郁起来,甚至感到有些羞耻。我痛苦地思忖,她是否提升了她周围每一个男人的道德感。
但接着,就要上甜点时,有人招呼男人们看看他们坐位卡的反面,并转到另一张桌子上去。我坐在一个电视女记者旁边,她在席间发表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尽管她从未在荧屏上发表过什么见解。我并没有在听,当我向后看时,我看到了……莫拉……她正死死地盯着我,目光严肃,几乎是气愤。我感到又愚蠢又悲惨。
她会在博物馆附近和我见面,一起吃午饭,然后我们去看莫奈的画。
——一百五十亿年来每一样东西都在从其他东西身边飞离,亲合力建立起来了,星座连接起来了,星星们相互围绕着慢慢地飘移,成了旋转的星群或星系,在巨大的运动中,星系更缓慢地开始形成星系团,那些星系团接着以线性的方式分布开来,于是有了几十亿光年的巨大的链或串状超级星系团。在这广阔壮观的宇宙变动中,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故发生了,一列碳和氮原子偶然排列融合成分子,出现了细胞,有机物腐败前的一个瑕斑——然后,天哪,宇宙间有了第一个有自己意志的实体。
来自神父的消息:
——Everett@earthlink.net
你好,对你的问题依次回答如下:祈祷书;白色法衣;牧师项饰配红衬衣;直接称呼神父,间接称呼尊敬的某某牧师(对主教就应称尊敬的主教大人);我的对手是蒂利希,不过有人会认为和我作对的是吉姆派克。偷走的十字架是铜的,有八英尺高。你让我觉得紧张,艾弗瑞特。
上帝保佑,
佩姆
——偷窃
今天下午在炮台公园。温暖的天气,人们都出来了。温和的秋风像一个女人在我耳边吹气。
鸽子在到处盘旋,翅膀挟着城市的飞沙碎石。在我身后,曼哈顿下城的金融大厦的天际线在阳光中勾勒出一个岛屿式的教堂轮廓,一座硕大的复合宗教建筑。
我碰到了一个手表贩子,留着长长的发绺,满脸堆笑。他穿着唱诗班的紫色袍子,个子很高。脚上崭新的白色耐克鞋也没有破坏他圣洁的外表。
“不用上发条,戴着洗澡,什么都能防,里面还有钻石呢,啥时候都准。”
一艘船出现了,像个鬼影,在港口油亮的闪光中,爱丽斯岛渡轮。我总是在看船。她忽左忽右,三层甲板上都是人,一直挤到栏杆。她鄙夷不屑地在纽约港停靠,舱壁沿边擦过。呜。桩在呻吟,噼啪声像是枪炮在响。
人行道上的那人以为人们追的是他,拔腿跑了起来。
游客闹哄哄地沿着梯板往下跑。照相机、摄像机,挂在他们肩上的惊呆了的孩子。
上帝啊,纽约的海滨有某些令人精疲力竭的东西,仿佛海里发出油味,船都是公共汽车,好像天空是挂着花哨挂历的车库,未来的月份早就被黑腻腻的手指翻过了。
但我回到了穿唱诗班袍子的小贩那里,说我喜欢那袍子的样式。我告诉他如果他让我看看商标我就给他一美元。笑容消失了。“你疯了,脑子有病?”
他把他的一盘子手表挪开了:“滚开,你别跟我掺和。”边说边左看右看的。
我穿着随便——牛仔裤,皮夹克里面穿了件条纹衬衣,再里面是T恤,没戴着标志我身份的十字架。
然后我接着走,在阿斯特广场他们把东西放在人行道上卖:有三件紫色的唱诗班袍子整齐地叠在一张塑料浴帘上。我拿起一件翻开领子,商标就在那里,“教堂长椅工艺”,洗衣店的标志来自程先生。
小贩是个一脸严肃的年轻混血儿,长着一头他们特有的浓密黑发,每件袍子要价十美元。我觉得合算。
他们来自塞内加尔,或是加勒比海,或来自利马、萨尔瓦多、瓦哈卡,他们找到一段人行道就开始做起买卖。世界上的穷人如浪潮席卷我们的海岸,就像是全球变暖后的海洋在上升。
记得有一次在去马丘比丘的路上,我在库斯科停下来听街头乐队演奏。当发现相机不见了时,游人告诉我第二天早晨可以在大教堂后面的市场把它买回来。仁慈的上帝,这真叫我恼火。但买卖赃物的是这些腼腆微笑着的库斯科女人,穿着红色和赭色的宽大防水衣,她们戴着黑色的圆顶窄边帽,把婴儿用布包裹在背上背着……那些英美人在货摊上乱找乱翻,好像在找他们失去的死者,我主耶稣啊,我怎能不接受这情景的正义性?
正如我在阿斯特广场所接受的那样。有双层斜坡屋顶的、褐色砂石建成的库柏联合会人民学院的阴影里,群鸟从广场上飞起。
往东一个街区,在圣马克广场,一个廉价旧货店售卖祭坛烛台,那是和袍子一起被偷的。二十五美元一对。我在那儿买了半打平装本侦探小说。为了学学这一行。
我在说谎,主,我只是在郁闷时读这些该死的东西。平装本侦探在对我说话,他的手枪和他的诡计安慰了我。他的世界在惩罚中被规定下来,如此可靠,而我认为你的世界更是如此。
我知道你在这个屏幕上与我同在。如果神学学士托马斯佩姆伯顿将丧失他的生命,他将在这里失去,将生命献给守护他的上帝。我的想象中,你不仅仅在我身边,在我衣领的英国淀粉浆里,在郊区牧师住宅的墙里,在教堂冰凉的石头门框里,还在闪烁的光标里……
——我们站在一幅很大的蓝绿色睡莲画前制定计划,问题在于她什么时候能够脱身。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有个保姆。一切都计划好了。我们没有身体接触,从地铁出来时也还没有,我们沿着台阶走,我为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她钻进车前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几乎有点悲哀,又在那一刻流露出无限的信任,我感到心里遭到了重重的一击。这本是我要的,并努力去得到的,但现在一旦她给了我,又立刻变成了她对我的依赖,好像我在一个秘密的婚姻中对某人起了誓,而这个婚姻的条件和责任又还未定义清楚。出租车开了,我想跟在后面跑,告诉她这一切是个错误,她误解了我。后来,我只能想她是多么可爱,我们是多么赏识对方,我不记得曾经感受到过如此强烈、清晰的吸引力。我并不在情网的边缘徘徊,我想像着自己要想最后得救,就应该与这个女人一起真实地生活。她生活在一种真实的状态里,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身心的完整,她的风度自然天成,不带任何这个时代的粗糙意识形态的痕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