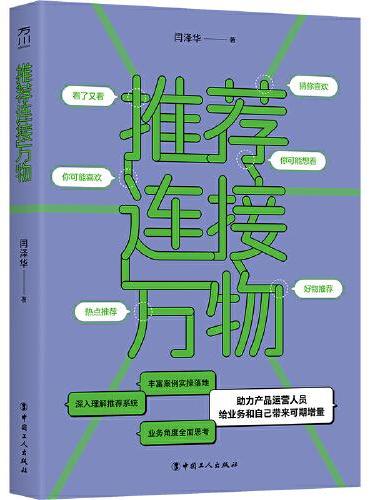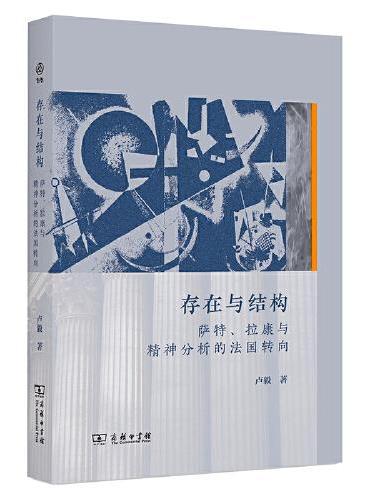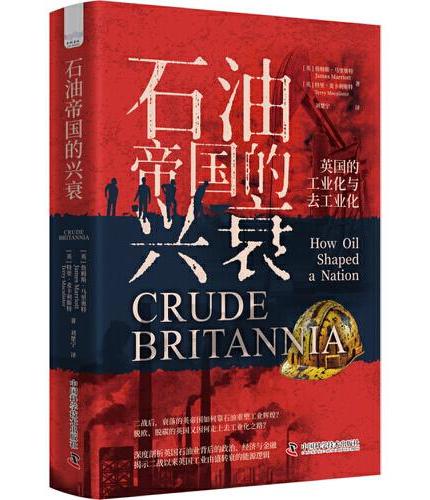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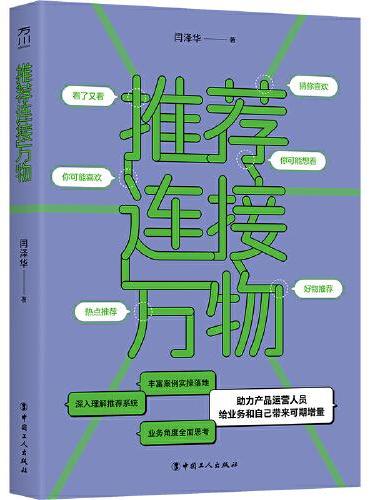
《
推荐连接万物
》
售價:HK$
63.8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165.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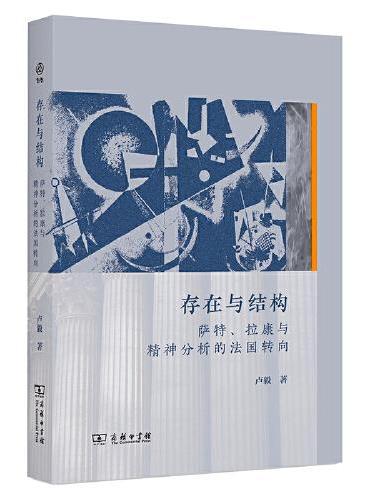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HK$
52.8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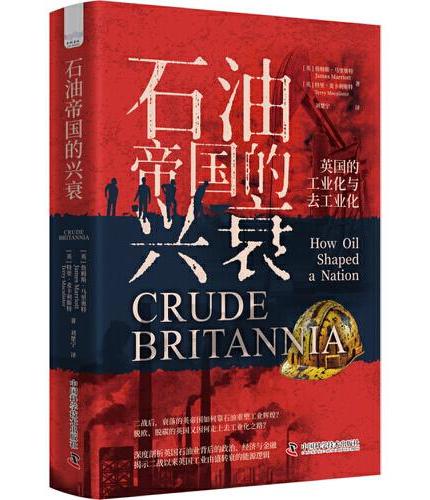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HK$
97.9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HK$
437.8
|
| 編輯推薦: |
★ 帕斯捷尔纳克——“纯粹的抒情诗人”、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瓦戈医生》作者,文学创作的另一种璀璨光芒。
蕴涵深广、风格独特的《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茨维塔耶娃语)的卓越成就,却它几乎完全遮蔽了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实绩。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最初的体验: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填补了这一空白,进一步展示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叙事文学领域的成就。
★ 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的首次完整译介
这里蒐集了帕斯捷尔纳克除《日瓦戈医生》之外的全部小说作品,它们大多在国内从未得到译介。它们是作家和他的主人公的“最初的体验”,灵动的通感和盎然的才情凸显了通向他美妙诗作与厚重长篇的清晰脉络。
★ 因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决定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
|
| 內容簡介: |
|
《最初的体验:帕斯捷尔纳克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初的体验》、《一个大字一组的故事》、《第二幅写照:彼得堡》、《无爱》、《柳维尔斯的童年》、《中篇故事》、《帕特里克手记》等13篇小说,也即除《日瓦戈医生》之外作家的全部散文体小说。这些作品多角度地表现了作家青年时代对于外部世界的独特理解和心理体验,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思考,以独特的诗学方式传达出对时代风云的沉思,高度关注被卷入历史洪流中的个性、特别是当代女性的遭遇,清晰地显示出书写一代知识者的命运、把一代人“归还给历史”的鲜明意向。这些作品所提出与思索的问题、观照生活的视角和刻画的形象,使其成为最终通向《日瓦戈医生》的必要艺术前阶。
|
| 關於作者: |
|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20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著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超越障碍》、《生活,我的姐妹》、《主题与变奏》,长诗《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自传随笔《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及《最初的体验》、《第二幅写照:彼得堡》、《柳维尔斯的童年》、《帕特里克手记》等13篇中短篇小说。他的创作,熔人文关怀、哲理思考和对生活的诗意感受于一炉,形象地折射出20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民族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艺术地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岁月里的命运、困惑、情绪与思索,其艺术表现手法兼具古典风格和现代特色,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 目錄:
|
最初的体验
阿佩莱斯线条
奇特的年份
一个大字一组的故事
对话
第二幅写照:彼得堡
无爱
寄自图拉的信
柳维尔斯的童年
一部中篇小说的三章
空中线路
中篇故事
帕特里克手记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柳维尔斯的童年
霍桑小姐也许不会这样做。但是有一次,柳维尔斯太太在并无缘由地和孩子们温柔地亲近时,却以其微不足道的理由对这个英国女人说了一些生硬的话,后者从此就离开了这个家。很快,一位憔悴的法国女人就不易觉察地取代了她的位置。后来叶尼娅仅仅记得,这个法国女人像只苍蝇,谁也不喜欢她。她的名字完全被忘却了,而且叶尼娅也不能说出,在什么样的音节和发音中可以碰到这个名字。她只记得,法国女人先是呵斥她,后来则拿起剪刀把熊皮上沾有血污的地方剪掉。
她甚至觉得,现在人们总是要对她叫嚷,所以头痛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还会经常疼痛,她再也弄不明白她心爱的书本上的那一页,这一页书在她眼前模糊一片,就像吃过午饭后的课本。
那一天长得吓人。母亲那天不在家。叶尼娅没有为此而遗憾。她甚至觉得自己因为母亲不在而高兴。
漫长的一天很快就在paéss 和futur antérieur 、给风信子浇水、沿着西伯利亚街和奥汉斯克街漫步等形式中被置之脑后了。这一天被忘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另一天、即她生命中第二个漫长日子的长度,是直到那天傍晚在灯下读书时,当一部情节进展缓慢的小说把她带入最无益的沉思之际,她才注意和感觉到的。当她后来记起他们在奥辛斯基住的那所房子时,它总是被她想象成她在第二个漫长的日子、在那一天结束时看到它的样子。这一天真的很长。户外已经是春天了。在乌拉尔艰难酝酿的、病恹恹的春天,随后便大范围地、蓬勃地破土而出,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就蓬勃而范围广阔地如期蔓延开来。照明灯只能烘托出晚间氛围的空旷。这些灯不亮,但却像坏了的果实那样因浑浊或透明的积水而从内部膨胀,胀得就像鼓起来的帽子。灯都不存在了。它们落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放在桌子上,或挂在房间里经过装饰的天花板上,女孩习惯在那里看到它们。其实,灯和房间的关联比它们和春季天空的关联要少得多,灯好像被移到了紧挨着天空的地方,就像药水被端到了病床边。它们全心全意地待在街上,在那里,仆人们的谈话在潮湿的地面上此起彼伏,渐渐稀少的水滴在夜间凝固了,结成了冰。这就是晚间照明灯消失的地方。父母都外出了。不过,预料母亲好像将在这一天归来。在这漫长的一天或最近几天里。是的,大概是的。或者,她也许会在无意中突然出现。那也是可能的。
叶尼娅准备躺到被窝里睡觉时,发现这一天很长,因为它也像那一天一样,于是她先是想拿起剪刀把衬衫和床单上这些弄脏的地方剪掉,后来又决定从法国女人那里拿来香粉把它们涂白,而就在她已经抓住香粉盒时,法国女人恰好走进来,随即打了她一下。全部罪过都集中到香粉上来了。
“她在扑香粉!竟有这么糟糕的事!”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她早就觉察到了。
叶尼娅放声大哭起来,因为挨打,因为受呵斥和感到委屈;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犯法国女人猜疑她犯的那种过错,她还知道自己曾犯有(她感觉到了这一点)比那女人所猜疑的要可恶得多的过错。看来——她在变迟钝前就迫切地感觉到了,连小腿肚子和太阳穴里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看来还不知道是这事是何以发生的,以及为什么随便怎样、无论用什么方式也要把它隐瞒过去。关节发酸,缓缓掠过融成一片的催眠般的暗示。这种折磨人、使人疲惫的暗示是身体的事情,这身体的举止就像罪犯,只对女孩隐藏它的意图,迫使她认为这次流血是某种令人厌恶的、可鄙的过。
“Menteuse !” 只是不得不否认,顽强地拒不承认这比什么都卑劣,不过处在介于无知的羞辱和街头事件的无耻之间的某一中间状态。她颤栗着,只得咬紧牙关,并忍住眼泪,靠紧墙壁。不能去卡马河了,因为还有些冷,河面上还漂动着最后一些流冰。
无论是她还是法国女人,都没有及时听到门铃声。业已造成的忙乱导致了她们像棕黑色毛皮那样无动于衷,而当母亲走进来时,那就已经迟了。她正好碰上女儿在流泪,而法国女人则满脸通红。她要求说明情况。法国女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解释说——没有称叶尼娅,没有——votreenfant ,”她说,也就是她的女儿在扑香粉,而她早就已经注意到并猜测到了。母亲没有让她说完——她的惊骇不是装出来的:女儿还不满13岁。
“叶尼娅,你?……上帝,竟到了这种地步!”(母亲当时仿佛觉得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似乎她早已知道女儿正在变坏,正在堕落,而她只是没有及时处理——于是就碰见她堕落到如此低级的程度)“叶尼娅,把事实全都说出来——否则就会更糟!——你干什么……”——弄香粉——柳维尔斯夫人本来大概想这样说,结果却说道:“弄这玩意儿?”她抓起“这玩意儿,”把它向上一扬。
“妈妈,不要相信mademoiselle ,我从来也……”她说着就号啕大哭起来。
但是这哭声却似乎让母亲听到了其中并不存在的愤恨的音调,还让她感到自己是有过失的,并且内心非常害怕;照她的意见,应当纠正一切,即便违反做母亲的本性,也应当“上升到合乎教育要求和合乎理智的高度”:她决心不陷入怜悯之中。她决定等到这让她深深苦恼的眼泪流完的时候。
于是她坐到床上,把镇静而呆滞的目光集中到书架的边沿。她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的气味。女儿平静下来之后,她又重新开始盘问她。叶尼娅用带泪痕的眼睛看着窗户,抽噎了一下。冰在移动,想必也在发出喧声。星光闪烁。空寂的晚夜寒冷而有韧性,但没有光泽,粗糙地变黑了。叶尼娅的眼睛离开了窗户。从母亲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一种不耐烦的威胁。法国女人站在墙边,整个一副严肃而专注于教训人的模样。她的一只手按侍从官的样式一动不动地紧贴着表链。叶尼娅重又看了一眼星星和卡马河。她拿定主意了。不顾寒冷,也不顾规矩,急忙说了起来。她虽然言语混乱,却不像是害怕和母亲讲这件事。母亲之所以让她把话说完,仅仅是因为她为孩子在讲述时用了那么多心思而惊讶。明白了——根据第一句话,她就一切都明白了。不,不是:根据的是她开始讲述时怎样深深地哽咽了一下。母亲听着,由于对这个瘦弱的小身体的温柔感情而高兴、喜爱并痛苦不堪。她真想扑上去搂着女儿的脖子哭一场。但是又想到要合乎教育要求;她站起身来,从床铺上揭下被子。她把女儿叫到跟前,开始缓慢而温存地抚摸她的头。
“好姑……”急促的话语脱口而出。她动静颇大地、阔气地走到窗户边,扭过头去不看她们。
叶尼娅没有看到法国女人。她含着眼泪,看着整个房间,只看见母亲站在那里。
“谁在整理床铺?”
问题没有意义。女孩哆嗦了一下。她开始可怜格鲁莎。然后母亲用她所熟悉的法语、一种生疏的语言说了些什么:严谨的表达。而后她以又完全不一样的腔调说:
“叶涅奇卡,到餐厅去吧,乖孩子,我马上也去那里,还要对你讲讲,我和你爸爸租下了多么美妙的别墅,为你们……为我们过夏天使用。”
照明灯又是自家的了,就像冬季里那样,待在家里、和柳维尔斯一家人在一起——热情、亲切而诚恳。妈妈养的雪貂在蓝色的毛纺桌布上玩耍。“中彩我将在布拉戈达奇 停留请等到受难周结束假如……”;其余的内容看不出来:电报的一角被折起来了。叶尼娅坐到沙发边上,倦怠而幸福。这样端庄而规矩地坐下,就像大约半年后在叶卡捷琳堡中学走廊里的一张冷冰冰的黄色长椅上坐下来一样,那时她考完俄语口试,得了5分,得知“可以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并说这种事不要紧,不必害怕,它还将不止一次地发生。她没有说出任何名称,也没有对她做出任何说明,但她补充说,现在她将亲自过问女儿的事情,因为她将不再外出。
法国女人因为做事马虎,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后就被解聘了。当人们给她雇来一个马车夫,她从台阶上走下来时,在平台上碰见了上楼的医生。他冷淡地回答了她的问候,没有和她说任何告别的话;她猜到,一切他都已知道了,于是脸色阴郁地耸了耸肩。
女清洁工站在门边,等候医生走过去,因为在叶尼娅所在的前厅里,比平时更久地回响着嘈杂的脚步声和石板发出的回声。少女走向成熟的第一次经历,就这样铭刻在她的记忆中:早晨街头叽叽喳喳说话的全部余音,顺着台阶缓缓上升,清朗地传入房子中;法国女人、女清洁工和医生,即两个有过失的女人和一位受聘的人,都被阳光、凉爽和梯阶发出的摩擦声清洗干净,也消过毒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