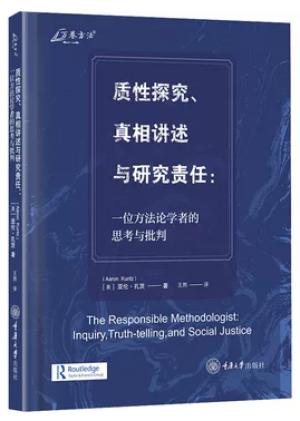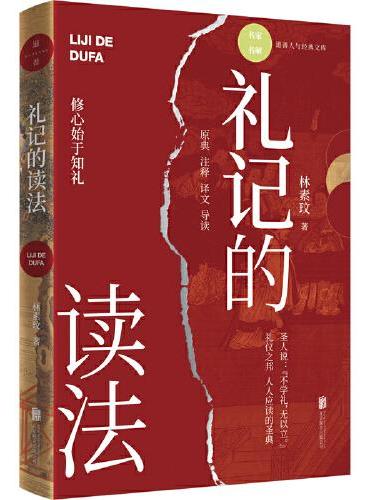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体重管理师培训体系
》
售價:HK$
85.8

《
财之道丛书·未来战争:硅谷与五角大楼的科技革命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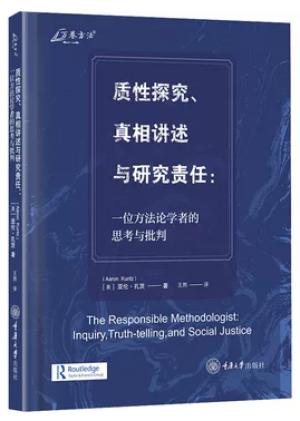
《
质性探究、真相讲述与研究责任:一位方法论学者的思考与批判
》
售價:HK$
49.5

《
从文化史到社会史:战后历史学家的思想轨迹
》
售價:HK$
107.8

《
问对问题赢学习:DeepSeek中小学生使用攻略
》
售價:HK$
65.8

《
目标感:小成果驱动下的价值交付
》
售價:HK$
1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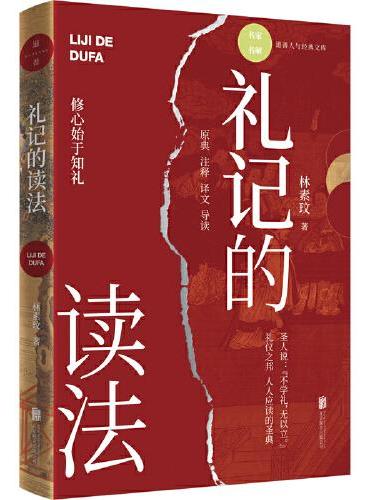
《
礼记的读法
》
售價:HK$
82.5

《
被低估的短命王朝:隋朝37年(强秦的翻版,盛唐的前奏!)
》
售價:HK$
75.9
|
| 編輯推薦: |
★ 电影版权被23家影视公司争相竞购!
★ 一部比《霍元甲》《叶问》更精彩的武侠大戏!
★ 全面展示一幅民国民间的武林画面,重温一段逐渐淡忘的峥嵘岁月。
他潜在民间身怀绝技,创派兴邦,他的故事也许比霍元甲和叶问更加传奇,更加励志!,他被称为民国武林中的最后一位大侠
|
| 內容簡介: |
|
《国术》讲述以这一时代为背景,从一个年轻的说书人赵学谨(赵有福)来北京闯荡,无意中介入到两家书场的矛盾中展开叙述。渐渐拉开中国近代一个真实武林世界的神秘面纱。主人公和他所接触的中国近代武林人士们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的广大武者,虽然他们不知道武术在中国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在为衣食生活而奔波,几乎忘了武术这一技能对他们生活所具有的实在意义。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武术,一直在寻找中华武术的出路。最终,这个憨直的小子赵学谨(赵有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为中华武术找到了位置。
|
| 關於作者: |
|
张军,生于1975年,于山西省太原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任山西青年报财经部首席记者,现为山西太原市政府机关干部。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2003年开始在《山西文学》、《都市》、《西江月》、《中国故事》等杂志发表小说。历史小说作品有《清代推理断案名家张问陶断案传奇》,《清末四大奇案》等系列中篇。
|
| 內容試閱:
|
序言
看过热销书,回忆录《逝去的武林》之后,我突然想写一个关于武者的小说。这应当是一个真实武林的故事。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这个神秘群体真正的生活状态。
书中的那些人既没有人能飞来飞去,干着杀人于无形之中的买卖;也没有人能于乱军之中杀个七进七出,一双肉掌打遍天下无敌手。他们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而只是活生生的凡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与其他行当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静悄悄的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之间,没有人能看出他们都是身怀绝技,藏而不露的神秘的武林中人。
这些人有些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贫苦人、手艺人,有些是专门做生意的买卖人,还有警察、学生。但无论是何职业,一脉相传的中华武术,早已经深深的藏在他们的骨子里和血液里。
民国初年,中华武术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快枪和大炮使武术没有施展之处,中国的习武者大都陷入迷惘之中:武术现在有什么用?老舍曾经这样描述:枪口还热着,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镳旗,钢刀和口马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与恐怖。
《国术》讲述以这一时代为背景,从一个年轻的说书人赵学谨(赵有福)来北京闯荡,无意中介入到两家书场的矛盾中展开叙述。渐渐拉开中国近代一个真实武林世界的神秘面纱。主人公和他所接触的中国近代武林人士们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的广大武者,虽然他们不知道武术在中国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在为衣食生活而奔波,几乎忘了武术这一技能对他们生活所具有的实在意义。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武术,一直在寻找中华武术的出路。最终,这个憨直的小子赵学谨(赵有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为中华武术找到了位置。
精彩章节阅读
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倒袁”声中一命呜呼,带着他没有做完的皇帝梦去见了先人。
副总统黎元洪做了民国第二任大总统,手握重兵的参谋总长段琪瑞升任内阁总理,蔡锷、唐继尧的护国军留在西南,李烈钧的护国军在广东站稳了脚跟,冯国璋、曹锟等袁世凯旧部也撤军回到驻地,宣布独立的各省又发电表示取消独立拥护中央。一场几乎燃遍全中国的战火这才平息下来。
虽然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打得轰轰烈烈,北京城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市井百姓,还是照样不紧不慢的过着生活。北京城的书场茶馆仍是红红火火,茶客如流。黄掌柜家的“客来香”书馆照旧每日鸡叫二遍就打开了门,伙计搬了梯子把写着“客来香”三个金字的招牌擦得亮亮的,收拾了桌椅板凳,摆好了茶具香茗,然后在书馆儿立个“口”字招牌,这就算开业了。
老北京的书馆一般早晨是没有客人的,只有到了上午十点钟才开场迎客,到了下午两三点才开场说书,但在天快放亮还没亮的时候仍有一笔生意可做。那就是瓦木匠、裱糊匠、打鼓的、拉车的这些个人会在这个时候来茶馆小聚一下。每人沏上一壶茶,各自给茶钱,谈谈前一天的生意,交流一下这些天的行情。这个时候的茶钱最便宜,茶叶当然也是最差的。一般是用别人喝过的剩茶叶都收集起来,倒在一个竹筐里,专门用槐角水浸泡后晒干,再用茉莉花一熏蒸,仍旧卖出来喝。好在手艺人图得只是个便宜,并不讲究这个。不同行业的人在不同的书馆茶社小聚。但凡愿意做这个生意的书馆茶社,早晨就在书馆儿门前立个“口”字招牌,以作招徕。
黄掌柜的“客来香”
就在东安市场的大马胡同路北。前面勾连搭建六间朝阳大瓦房,外边一圈用竹子编的篱笆墙,上支下摘的窗户,二十几张八仙桌,既干净、又敞亮。大堂正中有个砖砌的说书台,说书台两旁柱子上挂着一副木刻的对联:“广轶事见闻水净花明饶雅趣,庆同人快聚茶初香半涤尘襟”。
门面房的后面是个四合院,院中搭有罩棚。和门面相对的是过厅,过厅两侧的厢房和过厅后面的后堂设“雅座”,大罩棚下设“散座”。夏季茶客们在罩凉棚下乘凉品茗,冬季罩棚四面罩上面布帘子封闭起来,院内生起火,整个茶馆内暖意盎然。再往后过一小山墙又是一个四合套院,伙计们住东西厢房,北房五间,三正二耳,是说书先生和茶客留夜的地方。南房有四间,是掌柜自己的住处。
东家黄掌柜早早的净了脸,漱过口,穿一身三蓝铁线夹衫,外套枣红色珠地铁红马褂,足蹬尖口黑缎鞋,走出了后院,看着伙计把店里店外收拾齐整,然后便站在门外迎客。
虽说“客来香”每日清晨的第一批客人,不过就是些来喝“槐角水泡过的茶叶”的拉车车夫,但黄掌柜活了四十三岁,做了三十年生意,一直信奉“再小也是生意”,“头单生意好,一日生意红”。所以每日清晨开门,他一定要亲自来迎第一批客人。
“马老板,李老板早啊。”
“不早没饭吃啊,黄掌柜不是也一样早么?您生意可是比我们做得大啊。”
“唉,拿我说笑话了不是。里边请!”
几个拉车的车夫和黄掌柜打过招呼,径直走到茶桌要茶水,然后便抓紧时间谈论些行内之事。
拉车的不比平常无事喝茶的闲客,只一会儿功夫车夫们便三三两两的来齐了,都是平时再熟不过的脸,黄掌柜看看人都齐了知道再不会有客来,便要收脚走回去。临转头时冷眼向东一瞟,却见东边斜对面仁义轩书馆的两个伙计拉拉扯扯推出一个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声音不是很大,隔着又远,所以听不大清楚。只听到几个字顺着传过来,隐约是“我们掌柜的……”
黄掌柜把身子又转回过来,一面瞧着那个人向这边走过来,一面猜想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眼见那人走近了,原来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穿一件粗蓝布夹褂,但那蓝色是沾了太多污渍的缘故,变得颜色深浅不一。一张脸也是好久没洗了,灰不溜秋的还有几道子指印。矮塌的鼻子,一嘴的碎牙,长相也极不堪,只有眼睛却是炯炯有神的,若是仔细迎了那人的眸子看,便让人突然感觉到这个人有种和普通人不一般的逼人气质。
那后生走到黄掌柜跟前,先鞠了一躬才道:“先生,我不是要饭的。我想找你们掌柜的说句话。”
黄掌柜没想到他会向自己鞠躬,而且一来就说自己不是要饭的,觉得有些意思,问道:“你找我们家掌柜的有什么事?”
“请掌柜的收我说书。”
老伙计老白里边走出来喊黄掌柜的,听了这后生的话笑道:“这孩子,你以为说书就那么容易么?别的不说,上台就要讲个精气神,腰板一直,眼一睁,醒木一拍,全场就得鸦雀无声,一齐支愣着耳朵要听下文。就你这一团灰泥似的,行么?”
后生头一抬:“人不可貌相,我,我现在这个样子是……饿的!你等我吃饱了!”
黄掌柜也扑哧一声笑起来:“吃饱了?你还是要饭哪。老白,给他拿两个窝头打发他走。”
后生见这两个人不替他喊掌柜,迈步就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还喊:“我找掌柜的,我会说书!”
老白一把没扯住,后生三步两步蹿进了茶社。老白急得在后边叫:“抓住他,把他揪出去。”
店里的伙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齐上来把他摁住就往外拖。那后生挣扎着还在喊:“怎么就都不让我见掌柜的呢,我说一段给掌柜的听听。一准收我!”
这时那些拉车的车老板们也不喝茶了,一起围上来看热闹。见是这个后生吵着要说书,一齐七嘴八舌的替他说话。
“就让他说一段吧。”
“反正现在除了我们哥几个也没外人,说个小段也没什么。”
“说好说赖都不是你们家的先生,不会砸了‘客来香’的牌子。”
众伙计见老主顾一齐为后生说话,都转了头看黄掌柜。黄掌柜还在犹豫,只听远处有人喊一声:“让他说吧。”
众人往喊声来处瞧,见书馆后门头站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穿一身长衫,瘦脸长眉,眼睛炯炯有神,身材削瘦,但立得笔直。这人大家都认得,是‘客来香’书馆的台柱子赵先生。赵先生在书馆呆了好多年了,论起说书来那算得上北京书界的红角了,北京城里但凡常听书的人,没人不知道“客来香”的赵先生。赵先生既然为这个小伙子说了话,黄掌柜当然不能驳他的面子,点点头道:“行,听赵先生的,你就站在这里给我们说一段,挑一个你最拿手的说。”
伙计见掌柜的发了话,使松开手。老白催促道:“快说吧,说完了给你拿两个窝头走路。”
后生看了看众人,转头又看了看说书台子,回过头来道:“我要到台上说,还要有醒木、扇子、手帕。”
“嘿,我说你小子还真要得全乎。让你在这里说一段就不错了。你说吧你!”
后生已经知道刚才那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是掌柜,不去理老白,却拿眼去瞧黄掌柜,黄掌柜则拿眼去看赵先生,只见赵先生已经捧了一杯茶坐在书台之下了,脸冲书台,慢悠悠的品着茶,这是要听那后生在书台上说书的意思。黄掌柜又点了一下头道:“好,只说一个小段。你去那台子上说。东西都让人给你预备齐。不过你给我听好了,说得好了可以让你说完一段,说不好让这些主顾们喝了倒彩,你就立刻打住,给我走人!”
“对,窝头你也别想要了。”老白补上一句。
后生使劲点了一下头:“行。”
后生人走上书台,伙计把醒木、扇子、手帕三样东西备在案上。底下一行人都坐了下来,伙计们也不干活了,袖着手站在后边看新鲜。
黄掌柜在台前找了个座位,方一坐下,只听那后生在上边啪得一拍醒木,脆响惊四座!黄掌柜抬眼再一看,虽然人还是方才那个人,破蓝布褂子还是那身破蓝布褂子,但眼前的人好像变了一个样。身板倍儿直,眼睛放光,整个人容光焕发,就连脸上的几道手印子,也好像变了包公额上的月牙疤!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候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
《七侠五义》八句五十六个字的开场白,让这后生说的是字字如钢,声声震耳。黄掌柜不由把方才一肚子小看的心思顿时抛得无影无踪。在心里反而暗赞一声。
只听那小伙子在台上继续讲道:“大宋朝四帝仁宗赵祯在位,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上下一心,社会安定。但美中不足的是,澄州干旱三年,颗粒无收,这老百姓啊,饿死了无数。朝廷呢,曾经也派了几个放粮官,放粮赈济灾民,不但情况未见好转,相反更加严重。为这件事,年轻的皇帝赵桢,十分不痛快。这一天升坐早朝……”
小伙子声音洪亮,入耳熨帖;吐字清晰,句句有韵。黄掌柜听书听了三十多年,已经是评书行家。只感觉此人的手、眼、身、气,轻、重、缓、疾都像是名家调教了来的,可谓是台上三两步,触到天尽头,口头四五句,人情都说透。刚有刚的妙,柔有柔的优,刚柔宜并济,处处把人扣。引得台下的车夫、伙计连连叫好,喝彩声不断,就这样一直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方才停下。
这时只听台下有人大喊一声:“糟啦!”
黄掌柜回头见是拉车的马老板,关切问道:“马老板,这书讲得不好么?”
马老板一拍大腿道:“讲得太好了,我他娘的听得入神了,把拉车生意给耽误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品茶听书呢。”
众车夫一听这才如梦方醒,一齐付了茶钱,纷纷离了座向外走。伙计们也方明白过来,走开来各忙各的。
后生见人们散了,走下台来,先找刚才帮自己说话的赵先生,但不知何时他已经走开了。只留了喝剩的半杯茶在桌上。只有黄掌柜还坐在那里,后生走到黄掌柜面前又鞠一个躬,问道:“掌柜,您肯留我说书么?”
这时黄掌柜再那他的样子,又恢复了萎萎缩缩的原样子,只有两只眼还是亮的,心中暗道:“真个是上了台像条龙,下了台像只虫。这样的人自己还真是少见!”他指指面前的凳子道:“你坐吧。”
后生看了看凳子,轻笑一声道:“掌柜的在这里,哪儿有我的位子。”
“我和说书先生不兴说这个,你还是坐吧。”
后生一听这话,知道有门,脸上禁不住带出些喜色,忙坐到了凳子上。黄掌柜回送喊一声:“端茶上来。”伙计刚答应一声,黄掌柜又补一句:“要上好的福鼎大白!”
伙计送茶上来,用滚水浇了,两团白气直冒上来,黄掌柜方和气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赵,叫有福。”
“打哪儿来的?听口音像是山西人吧。”
“山西晋中祁县人。”
“什么时候来得北京城?老家过不下去了?家里还有人么?”
“我娘生弟弟的时候难产死了,我爹拉扯着我们哥俩个长大。家里有五亩地,都种了白蜡杆,祖上传下来做蜡杆的手艺。靠卖这个,老家还能过得去。”
“白蜡杆?是做枪做棒用的吧。你爹会武艺啊?”
“掌柜的,我们祁县一带不外乎三种人,一种是东家,一种是伙计,还有一种便是专为人家送镖护院的。我祖上原来也是干镖行买卖,后来不知怎的连走丢了几次镖,便退出镖行,改做白蜡杆的生意,但武艺并没有丢。再后来晋商一个接一个的倒了,东家没剩几个,伙计越来越多,送镖护院的就很少有生意可做了。倒是晋中好武之风还没有失,白蜡杆的生意虽不如前,也还凑和。”
“你也会武?是哪门哪派的?”
“我们那里练的都是形意拳。至于哪门哪派,父亲还真没跟我们说过。”
“你不知道自己练的是哪派的形意拳法?”黄掌柜透过热腾腾的两团茶雾盯着赵有福。
“都说‘穷文富武’,练武要花时间精力,富人练武,不过是多花一些钱罢了,还可以防身健体;穷人习武,只会糟蹋钱,到最后凭一身武艺为盗,那就不是好事了。所以古人有说法:富不教书,穷不练武。到我太爷爷那辈大人就不逼着子弟习武了,我爷爷还会个三拳两腿的,到父亲那辈就只见过没练过,我和弟弟都改了读书,希望能靠读书光耀门第。弟弟读书不行,我念书还好。父亲一直供我念完了小学堂,然后送我到省城读中学。在省城我头一次听到评书,一下子就入了迷。到最后竟丢了学业,一头扎进书馆。后来,父亲听说我废了学业,来太原痛打了我一顿,要我回去跟他卖蜡杆。我知道这一回去就再没有出来的机会了,半路上歇宿的时候跳后窗逃了。不也再回太原,就径直来到了北京。所有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和路上的吃食。到北京已经分文皆无,只好一边讨食一边到书馆打问想找一件事做。”
“原来你这身讲评书的本事是自学的。自己个儿琢磨就能学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是个奇才!”
“掌柜的过奖了,太原有几位讲得好的先生也给评点指教过,光靠自己悟没有人指点,也不行!”
“嗯,我让你留我这儿。不过话先说到前头:管吃管住,每五天有一天是荤菜,住的是后院正房;头一个月只有三块大洋,第二个月按场子给钱。讲好了我亏不了你。一年之内不许转场。你觉得怎么样?”
“成,只要让我说书,不要钱也成。”
黄掌柜呵呵一笑,站起来拍拍赵有福的肩:“不要钱不成,你还要孝敬父亲,娶媳妇,没钱哪儿成?”
二
黄掌柜让老白给赵有福弄了一卷铺盖,到后院正房东头住下。一般说书先生都有家,没有人会住在书馆。只有赵先生的老婆在保定,膝下没有子女,只一个人在北京,所以单占了一处明房。刚才听赵有福讲完书,便到后院撒米喂麻雀。抬头见老白领着方才那个说书小伙子抱着一卷铺盖走进来,便留了意,直起身站在了门口仔细瞧那年轻人。
两个人走过来,老白向赵先生先问了个好,然后对赵有福道:“这位赵先生可是咱们书馆的台柱子,只要是赵先生的书场,那‘客来香’一定是爆满!方才要不是赵先生,你还真没机会上台露这一手!”
赵有福鞠个躬道:“我叫赵有福,谢谢赵先生!今后还请赵先生多指点!”
赵先生笑笑道:“我都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又问老白:“安排他住哪儿啊?”
“住您隔壁,东头。”
“噢,夜场不回的先生也都住那儿,有些乱啊。我看这样吧。我一人占着两间正房也浪费,让他住我外屋吧。你说呢,赵有福。”
“那打扰先生了,我还是住东屋吧。”
“别说客气话儿,我里屋你外屋,只有我打扰你,你是扰不了我的。你要是嫌弃,我再不说二遍话。”
老白一扯赵有福的衣角,赵有福立刻道:“行,我住外屋,多谢赵先生!”
老白也替赵有福谢过一回赵先生,领着赵有福进了赵先生的家。
赵有福走进堂屋去,只见堂屋正中上面,一张红木两节柜,上面摆着笔墨纸砚、一只枣红色的紫檀醒木、几本杂书,两个盘龙的青花瓷瓶。条案两边列着四把紫檀椅子,上面还铺了紫缎的椅垫子。正中屋梁上垂下来一盏电灯,正照着下面的一张四仙桌,上面是茶盘子里放好了茶壶茶杯。雕漆的烟盒子,几根火柴。靠东边一张白木茬的光板床,胡乱扔着炕帚、剪子等杂物。
赵有福把铺盖放在椅子上,走过去收拾床铺。老白打个招呼走了到门口,又和赵先生说了一会儿话,这才离开。赵先生慢慢的踱进来,拉了一把椅子坐下,看着赵有福收拾床铺,说道:“你这个名字不好,说书人得有个响亮的名号,我给你起个艺名好不好?”
赵有福笑道:“那是再好不过,听说起艺名的时候还要烧香呢!”
“那是拜师入门起艺名才烧香拜祖,你已经艺成出师了,不必再拜师父。艺名就叫做赵学谨,你看如何?”
赵有福听了放下手中的活计转过身问道:“赵学谨?这个名字很雅!请问赵先生,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么?”
“谨,慎也。《诗经-大雅》里头有两句话。一句是‘以谨无良’,另一句是‘以谨罔极’。前一句的意思是不和奸狡诡诈之徒交往,不受他们的引诱和欺骗。后一句的意思是做人要行的正走的端。这就全仗一个‘谨’字。若是按老百姓的话,为人小心谨慎,方能平安一世。”赵先生讲完这一席话,自己也觉得很是满意,顺手从桌上拿起一块醒木,放在手里拍着,眯起眼来瞧着赵有福。
赵有福听了走过来道:“先生起得名字真不错!我往后就用这个名了。我先给您行个大礼!”说完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
赵先生的书场安排在晚上,下午没什么事,便在屋子里请赵有福再说一段评书。赵有福也想着请赵先生指教,便摆了书桌,拿了醒木、扇子、手帕正儿八经地说了一段《三侠五义》。赵先生听完,嘴里连连赞叹着:“没想到自学也能学到这个份上,你从娘胎里出来,便注定是要干这一行的。”
当晚赵有福起艺名的事告诉黄掌柜,黄掌柜说这是个大事,要好好操办,晚上赵先生下场之后,黄掌柜在后院摆了一桌席,请赵先生坐在上首,重新说了一遍改名的事,赵有福重又向赵先生磕了三个头。过去艺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严格遵循师承关系。做艺者必须磕头拜师才算有了门户,同行才会予以承认。否则,将会被同行骂为“没爹”,到处受排挤。赵先生日里说赵有福艺成出师,不必再拜师父那是自谦的话。到了席上,黄掌柜替赵有福说出拜师的话,赵有福也再三恳请。赵先生本是很喜欢这个小伙子的,便一口答应。
徒弟分为“授业”、“拜门儿”、“寄名”三类。授业即“入室弟子”,大多数从幼年学艺,受到较系统的传授;“拜门儿”一般是带艺投师,在原有基础上再受些指点。以上两种都有拜师仪式;“寄名”则无拜师仪式,只凭一封信或一句话就算某老师的弟子了,故又称“口盟”。赵有福作了赵先生的口盟徒弟,黄掌柜掏了十块大洋,八块钱让赵有福转送赵先生,作为拜师礼;两块钱留着让他到沽衣店买件八成新的像样的上场衣服。赵有福从今个起就改叫赵学谨了。
第二天赵学谨坐在书场后排流水座上听了一天书,第三天上午场的时候便在书馆门前挂起了写着“赵学谨”三个字的水牌。
但凡在场子唱戏、评书、说相声这类行当,一靠身上的真本事,二靠有朋友和喜欢自己的观众捧场。捧角、捧角,不捧难成角!捧角的人按现在的话叫“粉丝”,英文叫做Fans。赵先生心疼徒弟,怕赵学谨第一次讲书冷了场,自个儿掏钱请客,请了十几个自己的“粉丝”到场助威。又掏钱专门请裁缝为赵学谨订作了一身上场服。第一场评书段子千挑万选,替赵学谨选了当时最热门的武侠评书《七剑十八义》。有师傅这么照顾着,赵学谨的说评书的底子又深,说起书来张弛有度,引人入胜,场下自然是叫好声一片。
赵学谨在台上连说了七天,台下叫好声喊了七日。渐渐的,但凡挂起赵学谨水牌的时候,听书的人就比别的上午场多出许多;赵学谨一下了场,请他吃饭,和他说话的茶客一个接着一个,应接不暇。明眼人都看的出来,赵学谨红了。
一个说评书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红起来,行话叫做“挑帘红”,是很不容易见到的。黄掌柜见自己的书场出了一个“挑帘红”,自然是很高兴。立刻就给赵学谨排了下午场和晚场。书钱也涨了,原来是一个月三块大洋,现在是三七分账。
大多数人喝茶听书的书客是在下午场和晚场过来,所以大书场在这两个场次安排的都是有一定功底和名气的演员;至于分账,小书场是倒三七分账,就是说书先生拿七成,书场拿三成;有名声聚人气的大书场是正三七,说书先生拿三成,书场拿七成。如果说书先生是名角,是五五分成;说书先生是北京城数一数二的红角,仍然是倒三七,书场只拿三成。所以赵学谨只用不到十天的功夫,就开始说下午场和夜场,拿了三七的分账,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三
赵学谨在京城书城站住了脚,一讲就是小半年,赵先生对这个徒弟也是十分照顾,师徒俩个处和如父子一般。有师父使劲捧着,赵学谨也争气,到了这一年刚入冬的时候,赵学谨已经是个北京城里响当当的名角了。“客来香”书馆的生意也因为赵学谨的名声人气更旺,但凡是下午场和晚场,场场都是客满。不仅仅是里头茶客爆满,外头还总有站着排队等着往里进的。黄掌柜为此把六间朝阳大瓦房,翻盖成了三层高的茶楼。翻修期间仍要营业,便把最后一进院子腾出来,所有伙计都在外边租房子住。
有钱好办事,也就三个月功夫,茶楼建好。新书场阔亮高大,直顶到二层的顶上,藻井精雕细刻,刻得是《三国》、《水浒》、《西游记》、《古渊剑》、《剑胆忠魂》、《三侠五义》等二十多本评书中的人物;书台高有五尺,花梨木做的书桌;二层面前书场一溜的半圆形西式栏杆装饰跑马廊,廊后是一间一间的包厢茶室。
黄掌柜这么一大弄,周边几家茶馆书社的生意受得影响不小,茶客减了不少。这些地方的掌柜的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便有人悄悄的借着听客请吃饭的名义把赵学谨请到酒楼雅座,酒过三旬,饭过五味之后,悄悄的透底说自己是受了某某书馆掌柜的请托,提出让赵学谨转场说书。酬金是三七开,书只要三成,七成归赵学谨。甚至有的小书馆提出是二八开,八成归赵学谨。只要赵学谨肯来,每场书开场时另有丰厚的谢仪红包。赵学谨每次听了都是冷冷一笑:“早干嘛去了?年初我饿得快要死了,除了黄掌柜没有一家收留我!就是给你们白说一段书听听,你们也像躲瘟疫似的把我赶出去。现在想捡现成的,晚啦!”
三次五次之后,赵学谨的态度这些人也就明白了,知道出再大的价钱也没用,便再没有人和赵学谨提这事,偷偷的挖黄掌柜的墙角了。但就这么善罢甘休,眼瞅着黄掌柜的“客来香”把他们碗里这口饭抢去一半,也实在是不甘心。暗的不行来明的,软的不行来硬的。京城几家书馆的掌柜向黄掌柜提出,今年要提前“请支。”
按着那时评书演出的规矩。每年年初时,京城书馆要集体邀请有名的说书先生一聚,然后在饭庄定上几桌酒席,于聚餐中商谈有关演出事宜,名为“请支”。席间,书馆主人根据这些名角的要求和演出书目的内容,制定出全年的演出计划。说书先生少则两个月,多则三个月要转一次场,就是去别家说书。
因为书馆要想多挣钱就必须请到有叫座能力的说书先生,才能上满堂座。而说书先生也愿意到地势好能上座的书馆说书。但一般的书馆也想要有名的说书先生,一般的说书先生的也想到好地方去说书。为了公平起见,便有了“转场”一说,两三个月说完一部书,说完一部书便要转一个场。能上座的书馆可以多留几个有名气的说书先生,但不上座的书馆也能捞着一半个名角来为自己压个轴;有名的说书先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上座的书馆说书,没名的说书先生也有在好书馆露脸的机会(但多半是上午场)。
这一回在醉仙楼摆了“请支”宴,北京城有点名气的四十三家书场的掌柜全来了。让赵学谨转场说书成了这回“请支”的热门话题。黄掌柜难犯众怒,替赵学谨答应了,赵学谨可以在外场说四个月的书。但赵学谨当着众老板的面说自己不干,谁爱说谁说去,自己只在黄掌柜的“客来香”说书。
黄掌柜劝道:“学谨,你师父赵先生和我是什么交情,相交二十年,吃住都在我这里,吃住免费,我一个大子都不让赵先生掏。可赵先生也得在外头转半年的场,这是做生意,咱不能呕这个气。和气生财嘛!今个儿这事我拿主意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别让我下不来台啊!”
赵学谨听完没有言声,将手中的一杯茶慢慢啜尽,才抬起头来道:“黄掌柜,我和师父不一样。师父是吃这碗饭的,指着这碗饭挣钱养家。我呢,我和师父、和各位说书的前辈并不是一路的,我充其量就是一个票友,不是你们这个圈里的。黄掌柜只要能给我一口饭吃,哪怕不给我说书钱,我也愿意呆在那儿。不过话说回来,黄掌柜既然开了这个口,我不能拨了黄掌柜的面子。黄掌柜也是人在江湖,不能和各位掌柜的伤了和气。我说个办法大家看行不行?我只去各位的书场里捧场说小段子,但不说转场说大书。要是转场说大书,我最多也只能去四家书馆。如果按我的建议,今年各家书社我都能去捧个场,献个丑。”
小书场的掌柜们自然觉得这样好,不然至少两年内还是轮不着请赵学谨进自己的书馆讲书;剩下几个大的有名气的掌柜就不怎么愿意了。可是赵学谨既然把话摞到这里了,“我不是为钱!”那就算是强着他来转场说大书,恐怕也不会使力气,只好也答应了。
众书场掌柜闹罢“请支”宴,定下了各位名角的出场轮次,一场北京评书界的纷争总算是平息。眼瞅着腊月已到,师父赵先生要回去陪自己那口子过年办年货,早早就回保定了。随着大年越来越近,家住外地的伙计和说书先生走了不老少,只有几个家住的远的,比如家在甘陕、两广、江浙的,才留下来在北京过年。好在茶客也少了,黄掌柜撤了上午场,上午只有清茶不说书,所以人手还能调用的过来。赵学谨回山西老家也不过是三四天的功夫,但他并不想回。说书的瘾还没有过足,自己在北京的脚跟也没有立稳,要是回去父亲把自己留下,那可就糟了。
到了腊月二十的时候,赵学谨说完下午场,刚到后台的时候,看见老白顶着一脑袋的白毛雪从后院走进来,一边拍着肩上头上的雪一边道:“今个儿雪真大!十年里没遇到这么大的雪!下得跟丢棉花似的。好在该回家的这时都已经到家了,不然出京的路可难走!”
赵学谨听说下雪了,便要换了衣服去赏雪。这时伙计走过来,传话说有几名书客请吃馆子,赵学谨走到前台见了这几名书客,一番好话谢辞了几位,然后回到后院自己的屋子。
赵学谨路过后院的时候,见雪还在下,却已经小了,纷纷扬扬,缓缓的落着,像一面大筛子往下筛着白面。雪已经积了很厚,房上地上都如镶了厚厚一层白玉似的,树木变成了琼枝玉叶,几个雪堆耸立在墙角,只有道路刚被扫过,只被铺上薄薄的一层白纱,盖着黑色的路。
赵学谨现在拿的是倒四六分账报酬,一个月能拿一百五六十块大洋,现在流行的獭皮袍子紫羔皮马褂还是买得起的。但他今年添置的还只是两件棉袍,一件老羊皮马褂,一件棉坎肩,一件棉裤,一件毛裤,两双羊毛袜子,两双棉鞋。赵学谨一向节俭惯了,而且山西的冬天要比北京冷得多,在北京这几件东西足够用了。
赵学谨换好了衣服准备出去时,这才想起自己找不到一起赏雪的伴儿。虽然自己在“客来香”交了几个朋友,但都不是有心赏雪的人;师父赵先生和一个姓李和账房先生倒是个文雅人,可惜都回了老家。赵学谨站在门前想了半天,仍是没想出一个人来。笑着自言道:“一个人赏雪虽然孤单了点,也别有一番情趣。”遂迈步走出了门。
赵学谨出了书馆向西而去,雪花迎面打来,轻轻的扑在脸上,大多数都跌落下去,也有淘气的的沾在脸上不肯下来,但很快便化成了水,这时候它们再后悔已经晚了。大街上的雪还没有扫去,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顺街向前望去,远远近近的一片白,远处的景物仿佛消失了,隐匿在大雪织就的白幕之后;近处的屋宇树石则各个顶着一层白被,偶有没有被雪遮尽的屋瓦枝桠,露出斑斑点点的黑色,像雪里寻食的鸟。
赵学谨只管走着赏雪,走过两家店面,冷不丁有人当面截住一拱手道:“赵先生赏雪啊。”
赵学谨一愣,见对面那人五十多岁,长眉细眼,削瘦的脸,穿一身灰市布棉长袍套一件玄色套扣皮背心,脚下蹬着一双“踢死牛”桐油浇底快靴。民国初年的时候乱穿衣,说书的一般还是那套长袍马褂,但大多数人只穿长短衫,也有穿中山穿的,一些赶新潮的人穿西装。这个人也穿着长袍马褂,不是同行便是满人。赵学谨也拱了拱手,问道:“请问您是……?”
对面那人笑道:“赵先生,我常去‘客来香’听书,就爱听您的书,但从没有和您说过话,所以您不认识我。”
赵学谨听了知道是自己的一个书迷,笑道:“承蒙您前来捧场,赵某在这里补谢了。您怎么称呼?”
那人道:“我姓敖,您唤我老敖就行了。我在京城做点小买卖,这几天没什么生意,早关了门,见雪下得小了,便要去‘客来香’听书。走到这里听刚走出来的人说先生今天改说下午场了,知道再去听不到您说书了,正站这儿犹豫着要不要去。可巧就碰见您了,您说这不是缘分么?”
赵学谨听那人自称是听客,又姓敖。敖是由满姓改过来的汉姓,再加上这一身行头,知道是满人无疑了。笑笑道:“您大雪天的还赶来听我说书,这份情我记在心里头了。下回您再来,跟我打声招呼,我让人给您加个龙须凳。”
龙须凳摆在书场最好的位置,能坐在龙须凳上的人,要么是有头有脸的人,要么是说书先生关系非常的人,要么是长时间花了大钱捧角的人。不管是谁,只要坐了龙须凳,面子上是很有光的。当然掏钱也是双份。
老敖听了一笑道:“坐龙须凳倒不必,您能赏光和我喝杯茶,吃顿饭,我便很是有面子了。”
老敖指着旁边一家菜馆道:“我想着赵先生刚下了场,未必就这么快吃了晚饭,不如就赏光到这家菜馆如何?您可千万别跟我说‘改日’二字,那样可就凉了我的这一片赤心啦!”
赵学谨本来是想打个招呼继续赏雪的,没想到话赶话却说到请饭的份上了,但既然是自己把竿子竖起来的,就怪不得老敖顺竿爬。再看老敖说得诚恳,把眼瞪圆了等着他答应,自己不好拨了他的面子。只好道:“恭敬不如从命,就简叨扰您一顿。”
“瞧您说的。”老敖听自己的“偶像”答应吃饭,乐得两条细眼眯得更细,一手拉着赵学谨进了菜馆,要了三层一间雅座。这间雅座不甚大,向北一间玻璃大窗,从窗子里往外望,白茫茫的一片其中夹着数不清斑驳的黑点,那些都是京城的民宅。
店伙计送上来一只烧的极旺火盆,递上来一张菜单。“点菜单”也是与时俱进,刚刚从西方学过来的,以前的时候都是伙计报菜名。老敖请赵学谨点菜,赵学谨请老敖点。两人彼此谦让一番,最后还是赵学谨拿了菜单,先点了一个山西的过油肉;老敖接过菜单,却没有看,对伙计说道:“来半片烤鸭,一盘香茹肉饼,还有三元烧牛头,雪花桃泥,核桃酪……”老敖还要点,赵学谨急忙道:“这些足够了,两个人哪里能吃得了?”
老敖笑道:“既然是请我一向敬重的人,当然不能小家子气。”
赵学谨道:“已经六样菜了,吃不了要浪费。您的心意我知道,不必在这上边过于破费!”
“那听您的,再点一个汤得了。”老敖又点了一道清汤燕菜,便让伙计下去备菜。
赵学谨见老敖虽然穿得普通,但点菜点的十分老道,所点之菜又价值不菲,心中有些好奇,问道:“老敖,您在哪里发财?我看您举止说话,是八旗的人吧!”
老敖对赵学谨一竖大拇哥笑道:“赵先生好眼力。都说说书先生知道的事多,什么也瞒不过你们的眼睛,这回亲眼见识了。”
老敖给赵学谨满上茶,继续道:“我祖上是镶黄旗的牛录额真(正四品佐领),一直世袭到我阿玛(满族称呼:父亲)那辈是第三世分得拨什库(正六品骁骑校)。轮我这辈,按每三世降一等的规矩,我袭了个太仆寺马厂协领的七品官,就是孙猴子在玉皇大帝那儿当的那个‘弼马温’。其实这个差使挺肥的,可是正赶上辛亥革命,宣统皇帝退了位,我这个差使就丢了。好歹祖上留的那点子家底还在,自己当了十多年‘弼马温’也攒了一些钱,就改行做了买卖。但旗人自打入了关,几百年里就没有再做过买卖,你说我做买卖能赚钱么?”
正说着,菜上来了。伙计把香茹肉饼,三元烧牛头,雪花桃泥,核桃酪、过油肉摆上桌,道:“两位先生,烤鸭需要慢烤,上菜比较慢,还得等一会儿。”
老敖点点头:“烤鸭这东西,是很讲究火候的。火候到位,鸭皮酥脆,油香浓郁;鸭肉细腻,鲜嫩滑润,不糟不柴。告诉你家大厨,我们不着急,让他好好烤!”
店小二笑着奉承老敖是行家,然后下楼去了。老敖伸出筷子给赵学谨布菜,将赵学谨面前的碟子装得满满的。赵学谨笑道:“不用这么客气,随便一点儿最好。不然就生分了。”老敖这才停了筷子,赵学谨又问道:“方才您说您做买卖不赚钱,可我看您现在的样子,却像是有些底子的!现在的生意一定已经转好了吧。”
老敖又是一竖大拇指:“我的这点底子都瞒不过赵先生的眼睛。”遂又敬了赵学谨一杯酒,道:“自打大清皇帝退了位,我的日子就是一日不如一日,出去做买卖赔钱,回家喝稀饭塞牙。一直到了去年,袁大总统的二儿子袁克文要买一匹西域的马,因为识不出好坏,便让人请行家来看。有个朋友恰好在袁克文的府上当清客,就推荐说有一个专门给皇上挑马的人,现在落魄了,但本事没放下。袁克文一听就让人把我叫到袁府里头了。马夫把那匹马牵过来,我上下打量了几眼,围着马转了两圈就告诉袁克文:这个不是真正的纯种西域贡马。袁克文问我何以见得?我说,纯种的西域贡马高有九尺,颈与身等,昂举若凤。后足胫节间有两距,毛中隐若鳞甲。那才是绝品。袁克文听了半信半疑,正好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也刚弄了一匹西域马回来。两相一对比,立辨真伪。袁大公子一高兴,便赏了我一根金条。我琢磨着做这买卖行又不要本钱,又来钱快。打那儿起就改行给京津两地的公子哥们相马赚钱。没一年的功夫,也混了个吃穿不愁。”
(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是有钱有才又会玩的四个人。张伯驹的生父张锦芳、叔叔兼养父张镇芳和袁世凯是表兄弟,其中张镇芳是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民国时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部部长。溥侗是道光长子奕纬的孙子。)
赵学谨道:“您哪儿仅是吃穿不愁啊,就凭您这相马的本事,日子过得要比我们说书的强得多了!”
“见笑了。”老敖再敬赵学谨第三杯酒,两人喝罢。老敖道:“人穷了就只想着吃饱肚子,穿暖了身子就行啦。等吃饱穿暖了,这才想着闲了要做什么事乐呵乐呵。打我玛法(满族称呼:祖父)起就是个听书迷,他老人家还是个说书票友,以前常在地安门的广庆轩里玩票。阿玛在世的时候,兵荒马乱,又闹义和团、又闹八国联军的,也没心思玩票;到我这辈的时候,生计所迫,听书已是奢侈,哪儿有闲功夫去做票友。到现在只会听,不会说了。不过,阿玛当年自个儿写了一本评书,一直盼着有个角儿能把这本书给说红了,说成传世之作,临蹬腿那天还念叨着这事。阿玛的遗愿一直在我心里头搁着,前些年为着混口饭吃东奔西颠,要请说书先生说红这本书,实在是有心无力。今年开始,日子过得消闲了,又想起这个事,便留了心。北京城里的几个名角,我也问过人家,人家觉得这本书不够分量,怕说冷了场子,没人愿意说。但我这个心思还是放不下,前两个月听说‘客来香’出了位姓赵的说书先生,那说书的本事是没得挑。所以才来捧场,打算瞅个时候请您出来说这事,可巧今个儿碰上了您了,再往后头拖,我怕失了机会,现在就和您说了这事吧。您先瞧瞧这个本子。”
老敖说着从袖笼子里掏出一本用黄宣纸装订的成的一本整整齐齐的书,双手捧了递过来。赵学谨也用双手接过来,见这本书大约三四百页厚,封面用薄羊皮纸装订,里边是工工整整的竖排蝇头小楷字,字体简洁老练,一看就是常使笔杆子的,却不像一个武将能写出来的字。但赵学谨并没有往深里想,只是在脑子里转了一念,便去看那书的内容。粗翻了几页,才知道是说中国四大名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少林拳之间的事。赵学谨想着老敖的父亲是个习武之人,所以才写武林之事,因笑道:“老爷子写评书也是三句不离本行啊。”
“那是,我阿玛虽说武艺不怎么样,可是总和武林这帮子人打交道,知道的事情自然比武林之外的人多一些。赵先生,您要是能把这本书捧红了,我把去年袁二公子送我的那根金条送您。”
“不必,我先看看再说。”
“那不能让您白忙活啊。您说《三侠五义》也是挣钱,说我阿玛这本书也是挣钱。但我阿玛这本书还得劳您费神改一改,又是新书上场影响您的进项,您要是一文的酬劳都不要,那显着我是占了您的大便宜,欠了您的大人情。我老敖可不是那种人!”老敖说着又掏出几摞子现大洋,当啷啷放在赵学谨的面前:“这三十块大洋是给您的定钱。全北京城我可找不出第二个既有德又有才的先生能帮我这个大忙了,您可一定不能推辞!”
赵学谨也是年轻气盛,把大洋往前一推道:“您这可是把我小瞧了。我赵学谨可不缺这几个钱。这书您交给我吧,要真是本好书,我给您把他说红了,替您了了这桩心愿;要是书写得不好,我也没办法,只好原物奉还。”
老敖推了几推,见赵学谨一脸正色,实在是不收,只好将大洋收回道:“这可真过意不去!头一回见面,就让您帮这么大的忙!”说罢连连敬酒,又力捧了赵学谨一回。赵学谨被酒劲和奉承话灌得晕晕乎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吃完得酒,什么时候回的茶社。一进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直睡到日上三竿,这才醒来。想起昨天老敖托付自己的事,如做了一场大梦一般,自己倒先怀疑起来是不是真在做梦。往袖里一摸,那本羊皮黄宣纸的书还在,这才相信确有其事。又想起没问老敖家住何处,有些遗憾,只好等老敖来找自己了。
赵学谨从床上爬起来,起涮干净,重换了一身衣服,到对过早点摊吃了半斤油条,喝了两碗豆腐脑。因为这天没有安排场子,便买了二两猪头肉,两个馒头,三样小菜装了一小碗,慢慢走回来放在桌上,当作午饭,进屋又泡了一杯乌龙茶,坐在炉边,一边品着茶一边翻看着这本书。这本书并没有题目,一开始杂七杂八,东拉西扯的说了一些晚清武林的轶事,文笔还算顺畅,不过并没有评书所讲究的纲目梁柱,情节文采也没什么突出的地方。赵学谨看了二十来页,就有些厌了,但再往后看,却看出点兴趣来。四大名拳之间的纷争和议的缘故,每派武术承接发展的历史,各种拳法套路实战的特点,江湖名家性格脾气的特点都讲得明明白白,生动有趣。赵学谨没想到江湖武林竟是如此一个样子,有爱有恨,有情有义,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江湖故事或让人喟然长叹,或让人怆然泪下,或让人忍俊不禁,或让人义愤填膺;江湖人物或让人恨,或让人怜,或让人怒其不争,或让人敬其不畏。赵学谨一口气看到天黑,那书上的字模模糊糊的再也认不清了,这才从书中的武侠世界中走出来。摸一摸脸上,竟然挂了两行泪珠,不知是何时流出的,又不知是为何人感伤而流。赵学谨笑笑,才听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叫,感觉有些饿得发慌,点亮了油灯,到桌上取了小菜放在火上,用馒头夹了猪头肉在火上烤。吃完了晚饭,又接着看。
到第二日吃午饭的时候,赵学谨看完了这部书,心里头已经决定要把它改成评书。这时已经临近年关,书场到腊月二十三便不再设书场,但还卖清茶。赵学谨便有了时间把这本书好好的改一遍。他备了华脱门的自来水金笔,美国进口的墨水,敬记纸庄的道林墨格稿纸,都是上好的文具,把自己关在屋中,一直改了二十多天,才将这本书改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