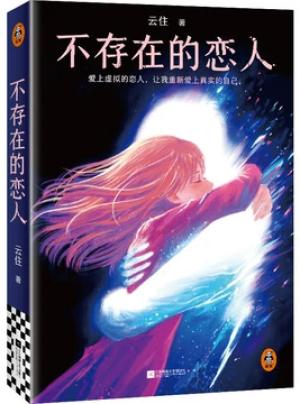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蚂蚁史诗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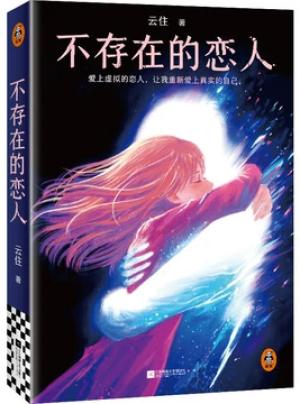
《
不存在的恋人
》
售價:HK$
54.9

《
《飞行的小酒馆》(猛犸译丛)
》
售價:HK$
65.8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插图版(1840-1937)
》
售價:HK$
96.8

《
新民说·庆丕回忆录:我与中国海关(1874—1921)
》
售價:HK$
74.8

《
围棋的故事
》
售價:HK$
74.8

《
AI超级个体:让创业更容易
》
售價:HK$
85.8

《
张居正大传
》
售價:HK$
65.8
|
| 編輯推薦: |
《中国动物文学大系》是对中国原创动物文学发展历史的回顾、梳理与总结,包括动物小说、动物散文等动物文学的主要样式,全面收录中国动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囊括中国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动物文学精华,是中国第一套最大规模的动物文学精品文库。
阅读这套书,让小读者领略大自然的壮阔瑰丽,感受动物世界的多姿多彩,体悟生命运动的炽热与鲜活,探寻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与共荣。
|
| 內容簡介: |
本书包括《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三部中篇动物小说。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大迁徙》写的是,在印度洋的一个蟹岛上,有成万上亿的小红蟹,每到雨季就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来一次大迁徙。它们不惧路途艰难,不顾骄阳似火,任凭汽车轮碾成肉泥,搭成尸桥,再列方阵,向着大海,向着繁衍地进军。作品中把小红蟹的远征、情杀、繁衍、新生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重点着墨的几只红蟹更是各具特性,呼之欲出。
《大毁灭》写旅鼠集体自杀,悲壮、隽永。《大拼搏》写褐马鸡与天敌拼搏,顽强、凄清。在读者掩卷之后,给人留下无限的回味。
|
| 關於作者: |
方敏,女,文学学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保护大熊猫唯一代言人。
1949年在重庆市出生,1956年到1969年在天津上小学中学,1969年到1976年上山下乡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1976年到1978年在河南鹤壁文化局任创作员,1978年到1982年在河南大学读中文系,1982年到1987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87到1988在《中国绿色时报》任记者编辑,1989到1998在《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任主任记者,1998到2004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编审。2004年退休。
著有长篇小说《早晨的潜流》、《孔雀湖》、《情义劫》、《玫瑰谷》、《大绝唱》、《山里山外》、《大迁徙》、《大毁灭》;中篇小说集《大拼搏》;中篇小说《天有道》、《不是为了祭奠》,长篇报告文学《黛青色的丰碑》;生态文学《熊猫史诗》;翻译长篇小说《浪迹风流》、《威兹小姐》等。
《大绝唱》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曁国家环保总局首届环境文学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中篇小说《大拼搏》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英文版入选联合国出版的《世界优秀小说选》。
|
| 目錄:
|
总序
探索生命之谜自序
大迁徙
大拼搏
大毁灭
作家与作品
作家相册
作家手迹
著作目录
获奖记录
一种新的文学开拓◎冯牧
|
| 內容試閱:
|
一
漫长的旱季。
从七月初到十一月底,几乎没有一滴雨水,也没有一丝季风,是蟹岛上几十年不遇的苦旱。
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默默承受着这一现实。落叶树毫不犹豫地把身上大大小小的叶片清除干净,连枝条也变成了黑褐色,抵御着灼热的威逼。常绿植物中的针叶树,像鸡毛松、竹叶松,也紧紧地把针叶缩成一团,尽量地保存自己残余的水分。粗大的藤本植物落光了叶子,枯干了藤皮,更加拼命地纠缠住高大的树干不放。树蕨,这些栖在树杈上,像巨大的盆景一样装扮着热带雨林的孑遗植物,如今也干巴巴、乱蓬蓬,像是废弃的老鸦窝。即使在最阴暗潮湿的山谷中,树干上苔藓,也如疥癣一般,青一块、黄一块地掉下来,令人惨不忍睹。
严酷的旱季,热带雨林里死一般静寂。不见了树枝上荡来荡去的长臂猿,不见了密叶间窜来窜去的小松鼠,甚至连蟹岛上的主要居民——红蟹,也仿佛被一阵风卷走了,踪影全无。
往日,你只要步入雨林,这种红色的螃蟹遍地皆是。它们从甲壳到腿钳到肚皮,浑身通红,像攀枝花一样打眼,像火苗一样明亮。它们总是爬来爬去地工作着,将遍地的落叶、浆果,拖回自己的洞穴。将蟹岛上百余平方公里的雨林清扫得干干净净,让人们得以悠闲地散步。它们不怕人,因为人类不食用也不伤害它们。它们也不怕其他动物,因为有坚硬的甲壳。它们只是不停地工作,吃进落叶和浆果,排出一粒粒棕褐色的粪便,滋养着密密的雨林。每当旱季将临,它们工作得更加忙碌,除了在洞中贮藏鲜肥的食物备用,还要用潮湿的叶子紧紧地堵住洞口,以防洞中的水分被旱季抽走。即使是在往年的旱季,它们也并不销声匿迹。哪怕一片云彩落下几滴打不湿地皮的小雨,它们也会从洞中爬出来,急急忙忙用红色的大钳子舀起树根边、树叶上的水珠,送进嘴里。而且在来来往往的碰撞时,互相还动一动眼睛,敲一敲地面,打个招呼。接着便趁着太阳还没露头,又匆匆忙忙潜回洞中,把洞口堵严。
然而,今年是几十年没有的大旱。不要说一滴雨水,就连一滴露水也没有。这些勤劳机敏的红蟹,自从钻进洞穴,就再也没露头,甚至一点动静都没有,莫非它们已被旱死在洞中?
但是,假如你来到雨林中,将耳朵贴着地面呆上一会儿,或闭上眼睛背靠大树坐上一会儿,就会听见一阵阵低沉、凝重的旋律,从深厚的地底下传上来,萦绕着整个雨林。这是一支古老悠长的乐曲。千百年来,它随着旱季和雨季的更替,时强时弱,时伏时起,仿佛在讲述着一个久远的过去。
六千万年前,蟹岛还是沉在印度洋底的火山,红蟹的祖先们聚居在火山顶的珊瑚礁石间,游玩、嬉戏。海底有丰富的水生动植物供它们择食,海底没有天灾人祸,平静、安定,任它们繁衍生息。但是,随着物换星移,随着地壳的运动,有一天,火山顶突然冒出了海平面,托着聚居在它头上的红蟹群。面对着蓝天、红日,面对着狂风、暴雨,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随着石灰岩盆地里海水的不断蒸发,红蟹这种用腮呼吸的水生动物,面临着灭绝。
百年、千年、万年过去了,小岛上长出了黄色的地衣,地衣演变出厚厚的苔藓,接着便有了绿色的小草、参天的热带雨林。这时候,一只两只,千只万只红蟹突然像从天而降一般出现了,把寂寥的雨林点染得红红火火,烘托得生气勃勃。这些不幸的小生灵,是怎样熬过千万年小岛和自身的演变而存活下来的呢?没人说得清。只是比起水生的祖先,它们的身体变小了,是因为食物的不足——雨林里只有落叶和浆果。它们的腮退化了,身体的边缘出现了类似肺一样的腮孔。它们还学会了用八条腿在地上爬而不是游泳,用两只大钳子打地洞而不是捕捉猎物。它们变得格外灵敏:对于晴天和雨天的气息,对于旱季和雨季的交替,对于白天和黑夜的变化,对于湿地和干地的选择。
就这样,红蟹变成了旱蟹,正像当年在水下时一样,重新以绝对优势占领了这个小岛,以致人们不得不将此地称为蟹岛。
就这样,一支古老悠长的乐曲,一年一度,循环往复,将祖祖辈辈求生存的业绩世世代代传奏下去。
也许是对水生祖先的祭奠,也许是海的不可解除的咒语,每当雨季来临,红蟹们总要进行一次浩浩荡荡的远征,从密林高地迁徙海边,交配产卵甩子。红蟹的后代只有经过海水的沐浴才能获得生命。
往年每逢十一月初,印度洋的季风频频吹来,就会降下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但是,今年这漫长严酷的旱季哟,直到十一月底还没有一丝一毫雨季的征候。于是,这支古老悠长的乐曲,越来越雄浑,越来越沉重,震撼着森林,震撼着大地……
二
风来了,这雨的使者,裹着印度洋上的潮湿气和海腥味,一路上折着跟头,打着呼哨,日夜兼程,直扑向久盼甘霖的热带雨林。树枝在晃动,树叶在舒展,彩蝶翻飞,蚂蚁出动,连穿山甲也从洞里探出了头。死寂的雨林开始复苏。
雨来了,这姗姗来迟的雨季的序幕,一来便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起初是豆粒大的雨滴,噼里啪啦,雹子似的砸在树叶、树干和干裂的黑土地上。接着,便像决了堤的天河,一股股白色的雨柱倾泻而下,无休无止,仿佛要将这雨林这蟹岛依然打入印度洋底。
于是,热带雨林重新获得生机。枯木般的落叶树眨眼间泛出青色,枝条上冒出一个个胀鼓鼓的芽苞,就像一张张干渴的小嘴,吸吮着甘美的琼浆。奄奄一息的常绿乔木振作起来,清理掉泛黄的旧叶,换一身翠绿的新衣。干涸的小溪又有了欢笑,扬起水花在石头上载歌载舞。
假如一阵大风吹过,把雨帘吹得稀薄,你又会发现,密林中肥厚的黑土地上,突然铺上了一层明亮的鲜红。这便是蟹岛上的土著红蟹。
凭着敏锐的本能,红蟹首当其冲,迎接雨的洗礼。当第一批雨点滴落,它们马上冲出洞穴。当大雨倾盆的时候,它们不像别的动物躲躲藏藏,而是一个挨一个地趴在地上,任狂风吹打,任暴雨浇下,雨一天不停,就一天不动,仿佛睡着了似的,在这水汪汪的天地间,做一个古老的美梦。
雨终于停了,梦立刻断了,红蟹们重新面临雨林的世界,第一个直觉就是腹中空空。林地上有狂风扯下来的落叶,有暴雨打下来的浆果,然而,在这雨林中,平均每公顷土地上的就聚集着一万多只红蟹,这有限的食物哪里够?于是,就有了捷足先登者、暴力相向者和无可奈何者。你瞧,在那棵高大的第伦桃树下,就正有一场争夺。
那是一颗丰满的第伦桃果,天知道它是怎样躲过苦旱的,颜色还是那样鲜红艳丽,果肉还是那样饱满多汁。说来有趣,最先发现它的是一只独眼的雄蟹,正应了独具慧眼一说。可是,当它把第伦桃果放在独眼面前,准备用两只大钳子剥去片状的花萼时,却遭到了袭击。
这是一只六岁的雄蟹,背壳直径大约七公分,不但肢体健全,而且透着股剽悍的生气,特别是那一对坚硬的大钳子,当独眼被它牢牢地抓住时,就像上了镣铐,休想挣脱。然而,凭着比硬钳大两岁的经验,独眼还是用长腿将第伦桃果推到一边,骨碌碌滚出好远。于是,又有了一场争先恐后的赛跑。不过,当两只雄蟹几乎同时到达目标时,它们都愣住了。
鲜美可口的第伦桃果旁正站着一只背壳直径约十二公分,即年龄在十岁以上的雄蟹。它只有一只巨大的钳子,却有一股无形的威慑力。年轻时它是密林中最凶猛的红蟹,凭着一对巨大的钳子、强健的体魄以及好斗的性格,它几乎打遍了整个密林,所向披靡。它的大钳子折断过好几次,每次都很快再生出来,重新披挂上阵。但当它步入老年后,折臂却没再生,尽管如此,独臂仍然保持着它的凛凛威风。
独眼向右边走了,凭着独具慧眼,它又发现一颗油柑果,虽然有些干瘪,味道也有些酸涩。硬钳向左边走了,凭着它的强悍,不妨选择别的目标再去抢夺。
独臂美滋滋地吸吮咀嚼着酸甜鲜嫩的第伦桃果,当它饱餐之后趴在地上稍息片刻时,一阵强劲的季风,裹着海腥味直向密林中灌来。独臂立即支起了身子,它好像听见了一阵密集的鼓点。顿时,它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片铠甲都紧张起来。是的,这是催征的战鼓,那个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
独臂庄严地举起那只巨大的钳子,重重地敲了下去。大地震颤了,顺着树根,随着小草,传递给密林中的每一只红蟹。立刻,正在打架的,匆匆收兵;正在进餐的,拖着食物;一股股、一道道、一片片红流涌向震源——独臂的站立处。
不能说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密密的雨林中,一亿多只红蟹聚集在独臂或像独臂这样有威望的老雄蟹周围,推推搡搡,横冲直撞,吵吵嚷嚷,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搅翻了似的,聆听它们的首领发布命令。
这是出发的命令,预示着一个艰难困苦、危机四伏的历程。
这是告别的命令,预示着成千上万个出征者将客死它乡,永不回头。
然而,凡是四岁以上的红蟹,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谁也不肯放弃证明自己成熟健壮的机会,谁也不肯放弃繁衍后代生生不息的职责。它们义无返顾地追随着、簇拥着它们的首领,组织起一支支浩浩荡荡的红色大军,开始了一年一度奔向海洋的大迁徙。
三
一条公路,宽广、平坦,横亘在两片茂密的雨林之间,像不可逾越的天堑。
三百年前,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美丽富饶、绿荫如盖的小岛。紧接着,便是肆无忌惮地占领。随着一幢幢漂亮别墅、一台台采矿机械的出现,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铁路,也把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像生日蛋糕似的切割开来。
随着人类的占领,小岛的土著——红蟹的领地在不断缩小。它们从公路、铁路、矿井、住宅区、网球场,以及人类企图占有的一切领域里撤退,躲进密密的雨林中。它们不曾抵抗,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成年红蟹的甲壳只有成年人一只拳头大小,假如它们敢于违背人类的意志,便会像那些被砍倒锯断连根挖除的百年古树一样,死无葬身之地。何况,那些古树也要比它们大上百倍千倍。
但是,今天,它们却浩浩荡荡地开赴出来,聚集在这条公路边的林地里,准备穿越人类设置的封锁线。
比较起来,老雄蟹独臂率领的队伍是最为庞大的一支。它们由大至小顺序排列,摩肩接踵横向铺开,怕有万只以上。应该说,这也是行动最迅速的一支。因为它们最先到达森林的边缘,并且像一道闸门似的驻守下来,封住了几公里长的出路。尽管后面的一支支队伍仍像红色的海浪,一排排地涌过来,却无法冲决这道闸门,只好无可奈何地在它们身后的密林里趴下来,耐心地等待。
独臂的队伍也在等待。曾经十几次往返这条公路的独臂十分清楚,敢于顶着火球样的太阳穿越公路的队伍,必然全军覆没。但是,要按捺住这上万只红蟹的远征大军,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们初上征途,正是精力充沛、兵强马壮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参加远征的红蟹,没有恐惧,只有好奇。终于,它们当中最不安分的一些,挣脱了独臂的束缚,侧着身子爬出了森林。
阳光把公路照耀得明晃晃的,就像一条宽广的河流。
然而,这些年轻的勇士们,还没来得及爬上路基,摸一摸那条河,就全部毙命了。无一幸免。它们的水生祖先,为它们遗传下那么多像菊花瓣一样的海绵体——腮肉。这些退化了的器官,虽然不再具有呼吸作用,却可以迅速吸收或者散发水分。而一旦腮内的水分蒸发干净,无论多么强健的红蟹,也会一命呜呼。
现在,那些迅速出动,又迅速死去的红蟹,星星点点地铺缀在路基上,一动不动,就像一丛丛鲜红鲜红的罂粟花,警示着密林边上的跃跃欲试者。这些刚刚成年的红蟹,没有留下后代,没有见到大海,甚至没有参加第一次冲锋,就这样草率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公路上,卡车、面包车、小轿车来往穿梭,发出或沉重或尖锐的呼啸,几乎片刻不停。这是公路的占领者人类发出的警告,威吓着森林边缘那些蠢蠢欲动者。然而,当年那些望风而逃的红蟹,今天却不曾有半步退后。它们固执地聚集着,等待着穿越公路的时刻。
独臂用那只巨大的钳子微微支起身子,临风而立,仿佛威严的将军。身经百战的累累伤痕,沧桑岁月的重重印迹,它的甲壳不再鲜亮红艳,变成凝重的深红,并且布满暗淡的白色斑点。只有那双突出的硬硬的眼睛,还是通红通红的,配上顶端两点闪闪发亮的漆黑,就像两颗大粒的红豆。现在,这双眼睛就正在凝神注视着,那一点点黯淡的夕照,一寸寸蔓延的阴影。
独眼比独臂活得轻松。年轻时,它曾是密林中最英俊的雄蟹。它的甲壳没有一点杂色,像纯净的红宝石一样泛着红晕。它的两只大钳子,挥动的时候弧度很美,很有韵律,几乎能迷住密林中所有的雌蟹。两年前,当它和一只美丽的雌蟹抱在一起时,遭到了袭击。那时候,它还没有尝试过独臂的厉害。它企图抗争,结果,不但丢掉了情侣,还丢掉了一只眼睛。从此,它改变了很多,不再和别的雄蟹争抢打斗。无法改变的是,它仍旧喜欢向雌蟹献殷勤。现在,它就正在挥动着两只弧度优美、富有韵律的大钳子。
那是一只壮年的雌蟹,有着红玛瑙一样玲珑剔透的美丽。奇特的是,在它甲壳的顶部,也就是在两只眼睛之间,排列着五颗钻石样的白点,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腊梅。花点接受了无法抗拒的诱惑,侧着身子,向独眼移过去。可是,正当它直立起来,准备扑进独眼的怀中时,一只坚硬的大钳子,牢牢地卡住了它。
又是硬钳,那只横行霸道的年轻雄蟹。独眼立即趴在地下,转身撤退。它只能拱手相让,不能再丢掉最后一只眼睛。
当独眼转过身时,一只紫色背壳的雌蟹正好爬过来,它转动着紫幽幽的眼睛,大概是想引起独眼的注意。独眼却视而不见,从它身边绕了过去。雌蟹紫背犹豫片刻,追上去,重新拦在独眼面前,更加卖力地转动眼睛。这一次独眼站住了,它举起一只红宝石般的大钳子,却并不划出优美的弧度,而是一下子将这只四岁的小雌蟹翻了个仰面朝天,然后连看都不看一眼,便扬长而去。
雌蟹紫背手忙脚乱地挣扎了好半天,才翻转身子,它疾速退到身边的树洞里,躲进了浓浓的阴影。这只可怜的雌蟹,平时在密林里,只要敢接近别的红蟹,就会招来一顿痛打,没有谁会同情它、帮助它,谁让它有一个难看的紫色背壳呢?它曾经搬迁过一片又一片的森林,希望找到一个和它颜色相同的伙伴。最后它失望了,只好离群索居,卑微地躲避着那些有着鲜红背壳的同类。此刻,它也只能躲在阴暗的树洞里,眼巴巴地看着独眼爬到一只挺着大肚子的雌蟹面前,讨好地挥动着大钳子……
就在这时,大地震颤了。这是独臂发出的命令:总攻击开始了!
千万只红蟹像红色的潮水,涌出森林,漫上公路。没有多久,绵延六七公里长的公路上,全部爬满了红蟹,每公里的路面上,就有七千只红蟹在运行。这是对占领者的反占领。
人类是肆无忌惮的。卡车、面包车、小轿车仍然呼啸着在公路上奔驰。准确地说,是从千千万万只红蟹的身上轧过。这些红蟹趴在地上只有两公分高,不可能看见飞奔而来的汽车,何况,它们那些细长扁薄的腿,本来是划水的桨。如今,在地面上侧着身子,靠前面的腿抓,后面的腿推,每分钟只能爬行六米。在这里,死是必然,生是侥幸。鲜红的甲壳变为碎屑,雪白的肌肉变为浆汁。折断的钳子成堆,轧扁的长腿如纸,公路上的蟹血肉横飞。
然而,铺天盖地的红潮,仍然一浪接一浪地涌出森林,漫上公路。这些后续部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它们必须从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死难者身上翻越过去,简直就是翻越一道道的鸿沟。它们爬行得更加迟缓,而这种迟缓,又增大了死亡的概率。但是,此时,生存或死亡,强大或弱小,都失去了实际意义。天地间,只存在一件事,就是不顾一切地穿越公路。
起初,独眼和大肚子,还有硬壳和花点,都紧紧地跟在独臂后头,第一批爬上了公路。可是,肥胖的大肚子爬得太慢,且时不时地用钳子拽住独眼的后腿。于是,它们俩便落了下来,并且被不断涌上来的红蟹所淹没。天知道它俩是怎样通过公路的。有时候轰隆隆一阵,车轮擦着它们的腿尖轧过去。有时候黑鸦鸦一片,阴影向它们身上扑过来。它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拼命地、一刻不停地爬。它们几乎到达公路边缘的时候,独眼伸出一只大钳子,奋力一拉,将肥胖的大肚子甩下了路基。然而,就在同时,它听到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放炮声。接着,一辆闪闪发亮的天蓝色的小轿车,在它身前两米处停下了。一个穿米黄色皮夹克的年轻人走出来,俯身看了看汽车前轮,然后从轮胎上拔出一只红宝石样的蟹钳,恶狠狠地扔在地上。同时,“呸”地一声吐掉了嘴边的雪茄烟头,开始卸换轮胎。
独眼盯着那只红宝石样的、熟悉的大钳子,忽然感到了周身的剧痛。它的左半边身子已经被轧烂了,除了那只被车轮带走的大钳子。但是,它右边的钳子还能动。唯一的眼睛还看得见。它开始用剩下的一只钳子抓着地面,慢慢地朝前蹭去。它看见了那股袅袅的青烟,闻见了雪茄烟迷人的香气。有一次,它在密林中也曾找到过这样一个雪茄烟头,它把它衔在嘴里,爬来爬去,不知吸引了多少年轻美丽的雌蟹……
就这样,独眼一毫米一毫米地向前移去,它再也听不见汽车的呼啸声,再也感觉不到周身的剧痛,只是觉得青烟越来越近,香气越来越浓。当它终于艰难地把那支雪茄烟头放到嘴边时,它那只独眼却永远也不会转动了。
独臂在密林边重新集结它的队伍。不用说,这是一支九死一生的队伍。没多久,依然浩浩荡荡的远征军又向着密林深处进发了。它们必须抓紧时间继续赶路,天黑以后,它们的眼睛便失去功能,将寸步难行。肥胖的大肚子、美丽的花点以及数百只雌蟹始终落在队伍的最后头。它们频频地回首,似乎在寻找那双弧度优美、富有韵律的红宝石样的大钳子。然而,它们却只看见尸骨成堆、一片红色的公路上,一股淡蓝色的青烟,在苍茫的暮色里袅袅地飘升……
四
薄暮时分,独臂的队伍来到一条湍急的小溪旁。这里好像刚刚下过一场雨,林地里铺着薄薄的一层落叶,翠绿和桔黄交相辉映,上面还点缀着晶莹的小雨珠,更显得鲜美诱人。这里那里,一颗颗一串串鲜红、天蓝、深紫、乳白的浆果,半遮半掩地藏在落叶中,仿佛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拉扯着远征大军的脚步。湍急的溪水流得更加欢快,雪白的浪花在石头上撞起一尺多高,让十米八米外的远征队伍也能看得清。
饥渴、肮脏、疲惫不堪,不等独臂发出命令,这些刚刚从死亡线上冲过来的红蟹,就开始了行动。起初,它们贪婪地扑向那些落叶和浆果,用长腿扒,用钳子撕,用嘴扯。霎时间,林地里响起一片“嚓嚓嚓”的咀嚼声。当然还是少不了争抢和打斗,于是又有了钳子咬住钳子的“咔咔”声,以及败下阵者匆忙逃窜的窸窸声,紧接着,它们又奋不顾身地冲进了清亮的小溪。
随着“扑扑通通”、“噼里啪啦”的声响,雪白的小溪立刻变成了红色。它们紧紧地趴在一块块或圆、或尖、或凸、或凹的石头上,任沁凉的溪水从身上不停地冲过。于是,腮孔、花状海绵体、以及全身的肌肉都变得胀鼓鼓的;于是,背壳上、钳子中、腿毛间隐藏的尘土污秽,连同长途行军的困乏、死里逃生的惊惧,都一起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于是,这些不安分的小生命,又开始在溪水中游戏打斗起来。这个一膀子把那个撞个趔趄,那个一钳子给这个迎头痛击。谁不注意,就可能被掀翻,十脚朝天没着没落被溪水冲出好远。谁不小心,又会被一只大钳子夹住甩上岸去。
你瞧,那只美丽的雌蟹花点,更是别出心裁,它骑在一只甲壳很大的雄蟹背上,挥舞着两只红玛瑙似的钳子,得意洋洋地驱赶着那只雄蟹逆水爬行。那只雄蟹和硬钳同龄,只有六岁,但它的背壳却像独臂那么大,足有十公分。说起来,它的营养并不丰足,在林地里,它从来不和别的红蟹争抢甜美的浆果,甚至连鲜嫩的绿叶它也很少问津。它常常心满意足地咀嚼那些干枯腐烂的黄叶子。旱季前后,当这些腐叶也不够争夺的时候,它又常常心甘情愿地趴在洞穴里挨饿。这是一只温顺的雄蟹,当它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吃饱喝足之后,陪着花点玩玩,又算得了什么?
肥胖的雌蟹大肚子就是这时来到小溪边的。它姗姗来迟,是因为要喂饱它那只大肚子实在需要时间。它站在那里,盯着花点看了一会,然后就悄悄爬到大壳身边,抓住它的大钳子,直起身来,将大肚子一挺,美丽的花点就“扑通”一声被挤落水中。于是,大肚子取代了花点,骑着大壳,挥动着大钳子,顺流而下,好不风流。
说来也巧,花点落水恰好砸在紫背的身上,这只卑微的雌蟹,正津津有味地学着花点的样子,挥动一双紫色的大钳,驱赶着肚子下边的圆石头。飞来横祸,搅了它的乐趣,它立即夺路而逃。但是晚了,怒气冲冲的花点已经举起两只大钳子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好像挤它落水的不是大肚子而是紫背。接着,旁边看热闹的红蟹们也来助兴,纷乱的钳子、长腿此起彼落、穷追不舍,一直把卑微的紫背打得退到小溪边,趴在草地上,奄奄一息,不再动弹。
这时,温顺的大壳已经驮着大肚子、从熙熙攘攘的红蟹群中穿过,爬了很远很远,几乎到了小溪的尽头。在这里,红蟹越来越稀少,特别是在两米开外的地方,有两块巨大的白石头,把明亮的小溪挤得只剩下细细的一小股。欢快的溪水流到那里,就会“咕咚”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零零星星裹在溪水中的红蟹,也同样是一去不再回头。
危险的悬崖!大壳首先警觉地抓住了水中的石头。接着,大肚子也惊惧地抠住了大壳的后背。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随着一股巨大的冲力,它俩被冲散、掀翻,跌跌撞撞地朝悬崖滚了过去,就像水流中的两片落叶……
当沁凉的溪水将大壳冲得清醒时,它正直挺挺地立着,像一块红通通的小石头,卡在那两块巨大的白石头中间。一只又一只被水流冲昏了的红蟹,没头没脑地撞在它袒露的肚子和伸开的长腿上,又慌慌张张地顺着大石头爬上岸去。大壳挥了挥两只大钳子,背壳却没有挪动。一只接一只的红蟹朝它撞过来,它根本无法让开,尽管卡在那里十分难受。它眼睁睁地看见十几个伙伴向它撞来,又向岸上爬去。它还看见肥胖的大肚子已经朝上游爬了很远,正用大钳子敲着地面,警告着溪流中那些得意忘形的伙伴。于是,大壳便老老实实地卡在那里,看上去,仿佛是种舒适安逸的享受。
夜深了,红蟹群终于安静下来,露宿雨林。
在凝固了似的远征大军中,有一只肥胖的雌蟹动了动。这是大肚子,它那个难得填饱、却容易饥饿的大肚子,搅得它根本无法安宁。以往,在它躲进自己的洞穴中时,总是要贮备足够的食物,以便半夜里饿醒了时,摸黑大吃大嚼一通。但是,现在它们是露营,它的周围只有红蟹,没有食物。现在,一半是凭借小溪明亮的反光,一半是因为饥饿难耐的本能,它发现了那片飘落下来的绿叶,便忍不住朝溪边爬了过去。不过,大约爬了一半光景,它迟疑地站住了,侧过身来,看着仍然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声响的伙伴,听着猫头鹰扑腾腾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它趴在那里足足有半个钟头,然后,仍侧回身,朝小溪边爬过去。当它终于用大钳子和嘴撕扯着那片鲜嫩肥厚的绿叶,全神贯注地喂饱它的大肚子时,它却没有发现,几个浓重的黑影,正悄悄地包抄过来。
那是几只蓝蟹,它们的外貌和红蟹相同,只是比红蟹大上一倍。它们的甲壳、钳子和长腿都是淡蓝色的,在月光下反射出蓝莹莹的冷光,显得阴森森的,无法证明它们不曾是红蟹家族的一支。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它们的颜色变蓝,身体变大,行为也变得乖张凶残。在蟹岛上,它们的数量很少,但栖息的地方最好,常常是在水边或潮湿的树洞中。每年雨季,它们也要去海边繁衍后代,但总是走在红蟹大军的后头。它们要等着养肥了身体才开始远征,不是靠落叶、浆果,而是偷袭红蟹的军营。
现在,这几只凶残的蓝蟹,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把大肚子红蟹撕成了碎块。大肚子那肥嫩雪白的肌肉,连同海绵状的腮体,以及刚刚咽下肚子,还没来得及改变颜色的绿叶渣,甚至连它那两只肥硕的大钳子里的肉,全被贪婪的蓝蟹抢吃一空。转眼之间,它变成了一副空空的躯壳。
这时候,从溪边的大树洞里,又爬出来几十只蓝蟹,它们迅速地爬到红蟹大军的宿营地,迅速地抓住最边缘的一只又爬回来,然后大快朵颐。要不了多久,小溪边便堆起了红蟹的残骸。
最先警觉的是雄蟹硬钳,它立即用大钳子急促地敲着地面。于是,它周围的红蟹醒了,独臂也醒了。要是往年,经验丰富又顽强勇猛的独臂,根本就不会睡觉,它会精神抖擞地密切注视着蓝蟹的偷袭,并及时发出警告,组织战斗。但这一次,这只年事已高的老雄蟹,实在是太困乏了。
愤怒的红蟹群立即发起了进攻。尽管它们的眼睛不像蓝蟹那样适应黑暗,尽管它们的身体和钳子比蓝蟹小得多,但是凭着它们的数量,也能像洪水一样把蓝蟹淹没。
暗淡的月光下,森林不再沉寂,这里那时,一团团蠕动的黑影,一阵阵钳子的折断声,一直搏斗到密林中透进淡淡的晨雾,凶恶的蓝蟹群才仓惶逃走。
黎明的到来,就是出发的时刻,红蟹的队伍重新在林地里争抢咀嚼着落叶、浆果,重新到溪水中洗澡、吸水、嬉戏、打斗。同时,它们还聚在溪水旁边那一堆堆死难者的残骸旁,踅来踅去,闻闻嗅嗅。然后,便迎着季风吹来的方向,跟着独臂,继续浩浩荡荡的远征。
这时,密林中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透明晶亮的雨点,把溪水边那些空空的蟹壳,冲洗得鲜艳夺目,就像一滩滩殷红殷红的鲜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