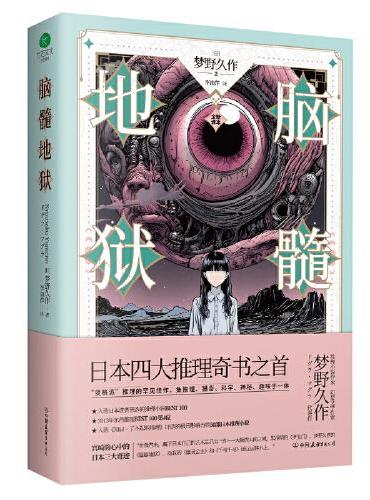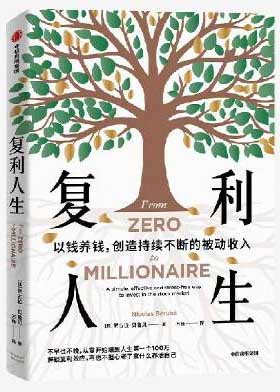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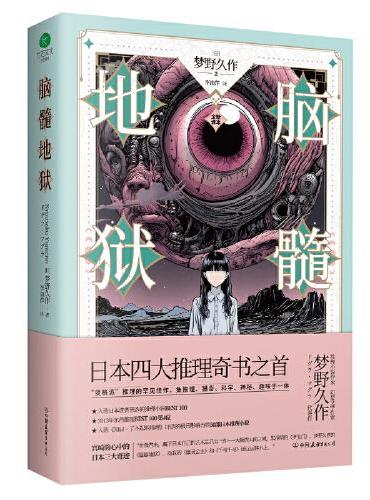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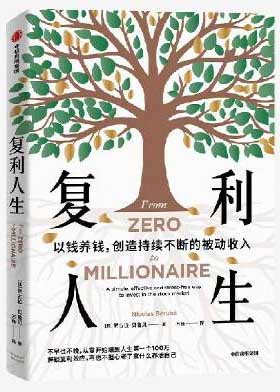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 編輯推薦: |
1.3个村庄+50位亲人 20年观察,看见他们,看见土地上樶为广大沉默的人群
“大多数中国人都如我的亲人一样,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本书中,作者黄灯历时20年观察,13年书写,以亲历者在儿媳、女儿、外孙女三种身份中转换,以微观视角深入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追踪50位亲人的命运流徙,展现中国农村在近二十年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真实境遇和复杂图景,引发读者对个体、乡村、时代等议题的深刻思考。
在黄灯看来,“没有谁可以漠视大时代呼啸而去的滚滚烟尘,没有谁的命运可以割舍与大时代的深刻关联。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
2.三个气质不同却各具困境的样本村庄,展现转型期乡土中国真实复杂的乡村图景
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黄灯从与自己生命产生紧密关联、气质迥异却各具困境的三个村庄出发,直面中国乡村的普遍性困境。丰三村代表现代性转型中被动的承受者,隐忍本分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凤形村展现乡村的活力与危机
|
| 內容簡介: |
“在亲人天聋地哑无法表达的境况中,我的写作,是一部三十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的经验史。我出入与我深刻关联的村庄,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
本书是非虚构领军作家、学者黄灯的作品,也是其代表作之一。继《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全国范围内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历时一年,爬梳整理13年来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追踪50位身边亲人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书中的他们面目不再模糊,而是“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起起伏伏,充满活力又潜藏隐忧。
身为亲人的黄灯,以文字重建与他们的精神联系,带给读者启发与深思。在时空的错落中,黄灯关注到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村落命运。在时代的裂变中,大地上的亲人们承受着个体与整体共生的命运。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
|
| 關於作者: |
黄灯,湖南汨罗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2016年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
入选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作品获“琦君散文奖”、“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奖、《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书(非小说类)、豆瓣年度图书等多种奖项。
|
| 目錄:
|
再版序言 用行动重建与亲人之间的关联 1
自序 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9
第一章 嫁入丰三村 19
一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21
二 我的婆婆和继父 42
三 兄弟姐妹的生存轨迹 64
四 打工记(一):第三代的出路 88
五 在惯性中滑行的生存 122
第二章 生在凤形村 139
一 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 143
二 素描:村庄里的亲人 167
三 打工记(二):出租屋里的叔叔辈 177
四 打工记(三):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 199
五 蹲守村庄的父亲 226
第三章 长在隘口村 249
一 村庄文化的根及 80 年代的日常生活 252
二 活力与隐忧,村庄当下的精神面影 276
三 打工记(四):我的同龄表兄妹 288
四 二舅眼中的村庄变迁 316
结语 如何直面亲人 343
后记 跨越时空的乡村书写 360
回望我家三代农民 367
附录 书中主要人物关系表 379
2006—2016 年访谈明细 383
|
| 內容試閱:
|
再版序言
用行动重建与亲人之间的关联
2017年2月,《大地上的亲人》出版后,我一直以为,这些以身边亲人为观照对象的文字,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在我印象中,他们在忙碌而繁琐的生存劳作之余,宁愿去打打麻将,宁愿去买买码,也不会去阅读一本和文学有关的冗长作品。
但很快,我发现这只是一种成见,从亲人们隐隐约约传递给我的信息看,我确信一旦笔下的文字与他们有关,其神色便显露出了一种另类的庄重:彩凤叔因为开饭店,交往的人多,有一次打电话郑重告诉我,必须准备两本签名本,以便送给一个认识的客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多次约我见面,只因杂事缠身,总是碰不上合适的时间,待到稍稍理顺,又碰上了持续两三年的疫情,我相信他读过书中关于妈妈的文字,我无意记下的,母亲对年幼孩子无条件的爱,可能会在某种时刻,牵引他回到少年时代,并勾起对早逝母亲的感念;还有七爹的外甥女明明,我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但她从我的简单记录中,梳理了妈妈的家族史,并对我生出了一份来自共同情感记忆的亲近;还有我的外甥女周婕,结婚后,她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年龄相近,初为人母,我们有着共同的育儿体验,她和我这个舅妈,总是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在我的相关帖子后面,不管她如何变幻化名,我总能辨认出她热心的留言;还有小敏,以前我是她大学任教的老师,她生性腼腆,对我总有一些生分,但在看到更多的来自文字层面的理解后,毕业多年,她反而愿意和我讲一些踏入社会的事情。更让我惊讶的是堂弟职培,因为婶婶去世时他才半岁,可以说对妈妈没有任何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这个字眼始终缺席于他的日常。弟媳婚后对丈夫的身世极为好奇,我对堂弟的叙述,成为她了解丈夫过去岁月的原始材料,在阅读中,她一点一点通过文字的连缀,还原了丈夫有限的童年片段。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在堂弟一家的聊天中,我早逝的婶婶,竟然会出现在自己仅仅陪伴了半年的儿子嘴中,仿佛她始终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注视孩子的成长,并未缺席堂弟艰难的长大过程。
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彼此都羞于公开谈论表达和被表达的话题,但不能否认,不同年代的亲人在书中的同时出场,事实上可以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中,促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理解和看见。我和身边的亲人,依仗文字,不经意中,也由此建立了一种隐秘的关联:我会持续关注他们的命运,他们也会暗中打听我最近的消息。
五年过去,面对已经定型的作品,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依旧是不知如何叙述笔下变化的村庄和亲人。文字的有限性,一方面,让我意识到非虚构作品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也让我进一步确信了记录的价值和意义。翻开泛黄的书页,我能回到当初和他们相处的场景,在字里行间,我再一次看到他们在各个角落的生存剪影。相比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现实图景,这些拙朴的印迹,帮我记住了亲人们曾经的气息和身影。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发酵,目睹他们的挣扎和韧性,我越来越感知到彼此之间牵念的珍贵,并进一步确信,哪怕平淡地活着,也自带庄重的尊严。
毫无疑问,我笔下的村庄,无论是丰三村、凤形村,还是隘口村,在这短短几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它们的面貌产生了切实的改变。以前的泥泞和石头小路,在“村村通公路、户户通公路”的惠农政策中,变成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硬化路面(隘口村甚至铺设了柏油路);村容村貌也变得更为整洁,垃圾满地的情况获得了根本改观,三个村庄都配备了统一的垃圾收集场地;随着道路的优化,孩子们念书也变得更为方便,就算村里没有小学,镇上小学的校车,已经可以便捷地来到村口接送。每次回家,我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所引导的资源,实实在在流向了更为广阔的乡村,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不少改变。
不能忽视的是,在乡村面貌改善的同时,也伴随了新的问题,其中最让村民诟病的,是村庄诸多工程的华而不实,诸如建牌坊、修凉亭、修健身场地、修小花园,甚至是大兴土木地建广场,几乎清一色地模仿城市居民需求,呈现出竞争性的面子工程特征,不但耗资巨大、使用率低、折旧快、保养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在地化实践,没有更多尊重村民的参与,事实上没有很好匹配村民的真实需求,在资源配置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养老和医疗的迫切需要。
面对城市发展的收缩状态和乡村条件的日渐改善,我留意到笔下的亲人,根据各自的条件,也作出了不同选择。
一部分人选择回流故乡,他们主要为年龄偏大、劳动能力减弱的群体。诸如,小珍叔,尽管在多年的打工岁月中,被人称作“跑江湖的人”,但随着年岁增加,还是回到了凤形村,在孩子们相继成家立业后,依照乡村的习俗,她挑起了带孙子的重任。事实上,我丰三村的哥哥和在街边依靠缝补送孩子念书的瑛国叔,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养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养老这个词,某种程度上,甚至算得上一种奢侈的结局。我的哥哥,因为生病,于2021年12月突然去世,只活了五十八岁;瑛国叔在孩子考上大学后,回到故乡没多久,也因病离开人世。他们活着时,尽管面对养老的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晚年的生活,还是有过美好的描述。可以预测,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因为生命的透支状态,一定会面临很多与疾病相关的挑战。让人安慰的是,哥哥的两个孩子结婚后,还算懂事,振声能主动挑起家庭的重担,一直坚持在外打工;时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能意识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她和丈夫在家乡小镇上经营了一家快餐店,劳动之余还不忘照顾身边的老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已经在西安成家立业,一切都还顺利。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依旧留在城市,他们主要为家庭负担重,在乡村找不到营生门道的群体。诸如,彩凤叔,尽管五十多岁了,但因为儿子勇勇尚在部队服役,还没有成家立业,加上建房子欠下的债务一直没有还清,她和丈夫魏叔,依旧选择留在三元里瑶池大街经营快餐店,只是随着广州流动人口的减少,他们的生意远远不如以前。还有我前面提到的丰三村侄子振声,因为长辈劳动能力的减弱,孩子开支增大,在老家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依旧留在东莞的工厂。同样让人欣慰的是,留在城市的人,诸如我的表妹春梅,选择进入表妹鸿霞的公司后,因为和丈夫勤劳肯干,加上为人诚恳,又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在公司极受领导和同事喜欢,在亲人资助下,他们在东莞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算是彻底安了家。而她对教育的重视,也终于迎来了成果,儿子琪荣在西北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面对2021年激烈的考研竞争,顺利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算是成功上岸。
拉开时空距离,我越发确信一点,我笔下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亲人,他们命运的流转,和这个时代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关联。他们无论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都和大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就业形势好,经济环境好,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就能拥有机会找到一个立足的位置;就业出现困难,经济形势恶化,他们作为最脆弱的群体,必然首先受到牵连。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
从写作的层面看,《大地上的亲人》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回过头审视,我发现这部作品,无意中包孕了我此后写作的基本母题。以近两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为例,尽管它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大地上的亲人》,但我知道,“二本学生”的话题,不过是“亲人”话题的自然延续。在“打工记(一):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二):出租屋里的叔叔辈”,“打工记(三):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中,作品提到的丰三村兄妹的孩子小敏、周唯、媛媛、沈亮,凤形村姑姑的儿子李炫、瑛国叔的儿子冯超、隘口村表妹鸿霞、春梅的儿子琪荣,他们的遭遇,都是中国不同年代二本学生命运的具体演绎,我不过从家族的微观视角,对这个群体进入社会的过程进行了粗疏的勾勒。我不否认,这种来自身边亲人的切近观察,让我对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来路和去向,滋生了更为直观的感知。说到底,无论关注的对象是身边的亲人,还是讲台下的学生,如何尊重个体在转型期中国的人生经验,如何通过非虚构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一复杂现代性经验的观察和思考,始终是我写作的焦点。从《大地上的亲人》开始,我就锚定了这一原点,并一直围绕它所包孕的视域,坚持创作实践。我想,这是我对这部并不完美的作品,格外珍惜的原因。
最后,说说家里的一件事情,表面看来,这件事和作品无关,但我始终认为,《大地上的亲人》作为文字形式的纸面驻留,反而坚定了父母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1987年,我们全家搬离凤形村,父亲退休后,一直念叨要回家,但因为老房子早已倒塌,无法居住,加上兄弟姐妹没有一人留守故乡,我们姊妹一直以老家无人照看为由,劝说他们不要回去。2020年,疫情稍稍缓解,已经离开故乡三十三年的父母,在辗转各地将孙辈带大以后,在双双七十一岁高龄时,再一次坚定了要回到村庄居住的心愿。他们不能容忍生养我们的土地,仅仅作为一个地名停留在我的书中,面对葬在故乡山岗的祖辈,这种长时间远离故土的疏离,在父母看来,无异于一种情感的背叛。这种强烈的回乡愿望,对我触动极深,父母的举动,第一次让我真切感知到“故乡”二字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乎是他们这辈子对我们子女的唯一诉求,老人的坚定,消除了我们现实层面的顾虑,支持他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回到故乡找到通道。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家人终于在已经废弃的旧居旁边,和堂弟职培共同建起了新居。
回到村庄的父母,像是重新激活了人生。这种彻底释放的状态,让我意识到他们为了生计,被迫远离故土的选择,多少是一种心灵的苦役。只不过在多年的忙碌中,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亲近土地的母亲,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劳作,养猪、养狗、养鸡、养鸭、养鱼,成为她的日常,家里再一次呈现了六畜兴旺的局面;辣椒、茄子、丝瓜、南瓜、空心菜、白菜,红红绿绿的就在屋前屋后,目力所及之处一片盎然。我当然明白父母的放松,来自退休生活的坚定屏障,但回到故乡的笃定,事实上帮我链接起了和故土的情感牵连。
2021年9月6日,在离开旧居整整三十四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湖南汨罗三江镇凤形村垛里坡—过夜。月光皎洁、万籁俱寂,我熟悉的一切,仿佛从未远离。爷爷当年挖下的池塘、水井还在,奶奶曾经纳凉的竹林还在,二十六岁离世的婶婶洗衣服的桥板还在,旧居埋在土里的石板门槛还在,我童年看过的星空还在,深夜凉风刮过竹林的沙沙声还在。
三十四年的光景,不过一个长长的梦境,我惊讶地发现,我多年来一直寻求的安宁,竟然在这一时刻神奇地充溢内心。第一次,我深刻地感知,相比用文字重建与亲人之间的精神联系,回乡的举动,才是行动层面和故乡亲人建立关联的开端。
借拙作《大地上的亲人》再版的机会,面对故乡,我要再一次深情地告白:无论离开多久,我始终是村庄的女儿。
2022年6月2日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民的前景等等问题有密切关联。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到他家过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曾私下问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 :“哥哥虽然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贫苦家庭的男子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我后来才得知,公公、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我认识她十年来,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我们竟然很自然地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大约七十五岁,身体还不错,小侄子十五岁,小侄女十二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替他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大家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早在90年代末,他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予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的她,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待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们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于是,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不适合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如果待在家里,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收入,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尽管在丈夫的资助下,家里在1998年已经建起了房子,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怎么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往好的方向走。每次得知寒暑假我们要带儿子回去,哥哥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 ;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妹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团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了问题。由于有单位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工程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这不但导致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哥哥、嫂子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拿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四姐一家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经济一直算是宽裕的,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可以接济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 ;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血汗钱,我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打电话向我们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问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她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不可避免地落到我们身上)。2015 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撑。想到90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被拖欠工程款,不得不隐匿在一个角落里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她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时,认识了本厂一个正式工,两人结婚,发展得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元一平方时,他们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 ;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来广州玩,也时常向我们宣扬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断然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
尽管从信仰的角度,我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让人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的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赶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妹妹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头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做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她就迫于舆论压力,草草休学。
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里采地菜时快乐地疯跑,脑后的红色蝴蝶结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妈妈执意出家的定,竟然让她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受到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怎么也想不明白女儿出家一事,只要家里有人来,她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