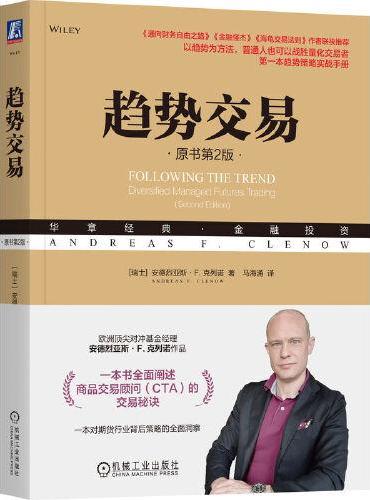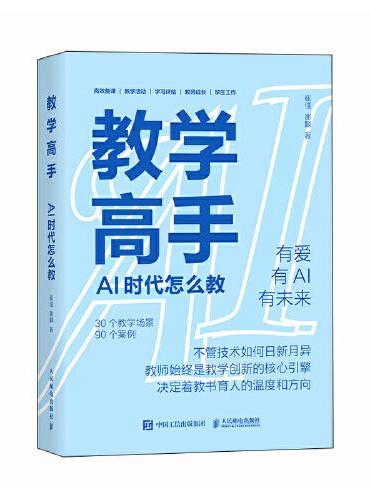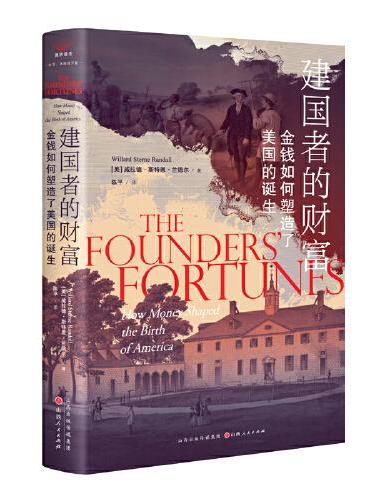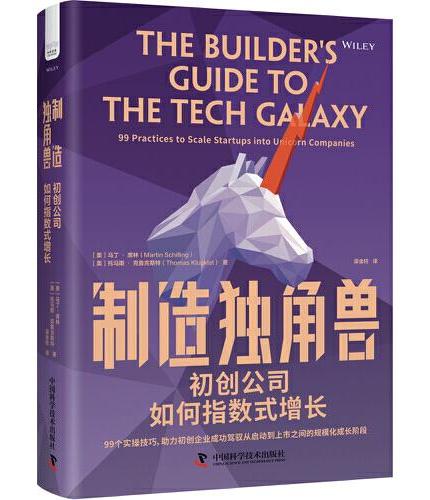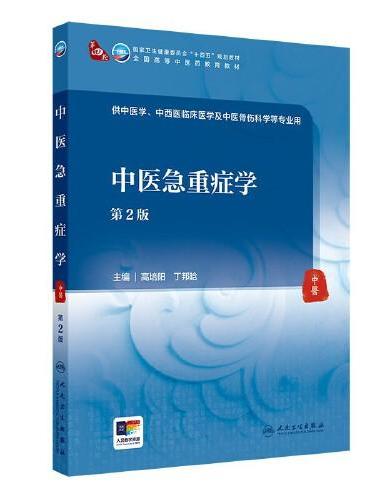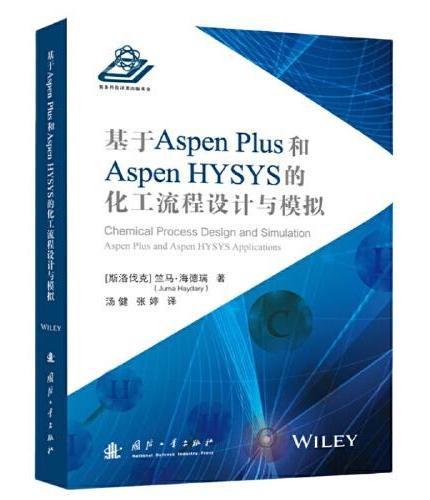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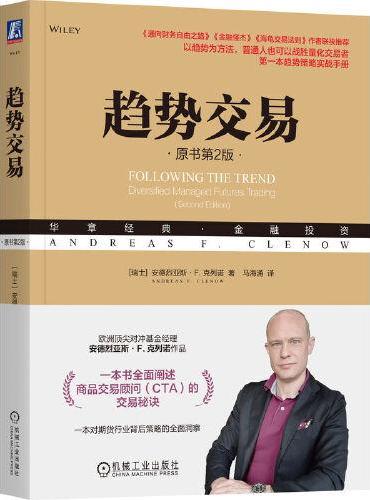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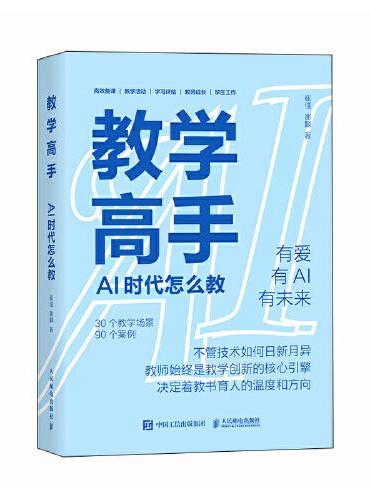
《
教学高手:AI 时代怎么教
》
售價:HK$
65.8

《
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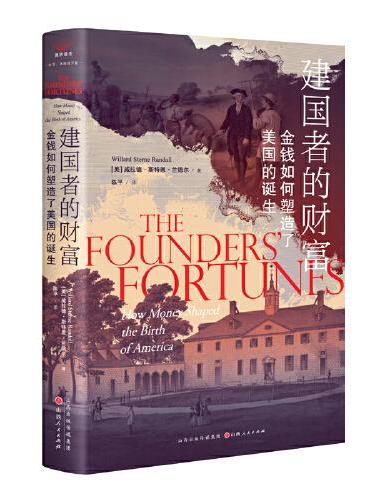
《
建国者的财富:金钱如何塑造了美国的诞生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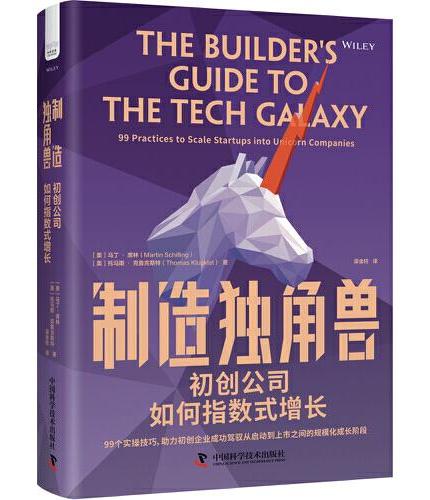
《
制造独角兽:初创公司如何指数式增长
》
售價:HK$
86.9

《
绿色黄金 : 茶叶、帝国与工业化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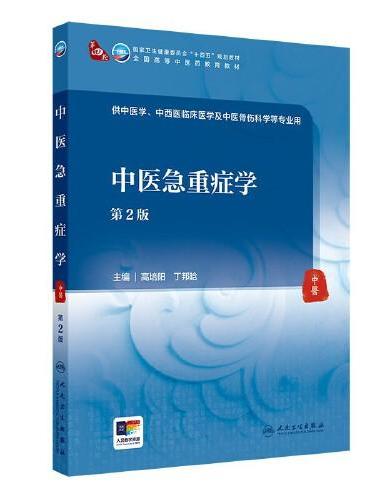
《
中医急重症学(第2版)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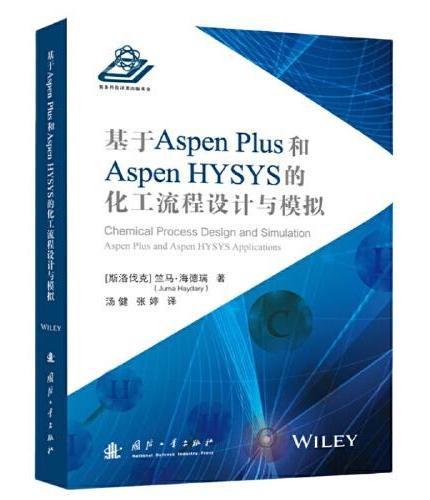
《
基于Aspen Plus 和 Aspen HYSYS的化工流程设计与模拟
》
售價:HK$
217.8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是许倬云先生亲自认可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自一本书里了解汉代农业的方方面面,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奠基于这种独特的农业模式概言之,汉代农业的特点是:小农经营的精耕细作方式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塑造出一种独有的农村经济模式
|
| 內容簡介: |
中国的统一在汉代得到巩固,而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似乎也在汉代确定,通过汉代农业来考察中国农业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倬云
由此,作者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汉代农业的种种情况:政府解决人口与土地问题的措施,土地成为被追逐的财富,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种方法与技术,农作之外的选择等。作者强调,中国精耕细作式农业以及以农业为基调的经济,其关键转换点在汉武帝时期。
与通常认为的不同,作者经过考察和分析发现,汉代的农业以小农户的小规模农作和劳力投入密集的精耕细作为基调;且汉代的农作方式具有相当的可调试性,根据时代、政治、经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以及土地本身的状况而适时变动,在不同的具体耕作方式间灵活转换。这种个体农户的精耕细作农业又与市场经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重商的农业经济模式,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也建基于此。
|
| 關於作者: |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年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获台湾大学“人文艺术类杰出校友奖”,2020年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
许先生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中西文化比较。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等,另有大众史学著作“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及《经纬华夏》等数十种行世。)
|
| 目錄:
|
导 论
第一章 政府对人口和土地占有问题的应对
农业和人民
对土地占有的限制
非经济措施
人口的迁徙和转移
政府公地的开发
小 结
第二章 土地成了被追逐的财富
工商活动的发展
对工商活动的限制
国家打击豪强
皇帝宠臣与权贵
地方权贵
地主制度的发展
结 论
第三章 农民的生计
地 主
佃农和其他农业劳动力
自耕农和小规模农作
农户的支出
第四章 农业资源
农作物
土壤及其改良
水利灌溉
第五章 耕作方式与方法
农作规模
一年多熟的体系
新耕作模式——代田
新的耕作方法——区种
水田耕作
农 具
小 结
第六章 农作之外的选择
Z活动
生产与市场销售
移 民
屯 田
农民起义
小 结
结 论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日文著作
西文著作
索 引
译后附言
|
| 內容試閱:
|
导 论
本卷研究的是汉代(前206—220)农业的发展。由于中国的统一经秦的短暂统治之后,是在汉代得到了巩固,而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似乎也是在汉代确定下来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通过研究汉代农业来考察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基本现象之一—悠久的农业文明,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中国的发展定向于斯也并非一种历史的定数。在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可能性,即发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当时,庞大繁华的市场中心四处可见,赚钱盈利和契约互惠的市井心态也盛极一时,这两种情况都是商业繁荣的沃土。[1]甚至在汉朝最初的一百年中,帝国政权也一直是在和颇具影响力的城市首领们进行斗争,这些人具有社会实力,对政治权威形成了威胁。[2]
我的意图正是找出两汉时期促使中国转变为农业经济的一些关键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汉以前,即战国时期的农业。
铁器工具的广泛应用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通过对古代聚居地和墓葬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工具,还在铁匠作坊的遗址中发现了用于铁器铸造的模具。这些器具的外形在不同的地区差别不大,虽然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从大类上讲,它们分别属于锹、锄、镰、犁、刀、斧和凿等。这些工具的形状和大小表明了它们在不同耕作阶段中的用途。考古报告中记载的锹和锄的数目,揭示出除草和松整土地大概占去了农民从播种到收获之间的大部分时间。换句话说,战国时期的铁器工具是农业精耕细作已经开始的证据:铁制的斧子和凿子在伐木造田中是非常有用的;铁制的犁铧可能意味着畜力牵引耕作已经开始,这从使用挖掘工具的手工耕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铁制工具比木制、石制或贝制工具更锋利,也更结实,但战国时期的铁制工具都是用模具铸造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比较轻。在辉县发现的犁铧,是在木制犁身上安装的一个“V”字形的小铁片。由于没有隆脊,又是钝角形状,这种专门作为木犁切割刃使用的犁铧,不可能进行深耕。因此,尽管战国时期的农耕是精耕细作的,而且很可能利用了畜力,但是与汉代的农业相比,它所达到的水平还是较低。[1]
战国时期曾修建一些灌溉系统,有一些规模还相当大。不过相比于秦汉时期的灌溉及治水工程,它们还是小型的,而且只见于渭河、漳河与山西诸河流域,以及淮河流域中的一小部分。例如,在黄河流域东部,最早的规模较大的灌溉系统是天井堰(约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末),它覆盖的不过是沿漳河20里的区域。由郑国的一位工匠在秦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规模是天井堰的十倍多。然而,汉代于公元前95年在泾渭流域修建的水利工程白渠,长度却达到了200多里。[2]大型水利工程的普遍兴建,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在汉代尤其有重要的发展。汉代的这些努力导致可耕地的扩展,木村正雄将之称为“次级农田”(secondary farming land)的形成,认为这是与古代帝国形成有关的条件。[3]正如考古证据所表明的,汉代以前的农用水源,较多来自田地附近的池塘和水井,而不是来自大规模的灌溉系统。[1]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尽管战国时期的水利成就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不如汉代,但它确实为汉代水利工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汉以前人们主要的谷类食物是稷、黍、麦和稻。稷和黍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它们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只是到了战国时期,麦和粟才获得了基本食粮的地位。豆类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流行作物,在山区尤其重要。稻米则仅限于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那里多沼泽的地形为人们提供了水源充足的天然稻田。[2]因此,在中国北方,也就是当时“中国”所指的范围,所有主要的作物都是旱作物,水利对于它们不像对于种植水稻那样重要。[3]
在战国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几项农作原则,它们日后对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一直具有指导意义。其中的一条就是重视农时。正如孟子论述的那样,儒家学说里的理想政府,是绝不会妨碍人们适时耕种的。孟子认为,在农田中的及时行动,要胜于拥有利器良具。他一再指出,如果在耕种百亩之田时不误农时,一个八口之家就不会有饿饭之虞,一个国家也能得到超出消费需要的充足的粮食。荀子在很多方面都激烈地批评孟子,但他对于不误农时的重要性却没有异议。荀子说,如果在春耕、夏锄、秋收、冬贮时不误农时,那么就会五谷丰登。[1]
在中国北方,霜冻来得早,春季时水分又蒸发得很快,人们确实不得不抓紧农时迅速行动,以便让农作物有最充足的生长时间。
古人还强调深耕的必要性。当然我们应当明白,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深耕。中文“深耕”这个短语的更为合适的英译可能是deep tilling。在古代的文献中,深耕这个词后面往往还跟着“细作”,它的意思是“通过打碎土块和铲除杂草而彻底地整治土地”。在中国北方,只有将土地的表层在翻耕之后打碎成可以覆盖耕地地表的细小颗粒,干燥的黄土地才不会很快失去水分。同时,种子深播于土壤里,就可以吸收来自地下水的水分,得到矿物质和有机质的滋养。[2]田间作业在整个作物生长期内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包括铲除杂草、翻松土地、给作物培土,以及加深畦间平浅的排水沟等。这种工作需要农民全身心的关注,中国农民在这上面付出的劳动和时间,超过了播前备耕和收获时所需劳动和时间的总和。在出土的各种战国时期的工具中,锹和锄在数量上最多,这有力地说明,使用锹和锄进行土地修整是当时农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在战国时期,肥料的使用非常普遍。很可能早在商代,动物和人的粪便就成了最常用的肥料。当时指称肥料的文字恰好就是表示粪便的文字。孟子曾说,一块百亩之田,如果施以粪肥,并由能干的农夫耕作,就足以养活九口人,但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即使施肥也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荀子和韩非解说过《老子》中一段涉及马粪的话,这段话是在讨论粪肥利用和农田灌溉时讲的,而施肥和灌溉都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增加财富。[1]
早在《诗经》的时代,人们就向神祈求摆脱蝗灾和其他虫害。但《诗经》里这首求祷的诗中还提到了火,因此很可能人们是将害虫捕捉到一起,用火烧死,或者是在耕种土地前放火烧田除虫。[2]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在进行农田整治以灭除虫害时,所依靠的完全是自己的双手。
《吕氏春秋》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由秦国的相国吕不韦召集众多学者编纂而成,其中的《任地》、《辨土》和《审时》三篇,很好地概括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可能都是些对农事并无第一手经验的文士,因为文章中提供的情况有些支离破碎。不过,这种知识也很可能是代表了当时最为成熟的技术,因此甚至理论家也将它们确定为基本的农业原则。这三篇文章的文本非常简短,一些部分多有讹误,需要古籍学者和农业史学家做出大量努力,以恢复它们的原意。[1]
《任地》开篇假托传说中开创了农业的文化英雄后稷之口,提出了十个问题:“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畎浴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2]这些问题揭示了战国末期的农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从土地整治、田间作业、庄稼种植、水分保持,一直到农作物的水源供给。但是最佳的庄稼长势仍得依赖适时的行动。因此,《审时》全篇都是讨论“适时”生长的庄稼与非适时生长的庄稼之间在生物形态上的差异。文章中涉及的作物有粟、稻、黍、麻、豆和麦。概括地说,《审时》这篇文章指出了适时种植的庄稼,要比过早或过迟种植的庄稼有更多的收成。抓住了农时的农民相比于耽误了农时的农民,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而且这些粮食分量更重,味道更好,营养也更丰富。文章对六种农作物的变异情况进行了简洁的描述,指出过早播种的庄稼容易只长枝叶,不长果实;而播种过迟则使果实缺乏充分的生长时间。[1]
《任地》与《辨土》这两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互为补充的。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大致是土地的治理和土质的改良。《任地》在提出十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认为农民事实上可以改变田地的状态,为农作物提供更好的土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2]当然,这些原则主要涉及的是土壤的改良。施肥是改良土壤的一种手段,《任地》中说得很明白,将粪与水同时施用,可以使农地变得肥沃。但仅仅这样尚不足以得到理想的地况,还要进行效用广泛的田间管理,而经常性的翻耕也可促进土地的肥沃和松软。认真地进行五遍翻耕和五遍锄草整治,可以使农作物的根深深植入下面湿润的土壤里,并避免长草和虫害问题,因为深层土壤通常能避免这两种东西。坚硬、黏质的土壤的水分较难保存,必须优先耕种。[3]这类农活事实上要求人们在种子下播之前就得付出大量劳力。
《辨土》的作者警告说,原本会有的好收成可能因三种情况而被毁掉:(1)农作物安排无序,挤在一起,相互妨碍生长;(2)垄沟占地多于庄稼占地,造成农地的浪费;(3)放任杂草掠抢地肥。作者建议,庄稼应一排排平行地种植,每排之间相隔一尺。如果农田地势高而且干燥,庄稼就应种在垄沟中,从而可以受到两边垄脊的保护,并吸收垄沟底部的水分。
如果农地低洼潮湿,庄稼则应种在垄沟之间的垄脊上,以防止水分过多。除了因地制宜之外,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充足的生长空间也都是对农作物有好处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提示,即好的收成取决于农作物的合理密度。如果三棵以上的庄稼长为一簇,就应将较弱小的连根拔除,以使较强壮的庄稼有更多的空间和养料。[1]
当然,很难断言在战国时期,这种先进的农业耕作是否已经普及。不过,撰写这些文章的学者却是从真实的实践中抽象出自己的理论的。
所有这些论述农业技术的文章都表明,战国时期的农业正在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而中国的农民直到今日仍在继续发展着这种集约式的农耕。这种精耕细作,即使是在战国时期农业那种相对初级的水平上,也需要巨大的劳动力投入。诸如《孟子》和《荀子》这样的古代文献,都假定一家农户的标准土地拥有量应是100亩。[2]一家农户则被假定有年迈的父母、一对夫妻和四个孩子,即一家八口人。这样一个农户要种植自用的全部蔬菜,饲养提供食用肉类的禽猪,纺织家庭所需要的丝绸(以及或许更重要的麻布)。孟子在其所倡扬的井田制理想中,设想了一种基本的农业共同体。共同体由八家农户组成,每个农户可以从君王那里领受100亩农田,另外还有5亩的土地用来居住和植桑养畜。这8户人家要共同耕种保留给领主的另外100亩土地,算作徭役。[1]这种理想化的土地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孟子的均平乌托邦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古代中国封建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土地是恩赐的特权,而劳役则是一种偿报形式。[2]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种在规模不超过主干家庭的小农户内部进行小型农作的图景。这种制度显然已相当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典籍《诗经》中描述的那种农奴制。农奴们虽然也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但他们是从领主那里获取包括衣服或许还有食物在内的生活物品的。他们在领主代理人的监督下,成百上千地一起结队耕种主人的土地,种出的粮食也都进了主人的粮仓。[3]如果西周时的情况确是如此,那么当时的封建领主可能还在扮演着军事殖民者和征服者的角色,以各地居民为农奴,以征敛的粮食作为自己的收入,当然,其中的一部分要归入更高一级领主的粮仓。[1]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制的国家被君主制的领土国家取而代之。随着封建社会解体,封建领主无法再拥有采邑和农奴,独立的农民便开始出现了。导致独立农民出现的因素不止一端,其中包括使用铁器工具开垦荒地,以及旧式封建贵族在国内和列国之间权力斗争中的衰落等。在新的君主制国家中,君主成了所有属民之上的唯一主人,无论他们是官宦还是农民。[2]
在战国时期,独立的农民摆脱了封建贵族,但是却没有脱离国家的控制。当孟子建议理想的井田制方案时,他似乎视为当然前提的是,国家拥有合法的权威和权力去改变民有土地的大小,并将这些土地分成均等的地块。在战国君主拥有的那种权威之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完成。孟子曾向滕文公提出其井田制设想,如果滕文公采纳这一建议,他很可能真有能力付诸实施,因为战国的国君确实直接控制着一些土地。《孟子》中还提到了一些农学家,即许行及其门徒,他们来到孟子当时所在的同一宫廷,就是请求国君赐给他们一块土地,并接受他们为臣民。[3]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推断说,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对某些土地确实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些土地被称为“公田”。[1]根据增渊龙夫的分析,族长在带领族人筑城建立城邦国家时,可能会在城市之外为自己保留一块专用的地区。尽管城邦集体(或更确切地说,城邦的整个统治集团)应当已经拥有城市附近大片的荒地,但在初始阶段,族长为自己划定的区域仍可能不是其绝对“专有”的。例如,《孟子》中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其中孟子提到周文王的苑囿是对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在里面采集薪草、捕猎鸟兽,而齐宣王的苑囿却完全是封闭的,这种差异表明,随着君主权力的增长,君主对公田的垄断也日渐增强。[2]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这类“苑囿”的名称,其中有一些面积辽阔,例如楚国的云梦泽包括长江中部的整个湖泊区域。这些所谓的苑囿可能不仅包括专门保留下来的狩猎场,而且包括所有因地理状况不好而未开垦的荒地,如山地、森林、沼泽和低地。这些荒地很难用石制、木制或贝制的工具加以开垦,但是当铁器可以较为便宜地得到时,人们就能够砍伐森林中的巨木,或者在沼泽地区挖沟掘渠排除积水了。到了孟子的时代,像许行和其门徒这样的农人,都是带着他们自己的工具周游四方的。[3]此外,根据一部编年史的片断记载,与孟子同时代的梁惠王,将他在逢忌泽的土地赐给了人们。[1]
有意思的是,同是这个梁惠王,曾经表示对人口增长停滞的担忧。[2]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存在着大量的荒地,而劳动力又有些不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墨子确认了这一事实,他指出,任何一个大国,即那些拥有万乘战车的国家,都拥有相对于其人口来说太多的土地。[3]不过,在《战国策》中,却含有与这两个说法相矛盾的记载。据说在魏国,到处都是房屋和农田,以致没有地方可作为牧场,来往的人流和车流看上去就像大批的军队在行进。[4]友于曾试图解释这种矛盾。他提出,战国时期各国的人口,特别是包括魏在内的六个东部国家,对于已经垦殖的土地来说是太多了,但是对那些尚未开垦的大片地区来说,还是较少的。[5]如果人们在被允许迁徙到他们能够得到新土地、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之前,不得不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地区,那么一个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助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能处置的那一小块土地,由此便产生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因此,战国时期标志着中国农业至少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向集约化耕作发展。这是人多地少的压力的后果,也是制度约束和技术限制的自然结果。
随着农耕集约化压力的不断增大,按照传统习惯让土地休耕已经不再可能。人们开始种植豆类作物,以恢复土地的肥力,结果使豆类成为最普通的食品之一。如果《氾胜之书》也反映了战国时的情况,那么当时有40%的农田是用来种植豆类作物的。[1]
多种作物轮种的做法代替了休耕。《吕氏春秋》中提到,在松土锄草各五遍并进行深耕之后,人们可以指望在年内得到谷子的好收成,而在下一年则可得到麦子的好收成。[2]即使土地没有了休耕期,轮流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也可使土地的地力不会枯竭。
与战国时期农业技术变化相对应的,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在一些国家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政治改革尝试,也对农业产生了影响。[3]当然,效果最卓著的,是商鞅在秦国进行的改革。他通过改组地方行政单位,将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建立起一个在强大的地域性君主国家控制下的社会。[4]官方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承认,实际上体现了自由而独立的小农此时的重要地位。
秦国的农民在服兵役时便成为士兵。按照战功行赏晋爵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处于一种介于真正的贵族和旧时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农奴之间的位置上。[1]同时,秦国还是唯一一个充分而系统地利用公田吸引外来劳动力,从而促进全国农业生产增长的国家。商鞅主导的战略思想,就是把秦国本国的劳动力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到秦国之外征战,让外来的劳动力代替他们从事生产。[2]这些移居秦国的新移民,虽然社会地位不如可以靠战功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秦国公民,但仍然是一种新型的农民,他们新开垦的土地不再受到封建采邑的束缚。这些自由的小农拥有他们正在耕种的土地。[3]
当秦始皇让人刻石谕示,已不再是封建农奴的自由农可以通过务农而致富时,他的话似乎确实有事实依据。[4]秦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朝,正如贺昌群所认为的,这个朝代代表了一次社会革命,它造就出自由独立的小农,反过来,正是由这些小农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又支持了这个新的政权。[5]汉朝将从秦朝继承这同一小农群体,作为帝国权力的支柱,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是这样。
(此处的书摘略去了注释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