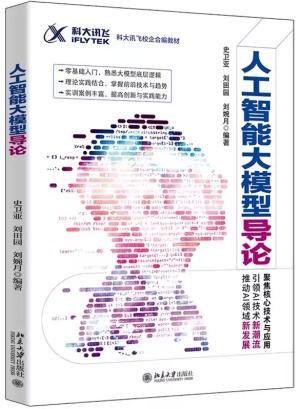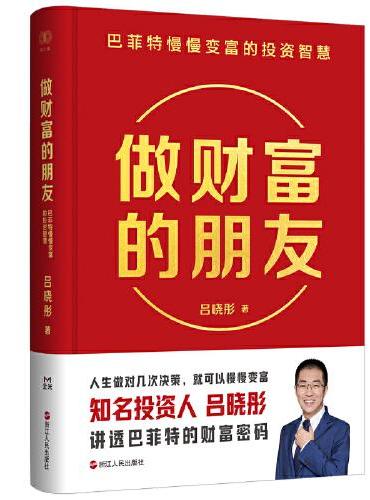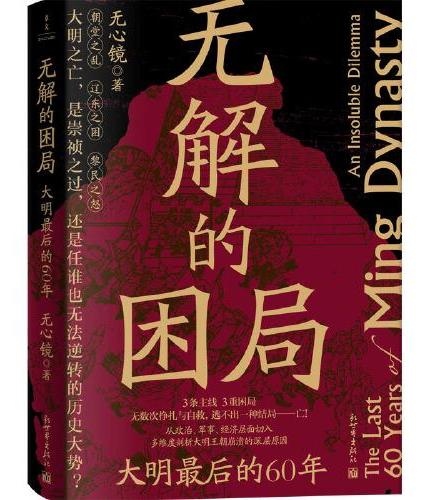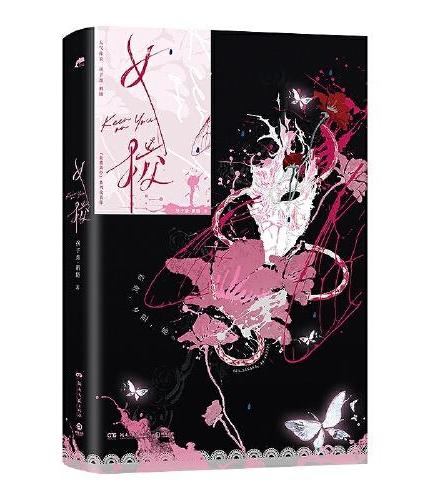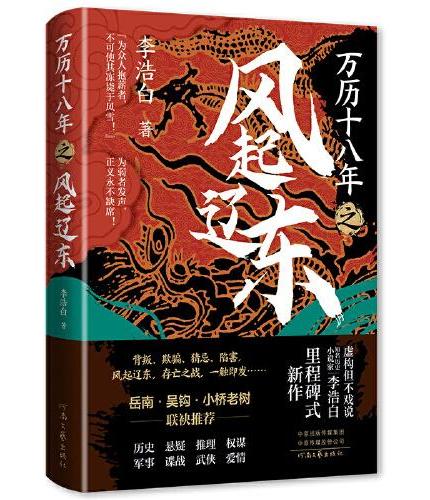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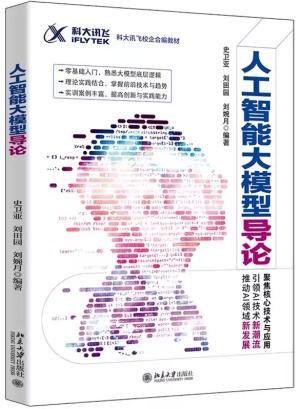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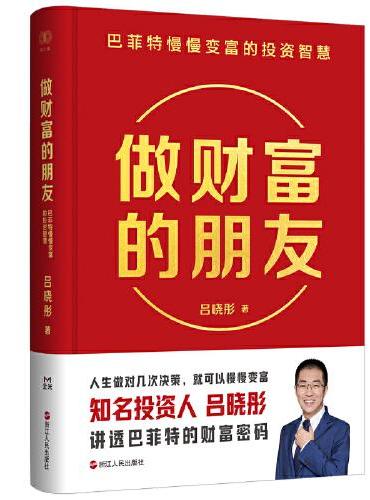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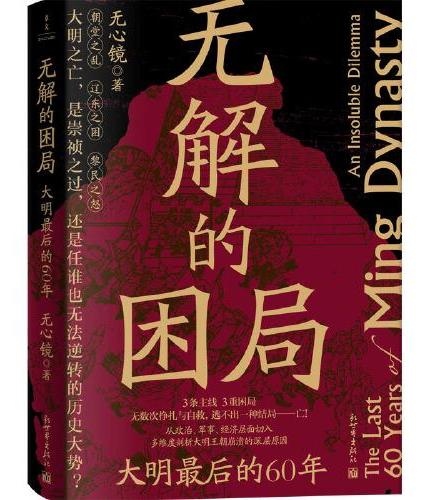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HK$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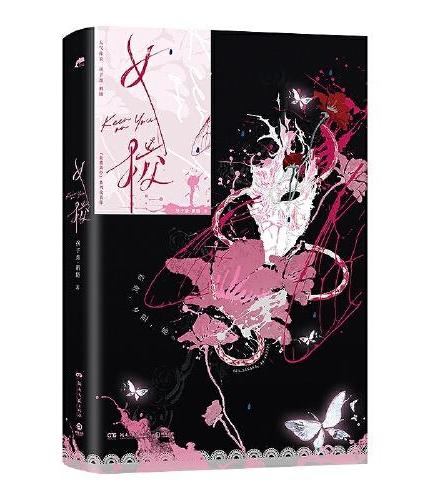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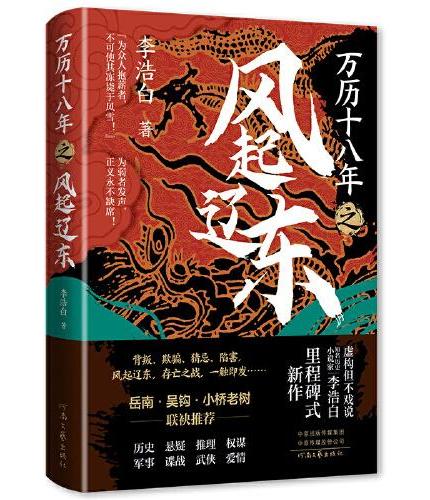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如何重新审视文艺实践、文本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如何重新激活文学艺术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对研究者而言,这都呼唤着一种更加融通的主体位置与研究视域。
本著没有刻意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做出区分,而是着意寻找一种更具活力的中间性的位置与更具贯通性的研究视野,既重视批评实践的历史意识,也尝试建立一种富于批评意识的历史视野,使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相互激发,从而重启文学与历史的关联。
|
| 內容簡介: |
|
新文学自发端起,就长久裹挟在新与旧、城与乡、现代与传统、抒情与史诗、文学与政治等一系列具有辩证性的历史构造当中,也在现当代中国纷纭的话语实践和形式的自反与重造中,呈现为开阔而复杂的光谱。本著的核心议题正在于将这些“构造”重新语境化与问题化,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辨析与探询贯穿新文学的诸多具体构造如何内在于现代性命题本身,又如何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结构,并尤其关注新文学家及其后来者如何在话语、观念与形式的“重造”中,重新为新文学开辟出自我批判的位置,激活新的历史能量。
|
| 關於作者: |
|
路杨,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博雅博士后,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助理教授、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有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评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新锐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优秀论文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等。
|
| 目錄:
|
第一编 积习与新路
“积习”及其反讽: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
“小说之名”与“后来所谓小说者”
“硬译”:语言的自新与翻译的政治
第二编 抒情与史诗
“反浪漫的罗曼司”:新文坛风尚中的沈从文
“新的综合”:沈从文战时写作的形式理想与实践
“抒情”与“事功”:从王德威“革命有情”说谈起
第三编 都市及其景观
借镜威廉斯:现代性叙事与中国城乡
从梦珂到“神女”:都市空间中的穿行与放逐
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
第四编 传统及其形变
形式与表意的悖谬:想象萧红与她的时代
英雄的位置:“革命中国”的想象与重写
寓“独语”于“闲话”:李娟与现代散文的传统
自叙传经验的反复:“90后”作家的90年代想象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积习”: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1932年12月)中交代以“南腔北调”为集子命名时写道:“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虽曰“不足为训”,鲁迅的这一“积习”却从来没有改掉,在“三闲”与“二心”、“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之中,反而还仿佛能看出些自得其乐的意思。
在鲁迅的众多表述中,“积习”一语反复出现,从自我反省到对这一反省的背叛,“积习”与“油滑”相类,构成了一种含混、悖反又捉摸不定的言说方式。“积习”作为一种修辞,在其字面意义与背后所指之间,存在着多重指涉又游移不定的复杂空间。回到“积习”一语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与言论语境之中,则可见出鲁迅在不同场合、文体及其背后的言说姿态、策略与针对性考量之间的张力所在。而在这诸多前提之下,这一言说方式也将从一种修辞表现,最终上升到文章结构乃至风格的层面。
一、“积习”:否定性的自我指涉
鲁迅常以“积习”一语对其写作进行自我指涉,并以《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一文中的解释和表白最为详尽: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
此外亦有“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1929年7月)一类的表述,也曾在《“感旧”以后(下)》(1933年10月)一文中,以此指称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些文白夹杂的作者: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这些表述首先指向的是在“文辞”的层面,由“作对”“常用成语”等带来的“字句”“体格”上的“古文气息”,有时也会继而将批判的笔触延伸到“文辞”背后的“思想”层面。而无论具体的论述方式如何,称之为“积习”,便首先在显性的字面意义上传达出一种负面的态度。然而,与这种字面上的负面意义相对,却有两方面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鲁迅自身态度的游移乃至反转:称“积习”是“不足为训”的,却继续在书名中玩些字眼上配对的把戏;称“积习”应当“荡除”,却仍拉来古文为文章作结。在《写在〈坟〉后面》的末尾,鲁迅竟甘冒前文之“大不韪”般这样写道:
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可见在实际写作中,鲁迅对他的“积习”虽自我否定却未必“真心悔改”,而在表达方式上,所谓的“积习”与继之而来的“积习不改”所构成的反转结构,则恰恰可能是有意为之的。二是在鲁迅的文章和语言内部,这些“字句”“体格”上的“积习”确实构成了某种独特的美感。正如木山英雄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文章里,古文字句和格调不同于那种伪风雅,及与质朴详实的现实主义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风格,因之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容裁的凝练美。” 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那里,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古典小说在“文辞与意象”上的浓厚兴趣与赞赏之辞 ,而其《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在“文言述学”的传统内部,通篇采用典雅简古的文言展开的学术著述。但需要辨析的是,鲁迅关于古典资源的修养与取用,造就出的是一种不同于陈旧的格律、体式与蕴思方式的美感与音乐性,这与周作人所批判的“文义轻而声调重”“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及其背后来自于“服从与模仿根性” 的写作(《论八股文》,1930年5月),已然发生了判然两立的改变。如若“积习”真的指向其表面上的负面含义与自我否定,那么施蛰存称鲁迅“新瓶装旧酒”的意见便也并不算错:“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 (《〈庄子〉与〈文选〉》,1933年10月)。但鲁迅既不承认所谓的古文修养在其白话文写作中的积极作用,还要以“积习”之名加以否定,却又执意将这一“积习”保有并实行下去,可见在鲁迅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当中,“积习”一语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明确、唯一且稳定的对应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