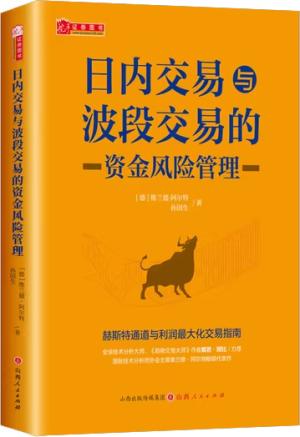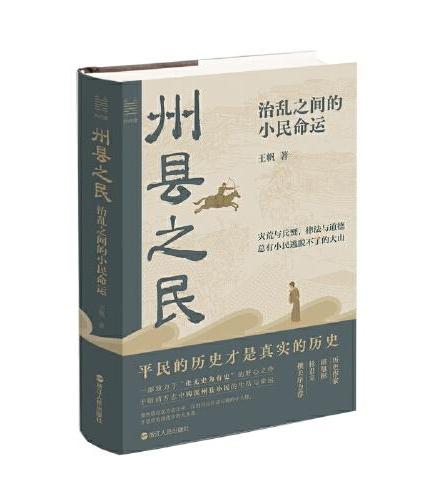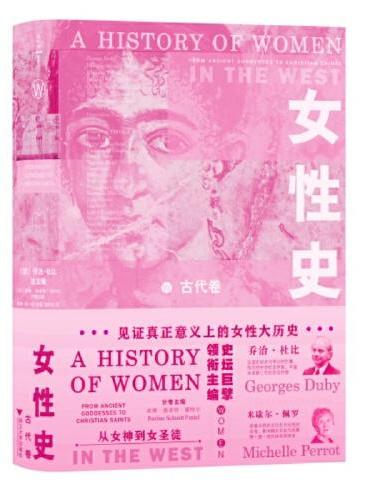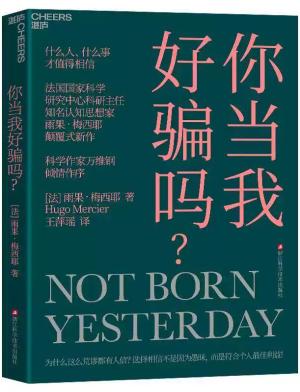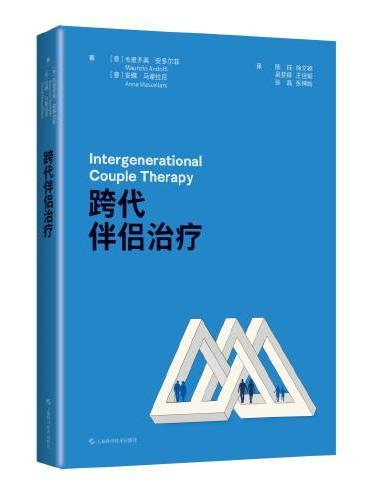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HK$
57.2

《
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格罗斯曼“战争二部曲”的第一部,《生活与命运》前传)
》
售價:HK$
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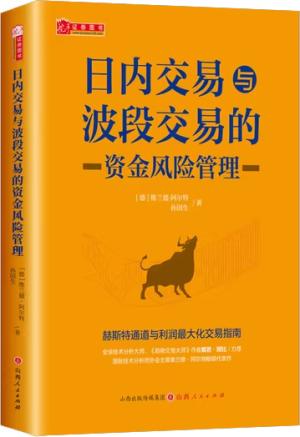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HK$
85.8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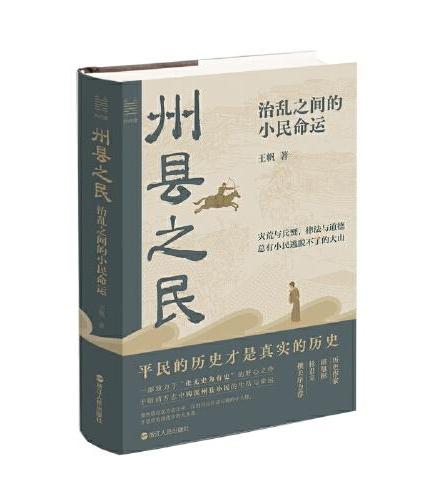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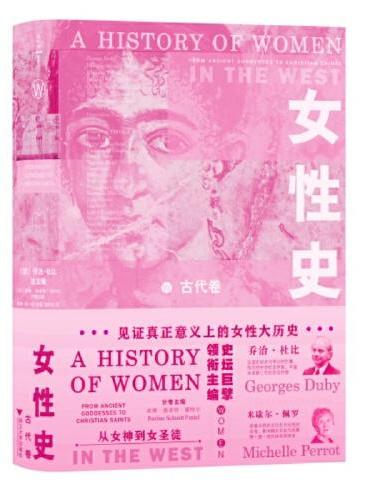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HK$
1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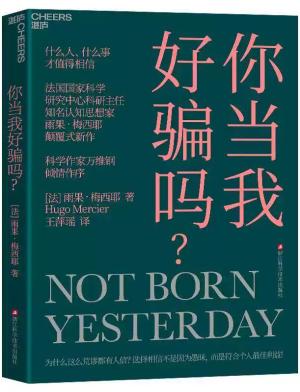
《
你当我好骗吗?
》
售價:HK$
1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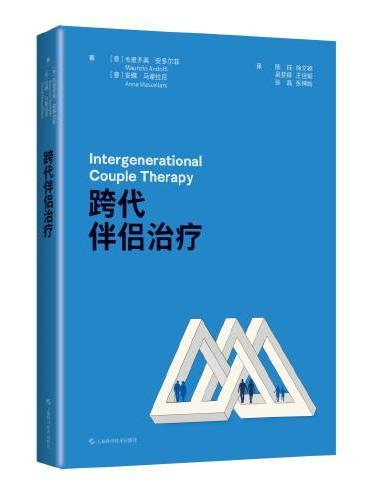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潜伏》作者龙一推荐
★黎明前的暗战,绝密野罂粟计划
★一张几近失传的地图,一次破茧而出的行动
★再现绥远地区解放前日伪、国共斗争的复杂性
|
| 內容簡介: |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归绥城,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为实施野罂粟计划,疯狂寻找一张几近失传的地图。在归绥城特务科工作的“我”,因执行任务时头颅中枪,间歇性失忆;即将赴任新科长的侯忠孝,昨日还是军统的王牌特务;表面粗枝大叶的崔板头,身份却是情报队队长;还有因公殉职的马科长,疑是被军统清除叛变的卧底……看似同一阵营的几人,各自怀有私心和秘密。国难当头,他们该何去何从?
作者将目光聚焦在小小的特务科,围绕日本实施野罂粟计划的关键——寻找地图这一线索,展现了抗战时期多方势力的风云变幻。野罂粟计划到底是什么?失踪的地图能否被找到?特务科的几人在其中起着怎样关键的作用?
黎明来临之前,迷雾重重,“我”能否恢复真实的记忆,冲出最终的黑暗……
|
| 關於作者: |
|
拖雷,本名赵耀东,1972年生,祖籍山西,现居呼和浩特,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寻仇记》《老金的底牌》《厄尔尼诺》《叛徒》等。
|
| 目錄:
|
上 迷雾/001
一道闪电让我从梦里惊醒。
等我彻底苏醒过来,才发现闪电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梦里。现在外面还是黑夜,我嗓子干渴,就在我准备喝口水时,发现黑影就在我的面前坐着。
他一动不动,像个阎王殿里的鬼魂。
中 破茧/129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要我流露出一点儿心软的意思,本田麻二会毫不犹豫地掏枪打死我。我只能杀了陈娥,也就在我抬起刀犹豫之际,陈娥突然站了起来,用胸口抵住了刀尖,狠狠地迎了上去。
我的心跳在那一刻仿佛骤然停止。
特务科的人也禁不住叫了几声。
陈娥倒在我的怀里,刀已经刺透她的胸膛……
下 交锋/237
我慢慢拧开硫酸瓶盖,里面呛人的气味让人窒息,我脑子里想起陈娥,她一直存在我的记忆之中,她理想坚定……想到她的死,我很后悔,我为什么不去营救她?而让她就牺牲在我的面前……我对不起她呀……恍惚中,我又想起惠子,仿佛听见惠子的歌声在屋里回荡着,那旋律和那歌声,让我觉得惠子根本没有死,就在我身边……
|
| 內容試閱:
|
白天跟着个鬼。
夜里顶着个神。
——归绥地区民谚
上
迷 雾
一道闪电让我从梦里惊醒。
等我彻底苏醒过来,才发现闪电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梦里。现在外面还是黑夜,我嗓子干渴,就在我准备喝口水时,发现黑影就在我的面前坐着。
他一动不动,像个阎王殿里的鬼魂。
引 子
1939年夏天,一支日本科学考察队在蒙古高原的西部某地,进行一项外人无法知道的科考任务,队员三十二人,向导一名,队长是江口正川教授。这位教授五十四岁,是个中国通,著有《中国西北考察记》《西域地质考》等著作,据说这位江口教授是第十次来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得到了日本军方大力支持,除了配备的五十多匹骆驼,各种物资,还备有先进的武器,这支科考队伍从归绥城出发,沿蜈蚣坝,过大青山,进入草原腹地……
半年以后,也就是1940年的春天,《蒙疆日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
我大日本帝国本着大东亚共同繁荣的原则,于昭和十四年派出以江口正川教授为首的中国西北科考团,考察团一行三十三人,深入蒙地,进行科考研究,科考团在草原某地不幸罹难,全团三十三人,无一幸存,魂亡异地……
这则新闻一出,各界哗然,对这次科考团的任务及人员死因有各种猜测,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百灵庙蒙政会的德王、汪伪政府,甚至是苏联的间谍情报组织,纷纷行动,他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情报组织截获日本军方一份电报,电报泄露了“野罂粟计划”的部分内容,原来日本考察队的科考仅仅是个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西北寻找一种代号为“黑蜘蛛”的矿物质,这种矿物质是日本生产的一种足以毁灭半个欧洲的生化武器的重要成分……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当地向导活了下来,秘密将“黑蜘蛛”所在位置的地图送回归绥城。不想这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各方蠢蠢欲动,一场争夺地图的行动,就这样悄悄地上演了……
一
我的故事还得从1941年8月8日说起。
那天是立秋。早晨看,天还不错,日头很亮,晴空万里,空中出现的几缕云,很像娘儿们身上撩人的薄纱。人走在大街上,身上没一会儿就会冒汗,丝毫感觉不到秋的凉意,可万万没想到,临近中午,忽然起了大风。风很大,竖起耳朵能听见,风里有鬼哭狼嚎声,当地人称这风是“鬼脸风”。风搅着黄沙,没一会儿,就把整个归绥城刮得天昏地暗,如同鬼城。也就是这个时候,特务科接到桃花公馆的命令,什拉门更村里发现抗日地下交通站。
这个命令来得很突然。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当时我和马科长还有崔板头三个人正在一起喝酒。崔板头不知道从哪里搞了点马肉,本来马科长姓马有忌讳,崔板头不好意思叫他,可马科长一点儿不在乎:“老子姓马,就是马了?那姓牛的连牛肉也不能吃了?岂有此理,吃,老子就爱吃马肉。”于是在特务科的食堂里煮了一锅,等热气腾腾的马肉上桌,马科长兴高采烈地说:“什么马肉驴肉,管?他的呢!这鬼天气,咱们能快活比什么都强。”
都说“香驴肉臭马肉,饿死不吃骡子肉”。可真正吃起来,这肉一点儿不臭。我们三个正喝得热火朝天,一个勤务兵跑了进来,报告说是桃花公馆的电话,让马科长去接。马科长正喝在兴头上,有点不情愿,勤务兵表现得很着急,不安地看着他。马科长坐不住了,日本人的电话,他胆子再大也不敢违命,于是他擦了把嘴角的油,跑出去接电话。
没一会儿马科长顶着一头土回来了,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他妈的,任务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鬼天气来,这酒喝不成啦!”
“怎么了?这好端端的酒和肉,什么任务至于这么着急?”崔板头眯着眼睛看着马科长。
马科长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日本人不让声张,任务还暂时保密。”
崔板头不屑地笑着说:“保密,保个屁密!我敢保证没出这个大院,对方就知道了咱们的行动。”
马科长检查了腰上的枪:“别废话了,你哥俩谁跟我走一趟,说不定一会儿真刀真枪地干上,我不能没有个帮手呀。”
马科长刚说完后,我酒劲正好上头,没等崔板头说话,抢着跟马科长说:“我跟您去吧,那里地形我熟。”
我的话刚说完,就知道,自己说得太冒失,我看见马科长瞪着眼睛看着我,他有点意外,像不认识我一样,上下打量着我。
“你小子不是喝醉了吧?”
我既然说了,话就收不回来,故意睁大眼睛,看着他说:“这一点儿酒,我刚湿了下喉咙。”
事实上,我能看出来一旁的崔板头,双手摩挲着腿,身子几乎要站起来,看样子他也要去,见我执意要去,就不跟我争了。临走他安顿我俩:“子弹不长眼,你俩小心点儿,这酒和肉都给你俩留着呢,快去快回。”
出了特务科,风越刮越大,呼呼的,空气里到处都是呛人的土腥味,所有的房屋树木被风刮得歪歪斜斜的,大街上空空荡荡,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次风了,归绥这个鬼地方,一年四季总刮风。当地人都说,一年只刮两场风,一场从东刮,一场从西刮,一场刮半年。我坐在汽车上,随着道路颠簸,头有点昏沉沉的,不一会儿在颠簸中,我竟然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见有人说到了,我睁开眼。
马科长站在车下正在交代任务,他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松,面沉似水,刚才还有点泛红的眼睛,现在一点儿不红了,眼里闪着机警的光。他吩咐着,让人全部下车,步行进村,这样不会引起村里人的注意。
我跟着马科长进了村,村里静悄悄的,这个季节按道理地里的夏粮都已打尽,村里总得有两个闲人,可真奇怪,走了一路,没一个鬼影:“这他妈的有点不对呀,咋连个放羊的人也看不到?”
马科长边捂着帽子边说:“也许是风大,人们都躲在屋里。”
说实话,到了现在,我有点后悔,后悔自己喝了点酒,头脑一热逞能人,可来也来了,就不能让马科长看出我是个 人。于是我振作精神,把手放进怀里,紧紧地握着枪,瞪大眼睛,警惕地看着四周。
前面有一个大院,看样子有半亩多地,大院两侧种的高大杨树。院墙是土墙,有两人多高。这个大院就是电话里所说的秘密交通站。
墙上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来回摆动着,我以为是人影,揉了揉眼,仔细一看,原来是几团风滚草,挂在墙头上。说实话,到了这会儿,我内心一点儿没感到害怕,反倒还有点兴奋,我目测了墙高,活动着腰腿,对马科长说:“让我上吧,我从后院墙上,你带着人从正门进。”
马科长看了看高墙,又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不相信我,我就对他说:“你忘了,从小我可是练家子,这墙头,我如走平地。”
这话我是吹牛。
马科长抬起脚踢了我两下。他看了下表,时间紧迫,说:“对方手上有枪,你小子给我注意安全,上吧。”
夸下海口,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特务科的两个兄弟一个站着,一个蹲着搭成人梯,我才爬上墙头。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上了墙后,我有点头昏眼花,胃里那些未消化的马肉和酒不断往上涌,我几乎快要吐了。我硬是忍住了,然后伏在墙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观察着院子里的动静,院南面正门后有影壁,北面正房是三大间,盖得很气派,这说明院子的主人是个有钱人。让人奇怪的是,院子里同样也是静悄悄的,既没有狗,也没有牲口什么的,就连只鸡都看不到。从外围看,这里一点儿不像是个住户人家,也不像有人在聚会(聚会总有一个放风的),不管如何,我决定还是跳进去再说。我翻过墙头,四肢有点不听指挥,落地时,扑通一声,我摔了个四脚朝天,脊椎骨钻心地疼。好在声音不大,我从地上爬了起来,顾不上拍身上的土,举着枪,紧张地观察着四周。
我身后的那两个小特务,也相继翻墙进了院。
一个特务去前面正门,准备从里面打开门闩,让院外的马科长进来。我有点按捺不住,马科长一进来,他会带着人冲向正房,那样我只能靠边站了。我心里想着要抢个头功,就一个人举着枪跑到了正房的门前,门是老榆木做的,本来我想的是,用脚踹开门,然后高喊着“谁也不许动”之类的话。可就在我刚抬起脚,里面传出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头部。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三个月。
我隐约听到窗外呼啸的北风,风声像个巨兽的呼吸,有时强烈,有时微弱,我周身冰冷,感觉那风已经吹进我的骨头里。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人死了,也就是这个鬼样子。我一个人平静地躺在棺材里,鼻子里能闻到棺材新鲜的木头香味,这种木头可能是大青山上的柏木,有一股奇特的香味。我还能看见我死去的爹妈也在这里,他们跟我一样,平平整整地躺着,我甚至叫了他们一声,他们应声转过了脸,朝着我笑了一下,又恢复到之前的模样。
那三个月之中,我能感觉出我的身子像张纸一般,忽起忽落。
当某一日,我渐渐地睁开了眼睛,眼前隐约站着一个丑陋的人,我还以为是阎王派来的无常小鬼。等我看清楚,才发现,这是一个长着大鼻子的外国大夫。他用细长的手指,在轻轻地揭开缠在我头上的纱布,他的动作很缓慢,他的手指像女人的手,又白又细,我发现这个大鼻子没有把我领到阴曹地府,而是把我带回了人间。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绚丽,新奇,陌生。
当他微笑着问我的名字时,我愣住了,很快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感到更加恐惧的现实,以前的那个旧世界,忘得一干二净。
“你想不起来,也别着急,慢慢会好的。”说完,大鼻子又用女人一样的手,给我掖了掖被子。
听这个大鼻子说,这是一家瑞典传教士在归绥城开设的医院。大鼻子本人也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他对我说:“你真的命大,再多一寸,你的命,就没了。”
大鼻子还告诉我:“因为子弹伤了你的神经,你现在是间歇性失忆,你现在的情况……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裤带没眼——记(系)不住’……”
他的俏皮话并没有逗乐我。
我努力去回忆过去,回忆自己是谁,可一切都是徒劳。我的脑海里仿佛全是黑夜里深不可测的海水,什么都不记得了,面对眼前的一切,我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看着大鼻子,一脸哀求地说:“那,那,我什么时候能恢复好?”
大鼻子叹了口气说:“如果恢复得好的话,也许能好;但也有种可能,就是一辈子也治不好。”
“啊?”我呆呆地看着大夫。
大鼻子大夫换了一种口气,他说:“我刚才说的可能,这一切前提都得看你恢复的情况。”
我一听“一辈子”,顿时泄了气,眼前仿佛能看到一个衰老的人,像个傻子一样,佝偻着身子,面对着月份牌发着呆。这个人无疑就是我,以后的日子,我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又昏睡了几天后,我能意识到,我还活着,这就是好,老人常说的福大命大,我终于活过来了。
大鼻子说得一点儿没错,枪伤让我真的得了间歇性失忆。不过没有想的那么糟糕,用他的比喻是,现在我的脑子更像是被烧坏的胶片,有的地方清晰,有的地方空白。
现在我头上有一个明显的疤。就在我头部的左侧,靠耳朵上面的位置,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伤疤,这个伤疤现在还没痊愈,那里空空的,风能直接钻进我的脑子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