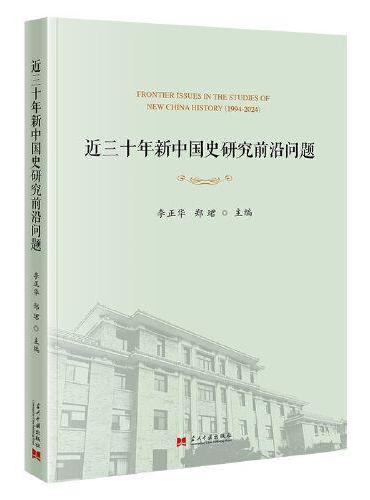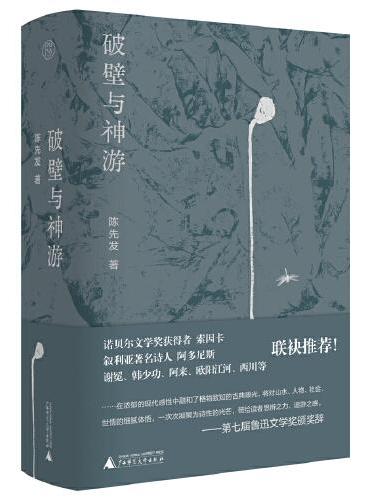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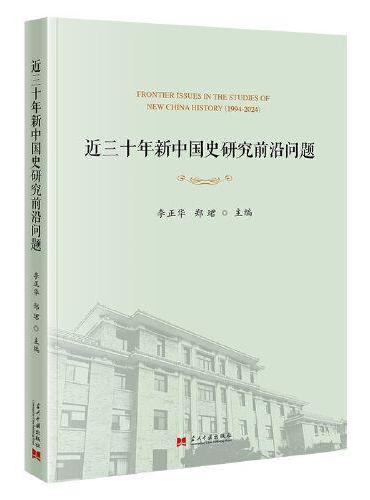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HK$
107.8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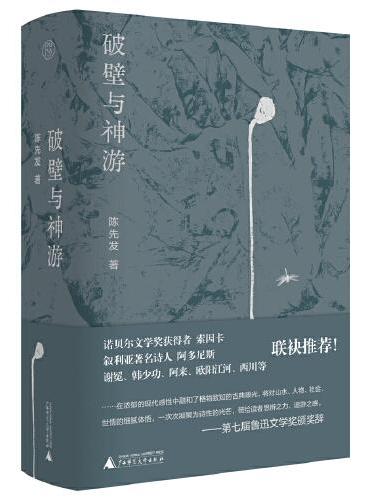
《
纯粹·破壁与神游
》
售價:HK$
90.2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小学《论语》,大学《春秋》代表中国精神的政治哲学至高圣典。得到近80万总订阅主理人熊逸代表作)
》
售價:HK$
96.8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
》
售價:HK$
61.6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HK$
140.8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HK$
107.8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HK$
657.8
|
| 編輯推薦: |
|
求是、求真乃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最核心的本质,而且这一思想和精神在西方哲学中是一脉相承的。本书论述了巴门尼德、柏拉图、波爱修、托玛斯·阿奎那、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西方主要哲学家关于“是”(to be)与“真”(truth)的论述,整体上提供了相关讨论面貌,并基于这一讨论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和论证。本书提出,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把 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 being,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应该把 truth 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应该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理解 truth。本书还提出,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
| 內容簡介: |
|
求是、求真乃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最核心的本质,而且这一思想和精神在西方哲学中是 一脉相承的。本书论述了巴门尼德、柏拉图、波爱修、托玛斯 ? 阿奎那、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 尔、海德格尔等西方主要哲学家关于“是”(to be)与“真”(truth)的论述,整体上提供了相关讨 论面貌,并基于这一讨论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和论证。本书提出,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把 being 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 being,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 应该把 truth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应该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理解 truth。本书还提出, 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
| 關於作者: |
|
王路,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逻辑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曾在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大学学习和访问研究。
|
| 目錄:
|
第一章 导论 1
一、费解的“存在” 2
二、“是”与“存在” 11
三、“真”与“真理” 19
四、求是、求真 26
第二章 对希腊文einai 的理解 29
一、系词用法 30
二、存在用法 33
三、断真用法 45
四、我的几点看法 49
第三章 巴门尼德的真之路 57
一、译文 57
二、分歧所在 62
三、疑难与问题 68
四、真 72
五、理解巴门尼德 76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83
一、翻译术语的问题 83
二、“S 是”与“S 是P” 94
三、范畴学说 100
四、《形而上学》 104
五、如何理解《形而上学》 112
第五章 中世纪的探求 116
一、波爱修 116
二、托玛斯·阿奎那 121
三、是的存在涵义 129
四、是本身与上帝是 134
第六章 近代哲学 142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是” 143
二、洛克论天赋原则和天赋观念 151
三、洛克论存在 157
四、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反驳 163
五、问题与谈论问题的方式 171
第七章 黑格尔的《逻辑学》 177
一、是与不 177
二、此是与存在 182
三、系词 187
四、出发点与此是 194
第八章 海德格尔的追问 200
一、例子 201
二、是的句法和词源 204
三、是者是 208
四、此是 212
五、真 221
六、是与语言 224
第九章 是、存在与真 233
一、是什么 233
二、是真的 237
三、存在 243
四、语言与逻辑 247
五、逻辑与形而上学 253
六、哲学的科学性 259
七、如何理解形而上学 265
附录1 Being 问题与哲学的本质 275
(开场发言) 275
(回应发言) 282
附录2 论“一‘是’到底论”及其意义 287
一、前辈的质疑 288
二、质疑与问题 292
三、如何理解形而上学 297
参考文献 305
索引 312
|
| 內容試閱:
|
这是自己花费精力最多的一本书,有关它的想法自然就会更多一些。我把这些想法讲出来,作为序。
最初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约是在 1979年。那是我跟着周礼全先生读研究生的第二年。由于研究方向是西方逻辑史,毕业论文选定了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了做论文,除了研究《工具论》,我也读了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形而上学》。读过之后,我的感觉是,不仅读不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而且对自己过去读过的那些哲学也产生了疑惑。我不明白,既然读过那么多哲学著作,为什么会不明白《形而上学》中的许多思想?那时我读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是英文版的,总是琢磨不透他说的那个 being,因而时常把握不住。它与一般哲学教科书通常所说的内容,比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发展变化的等等,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既然《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又是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也就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阅读和理解。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为什么阿维森纳说他读了 40遍才开始明白形而上学。只是当年做研究生论文的时候,我对《形而上学》只字未提。这里虽有取巧之嫌,主要还是不敢问津。
1982年,美国著名哲学家埃尔曼教授来我国做为期 7天的讲学,题目是科学哲学,我做翻译。其间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埃尔曼教授讲课的最后一天,结束时有一个简短的致谢仪式。别人的发言我都忘记了,但是查汝强先生有一段话,我却牢牢记在心里。他的大意是说:通过与埃尔曼教授的交流,我们发现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比如关于“真理”这个问题的探讨。埃尔曼教授讲了许多关于“真理”的探讨,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许多关于“真理”的探讨,我们讲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人类在认识发展的长河中,总是在不断逼近“真理”。我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机械地把“真理”都翻译成“ truth”。我想,在场的听众大概不会产生什么疑问。但是我不知道埃尔曼教授对这段话怎么想。其实,我当时的感觉可说是有些“震惊”。埃尔曼教授讲了 7天课,天天都在讲“ truth”,但是他明明讲的是“是真的”(is true)这种意义上的“真”(truth),根本不是“真理”,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真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我在翻译中也没有使用“真理”,而是用的“真”这个概念,比如“句子的真”、“命题的真”,等等。查先生竟然能够如此理解,而且他的英文还是不错的,真是不可思议!我当时的明确感觉是,他没有听懂埃尔曼教授的讲课,由此推想,学员中大概也有不少人和他一样。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有些什么问题,一时又说不清楚。从那以后,我在研究中一直比较关注和思考与“真”和“真理”相关的问题。①
以上背景说明,在很早的时候,“是”与“真”就成为理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不过在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好在它们作为问题在我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时时出现。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只要它们之间有联系,认识到它大概就是迟早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究竟是什么时候确切地认识到“to be”乃是“是”而不是“存在”,什么时候认识到“truth”乃是“真”而不是“真理”,并且什么时候确切地认识到“是”与“真”有密切的联系,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 1990年在完成《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翻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明确的上述认识。
获得这样的认识是一回事,把这样的认识阐述出来则是另一回事。由于语言方面的困难,我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和慎重的态度。在弗雷格译著的序中我谈了与“真”相关的问题:
关于“ Wahrheit”。在本书中,我把这个词一律译为“真”,把它的形容词“wahr”译为“真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有两个相关的词,一个是 “Wahrsein”,这个词实际上是“ ist wahr”的名词表达,我译为“实真”;另一个词与这个词相区别,即“ Fürwahrhalten”,这个词实际上是“(etwas)für
① 王路:《寂寞求真》,文联出版社 2000年版(以下只注书名),第 69-70页。
wahr halten”这一表达的名词形式,我译为“看做真”。应该注意的是,国内对“Wahrheit”有“真”、“真理”、“真理性”和“真实性”等译法,与之相关的词及各种词类形式的译法也极不一致。①
1992年,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文《“是”的逻辑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从逻辑的角度详细阐述了“ S是 P”这种基本句式以及对它的研究的不同结果,并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是”的系词特征以及它在印欧语言中的特性。除了逻辑和语言学的解释外,我非常简要地提到“是”与“存在”的区别以及围绕这种区别形成的争论,我还指出, “‘是’(比如:‘einai’、‘esse’、‘be’、‘Sein’、‘être’,等等)这个词本身就有本体论的涵义,意为存在”。但是我沿袭通常的说法避开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仅仅点到为止。
真正开始想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在 1995年以后。特别值得提到的是, 1995年,周礼全先生从美国回来,我与他讨论了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关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看法,谈了我对“是”与“真”的一些看法,还表示自己想把这一工作做细。周先生关于中世纪逻辑谈了许多看法,但是对形而上学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后来他回美国给我来了一封信,劝我还是抓紧时间把《中世纪逻辑》一书写出来。他认为,这是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可行性也很大。至于形而上学这种比较“玄”的东西,闲来把玩一下即可,不必当真。其实周先生一直在研究元哲学,与我谈过许多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我十分明白他说的“玄”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接受周先生的建议,但是他的态度和意见促使我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为了阐述这个问题,我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 199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文《论“真”与“真理”》。澄清对于“真”的理解,乃是理解“是”的必要的一步。其实,在这篇文章的第四节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的论述的时候,我已经谈到了亚里士多德对“是”的论述,并且简要谈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没有展开而已。随后在 1997年,我发表了论文《如何理解“存在”?》。文章提到康德的著名论题“是( Sein)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并且指出“存在”的译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主要讨论却集中在“存在”(existence)上。
①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序,王路编译,王炳文校,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以下只注书名),第 17页。
我认为,作为准备工作,这两篇论文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总是把“真”与“真理”混为一谈,或者分不清关于“存在”的研究与对“是”的存在解释的区别,那么对于如何理解“是”这个形而上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无法说清楚。经过这些铺垫之后,我终于在 1998年发表了论文《“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德格尔》,把我关于“是”的看法以一种案例分析的方式阐述出来。以后的文章不过是这种案例分析的继续,就不用再多说了。
在阐述自己思想的过程中,一些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有几个人是值得提到的。
一个是学兄王生平。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对他说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翻译错了,应该翻译为“语言乃是是之所在”。这等于把我的观点公布于世。由于他的文章发在报纸上,马上就有了一些反应。其实,我和他是老同学,经常讨论一些问题。我和他谈过许多关于“是”与“真”的看法,完全是出于好玩,纯粹是聊天。他却非常重视我所说的那些东西,认为很重要,并一再希望我能够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坦白地说,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说明确实起到了一些“敦促”作用。别的不说,我关于海德格尔和笛卡尔的那两篇文章就是他直接约稿,经他推荐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
另一个是学兄罗家昌。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常常提出一些批评。他对我最大的批评就是认为我鼓吹“逻辑万能论”。直到我关于巴门尼德的文章发表以后,他的这种观念才有所改变。此外,他也总是非常热情地把他看到或听到的一些相关意见告诉我。从他那里,我不仅获得一些具体的意见,包括公开发表的和私下讨论的,而且比较好地理解一些不同哲学背景的人对我所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的。
在前辈中,汪子嵩先生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讲述他自己在撰写哲学史过程中对 to on这一问题的思考变化,而且把他与王太庆先生在电话中交谈的一些具体意见和思想,把王先生关于希腊文 einai的一些看法转告给我,从而使我在向他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间接地向王先生学习。此外,汪先生不仅送给我一些珍贵的外文资料,甚至他后来那两篇关于“是”的文章也是在发表之前先寄给我看的。
梁存秀先生和叶秀山先生对我也有直接的帮助。梁先生知道我研究“是”,曾把他的学生李文堂的博士论文《费希特的“是”论》推荐给我,向我讲述了他的观点并建议我与他进行讨论。我和叶先生的交流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他在社科院大楼 9层哲学所的那间“小屋”,我去过多次。叶先生对我的一些看法是持批评意见的,我与他也有过争论。这些批评和争论总是促使我进一步深入思考。特别是,与叶先生面对面的交流,使我不仅可以向他请教学习,而且得以直接接触和体会到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于西方哲学的思考方式,并且得知由此产生的思想结果,对我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
此外,我的许多好友对我考虑的这些问题也一直给予关注。韩水法曾邀请我在他主持的北大哲学沙龙上讲述过“真”与“真理”的问题。王晓朝邀请我参加清华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古希腊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述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与《形而上学》。黄裕生和马寅卯邀请我在他们主持的社科院哲学所纯粹哲学论坛上讲过两次关于“是”的问题。这样的学术交流机会使我不仅可以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能够直接听到不同意见和批评,收益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除了这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在私下里我与许多朋友,包括靳希平、倪梁康、谢地坤等西学专家,也曾就“是”的问题进行过直接的讨论,获益匪浅。
坦白地说,在交往中我也有一些深深的遗憾。周礼全先生知道我想写这本书后,曾经写信给我,建议我去拜访王太庆先生、苗力田先生等几位老先生,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他说,他们和汪子嵩先生一样,都是他的老朋友。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写信帮我联系。我虽然很想向这些老专家请教,却不太愿意麻烦远在异乡的老师,自己又有些懒,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因此拜访的事一拖再拖。 1999年在社科院召开的中国哲学 50周年大会上,我见到了王太庆和苗力田先生。由于苗先生学生太多,身边总是簇拥着许多人,我也就没有去凑那份热闹,心想以后总会有机会,倒是与王先生聊了很长时间,并说好以后登门拜访。不幸的是,此后不久王先生和苗先生先后去世。失去向这两位西方哲学专家、特别是古希腊哲学专家当面请教的机会真是不应该。回想起来,有遗憾,也有自责。我确实是有些太不主动了!
在我的学术交往中,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我利用一切与外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向他们询问关于“是”与“真”的问题。在无数次直接的面对面交谈中,我一边请教问题,一边印证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在思考他们的回答,包括观察他们的反应,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更加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至少基本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研究中发现一个问题,产生一个想法,形成一种观点甚至一种理论,并最终把它阐述出来,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的观点的提出,最初是以批评的方式出现的。简单地说,我认为以“真理”翻译“ truth”是错误的,以“存在”翻译 “to be”也是错误的,这样的翻译导致对西方哲学中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的曲解。在提出批评的过程中,我也处于被批评的地位,我的看法也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种意见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批评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建设”。用过去的话说,就是不能只“破”不“立”,而应该又“破”又“立”。我同意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地说,它要求除了批评以外,还应该有些别的什么。我在本书所做的,虽然有批评,但是主要的还是那些批评之外的东西。至于它是不是“建设”,或者说“建设”得怎么样,则要由读者去评价了。
关于学术批评本身,我曾经在《哲学研究》 2002年第 3期上专门进行了讨论。因此,读者可以相信,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对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包括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我认为,学术批评是哲学发展的生命所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对于大家的批评,我不仅会认真对待,而且会非常感谢。
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不久,我离开社科院哲学所,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这两个单位都是周先生工作过的地方,只不过他是先在清华,后到社科院,而我则是从社科院来到清华。周先生曾给我讲过许多清华的往事,包括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以及所谓清华学派。前些日子他在电话中还说,下次回北京要到清华,带着我去看一看他在清华住过的地方,走一走他在那里经常行走的路线,讲一讲当年的故事。周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很动情,我也非常感动,因为对我离开社科院的想法他最初是不太支持的。2000年我到新泽西看他的时候,他从自身经历出发,给我讲他当年为什么主动从大学来社科院,委婉地告诫我未来的几年对我、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劝我慎重考虑。我也许真的不是一个好学生,常常不听老师的话。就像写这本书一样,在去留的问题上,我最终还是自作主张。但是,周先生总是那样宽厚,一旦我作出决定,他就会全力支持。如今回想起来,在新泽西,他是那样耐心地听我讲我(本书)的思想观点,和我讨论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在电话里、在书信中又是那样关心询问我的调动情况。很难让人相信,他所做的是他本来并不赞同的事情。一如许多学兄朋友所说:“你有一个好老师!”其中一个“好”字,怎么理解大概也是不会过分的。这里,我把我在社科院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在清华大学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献给周先生,对他多年的关心与教诲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以上提到的所有师友!没有他们的帮助,读者在今天是不可能看到这本书的。
我还要衷心感谢北京书生公司!多年来它一直资助我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要求,不求任何回报。
感谢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对本书的资助!本书从 1998年立项,成为社科院基础研究课题;2002年申请延长一年,获得批准。
感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图书资料室张敏同志!多年来她在图书资料借阅方面一直给予全力支持。
感谢《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哲学译丛》)、《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清华哲学年鉴》《哲学门》《中国学术》等学术刊物!它们发表过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内容,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
感谢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陈亚明!本书从列入出版计划到最后编辑出版,都是在她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
感谢人民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2002年
再 序
时光流逝,讨论 being问题已有多年。想当初,先师周礼全先生曾劝我,形而上学这种比较“玄”的东西,闲来把玩一下即可,不必当真。我本以为,指出应该把 being翻译为“是”,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 being,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不过是指出一条理解西方哲学的途径,过后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会受什么影响。谁知涉足之深,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又被冠之以“一‘是’到底论”的代表,似乎有些欲罢不能。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十年前出版《“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随后又陆续写出三本相关著作:《逻辑与哲学》(2007年)、《读不懂的西方哲学》(2011年)、《解读〈存在与时间〉》(2012年)。如果说这几本书是一个研究系列,我最看重的还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一书。它是开创性的工作,而后来的工作其实都是沿着它的方向,以文本为依据,进一步论证该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就我个人而言,一项智力活动变得有些像“力气活”,实属无奈。好在也有收获。一方面,我在深入阅读文本过程中对西方哲学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我的工作获得反响:有赞同,也有批评,这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非常欣赏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的一个比喻:下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跑车。方向对了,开得快一些、慢一些,总是可以到达目的地的;方向错了,开得越快,离目的地越远。重温旧著,更加自信:它的方向是正确的。
此次再版,除对原书文字做一些必要修改外,删去原来两个附录,新增三个附录。这样也给本书带来新意。
感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动态》和《中华读书报》!它们发表了本书附录中的内容。
衷心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夏青编辑!她为本书的再版做了大量工作。感谢人民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再版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2012年岁末
又 序
我喜欢《“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这本书。我认为,它应该而且值得获得学界的重视。
今天,我的观点被称为“一‘是’到底论”,我还被称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围绕这一观点我写过不少东西,但最主要的观点最初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后来所做的工作,我觉得,都是书中观点的细化,许多属于“力气活”。虽然在具体研究和讨论中会生长出一些东西,认识会有一些提高,思想也会有一些发展,还会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近年来提出的“加字哲学”概念),但是最主要的观点,用流行的话说,具有开创性的观点,还是在这本书中提出的。
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把 being译为“是”,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 being,应该把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最初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一些认识还比较直观。经过这些年的讨论,我已经能够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了。这是我的进步,也是学界的进步。
新增两个附录,体现出我说的进步。进步是重要的,学术一定要有进步。
感谢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同仁和朋友!感谢赵敦华、尚新建和韩水法教授!他们曾以 being为题,为我的著作专门组织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一次是 2011年 3月 18日,题目是“ Being问题研讨会——王路教授新书《读不懂的西方哲学》争鸣”;一次是 2018年 1月 6日,题目是 “Being问题与哲学的本质——王路教授新书《一“是”到底论》学术讨论会”。讨论的著作虽不相同,讨论的问题和观点却是同一个,这就是 being问题。从“ being问题”到“ being问题与哲学的本质”,也显示出讨论的深化和认识的发展。所以我说,我们都在进步。
感谢学界同仁和朋友!感谢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讨论,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帮助我并和我一起进步!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梁斐女士,她为出版本书付出辛勤的劳动!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所有为出版本书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2023年 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