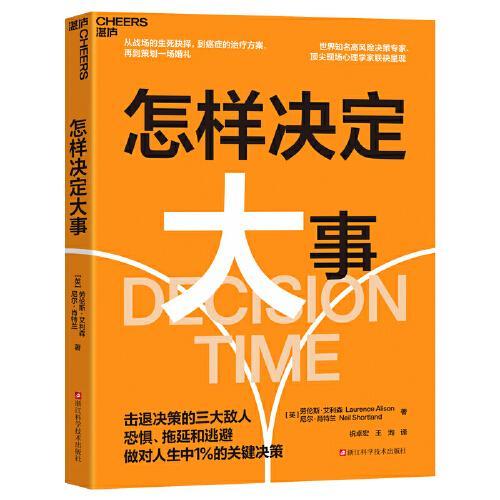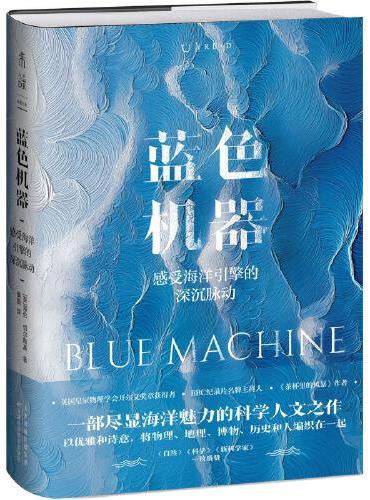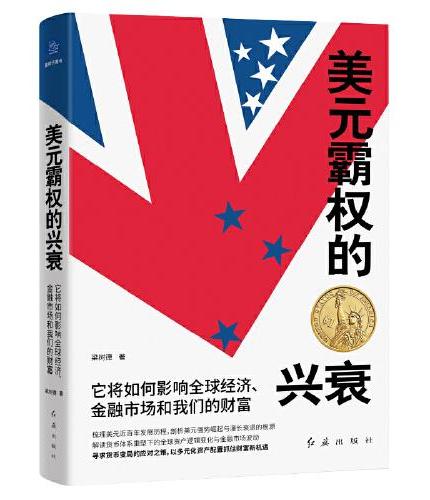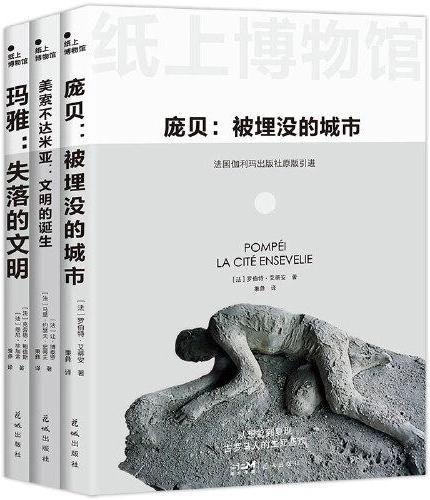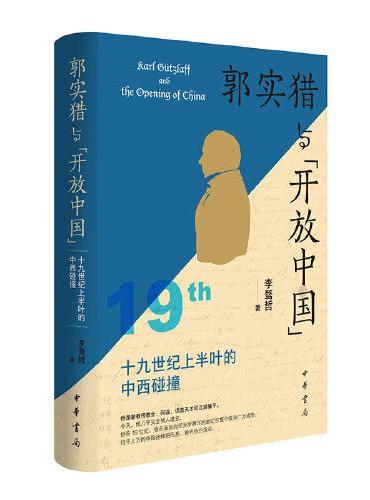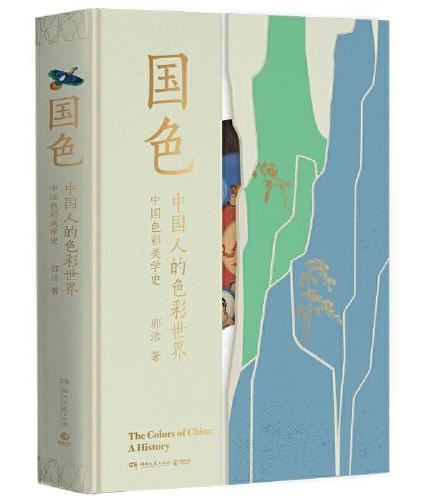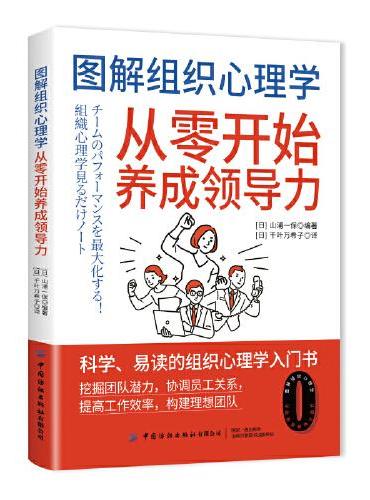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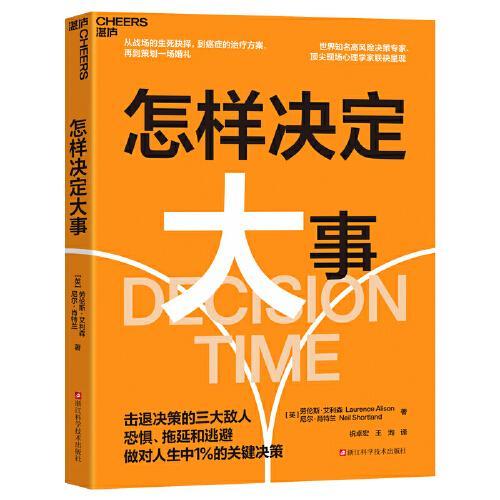
《
怎样决定大事
》
售價:HK$
1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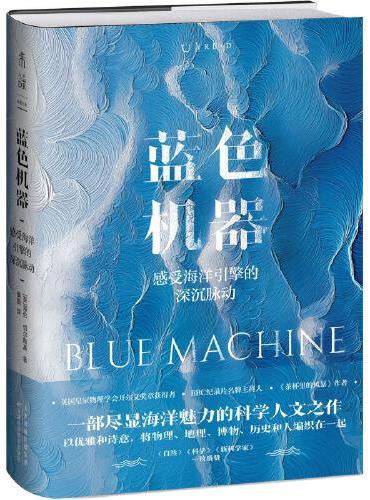
《
蓝色机器:感受海洋引擎的深沉脉动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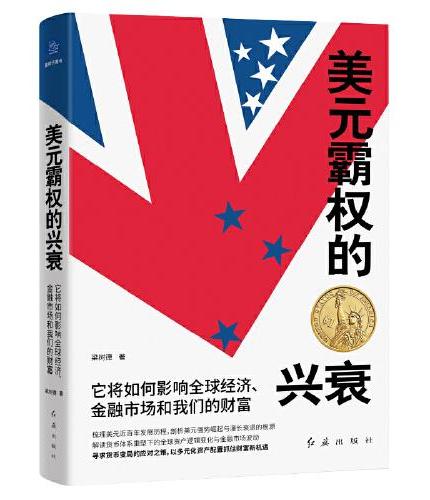
《
美元霸权的兴衰: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我们的财富(梳理美元发展历程,剖析崛起与衰退的根源)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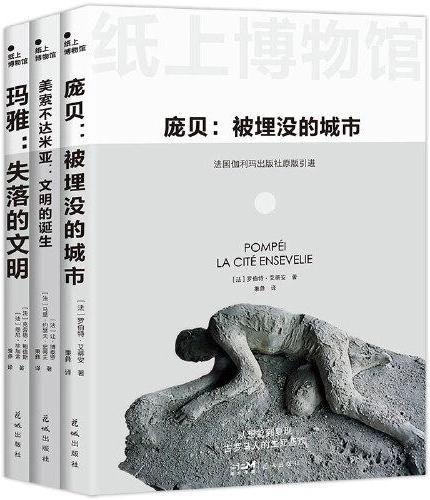
《
纸上博物馆·文明的崩溃:庞贝+玛雅+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450+资料图片,16开全彩印刷)
》
售價:HK$
2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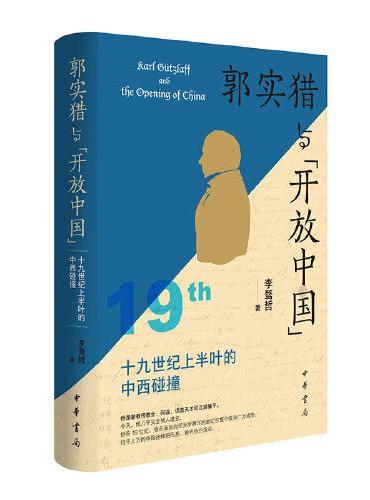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HK$
74.8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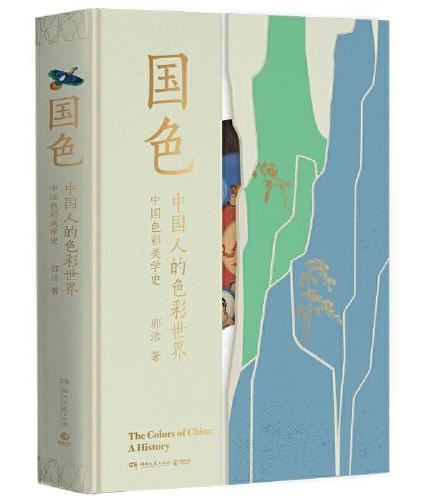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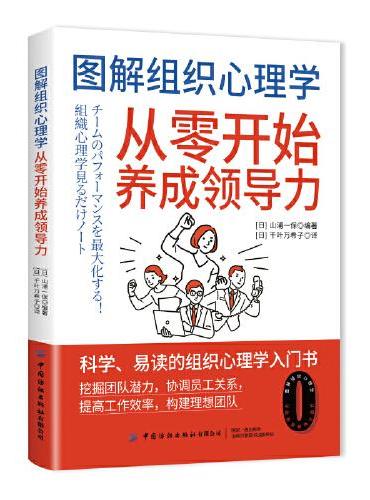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此处躺着我的妻子:让她在此长眠! 如今她在安息,我也得以安息。”
熟悉罗斯的读者都知道,罗斯的婚姻生活堪称灾难。被第一任妻子用假怀孕骗婚,与第二任妻子多年爱情长跑后进入婚姻殿堂,最后以为和平分手,却不料对方用一部《走出玩偶之家》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再一次感受到婚姻的背叛。
正是带着这种切肤之痛,罗斯写下《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这里“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其实是“我作为某某女人的男人的一生”。如果你不相信男人也可以是婚姻的受害者,是被摆弄操纵的提线木偶,那就看看塔诺波尔与莫琳的事迹吧。看一个带着担起责任觉悟的男人,和一个立志成为缪斯的女人,如何在婚姻战场厮杀缠斗,不死不休;或者看罗斯如何效仿福楼拜,把艺术变成储存仇恨的便壶。
|
| 內容簡介: |
《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出版于1974年,是罗斯的第七部长篇小说。
小说讲述了彼得?塔诺波尔,一个前途光明的大学生、一个兢兢业业的教授、一个胸怀大志的作家,怎样在失意的情场和毁灭性的婚姻生活中,在不同类型的女人特别是妻子的纠缠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全书采用故事中套故事,情节中插情节的新颖结构,层层深挖这个身处逆境不能自拔、惨遭厄运无法脱身的男人的痛苦根源。通过将绝望的虚构与灼人的真实交织,人物的优柔寡断与极端残忍并置,罗斯创造出一场关于男女之间致命僵局的凶残悲剧。
|
| 關於作者: |
菲利普?罗斯(1933-2018)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1959年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受到瞩目,此后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赢得国内外的高度认可。2012年宣布封笔,一生共创作29部小说,代表作有《波特诺伊的怨诉》《鬼作家》《萨巴斯剧院》《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秽》等。
|
| 內容試閱:
|
我不知道对这种精神分析的适应性是否等于那位神经病医生所不熟悉的文学思维习惯,也就是说,我不得不用超医学的方式来看待我的偏头痛,就像我用同样的方式看待米莉?蒂尔,汉斯?卡斯托普或阿瑟?丁梅斯代尔牧师所患的疾病一样,或者像思考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的过程,或者像探寻果戈理小说中科瓦廖夫暂时失去鼻子的“含义”。寻常人可能会抱怨:“我得了这该死的头痛病”(就这样说说了事),可我却像一个有高度文学修养的学生或一个把自己身体涂成蓝色的原始人,倾向于将偏头痛视为某种象征,某种揭示或“神灵的显现”。只有对于一种生活或一本书的结构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视之为孤立、偶然或无法解释的。可我的偏头痛又象征着什么呢?
我琢磨出来的可能性不能满足一个像我自己这样“老于世故”的学生,跟《魔山》,甚至跟《鼻子》相比,我自己的故事的质地单薄到了透明的程度。这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在我刚开始腰别手枪时,我就发现自己是个无能之辈,这或是出于我青春期对生老病死的恐惧,或是出于传统的犹太人对暴力的憎恶——一个显得过于陈腐、简单、“容易”的解释。一个更吸引人的,或许最终也不难理解的想法,则与心理内战有关。这种“内战”爆发于这两者之间:一个是曾经满怀梦想的、贫穷的、无助的孩子的我,一个是渴望成为的独立的、健壮的、有男人气概的大人的我。我在回忆时,文书巴特尔比消极而又倔强的口头禅“我宁可不这么干”犹在耳畔,教唆那个孩子的我,致使他孤立无援。可这会不会只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小男孩的声音,对号召履行男人职责或警察职责的回应呢?不,不,这太老套了,我的生活肯定比这复杂微妙得多,类似《 鸽翼》的情节。不,我无法想象自己写出一部在心理层面上如此工整流畅的小说,更不要说自己照这样生活了。
虽说她性格上的所有这一切感动了我,但奇怪的是,我对她的肉体就像第一个夜晚那样,还是那么厌恶。我自己倒是能达到高潮,但完事后却感觉这种“达到”糟透了。早些时候爱抚她的身体,她生殖器的质感让我感到不安,两腿之间的褶皱摸上去异常肥厚。当我假装对她的裸体感兴趣而细看时,我发现那里的皮肤显得枯萎变色,叫人震惊。我甚至觉得我仿佛是在低头注视着莉迪亚某个未婚姑母的私处,而不是一个未满三十岁的健康的年轻女人的私处。我不禁由此联想到她在少女时期被她父亲摧残的情景。当然这种想法显得文邹邹的而又富有诗意,难以使人接受——但不管它多让我忧惧,这里面并不包含耻辱。
自此,读者可以自行想象,二十四岁的我是如何应对自己的恐慌的:第二天早晨,我很干脆地吻了她的私处。
“别这样,”莉迪亚说,“拜托你别这样。”
“为什么不呢?”我期待她会回答:因为我那儿太丑了。
“我跟你说过。我不会有高潮。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像个走遍天涯海角,见过各种世面的圣人那样对她说:“你对这一点太过于介怀了。”
她的大腿还不及我的前臂长(我想,跟斯拉特女士的鹦鹉长度相当),只有在我的双手用力将它们分开时才叉开。我用张开的嘴吻了她那干巴巴的、呈褐色的久经摧残的部位。这一举动既没让我感到高兴,也没让她觉得欢喜;但至少我做了我一直害怕做的事,把我的舌头放在她饱受摧残的地方,就好像——我忍不住想这么说——这么做是对我们两个的救赎。
就好像这么做是对我们两个的救赎。这种想法既夸张又浅薄, 我确信,是从“认真的文学研究”中生长出来的。爱玛?包法利读了太多她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我则读了太多对我这个时代的爱情故事的批评。把我“吃”她看作是领取某种圣餐的想法的确非常诱人,虽说在须臾间的迷恋之后我便抛弃了它。不错,无论关于我的偏头痛还是我同莉迪亚之间的性爱关系,我一直竭力反对那些夸张和好听的解释;但我确实认为,我的生活同那个时代一些文学评论家一直津津乐道并显露才华的主题内容日趋相似。我自己也可以十分讨巧地写出一篇优等的大学毕业论文:《犹太人生活之基督诱惑:论“求婚灾难”的讽刺意义》。
就这样,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虽尽量地“领取圣餐”,却无法抑制我那可怕的厌恶,也无法消除被拒绝时感到的羞辱:既相信又不相信那郁郁不乐的回应。
不,假如有人是“丑恶的”,那就是我。我渴念莎伦那甜美的淫荡,她那玩儿似的不知羞耻的色欲。我常视之为她的“绝对音感”,即对我们的任何欲念万无一失地精准迎合——甚至当我在莉迪亚身上苦干,想起她所受的肉体折磨时,我还是会渴念、回味和幻想着与此形成对比的莎伦的一切。所谓“丑恶的”,是指女性身体不完美引起的反感、苛求,指发现自己是一个最为好莱坞式的冷血观念的信徒,这些观念包括什么是能引起性欲,什么不能;所谓“丑恶的”——令人担忧、叫人羞愧、使人愕然,是指像我这样自负的青年竟会如此沉迷于自己的情欲。
我常觉得自己在性方面的反应能力尚未成熟,如果情色没有使我感到特别孤独,却仍给我其他正当理由来怀疑我自己。
要看到性欲在这个羞怯的女人体内苏醒真是不易啊!还有胆量——因为如果她有胆量的话,她恐怕就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我见她仍在成功的边缘徘徊。她颈前的脉搏在不规则地跳动,下巴紧张地往上抬,灰眼睛充满欲火——只差一码、一英尺、一英寸就要到达战胜自我禁欲的彼案了!啊,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真诚的努力——两人的骨盆不停地扭动,仿佛要把骨头碾碎;手指紧紧抓住对方的臀部,汗水从头到脚湿润了皮肤,涨红的脸颊(我们几乎虚脱)紧紧地贴在一起,以至于事后她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的脸第二天早晨刮胡子时一碰就痛。说真的,我不止一次想到我可能会死于心力衰竭。“虽然这也值得。”当苏珊最终表示要睡觉时,我轻声说道。我常常用手指沿着她的颧骨摸过鼻梁,查看有无眼泪——准确地说,有无那一滴眼泪。她很少允许自己多流一滴泪,这种勇气与脆弱的感人结合。
喋喋不休倾诉不满,即使是对自己的爱人,对苏珊?麦考尔来说,就像吃饭时把手肘搁在餐桌一样,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她告诫自己说,把那些令她心痛的事当成无关他人的自己的事,这才叫表现得体,免得别人无关痛痒地来一句“这可怜的有钱的小丫头”。尽管显而易见,但她之所以如此可笑地沉默寡言,对生活如此逆来顺受,是因为她想放过的正是自己。她才是那个不想别人提及她的生活,或不去想或放任不管她的生活的人,甚至在她以自己的无奈和顺从的方式苦熬时亦如此。两个人对所丧失的东西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个像街头斗殴中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小孩,只知道闷着头、挥舞着瘦弱的手臂冲进人群加入混战;另一个则逆来顺受,疲惫不堪,任人践踏。即使苏珊意识到她不再需要节食,认识到她所表现出的比以前更强烈的欲望不仅“无妨于”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而且使她更有魅力和吸引力的时候,她对一切(除了药物以外)也依然是一贯节制和忍耐的态度,说话声音依然轻柔,目光依然羞怯得避免直视,红褐色的头发在细长的脖颈后边中规中矩地扎成一个发髻,依然恬静、缄默,仅有一滴眼泪,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她是与莫琳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如果不是另一个性别的话。
我有一对乳房,一个阴道,这些肢体、皮肤——可没有生命。只要给我一点点生命就行了,作为回报,你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上这儿来释放你妻子带给你的烦恼。不管白天黑夜。你甚至不必事前打电话告知我。”
一言为定,我说。心碎者救助心碎者。
对于那些在五十年代发育成熟,并渴望加入成年人行列的年轻人来说,正如一位当事者所写的那样,个个都想自己是三十岁,因为娶妻成家能给自己带来道德威信,很少是因为妻子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仆或“泄欲对象”。正派和成熟,作为一个年轻男子的“严肃认真”,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正因为人们认为现实情况正好相反:鉴于这了不起的世界显然是男人的世界,只有在婚姻的范畴内一个普通的女子才有希望得到平等和尊严。事实上,我们时代的女性捍卫者引导我们相信,我们剥削和贬低的是我们不与之结婚的女人,而非我们与之结婚者。通常认为,一个未婚的单身女子甚至不能自己去看场电影或上饭馆吃饭,更不用说做阑尾切除手术,或驾驶大卡车了。那么这就得靠我们跟她们结婚来给予她们这个社会普遍拒绝她们的价值和目的。假如我们不跟女人结婚,那么谁跟她们结婚呢?啊,我们男性是唯一能担此重任的人:招夫择婿开始上演。
无怪乎我这一辈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男青年对娶妻成家不屑于顾,他宁愿吃罐头食品或自助餐馆,自己扫地,自己铺床,不受法律约束,有可能的话就随时随地交交女友,做做爱,一不合意就分开,不在乎被人指责“不成熟”,或者暗中或公开搞“同性恋”, 再或者纯粹是“自私”,害怕承担责任”,做不到“致力于一种长久的关系”(这是制度的漂亮说辞)。最糟糕也最令人感到羞耻的是,这位自认为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人实际上是“爱无能”。
在五十年代,有关人们有没有能力去爱的担忧比比皆是——我敢说,其中大部分来自那些年轻女性,她们担忧的对象是那些年轻男性,他们不怎么想要她们给他们洗袜子、做饭、生儿育女,然后再花余生去照料他们的子女。“可你就不能爱别人了吗?除了你自己之外,你就不能想一想别人吗?”这一五十年代绝望的女性的语言,翻译成简明易懂的英文,大意就是“我想结婚因而我想你跟我结婚”。
现在我深信,那时节自诩为爱情专家的三十来岁年轻女子,并不清楚地知道她们视为爱的情感有多大程度上是由生存本能所驱动,或者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占有和被占有的渴望,而不是出于她们自己及女性特有的纯粹而无私的爱的蕴蓄。男人究竟有多可爱?尤其是那些“爱无能”的男人?不,有关“专注于一种长久的关系”这一话题,远非许多年轻女性(以及她们的择偶)能够谈论或在当时能够充分理解的:更多的是女性的依赖性、无力自保和脆弱性这一事实。
当然,女人们凭借其天赋的才智、理性和个性,感受和对付着这一严峻现实。可以想象 ,当时有些女性拒绝步入那种披着爱情外衣的自我欺骗的深渊,做出了勇敢的真正的自我牺牲的抉择;同样,众多不幸也降临在一些女人身上,她们因为自己的无依无靠而做出种种安排,并且从未能放弃对这些安排抱有的浪漫幻想,直到他们双双走进律师办公室,男方抛出那个被称为离婚抚养费的救生圈为止。人们说,这个国家前几十年里在法院闹得轰轰烈烈的抚养费之争,堪比十七世纪遍及欧洲的宗教战争,其本质实际上是“象征性的”。我的推测是,抚养费之争与其说是种种哀怨和心痛的象征,倒不如说往往有助于澄清那些通常被隐喻所遮盖的东西,种种婚姻安排也是由双方利用这些隐喻伪装起来的。我认为,由抚养费引发的惊恐和愤怒程度,使原本精神健全、足够文明的人表现出来的残暴,证实了法庭上一对对男女开始意识到——令人震惊同时也是令人汗颜地——意识到一方在另一方生活中实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才糟到这种地步。”怒不可遏的敌对双方也许会这么说道,彼此怒目而视——可即便这样,也只是希图继续掩盖一个最不光彩的事实,即事情原本就是这么糟,一贯如此。
除此之外,另有其他方面使我看来明显有别于我的同代人:我读书,我想写书。支配我的不是金钱、玩乐和规矩,而是艺术,具有真挚的道德多样性的艺术。
在我的书桌上方,没有贴有帆船、理想住宅或包尿布小孩的照片,也没有远方海岛的旅行明信片,却只有福楼拜的话,那是我从他给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抄下来的忠告:“生活要像资产阶级那样,有规律,有秩序,你才可能在工作中激流勇进,富于创新。”我欣赏这话中的智慧,欣赏来自福楼拜的才智,但在二十五岁这个年龄,即便我致力于小说艺术,以自律、严苛(和敬畏)向福楼拜看齐时,我仍希望我的生活有一点创新,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假如不是激流勇进的话,至少要有趣味。说到底,福楼拜本人在安坐在他的圆桌旁,成为现代文学的孤苦隐士之前,不也曾经作为绅士加流浪汉前往尼罗河畔,攀爬金字塔,同皮肤黝黑的舞女们纵情享乐吗?
是的,这确实就像我在小说中读到的那些严酷而难以克服的困境,就像托马斯?曼在做自传式素描时所写的那样,我已经选它作《一个犹太父亲》的两句引言中的一句:“所有现实都是极其严肃的,只是道德本身,现存的道德观念,阻止我们忠实于我们青年时代坦率的非现实主义。”
你也许甚至会说,我的日常生活即将演变成的苦难,不过是命运女神在面对“美国文学金童”(一九五九年九月《纽约时报书评》用语)时的微笑,并赋予她这个早慧的宠儿一点必需的文学灵感罢了。想要复杂性?想要困难?想要棘手?想要致命的严肃?都给你!
当然我还想要的是,我这棘手的生活应该处在一个相当高尚的道德高度,一个介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与《鸽翼》之间的高度。另一方面,即使是“金童”也不能期望获得一切:我遇到的不是严肃小说中棘手的现实,而是肥皂剧中棘手的现实。虽然抵抗力十足,但不是我要的那种类型。尽管也许并非如此,但我承认,如果说肥皂剧有主角的话,莫琳只是其中的一个。
“十分坦率”的写作并不意味我从感情中大幅收缩。不过话说回来,我为什么应该收敛我的感情呢?看来也许我的仇恨并没有被完全改造——也许我在把艺术变成存储仇恨的便壶,像福楼拜所说的那样,我不应该把艺术变成自我辩护的众多伪装——因为如果反之才是文学作品的话,那么这就不是文学了。卡伦,我知道我不是这样教班里的学生的,可那有什么呢?我要找个像亨利?米勒,或者塞利纳那样的恶棍来代替居斯塔夫?福楼拜来做我的主角,因而我也不会成为我在早期立志成为的那种威严的作家,那时候在我和审美超脱之间还不存在什么被称为个人经验的东西作为隔阂。或许现在该修正我有关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像我的对手的律师喜欢称呼的“艺术大师”)的思想的时候了。
我得说,他对批评的免疫力实在是令人目眩。别看这位医生脸色苍白,走路一瘸一拐,可我在那些彷徨犹豫、自我怀疑的日子里,他的坚不可摧是我热望的一种境界: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即使我不对,我也会坚持,坚持,寸步不让,这样到后来我就是正确的了。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离开他,出于对他一身“盔甲”的钦羡,希望那种难以攻克的精神能传我些许。是的,我想,这个高傲的狗娘养的德国人,他在给我树立榜样。我只是不愿告诉他,不让他得意。只是谁会说他不知不晓呢?只是谁说他心知肚明呢,除了我之外?
“你知道吗,或许是你的脸皮太薄了,或许三十岁正是脸皮该厚一点的时候了。”“毫无疑问。我相信,你们这些像犀牛一样皮厚的人生活得更好。不过我的脸皮就是我的脸皮。恐怕你用手电筒就能照透它。所以还是给我一些别的建议吧。”
此处躺着我的妻子:让她在此长眠! 如今她在安息,我也得以安息。
——约翰?德莱顿,《给他妻子的墓志铭》
你就像——像是她的牵线木偶!她使劲拉——你就跳!
告诉我她死了。我将坐穿牢底。就让那个精神变态的说谎者去死。这世界将变得好些。
“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人类的记录,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支柱,一种基石,帮助人类忍耐并取得胜利。”
“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忍耐,并且能取得胜利。人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具有永不衰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我把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寻思:“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你怎么会写出《喧哗与骚动》的?你怎么会写出《村子》的?你怎么样会写出谭波尔?德拉克和‘金鱼眼’的?”
阅读时,我还时不时看一眼小五号开罐器,莫琳的代用阳具,再看一眼自己的。忍耐?取胜?我们是幸运的,先生,我们早晨起来还能穿上自己的鞋子。这是我要对那些瑞典人说的话(如果他们要我说的话)。
此时,我的眼睛在流泪,牙齿在打战,全然不是一个摆脱了惩罚、重又成为自己的主人和权威的人的模样。我转向苏珊,她仍坐在那里,蜷缩在她的大衣里,看起来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孤立无援。这使我感到羞愧。坐在那儿等着。啊,我的上帝啊,我在想——现在轮到你了。你是你!我是我!这个我就是我,是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