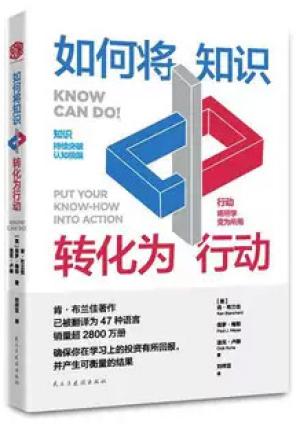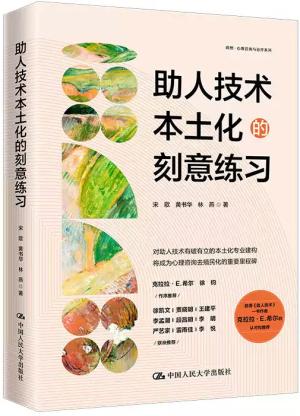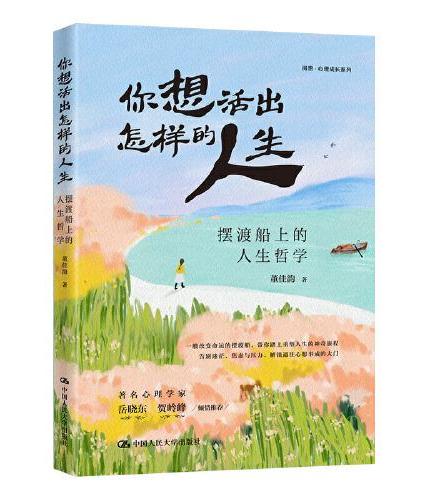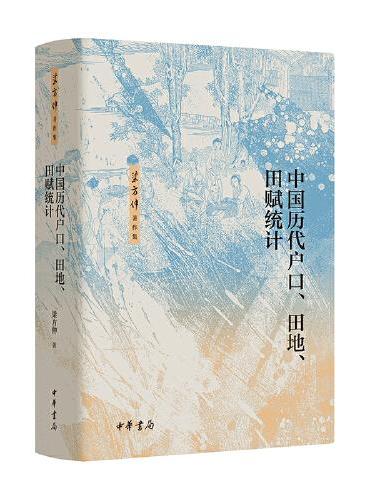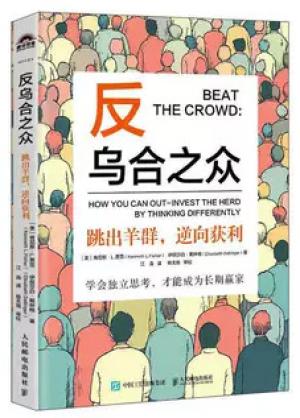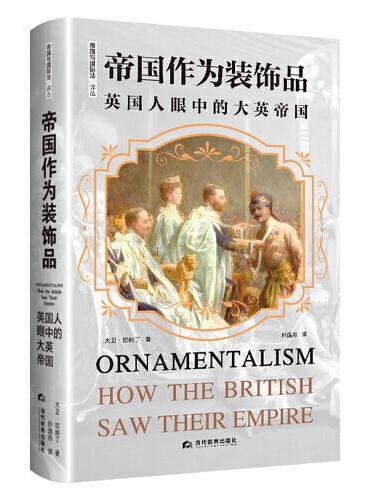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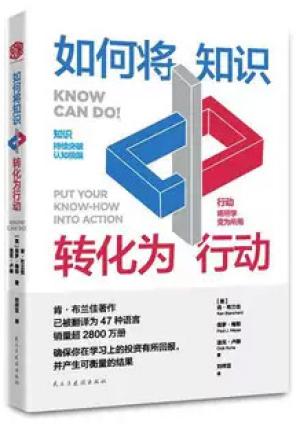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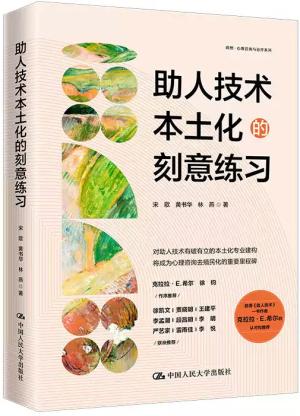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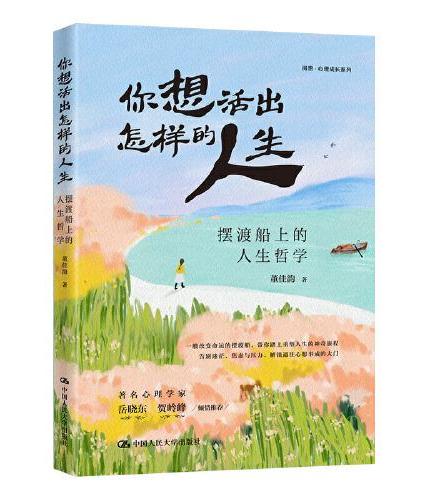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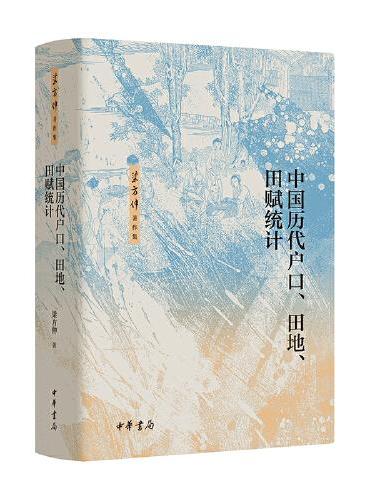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1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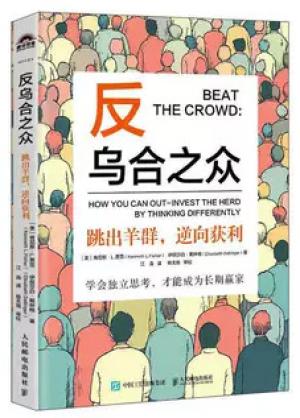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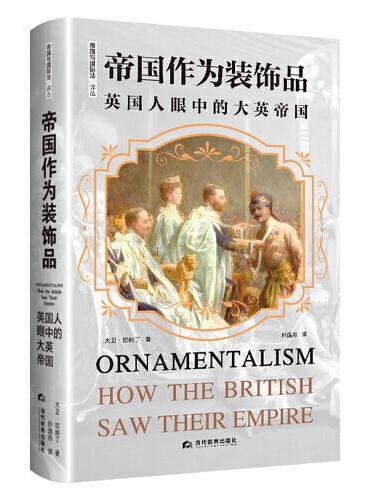
《
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
《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全新修订,新增数万字;著名作家邱华栋作序推荐,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晖、北大学者张慧瑜联袂推荐
|
| 內容簡介: |
《工厂男孩》系“工厂三部曲”丛书之一,是一部以真实的工厂生活为背景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家丁燕在其成名作《工厂女孩》引发巨大社会反响后,又将写作视线投放到了工厂男孩。为深入理解工厂男孩的生活,作家住进了工厂宿舍,在看过一张张明亮肆意的面孔、听过一个个悲喜聚离的故事后,前后历时两年创作了这部非虚构作品。
这部作品展现了工厂男孩常态化的生活真相和精神状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理解现代工业洪流下普通个体的命运有着重要意义。
|
| 關於作者: |
|
丁燕,“70后”代表作家之一。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至2010年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后定居广东东莞。自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工厂女孩》《工厂男孩》《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等多部作品。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提名奖、文津图书奖、《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百花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
|
| 目錄:
|
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第二章 住进工厂宿舍
第三章 工厂路的秘密
第四章 男工来到电子厂
第五章 午餐插曲
第六章 十九岁出门远行
第七章 母与子的战争
第八章 追时代的“90 后”
第九章 学生工的抗争
第十章 给“ ”打电话
第十一章 模具厂里的钢铁男工
第十二章 工厂之外的“泥土生活”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如果电子厂是一座庙宇,那利润便是它的供奉对象。
每一个走进电子厂的人,都需要通过不断的身份认同,才能找准新的定位。一旦进入电子厂,便是进入了利润游戏;一旦进入电子厂,便成为利润机器的细小齿轮;一旦进入电子厂,无论在里面如何龇牙惨叫,待试图讲给别人听时,却不知从何谈起。
A326,是一间没有桌子的男工宿舍——五张高低床靠墙摆开,吊扇下空空荡荡。男工的东西比女工少得多。这个宿舍和女工宿舍完全不同:那里因为有各类布帘,让人生出一种温馨之感;而这间屋子如原始洞穴,就那么赤裸裸打开,毫不掩饰,一眼望去尽显破败、狼藉、晦暗。
我来到这间屋子,是为着跟住在这里的男孩聊聊,了解他们各自的故事。
十七岁的王小门来自河南,一张蜡白的脸,眼神涣散,神情阴郁。当我向他提第一个问题时,这少年便用翻白眼来回应我。他眨巴着眼睛说出自己的名字时,脸部肌肉微微跳动,越发显出孩子气的恼怒。他用流水账总结自己:“进厂才一周,在制造部当作业员,干组装。”
他尽量用最简短的语言应付我,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干巴巴的对话。看我一时间不会收工,他便决意反抗,将话锋一转:“其实,我去年就在这儿干过半年。”
看到我惊诧地瞪眼,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他当然知道这里要“站”,他也不想来,但又没找到别的活。
我顺嘴一问:“你做的是什么产品?”这次轮到他惊诧瞪眼:“产品?我做的是货吨。”工厂生产线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分工,这样劳作效率更高,品质更可靠。生产线都是小批量、多批次按订单生产,员工根本不知道产品的名称,干脆一律叫货。无论电视、照相机、手机、钟表、眼镜、手袋,还是电玩、五金、塑胶件,在拉线旁操作的那个人看来,千篇一律,都是货。
我问他晚上怎么打发时间,他说看小说。我于是朝他的床铺扫描过去,却没看到一本书。他又扳回一局地笑了起来:“我在手机上看哦!”
“看小说看入迷,第二天迟到怎么办?”我追问道。
他挪开枕头,咧嘴笑:“我有法宝!”除了手机定时外,他备有两个小闹钟,放在枕头两侧。那两个巴掌大的小东西,像两个小婴儿,到了钟点就一起啼哭,将他从最沉的梦中唤醒。我抬眼端详他——灯光昏黄,烘托出眼睫、鼻翼很立体。
这样的面孔,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抵抗这样的粗陋……我莫名心痛。
他说,打工虽然是混江湖,可混也有混的章法。他坦言十四岁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三年时间总结了两句话:“不要迟到”“要快”——迟到的错误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晃晃,就等着挨训和扣钱吧;而一旦起床慢了,穿衣就慢,洗脸上卫生间也慢,及至吃饭慢,到车间动作慢……归根结底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字:慢!
王小门没有女朋友。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看缘分吧”。以前他听别人说,“电子厂是姑娘村,五金厂是和尚庙,制衣厂是婶子店”,等他到了电子厂,乌压压都是大老爷们,只零星地见到过几个婀娜多姿的女孩,还没等他细细打量,对方就即刻消失在人海。
他有时会去厂门外的士多店(杂货店)前打台球,让眼睛换一个频道。每天看的都是生产线上的黑色周转胶箱、不锈钢机壳、绿色线路板、白色无尘衣,当看到正打台球的女孩趴伏时,他便咧嘴笑。
我问他:“发工资那天都干啥?”
“吃炒菜、喝啤酒喽。”他不喜欢喝白酒,因为自己有病,医生不让喝。他的皮肤那样白,是因为有病?对于这一点,他绝口不提,我也不好问。
再次见面时,王小门带来了同学邵新磊。两个人简直是“黑白配”——邵新磊个子矮小,头发浓密,脸庞黝黑,五官刚硬,十指粗短。
邵新磊说他“第一次进厂”非常拘谨忸怩。来电子厂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阳门卖糖葫芦。但邵新磊用干巴巴语调描述的北京,和升国旗的北京没什么太大关系。他口中的北京是粗鄙、阴沉和疲倦的。朝阳门卖糖葫芦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早出晚归。邵新磊穿行在巨大的摩天楼高架桥间,他目光所及的顾客大多古怪:古怪地臃肿,古怪地散发香气,古怪地发出尖锐笑声。深夜躺在胡同小平房的木板床上,整个人黏涩得快要发出咸臭味。他真想赶快逃跑,趁那股臭味尚未溢出。
和他一起卖糖葫芦的六个人,是他的舅舅、姨姨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家族作坊流水线:女人制作,男人销售;每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所以,邵新磊说:“卖糖葫芦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
邵新磊的父母总是吵架,而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不耐烦,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家里还有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弟弟。他初二时便辍学,但并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师讲的听不懂”“父母想让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于是,他选择了去北京卖糖葫芦。
在北京忙碌一天捏着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仿佛能把五脏六腑捣烂,令他咽不下米粒。有时卖得不好,他索性不吃饭。饥一顿饱一顿,让他不仅仇恨糖葫芦,也仇恨北京——“那地方不是人待的”。
电子厂站着上班是累,可卖糖葫芦更累——“还要喊”。对邵新磊来说,“喊”带给这个男孩的羞耻感,远甚于“站”。而试图张开的嘴巴里,仿佛插满了碎玻璃片,每喊出一声都是哀鸣,完全不像职业小贩。他那样以此为耻,又能揽到多少客人?只是机械地喊而已。
现在,他“身累心不累”——在电子厂,只需把分配的活做好就行,下班可完全放松。电子厂的工资明码标价——“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吃饭无须看别人的脸色。
在北京,他学会了抽烟——其实他学会的是抽烟时男人们如何点火和骂粗口的安惬。
邵新磊也没有女朋友。不是不想找,而是——“还没找到”。
我对他说:“慢慢找,总能找到。”王小门听了后一个劲儿地冷笑,轻蔑评价道:“做梦!”
朱文十九岁,湖南湘西人,中等个子,挺着小肚腩,油嘴滑舌,是个老江湖;卢开元十七岁,四川达州人,黑瘦周正,性情温和。看我进来,卢开元把吊在床沿边的袜子收起,又让赤着上身的朱文披上衣服,这种沉稳细致在男工宿舍很少见。
朱文两个月前来到电子厂,之前在塘厦镇那里的工厂做焊锡。他父亲在佛山工厂做,母亲在老家种地。父母在他五六岁时离家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后,母亲回到老家。他是独生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外面闯,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如果有事,他会给母亲打电话,上个月还给母亲寄去了一千元——“不是老妈缺钱,而是多余的钱放在老妈那里更安全。”
卢开元此前在深圳五金厂干数控,也是站着上班,所以到这里并没有不习惯。他父亲在内蒙古打工,母亲在老家种地,家里同样有还在上小学的弟弟。他初中毕业后想上高中,但分数不高,只能去一般高中,又不想读技校,于是便放弃求学——“出来混一下也好”“认识一下社会”。他感觉在电子厂工作和寄宿学校差不多。但合同期满后,他“不想再在工厂做了”“想回家学门手艺”。
他的情感生活一片空白。他叹息:“没钱没资本。”他说现在的女孩又简单又直接,她们喜欢玩,“玩爽了再说别的”。
“怎么玩?”我不解地问。
“花钱呗!”有些女孩根本不给家里寄钱,每月工资都花得所剩无几:买衣服、化妆品、新款手机,吃大餐,美甲,唱 K,喝咖啡。自己的钱不够,就找个给自己花钱的男朋友。一起玩几天可以,可说到结婚,根本没门。
所以,卢开元说自己听听情歌就好,不能多想,想想就会心生悲凉。
四个男孩虽长相各异,来自不同地区,却有诸多共同点:皆为“90 后”,父母皆四十岁上下,并且都是父亲在外打工而母亲在家操持;皆未能上高中;皆抽烟。这些“90 后”男孩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和父母辈不同,甚至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不同。他们喜欢到有老乡或熟人的厂里。王小门和邵新磊是同学;朱文有老乡在电子厂;卢开元的叔叔在电子厂旁的工业园做事——“让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到这里的。”原来电子厂三千人之间,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事关系,有些还是老乡、亲戚、熟人等关系。
夜里,工厂路的网吧、台球、小餐厅等各类小店中,总是聚着一群男孩。他们崇尚影视剧里的江湖义气,有自己的“江湖”。躺在宿舍时,他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他们无须按月给家里寄钱。他们都不用为房子费心——在每个人的老家,作为第一代打工者的父母都盖起了楼房;他们虽都在外打工,但自知这是临时行为,总在不断寻找出路;他们并不排斥重返老家——如果老家发展了,工作机会多了,也可以回去。
“追时代”频频出现在他们口中——好像这个现成的时代,需要用“追”才能赶上。而他们确实是在努力地“追”。先从外形上“追”——衣着、发型、说话的腔调,都从电影、电视、周围的人那里模仿;再从态度上“追”——他们很少紧张、愤慨、焦虑,更崇尚自由、轻松、愉快。“挣钱当然重要,可太受气了也不行。”卢开元如是说。
他们最紧要去“追”的,当然是——女朋友。
朱文是这四个男孩中的老江湖,老江湖总是滴水不漏——绝不会把失望、担忧、疑惑露给你看。老江湖给你看的,都是他最得意的东西。他坦言自己有马子,是在惠州打工时认识的——他和她在同一条拉线上,他便展开了追求攻势。
“追女孩谁不会啊!”他的嗓音磁性放电,一副如鱼得水的模样。他说自己曾经为了追女孩,一个月花了七千多块钱。即便宿舍里的视听效果异常喧哗热闹,但那“七千多”还是有种意外的杀伤力。
“那你当时一共有多少钱?”
“两万!”他毫不讳言。
他说他十二三岁就知道“泡妞的事”。他很早就通晓如何和女孩搭讪。他懂得怎样低下腰身极尽讨好之能事。他会讲笑话,具有男工中鲜见的喜剧天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