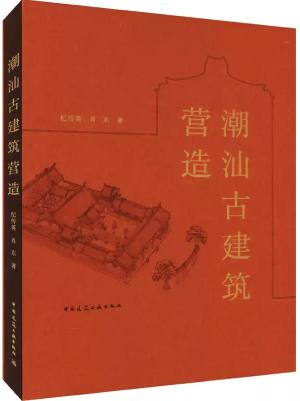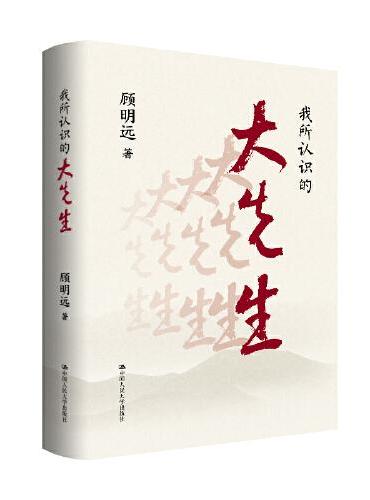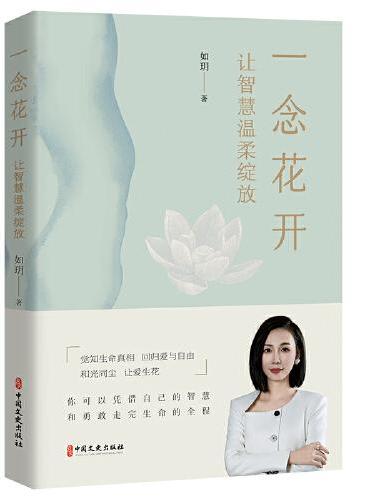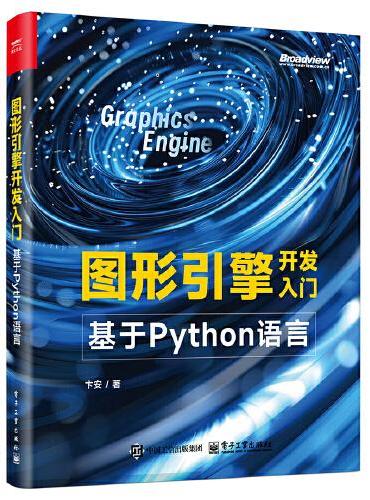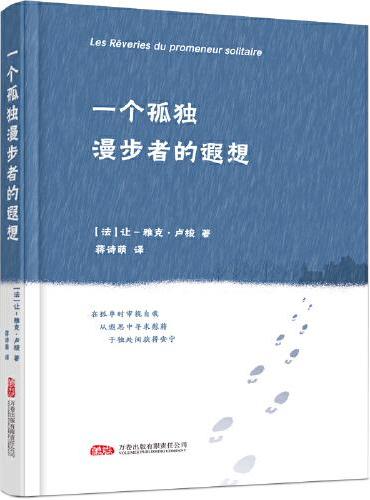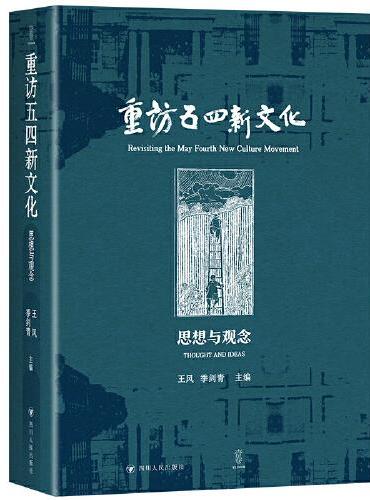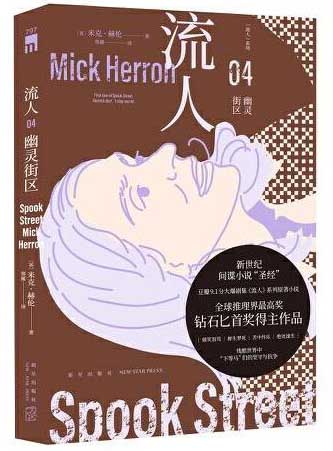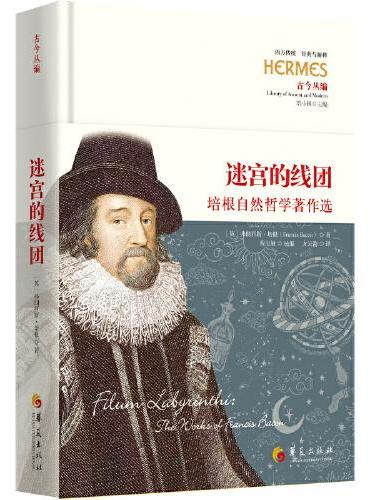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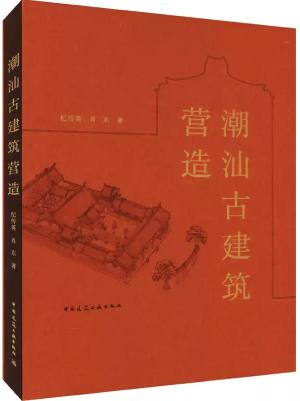
《
潮汕古建筑营造
》
售價:HK$
2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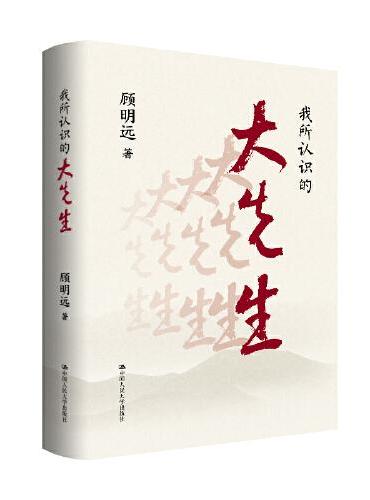
《
我所认识的大先生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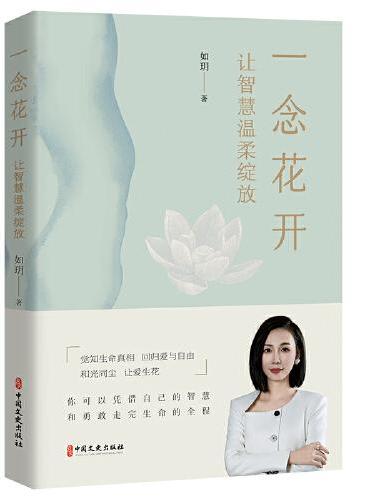
《
一念花开:让智慧温柔绽放
》
售價:HK$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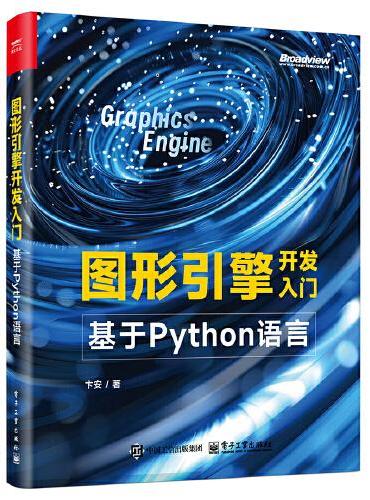
《
图形引擎开发入门:基于Python语言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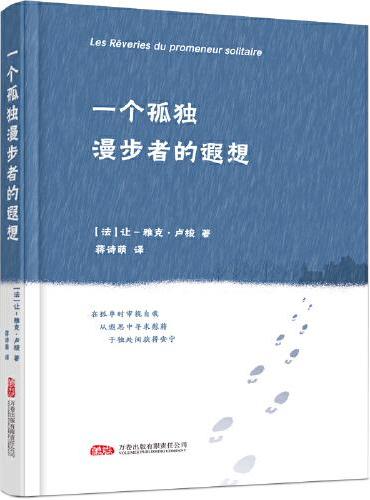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
售價:HK$
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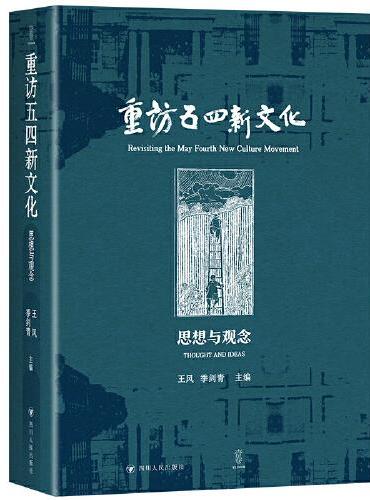
《
重访五四新文化:思想与观念(跟随杰出学者的脚步,走进五四思想的丰富世界)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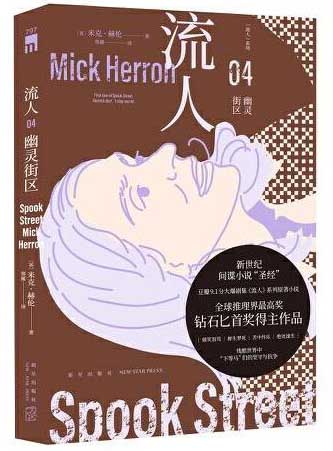
《
流人系列04:幽灵街区 午夜文库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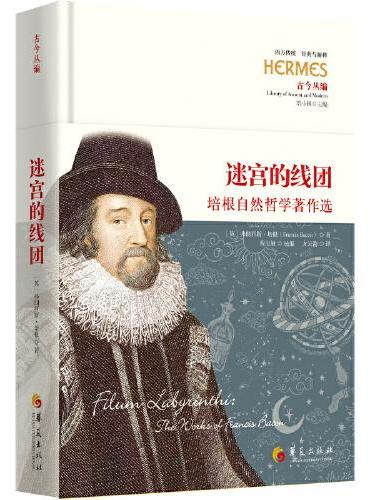
《
迷宫的线团:培根自然哲学著作选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
鲁迅文学奖提名,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全新修订,新增数万字。北大学者张慧瑜作序,作家邱华栋、文学评论家王晖联袂推荐
|
| 內容簡介: |
《工厂女孩》系“工厂三部曲”系列之一,是一部以真实的工厂生活为背景的非虚构作品。
作家丁燕为深入理解工厂女孩的生活,进入工厂卧底打工,经历了大半年真实的工厂打工生活,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工厂女孩鲜活而真切的故事,描绘了工厂女孩的青春、爱情与梦想。
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理解现代工业洪流和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
| 關於作者: |
|
丁燕,“70后”代表作家之一。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至2010年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后定居广东东莞。自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工厂女孩》《工厂男孩》《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等多部作品。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提名奖、文津图书奖、《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百花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
|
| 目錄:
|
第一章 飞跃电子厂 1
第二章 啤工初体验 15
第三章 阿凤的故事 30
第四章 插嘴事件 41
第五章 玛丽的爱情 54
第六章 第二面生命 70
第七章 深夜尖叫的赵兰花 84
第八章 怀揣菜刀的女孩 98
第九章 从女工到女生 107
第十章 阴性帝国 127
第十一章 北方出逃 139
第十二章 厚街有女初长成 148
第十三章 梅娇梅娇我爱你 160
第十四章 疼痛的肉身 175
第十五章 不告而别的舍友 186
第十六章 想当作家的女工 201
第十七章 从“五妹”到“主管” 223
后记 244
|
| 內容試閱:
|
打卡机上显示的时间是 6:58 。我笑了,同时心里发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 6:52 。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装,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我已经变得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因为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 29 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那边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一张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二
118 号!
我打了个寒战。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从啤机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时,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跟我一块儿。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根。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
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她的脸色是那样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再次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阿凤干活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 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 C 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这样他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 QC 关。阿凤将对 QC的声讨扩大化,扩大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工作过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玩具的销售旺季,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她的小老乡喊:“ 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一样。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仿佛变得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大约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 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离职,第一时间,就是把那帽子摘下来。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原来,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省的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一些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家乡的普通话。
在这个工厂的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了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即刻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找经理“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厂里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三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机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如雨下……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它们像是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需要加油,也会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产品,像某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她手脚也慢,被拉长训斥后,她还被罚不准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屈辱。于是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跟着,奇迹发生了,她的速度提了上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因为她们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吃午饭。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一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达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只有二十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剧。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他却浑然不觉。电视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形成反差。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我们这些普工稍高一点儿,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 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常常忙得头昏脑涨。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