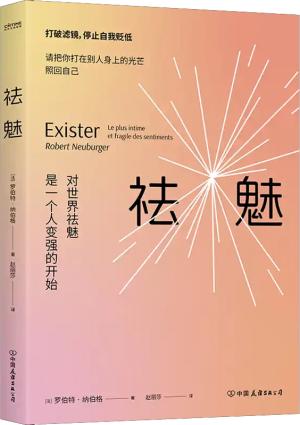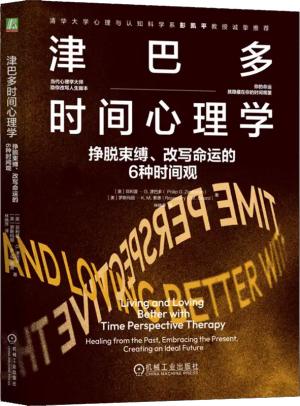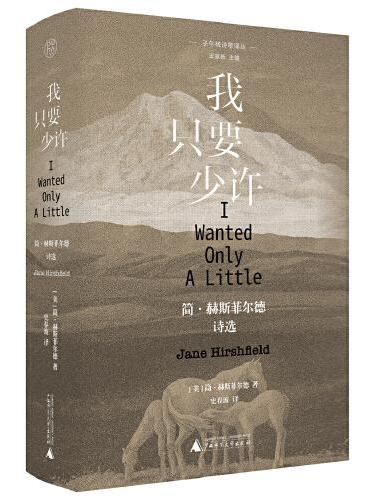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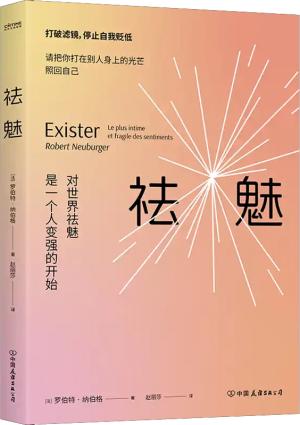
《
祛魅:对世界祛魅是一个人变强的开始
》
售價:HK$
62.7

《
家族财富传承
》
售價:HK$
154.6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HK$
55.8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HK$
110.9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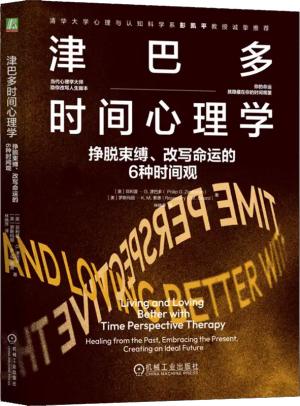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大英博物馆东南亚简史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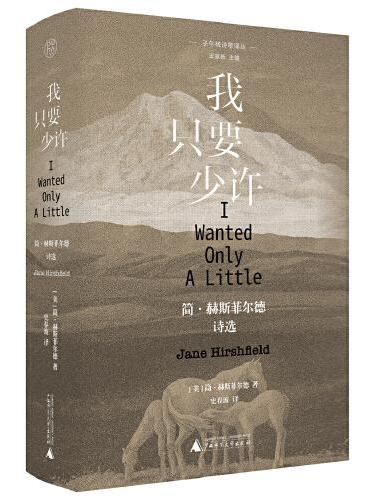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
| 編輯推薦: |
再探一代人心灵悲欢纹理,重读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诗歌
无想象力则不可抵达的神奇境遇,无处不在又至远至近的诗学王国
北京大学吴晓东经典力作,一堂镜花水月的中国新诗课
细雨/水中/镜子/远方/自然/古陵/猫眼/城池
戴望舒/卞之琳/海子/何其芳/北岛/李金发/废名
|
| 內容簡介: |
|
《辽远的国土: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是北大吴晓东教授的一部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诗性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作品,展示了风雨如晦的二十世纪中,北岛,废名,戴望舒等一系列诗人丰富,沉郁而具有深度的吟唱。书稿融汇了吴晓东教授对20世纪中国现代诗的概括、对“远方”“镜子”“自然”“时间”等诗学经典意象的文学阐释、对现当代“文学性”的研究和理解、对诗人精神世界的探问以及对千载“诗心”的领悟等方面的内容。在对诗歌艺术结构的精细解读和对诗人心灵世界的深入解析中,捕捉和传达了内在的诗性,同时展示了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的诗学轨迹和精神侧影。
|
| 關於作者: |
|
吴晓东,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年至1994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担任共同研究者,1999年至2000年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讲学,2003年至2005年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2016年被聘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入选北京新世纪社会科学“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文学的诗性之灯》、《废名·桥》、《二十世纪的诗心》、《文学性的命运》、《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梦中的彩笔》、《废墟的忧伤》、《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如此愉悦、如此忧伤》、《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等。
|
| 目錄:
|
上篇 寻梦与乌托邦
寻梦: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 /003
镜子: 临水的纳蕤思 /019
穿透: 对乌托邦远景的召唤 /070
远方: 只有一种生活的形式 /075
自然: 生态主义的诗学与政治 /085
下篇:彼岸与布托邦
漂泊: 东方的波德莱尔 /107
理趣: 废名的出世情调和彼岸色彩 /120
河陵: 想象中的“异托邦” /127
想象: 20 世纪中国诗人的江南 /144
凤凰: 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 /150
求索: 北岛“走向冬天”之后 /194
时间: 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到的 /209
外篇:其他诗意
乡愁: 尺八的故事 /217
无限: 20 世纪的新诗与诗心 /243
入城: 现代诗人笔下的外滩海关钟 /251
流亡: 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 /256
冰雪: 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 /303
死亡: 永远的绝响 /342
传统:《启明星》与燕园诗踪 /357
情境: 关于诗歌形式要素的一堂课 /371
后记: 诗心接千载 /394
|
| 內容試閱:
|
后记: 诗心接千载
出于对废名的偏爱, 也喜欢上了废名喜爱的一些中国古典诗句。在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随笔》 中, 废名称: “中国诗词,我喜爱甚多, 不可遍举。”在有限的数百字的篇幅中, 他着重列举的有王维和李商隐的诗句: “我爱王维的‘春草明年绿, 王孙归不归’。 因为这两句诗, 我常爱故乡, 或者因为爱故乡乃爱好这春草诗句亦未可知。”还有李商隐《重过圣女祠》中的两句: “一春梦雨常飘瓦, 尽日灵风不满旗。”称这两句诗“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中国绝无而仅有的一个诗品”。 废名对自己的这一略显夸大其词的判断给出的解释是:
此诗题为“重过圣女祠”, 诗系律诗, 句系写景, 虽然不是当时眼前的描写, 稍涉幻想, 而律诗能写如此朦胧生动的景物, 是整个作者的表现, 可谓修辞立其诚。 因为“一春梦雨常飘瓦”, 我常憧憬南边细雨天的孤庙, 难得作者写着“梦雨”, 更难得从瓦上写着梦雨, 把一个圣女祠写得同《水浒》上的风雪山神庙似的令人起神秘之感。 “尽日灵风不满旗”,大约是描写和风天气树在庙上的旗, 风挂也挂不满, 这所写的正是一个平凡的景致, 因此乃很是超脱。
废名因为“一春梦雨常飘瓦”而“常憧憬南边细雨天的孤庙”,我则因为废名的解读而愈发感受到晚唐温李的朦胧神秘。除了晚唐, 废名还喜欢六朝。 日本大沼枕山有诗云: “一种风流吾爱, 南朝人物晚唐诗,”用到废名身上其实更合适。 废名喜欢庾信的“霜随柳白, 月逐坟圆”, 称“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 并称杜甫的诗“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也是从庾信这里学来的, 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 在写于抗战期间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 废名曾不惜篇幅阐释庾信《小园赋》中的一句“龟言此地之寒, 鹤讶今年之雪”, 称那只会说话的“龟” “在地面, 在水底, 沉潜得很, 它该如何地懂得此地, 它不说话则已,它一说话我们便应该倾听了”, 我对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记录的作者历经战乱年代的不说则已的“垂泣之言” 的“倾听”, 也正因为废名对《小园赋》中的这句诗的郑重其事的解读。还有废名的“破天荒” 的作品———长篇小说《桥》。 《桥》 虽然是小说, 却充斥着谈诗的“诗话”。 《桥》中不断地表现出废名对古典诗句的充满个人情趣的领悟。 如《桥》一章男主小林有句话:
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你想, 红花绿叶, 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 ———朝云一刹那见。
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则称许说“也只有牡丹恰称这个意, 可以大笔一写”。 在《梨花白》一章中, 废名这样品评“黄莺弄不足, 含入未央宫”这句诗: “一座大建筑, 写这么一个花瓣, 很称他的意。”这同样是颇具个人化特征的诠释。 废名当年的友人鹤西甚至称“黄莺弄不足”中的一个“弄”字可以概括整部《桥》, 正因为“弄”字表现了废名对语言文字表现力的个人化的玩味与打磨。 鹤西还称《桥》是一种“创格”, 恐怕也包括了对古诗的个人化的阐释。“黄莺弄不足, 含入未央宫”经废名这样一解, 使我联想到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名句“我在田纳西州放了一个坛子”以及中国当代诗人梁小斌的诗句“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 并在课堂上把这几句诗当成诗歌中“反讽”的例子讲给学生, 同时想解说的是, 废名对古典诗歌的此类别出机杼和目光独具的解读, 其实构成的是在现代汉语开始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中思考怎样吸纳传统诗学的具体途径。 废名对古典诗歌的诸般读解也是把古典意境重新纳入现代语境使之获得新的生命。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进行的是重新阐释诗歌传统的工作, 古典诗歌不仅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遥迢的背景, 同时在废名的创造性的引用和阐释中得以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重新生成, 进而化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悟的有机的一部分。 正是废名在使传统诗歌中的意味、 意绪在现代语境中得以再生。 在这个意义上说, 废名是一个重新激活了传统“诗心”的现代作家。
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对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佳句、 美感乃至潜藏的“诗心”的领悟, 也深深地受惠于现代作家的眼光。
当年在高中课堂上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文中引用的“采莲南塘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早唤起我这个漠北之人对于杏花春雨“可采莲”的江南的想象和神往。而学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 后背下来的却是鲁迅引用的陶渊明《挽歌》中的那句“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一时思索的都是这个“何所道”的“死”。上大学后读郁达夫, 则喜欢他酷爱的黄仲则的诗句“如此星辰非昨夜, 为谁风露立中宵”, 脑海中一段时间里也一直浮起那个不知为谁而风露中宵茕茕孑立的形象。后来读冯至的散文, 读到冯至说他喜欢纳兰性德的“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 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才逐渐体会到另一种历经天凉好个秋的境界之后依旧情有所钟的中年情怀。读林庚, 喜欢他阐释的“无边落木萧萧下” (杜甫)和“落木千山天远大”(黄庭坚), 从中学习领会一种落木清秋特有的疏朗阔大的气息。 沈启无说当年林庚“有一时期非常喜爱李贺的两句诗,‘东家蝴蝶西家飞, 白骑少年今日归’。 故我曾戏呼之‘白骑少年’, 殆谓其朝气十足也”。 于是留在我脑海里的林庚先生就始终是一个白骑少年的形象, 这一“白骑少年”也加深了我对林庚先生所命名的“盛唐气象”和“青春李白”的理解。至于沈启无本人则喜欢贺铸的词“凌波不过横塘路, 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 月桥花院, 琐窗朱户, 唯有春知处”,称“这个春知处的句子真写得好, 此幽独美人乃不觉在想望中也”。 这个“幽独美人”由此与辛弃疾的“灯火阑珊处”的另一美人一道, 一度也使我“不觉在想望中也”。
读卞之琳, 喜欢他对苏曼殊《本事诗之九》的征引: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卞之琳的《尺八》诗和他华美的散文《尺八夜》都由对这首“春雨楼头尺八箫”的童年记忆触发。 我后来也在卞之琳当年夜听尺八的日本京都听闻尺八的吹奏, 再次被苏曼殊这一“性灵之作” (林庚先生语)深深打动。与卞之琳同为“汉园三诗人”组合的何其芳则颇起哀思于“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的比兴, 从中生发出的是自己生命中难以追寻的家园感。 一代“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的孤独心迹正由这句古诗十九首反衬了出来。
读端木蕻良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短篇小说《初吻》, 则困惑于小说的题记“鸟何萃兮蘋中, 罾何为兮木上”, 觉得这称得上是屈原的“朦胧诗”, 不若林庚所激赏的以及戴望舒曾在诗中化用过的那句“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那般纯美。同是《诗经》, 张爱玲喜欢的是“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称“它是一首悲哀的诗, 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 而周作人则偏爱“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大约鸡鸣风雨中也透露着知堂对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的深刻预感。
……
这些诗句当然无法囊括古典诗歌中的全部佳句, 甚至也可能并不真正是古诗中好的句子, 尤其像废名这样的作家, 对古典诗歌的体悟, 恐怕更带有个人性。 但现代作家们正是凭借这些令他们低回不已的诗句而思接千载。 古代诗人的遥远的烛光, 依然在点亮现代诗人们的诗心。 而这些现代作家与古典诗心的深刻共鸣, 也影响了我对中国几千年诗学传统的领悟。
与读小说不同, 读诗在我看来更是对“文学性”的体味、 对一种精神的怀想以及对一颗诗心的感悟过程。 中国的上百年的新诗恐怕没有达到二十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 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缺里尔克、 艾略特那种深刻的思想, 但是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藉着整个二十世纪, 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 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二十世纪, 如果没有这些诗歌, 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 没有什么光亮能胜过诗歌带来的光耀, 没有什么温暖能超过诗心给人的温暖, 任何一种语言之美都集中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之中。 尽管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诗歌也饱受“难懂”“费解”的非议, 但正像我在本书中引用过的王家新先生的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
比如说杜甫晚年的诗, 比如策兰的一些诗,
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
399辽远的国土: 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
艺术难度所在;
它们是诗中的诗, 石头中的石头;
它们是水中的火焰,
但也是火焰中不化的冰;
这样的诗就需要慢慢读, 反复读,
(好是在洗衣机的嗡嗡声中读)
因为在这样的诗中, 甚至在它的某一行中,
你会走过你的一生。
我所热爱的正是这种“诗中的诗, 石头中的石头”。 而其中“水中的火焰”以及“火焰中不化的冰”的表述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有想象力的论诗佳句, 道出了那些真正经得起细读和深思的诗歌文本的妙处。 王家新所喜欢的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的诗句, 也正是这种“诗中的诗”。 在诗圣这样的佳构中, 蕴藏着中国作为一个诗之国度的千载诗心, 正像在冯至、 林庚、 戴望舒等诗人那里保有着中国人自己的二十世纪的诗心一样。
我对新诗研究的早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本科二年级时上洪子诚老师的当代文学史课。 我从事文学研究的理想也正是在洪老师的课上萌发的。 我的篇学步阶段的诗歌评论就是因为受洪老师课程的影响, 写于本科二年级下学期, 题目是《走向冬天———北岛的心灵历程》。 我会永远记得 1987 年那个寒冷一月的雪后黄昏, 自己在故乡边陲小城买到第 1 期《读书》,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那种难以言喻的狂喜的心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洪老师的影响下写出篇研究性的文章, 是促使我走上今天这条以教书和写作为生的道路的重要因由之一, 因此, 多年来自己一直对洪子诚老师和当年他的课程心存感激。 《走向冬天———北岛的心灵历程》 发表后, 洪老师给我提了宝贵的意见,建议我关注北岛们在 1976 年以前曾经就接触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资源, 那次在课间向洪老师请教时洪老师的神态直到 20 多年后的今天依旧历历在目。 孙玉石老师也对我的这篇诗歌研究的习作给予鼓励。 也是在课间。 那是本科三年级的第二学期, 我选了孙老师现代诗导读的课程, 早培养了我对现代诗歌的文本解读的意识。 也正在孙老师一个学期的课程上, 参与诗歌文本解读文字的写作和诗歌解读的课堂讨论, 我逐渐感到自己终于一窥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堂奥, 也多少决定了我在跟随孙老师读博士学位期间选择“象征主义”作为博士论文的论题。 再后来照亮我的则是谢冕老师的《新世纪的太阳》等诗学著作, 谢老师开阔的视域和恢宏的气势, 使我反思自己在问学的道程中所为匮缺的精神和气质。 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写的一些诗歌方面的文章, 也正是受这几位老师深刻的影响的结果, 所以我把这本诗歌论集的编辑, 呈献给这几位老师, 以表达我对引我走上诗歌研究道路的老师们的衷心谢忱。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 与谢冕老师、 孙玉石老师、 洪子诚老师、 张剑福老师以及臧棣、 姜涛二兄一同参与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的活动, 我也加强了关于诗歌的阅读和写作, 陆续写出《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北岛论》《“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王家新论》《临水的纳蕤思》 《尺八的故事》,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等与诗歌相关的文章, 试图从中体味所谓世纪的“诗心”, 也在思考诗歌带给人类的“乌托邦”属性。
本书的名字就来自于我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所建构的想象世界的体悟。 以戴望舒、 何其芳为代表的一代诗人对“辽远的国土”的怀念, 也正是人类固有的“乌托邦”情结的体现,而诗歌是建构乌托邦想象的好的家园。 但诗歌也是适合“异托邦”想象的“居所”, 中国现代诗人也在同时构筑褔柯意义上的“异托邦”, 进而生成的是 20 世纪远为繁复的诗歌世界。
在中国现代诗歌众多的群落和流派中, 我长久阅读的, 是 20世纪 30 年代以戴望舒、 卞之琳、 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尽管这一批诗人经常被视为脱离现实的, 感伤颓废的, 远离大众的, 但在我看来, 他们的诗艺也是成熟精湛的。 “现代派”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常有的专注于诗艺探索的时代, 诗人们的创作中颇有一些值得反复涵泳的佳作, 其中的典型意象、 思绪、 心态已经具有了艺术母题的特质。 这使戴望舒们的诗歌以其艺术形式内化了心灵体验和文化内涵, 从而把诗人所体验到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所构想的乌托邦远景通过审美的视角和形式的中介投射到诗歌语境中, 使现代派诗人的历史主体性获得了文本审美性的支撑。
这批年青诗人群体堪称一代“边缘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阶级对垒、 阵营分化的社会背景下, 诗人们大都选择了游离于党派之外的边缘化的政治姿态; 同时, 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和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 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 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 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陌生感以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 五四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摧毁了他们纯真的信念, 于是诗作中普遍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意向, 充斥于文本的, 是对“辽远”的憧憬与怀想:
我觉得我是在单恋着,
但是我不知道是恋着谁:
是一个在迷茫的烟水中的国土吗,
是一支在静默中零落的花吗,
是一位我记不起的陌路丽人吗?
———戴望舒《单恋者》
无论是“烟水中的国土”“静默中零落的花”, 还是“记不起的陌路丽人”, 都给人以一种辽远而不可即之感, 成为“单恋者”心目中美好事物的具象性表达。 而“辽远”更是成为现代派诗中复现率极高的意象: “我想呼唤/ 我想呼唤遥远的国土” (辛笛《RHAPSODY》);“迢遥的牧女的羊铃, / 摇落了轻的木叶” (戴望舒《秋天的梦》); “想一些辽远的日子, / 辽远的, / 砂上的足音” (李广田《流星》);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 /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戴望舒《烦忧》); “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 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 和一些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 (何其芳《画梦录》)……在这些诗句中, 引人注目的正是“辽远”的意象,其“辽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乌托邦情境所不可缺少的时空距离,这种辽远的距离甚至比辽远的对象更能激发诗人们神往与怀想的激情, 因为“辽远”意味着匮缺, 意味着无法企及, 而对于青春期的现代派诗人们来说, 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就越能吸引他们长久的眷恋和执迷。 正如何其芳在散文《炉边夜话》中所说: “辽远使我更加渴切了。”这些“辽远”的事物正像巴赫金所概括的“远景的形象”, 共同塑造了现代派诗人的乌托邦视景, 只能诉之于诗人的怀念和向往。 当现实生活难以构成灵魂的依托, “生活在远方”的追求便使诗人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投向只能借助于想象力才能达到的“辽远的国土”。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
我, 我是寂寞的生物。
———戴望舒《我的素描》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构成了一代年青诗人的自画像, 由此也便具有了形塑一代人群体心灵的母题意味, 继而升华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 人们经常可以从一些并不缺少想象力的诗人笔下捕捉到令人倾心的华彩诗句或段落, 但通常由于缺乏一个有力的象征物的支撑而沦为细枝末节, 无法建立起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诗学王国。 而“辽远的国土”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象征物, 它使诗人们笔下庞杂的远景形象获得了一个总体指向而具有了归属感。 作为一个象征物, “辽远的国土”使诗人们编织的想象文本很轻易地转化为象征文本, 进而超越了每个个体诗人的“私立意象”, 而成为一个“公设”的群体性意象, 象征着现代派诗人灵魂的归宿地, 一个虚拟的乌托邦, 一个与现实构成参照的乐园, 一个梦中的理想世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现代派领袖人物的戴望舒把自己所隶属的诗人群体命名为“寻梦者”。
一代“寻梦者”对“辽远”的执着的眷恋也决定了现代派诗歌在总体诗学风格上的“缅想”特征。 “缅想”成为一种姿态, 并从文字表层超升出来, 笼罩了整个诗歌语境, 规定着文本的总体氛围。在诗人笔下, 这种“缅想”的姿态甚至比“远方”本身所指涉的内涵还要丰富。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把艺术视为“与天堂交谈的一种手段”, “寻梦者”们对“辽远”的缅想也无异于与理想王国的晤谈。 但这并不是说诗人们借此就能实现对不圆满的现世的超逸,事实上, 诗人们对远方的缅想背后往往映衬着一个现实的背景,恰恰是这个现实的存在构成了诗歌意绪的真正底色。 这使得诗人们的心灵常常要出入于现实与想象的双重情境之间, 在两者的彼此参照之中获得诗歌的内在张力。 譬如李广田的这首《灯下》:
望青山而垂泪,
可惜已是岁晚了,
大漠中有倦行的骆驼
哀咽, 空想像潭影而昂首。
乃自慰于一壁灯光之温柔,
要求卜于一册古老的卷帙,
想有人在远海的岛上
伫立, 正仰叹一天星斗。
这首诗正交织了现实与想象两种情境。 岁晚的灯下向一册古老的卷帙“求卜”构成了现实中的情境, 同时诗人又展开对大漠中倦行的骆驼以及远海岛上伫立之人的冥想。 诗人“望青山而垂泪”, 进而试图寻求自我慰藉, 对古老卷帙的求卜以及对远岛的遥想都是找寻安慰的途径。 但诗人是否获得了这种“自慰”呢? 大漠中空想潭影的饥渴的骆驼以及远方伫立者的慨叹只能加深诗人在现实处境中的失落, 构成的是诗人遥远的镜像。 因此, 仅从诗人的落寞的现实体验出发, 或者只看到诗人对远方物象的怀想,都可能无法准确捕捉这首诗的总体意绪。 文本的意蕴其实正生成于现实与远景两个世界的彼此参照之中。这种现实与想象世界的彼此渗透和互为参照不仅会制约诗歌意蕴的生成, 甚至也可能决定诗人联想的具体脉络以及诗歌的结构形式。 试读林庚的《细雨》:
风是雨中的消息
夹在风中的细雨拍在窗板上吗
夜深的窗前有着陌生的声音
但今夜有着熟悉的梦寐
而梦是迢遥或许是冷清的
或许是独立在大海边呢
但风声是徘徊在夜雨的窗前的
说着林中木莓的故事
忆恋遂成一条小河了
流过每个多草的地方
是谁知道这许多地方呢
且有着昔日的心欲留恋的
林中多了泽沼的湿地
有着败叶的香与苔类的香
但细雨是只流下家家的屋檐
渐绿了阶下的蔓生草
这是现代派诗中难得的美妙之作, 我们从中可以考察一种内在的乌托邦视景如何可能制约着诗歌中物景呈现的距离感。 诗中交替呈现“远景的形象”与切近的物像。 关于窗前风声雨声的近距离的观照总是与对远方的联想互为间隔, 远与近的搭配与组接构成了诗歌的具体形式。 诗人由窗前的“陌生的声音”联想到梦的迢遥以至“大海边”, 但迅速又把联想拉回到“夜雨的窗前”; 从风声述说的“林中木莓的故事”, 联想到“忆恋”的小河流过许多无人知道的地方, 再联想到“昔日的心”的留恋, 但马上又转移到对“流下家家的屋檐”的细雨的近距离描述, 整个结构仿佛是电影中现实与回忆、 彩色与黑白两组镜头的切换, 给读者一种奇异的视觉感受。 诗人的思绪时时被雨中的风声牵引到远方的忆恋的世界,又不时被拍打在窗板上的雨声重新唤回到现实中来。 远与近的切换其实体现的是诗人联想的更迭, 这正是联想与忆恋的心理逻辑, 《细雨》的结构形式其实是联想与追忆的诗学形态在具体诗歌,文本中的体现和落实。 《细雨》由此别出机杼地获得了对乌托邦视景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遥远与切近的两组意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和秩序, 构成了想象和现实彼此交叠映照的两个视界,从而使乌托邦远景真正化为现实生存的内在背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