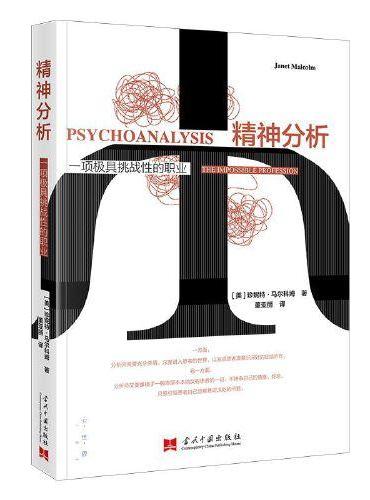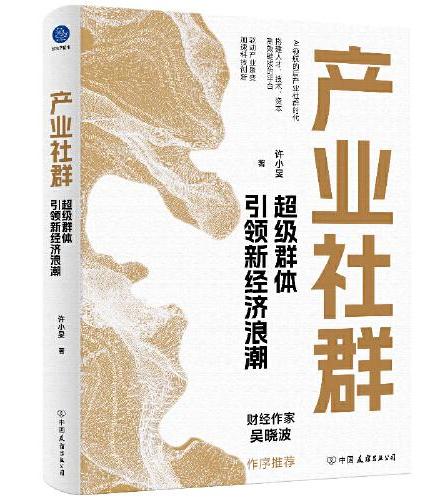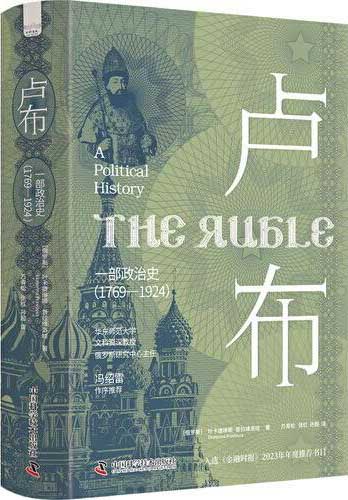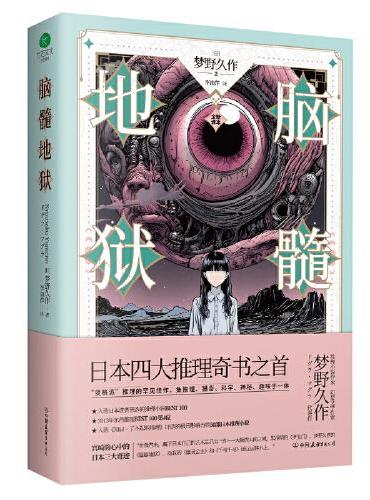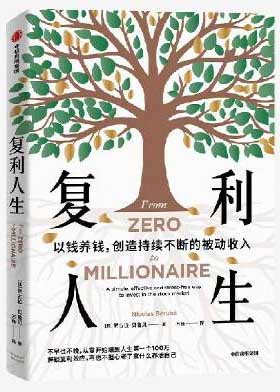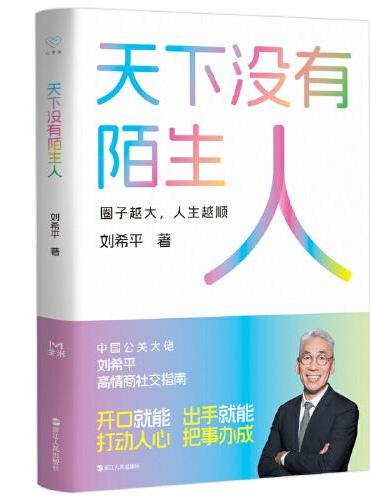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HK$
74.8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HK$
68.2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HK$
119.9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天下没有陌生人
》 售價:HK$
61.6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編輯推薦:
40多年来国际政治研究者必读书目
內容簡介: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杰维斯以研究核威慑理论活跃于国际政治学界,到70年代,借鉴认知心理学所著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使其蜚声国际政治学术界,他也借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微观层次国际政治理论。
關於作者:
罗伯特?杰维斯(1940—2021) 著名国际政治学学者,哥伦比亚大学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国际政治学教授。1940年4月生于美国纽约,1962年毕业于奥伯林学院,196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后一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国际政治学讲座教授。
目錄
译者前言 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1
內容試閱
增订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