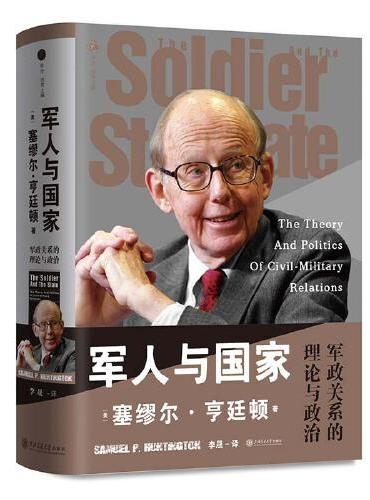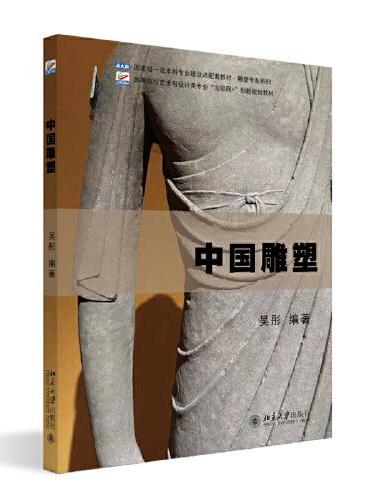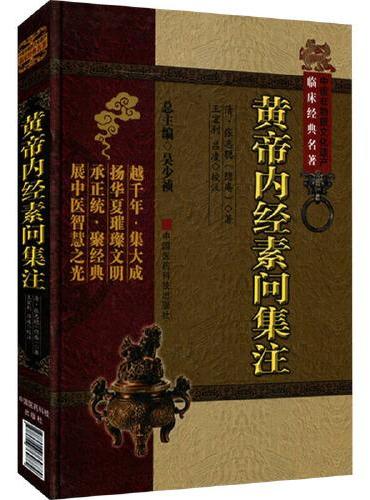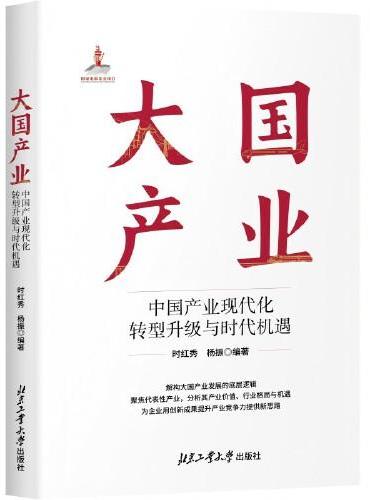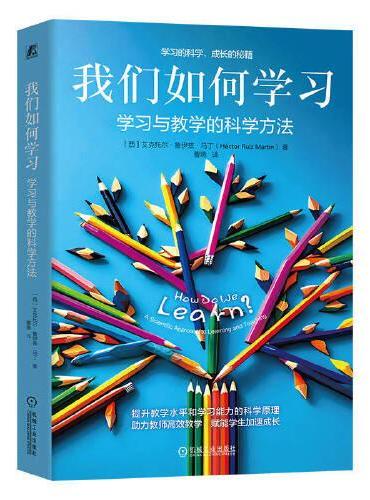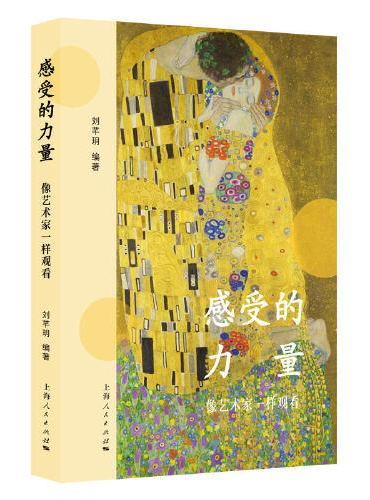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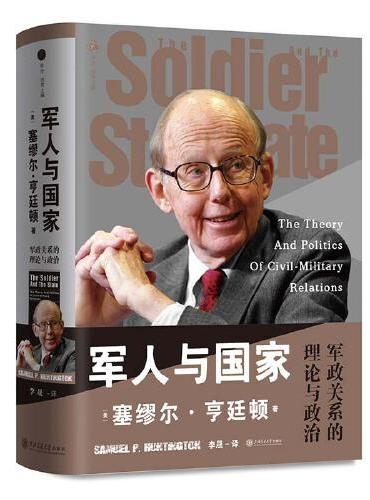
《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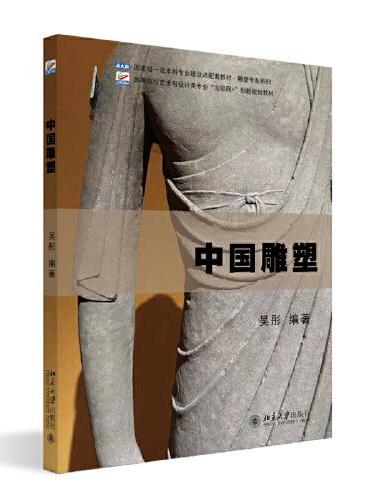
《
中国雕塑 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类专业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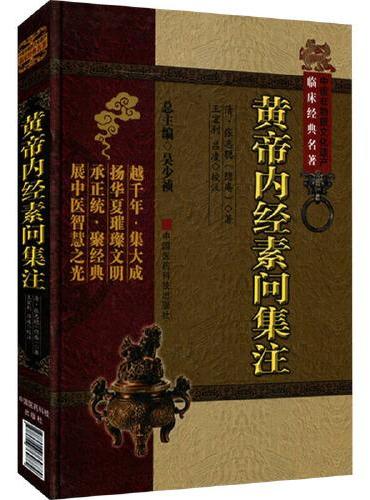
《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
售價:HK$
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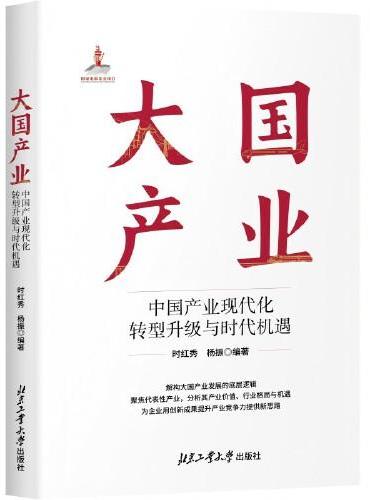
《
大国产业—中国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与时代机遇
》
售價:HK$
86.9

《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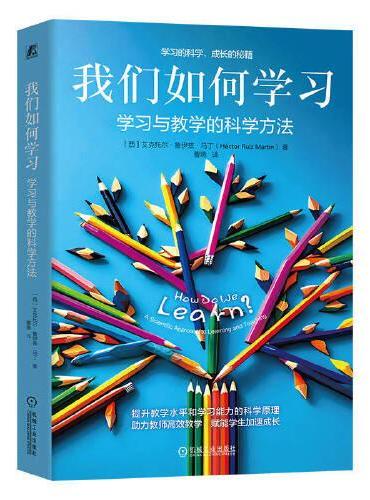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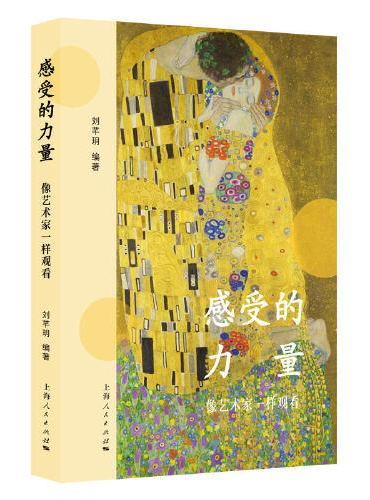
《
感受的力量--像艺术家一样观看
》
售價:HK$
57.2

《
诗词串起中国史:按照朝代顺序用诗词串起一部中国通史。
》
售價:HK$
264.0
|
| 編輯推薦: |
1. 作者余光中因一首《乡愁》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其散文创作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力,被誉为“文坛璀璨的五彩笔”、“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在大陆、香港和台湾都拥有较大读者群。
2. 从大陆到港台,从中国到欧美,余光中的一生都在漂泊,却认定大陆永远是自己的母亲,他的文字时刻都能引起游子的共鸣。
3. 作者学贯中西,是永远的华语文学大师,他的散文写尽一代人的乡愁、记忆与青春,传递跨越半个世纪的纯粹与感动。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名篇合辑,精选了作者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如《书斋·书灾》《何曾千里共婵娟》等。本书以“生活”与“文艺”为主题,包括生活智慧、文化思考、艺术审美等内容。书中有壮阔铿锵的大手笔,有细腻柔绵的小写意,还有深沉真挚的情感和思考,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读者阅读此书可以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内心,感受大师丰富的精神世界。
|
| 關於作者: |
余光中(1928—2017)
文学家、诗人、学者、翻译家。
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在华语世界影响深远,其作品被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中。
代表作品有《白玉苦瓜》《乡愁》《听听那冷雨》等。
|
| 目錄:
|
第一章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书斋·书灾
望乡的牧神
花鸟
假如我有九条命
一笑人间万事
日不落家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失帽记
第二章 万家灯火,人间百态
蝗族的盛宴
借钱的境界
朋友四型
幽默的境界
开你的大头会
钞票与文化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车上哺乳不雅?
第三章 纸上春秋,笔下山河
猛虎和蔷薇
诗的三种读者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何曾千里共婵娟
另一段城南旧事
第四章 对话缪斯,牧神午后
梵谷的向日葵
现代绘画的欣赏
毕卡索——现代艺术的魔术师
论披头的音乐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
| 內容試閱:
|
《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 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致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所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联副》
《开你的大头会》
世界上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辩一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仅仅消磨光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会场虽非战场,却有肃静之气,进得场来,无论是上智或下愚,君子或小人,都会一改常态,人人脸上戴着面具,肚里怀着鬼胎,对着冗赘的草案、苛细的条文,莫不咬文嚼字,反复推敲,务求措辞严密而周详,滴水不漏,一劳永逸,把一切可钻之隙、可趁之机统统堵绝。
开会的心情所以好不了,正因为会场的气氛只能够印证性恶的哲学。济济多士埋首研讨三小时,只为了防范冥冥中一个假想敌,免得他日后利用漏洞,占了大家的,包括你的,便宜。开会,正是民主时代的必要之恶。名义上它标榜尊重他人,其实是在怀疑他人,并且强调服从多数,其实往往受少数左右,至少是搅局。
除非是终于付诸表决,否则争议之声总不绝于耳。你要闭目养神,或游心物外,或思索比较有趣的问题,并不可能。因为万籁之中人声最令人分心,如果那人声竟是在辩论,甚或指摘,那就更令人不安了。在王尔德的名剧《不可儿戏》里,脾气古怪的巴夫人就说:“什么样的辩论我都不喜欢。辩来辩去,总令我觉得很俗气,又往往觉得有道理。”意志薄弱的你,听谁的说辞都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是正在侃侃的这位总似乎胜过了上面的一位。于是像一只小甲虫落入了雄辩的蛛网,你放弃了挣扎,一路听了下去。若是舌锋相当,场面火爆而高潮迭起,效果必然提神。可惜讨论往往陷于胶着,或失之琐碎,为了“三分之二以上”或“讲师以上”要不要加一个“含”字,或是垃圾的问题要不要另组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而新的委员该如何产生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等等,节外生枝,又可以争议半小时。
如此反复斟酌,分发(hair-splitting)细究,一个草案终于通过,简直等于在集体修改作文。可惜成就的只是一篇面无表情更无文采的平庸之作,绝无漏洞,也绝无看头。所以没有人会欣然去看第二遍。也所以这样的会开完之后,你若是幽默家,必然笑不出来,若是英雄,必然气短,若是诗人,必然兴尽。
开会的前几天,一片阴影就已压上我的心头,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烦。开会的当天,我赴会的步伐总带一点从容就义。总之,前后那几天我绝对激不起诗的灵感。其实我的诗兴颇旺,并不是那样经不起惊吓。我曾经在监考的讲台上得句;也曾在越洋的七四七经济客舱里成诗,周围的人群挤得更紧密,靠得也更逼近。不过在陌生的人群里“心远地自偏”,尽多美感的距离,而排排坐在会议席上,摩肩接肘,咳唾相闻,尽是多年的同事、同人,论关系则错综复杂,论语音则闭目可辨,一举一动都令人分心,怎么容得你悠然觅句?叶慈 说得好:“与他人争辩,乃有修辞;与自我争辩,乃有诗。”修辞是客套的对话,而诗,是灵魂的独白。会场上流行的既然是修辞,当然就容不得诗。
所以我最佩服的,便是那些喜欢开会、擅于开会的人。他们在会场上总是意气风发,雄辩滔滔,甚至独揽话题,一再举手发言,有时更单挑主席缠斗不休,陷议事于瓶颈,置众人于不顾,像唱针在沟纹里不断反复,转不过去。
而我,出于潜意识的抗拒,常会忘记开会的日期,惹来电话铃一迭连声催逼,有时去了,却忘记带厚重几近电话簿的议案资料。但是开会的烦恼还不止这些。
其一便是抽烟了。不是我自己抽,而是邻座的同事在抽,我只是就近受其熏陶,所以准确一点,该说闻烟,甚至呛烟。一个人对于邻居,往往既感觉亲切又苦于纠缠,十分矛盾。同事也是一种邻居,也由不得你挑选,偏偏开会时就贴在你隔壁,却无壁可隔,而有烟共吞。你一面呛咳,一面痛感“远亲不如近邻”之谬,应该倒过来说“近邻不如远亲”。万一几个近邻同时抽吸起来,你就深陷硝烟火网,呛咳成一个伤兵了。好在近几年来,社会虽然日益沉沦,交通、治安每况愈下,公共场所禁烟却大有进步,总算除了开会一害。
另一件事是喝茶。当然是各喝各的,不受邻居波及。不过会场奉茶,照例不是上品,同时在冷气房中迅趋温吞,更谈不上什么品茗,只成灌茶而已。经不起工友一遍遍来壶添,就更沦为牛饮了。其后果当然是去“造水”,乐得走动一下。这才发现,原来会场外面也很热闹,讨论的正是场内的事情。
其实场内的枯坐久撑,也不是全然不可排遣的。万物静观,皆成妙趣,观人若能入妙,更饶奇趣。我终于发现,那位主席对自己的袖子有一种,应该是不自觉的,紧张心结,总觉得那袖口妨碍了他,所以每隔十分钟左右,会忍不住突兀地把双臂朝前猛一伸直,使手腕暂解长袖之束。那动作突发突收,敢说同事们都视而不见。我把这独得之秘传授给一位近邻,两人便兴奋地等待,看究竟几分钟之后会再发作一次。那近邻观出了瘾来,精神陡增,以后竟然迫不及待,只等下一次开会快来。不久我又发现,坐在主席左边的第三位主管也有个怪招。他一定是对自己的领子有什么不满,想必是妨碍了他的自由,所以每隔一阵子,最短时似乎不到十分钟。总情不自禁要突抽颈筋,迅转下巴,来一个“推畸”(twitch)或“推死它”(twist), 把衣领调整一下。这独家奇观我就舍不得再与人分享了,也因为那近邻对主席的“推手式”已经兴奋莫名,只怕再加上这“推畸”之扭他负担不了,万一神经质地爆笑起来,就不堪设想了。
当然,遣烦解闷的秘方,不止这两样。例如耳朵跟鼻子人人都有,天天可见,习以为常竟然视而不见了。但在众人危坐开会之际,你若留神一张脸接一张脸巡视过去,就会见其千奇百怪,愈比愈可观,正如对着同一个字凝神注视,竟会有不识的幻觉一样。
会议开到末项的“临时动议”了。这时最为危险,只怕有妄人意犹未尽,会无中生有,活部转败,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什么新案来。
幸好没有。于是会议到了最好的部分:散会。于是又可以偏安半个月了,直到下一次开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西子湾
《诗的三种读者》
不时有人会问我:“诗应如何欣赏?”
这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如果问者是一个陌生人,我就会说:“那要看你对诗有什么要求。如果你的目的只在追求‘诗意’,满足美感,那就不必太伤脑筋,只要兴之所至,随意讽诵吟哦,做一个诗迷就行了。如果你志在做一位学者,那么诗就变成了学问,不再是纯粹的乐趣了。诗迷读诗,可以完全主观,也就是说,一切的标准取决于自己的口味。学者读诗,却必须尽量客观,在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在进入一首诗的核心之前,更需要多认识那首诗的背景和环境。学者对一首诗的‘欣赏’,必须建基在‘了解’之上。如果你志在做一位诗人,那读法又不同了。学者对一首诗的责任,在于了解,不但自己了解,还要帮助别人了解。诗人面对一首诗,尤其是一首好诗,尤其是一首新的好诗,往往像一个学徒面对着师父,总想学点什么手艺,不但目前使用,更待他日翻新出奇,把师父都比了下去。学者读诗,因为是做学问,所以必须耐下心来,读得彻底而又普遍,遇到不喜欢的作品,也不许绕道而过。诗人读诗,只要拣自己喜欢的作品就行,不喜欢的可以不理——这一点,诗人和一般读者相同。不同的是:一般读者读了自己喜欢的诗,就达到目的了,诗人却必须更进一步,不但读得高兴,还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善加利用。譬如食物,一般读者但求可口,诗人于可口之外,更须注意摄取营养。”
当然,学者和诗人在本质上也都是读者,不过他们都是专业的读者,所以读法不同。非专业性的读者,可以称为“纯读者”。“纯读者”之中未必没有博学而高明的“解人”,只是他们不写文章,不以学者自命而已。
一般的纯读者,往往在少年时代爱上了诗。那种爱好往往很强烈,但也十分主观,而品味的范围也十分狭窄。纯读者对诗浅尝便止,欣赏的天地往往只限于三五位诗人的三五十首作品。因为缺乏比较,也无力分析,这几十首诗便垄断了他的美感经验,似乎天下之美尽止于此。纯读者的兴趣往往始于选集,也就终于选集,很少发展及于专业,更不可能进入全集。且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因为未选李贺,所以纯读者往往不读李贺。至于杜牧,因为所选九首之中,七绝占了七首,所以在纯读者的印象之中,他似乎成了专用七绝写柔美小品的诗人了。纯读者的品味能力,缺少锻炼,无由扩大,一过青年时代,往往也就不再发展了。
我在少年时代读诗,自命可恃直觉与顿悟,对于诗末的注解之类,没有耐心详阅。这种“不求甚解”的天才读法,对付“床前明月光”和“桂魄初生秋露微”一类的作品,也许可以,而遇到典故复杂背景特殊的一类,就所得无几了。学者读诗,没有一个能不看注解的。要充分了解一首诗,不能不熟悉作者的生平与时代,也不能不分析诸如格律、意象、结构等等技巧。中国的传统研究往往太强调前者,西方的现代批评又往往太注重后者,如能两者相济,当较为平衡可行。诗的讲授、评论、注解、编选、翻译等等,都是学者的工作。
诗人又是另一种特别的读者。苏轼读诗,和朱熹读诗是不一样的。诗人读诗,固然也求了解别的诗人,但是更想触发自己创作的灵感。所以苏轼读了陶诗,便写了许多和陶之作。东坡集中,和韵次韵之作,竟占五分之一以上,那首有名的“人生到处知何似”也是为和子由而写的,但子由的原作却无人读了。杜甫之名句“转益多师是汝师”,正说明了,要做诗人,就要放开眼界,多读各家作品,才能找到自己要走的大道。低下的诗人只能抄袭字句,高明的诗人却能脱胎换骨,伟大的诗人则点铁成金,起死回生,无论所读的作品是好是坏,都能转化为自己的灵感。
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
读者赏花。学者摘花。诗人采蜜。
一九七九年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