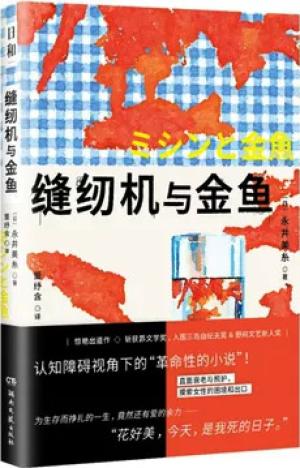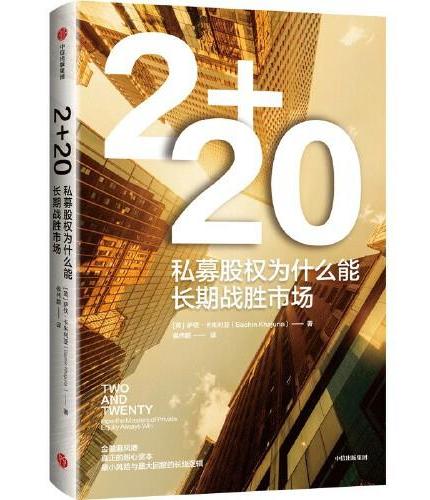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HK$
68.2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HK$
41.8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HK$
54.8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HK$
63.8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HK$
86.9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HK$
32.8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HK$
86.9
編輯推薦:
移民之国的一场人性试炼战争、贫困、动乱、流感……在这失控的岁月里,我只想竭尽全力地活下去!美国版《活着》真实描摹德裔美国人不堪回首的“敌国侨民”岁月当我的名字成为我与生俱来的罪过,当身份成为偏见与仇恨的理由,我们只能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融化坚冰。取材自作者真实的家族经历作者的母亲就是书中在1918年流感肆虐时降生的那个小女孩。作者用诗意的语言,让百年前的历史在字里行间鲜活重现。
內容簡介:
1918年,随着美国对德宣战,反德情绪像流感一样席卷全美。在美国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上,德国移民沃格尔一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仇恨和偏见,一场身份认同危机悄然来袭……
關於作者:
凯伦·休梅克(Karen Shoemaker),美国作家、教师。其作品曾发表于《纽约时报》《伦敦时报》。著有短篇小说集《夜晚的声音》(Night Sounds and Other Stories)等。
內容試閱
窗外,平原一望无垠,没有色彩,也没有变化。清晨看起来像是正午,整个白昼也可以如同夜晚一般。地平线,即天空与地面相接的那条线,消失了;远处与近处毫无区别。透过结了霜的车窗向外看去,若有任何形状出现,那形状也只有大小之分。大多数时候,你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