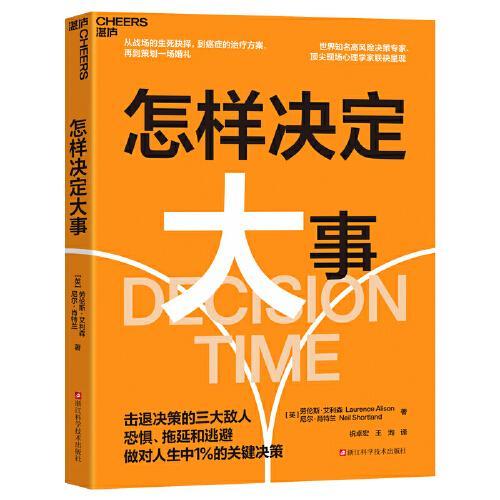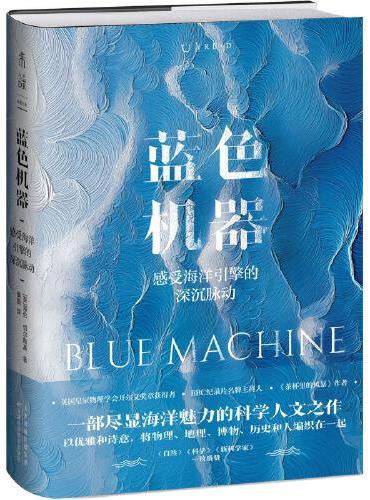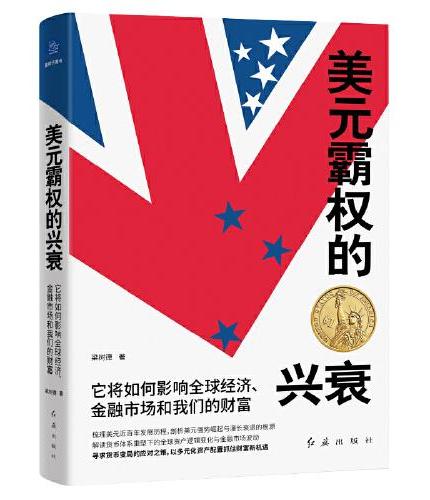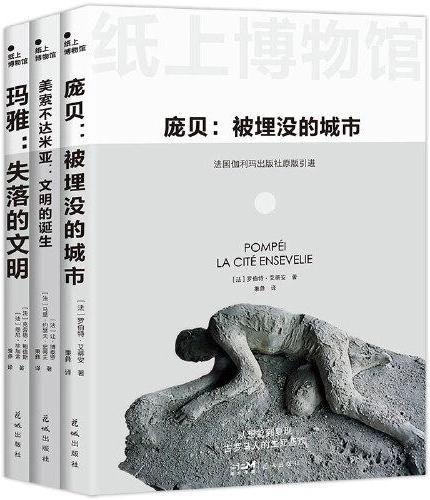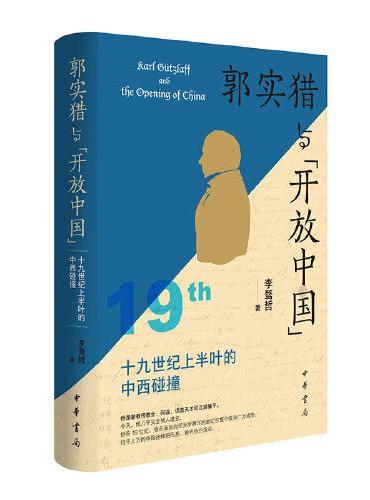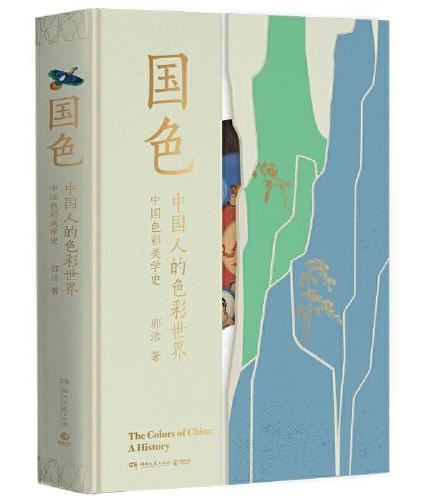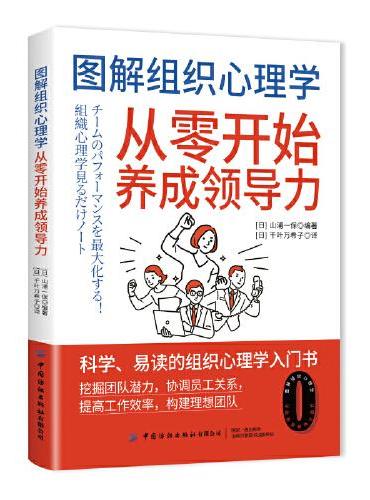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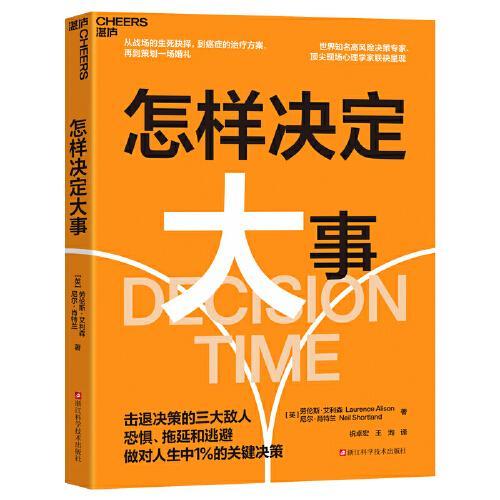
《
怎样决定大事
》
售價:HK$
1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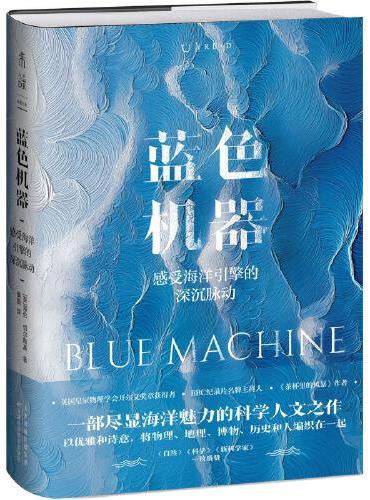
《
蓝色机器:感受海洋引擎的深沉脉动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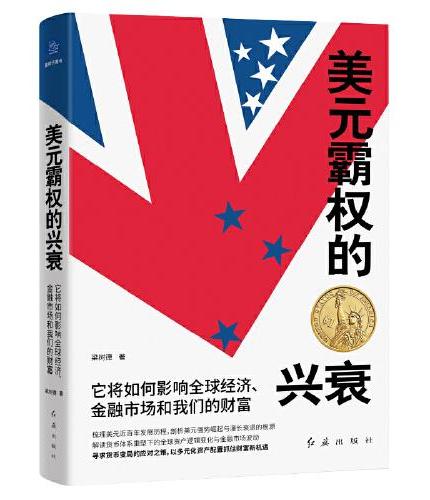
《
美元霸权的兴衰: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我们的财富(梳理美元发展历程,剖析崛起与衰退的根源)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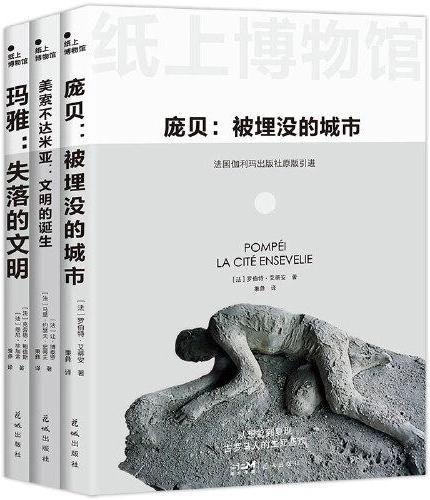
《
纸上博物馆·文明的崩溃:庞贝+玛雅+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450+资料图片,16开全彩印刷)
》
售價:HK$
2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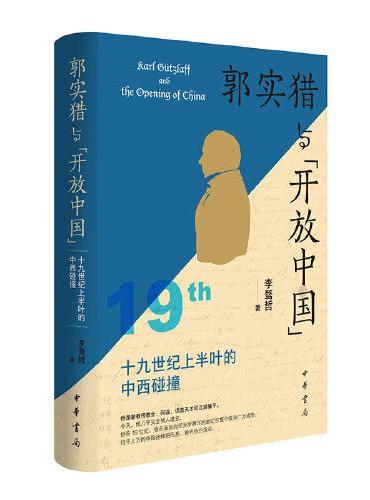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HK$
74.8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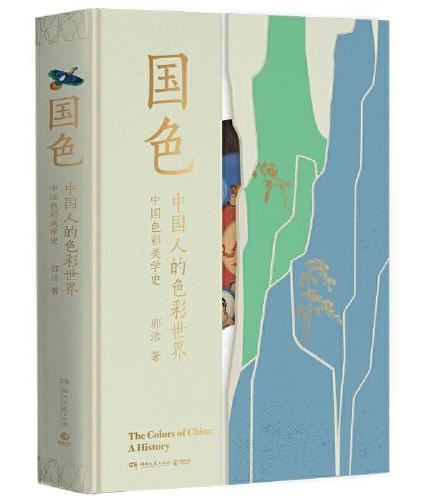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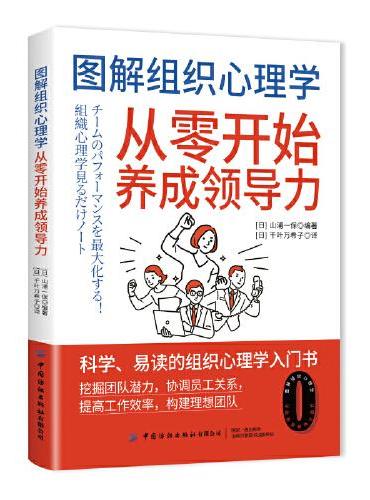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荣获英语文学界备受尊崇的奖项布克奖,掀起“去欧洲中心叙事”文学阅读热潮
因其精湛的写作艺术与深刻的人文关怀,2021年布克奖评委们称赞《承诺》是“一部杰作”,是“21世纪小说繁荣的证明”,故而将布克奖颁给了它。同时,作者达蒙·加尔格特与当年的国际布克奖得主达维德·迪奥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一道,将国际出版人、评论界及读者的焦点转向欧洲之外的文学叙事,形成一股强大的非洲文学力量。
年少成名,三度入围布克奖,库切之后最耀眼的南非作家!
达蒙·加尔格特是南非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7岁即写出长篇处女作,曾获多项文学大奖提名,并三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最终凭借《承诺》摘得2021年布克奖,成为继纳丁·戈迪默、J. M. 库切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南非作家,是不可错过的当代英语文学写作者。
声音如海浪翻涌,视角如镜头游移——现代文学艺术的当代传承
《承诺》完美继承并改造了现代主义的叙述技巧,文字灵动细腻,自由移动的视角在人物、动物之间切换,是一部电影感十足的“多声部”小说,令人赞叹。布克奖评委会、文学评论家甚至将加尔格特与现代文学大师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相提并论。
“他
|
| 內容簡介: |
“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倒台,
你瞧,现在我们离彼此很近,如此亲密,会死在一起。
我们仍需解决的,只有那些针对活人的遗留问题。”
四场葬礼,三十余年,两个种族,一份承诺。
1986年春,妈。
1995年冬,爸。
2004年秋,阿斯特丽德。
2018年夏,安东。
差不多每隔十年,斯瓦特家族的成员便会聚在一起,为又一位逝去的亲人举行葬礼。
季节交替,时局变更,欲望、偏见,以及一份久未兑现的承诺,却始终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小说以电影镜头般的灵动视角、海浪般起伏的文字,讲述一家一国的命运与前途。
|
| 關於作者: |
作者 | 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1963— )
南非小说家、剧作家,曾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戏剧。十七岁即写出长篇处女作《无罪的季节》,目前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和四部剧作。
其作品曾获英联邦作家奖、国际都柏林文学奖、沃尔特·司各特奖提名,三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最终凭借《承诺》摘得2021年布克奖,成为继纳丁·戈迪默、J. M. 库切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南非作家。
译者| 黄建树
生于湖北宜都,现居湖北武汉。上班时编书,下班后读书、买书、译书,以及养娃。
|
| 內容試閱:
|
透过客厅的玻璃推拉门,阿莫尔能看见那两个人,一位是她姑父,另一位是面露疑色的牧师。她能从小山的山顶看见整栋房子的正面,所有的窗户一览无余,所以她才喜欢坐在这里,虽然她不该独自这么做。一楼从来没这么热闹过,许多人影在房子里四处走动,宛如玩具大厦里的玩偶。可她并不在意他们。她眼里只有一扇窗户,是楼上从左往右数的第三扇,她一边看,一边想,她就在里面。要是我走下小山,走上楼梯,她一定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等我。像往常一样。
而且她能看见有人在里面走动。看身形,是个女人,正忙得团团转。若是半闭着眼,阿莫尔能想象那人就是她母亲,如假包换,她已重获健康强壮的体魄,正在清理床边的那些药物。再也用不着了。妈又好起来了,时光已然倒流,世界完好如初。就这么简单。
可她知道,她只是在假装,房间里的人不是妈。是萨洛米,当然是她,她一直待在这座农场里,或者说,她一直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我爷爷谈起她来总这么说,噢,萨洛米,我买这块地的时候顺带雇了她。
稍事停顿,好好观察一番,这时萨洛米正将床单从床上取下来。那个壮实的女人穿着旧衣服,是多年前妈给她的。头巾绑在头发上。她光着脚,脚底很脏,都开裂了。她的手上也有伤痕,是无数次碰撞后留下的擦伤与疤痕。据说她跟妈同岁,四十,不过更显老。很难讲她到底多少岁。生活中的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戴着面具,如同雕像一般。
但有些事情你确实知道,因为你亲眼见过。萨洛米不动声色地打扫房子,给住在里面的人洗衣服,也曾以同样的态度照顾生病的妈,陪她走完最后一程,帮她穿衣服,脱衣服,用一桶热水和一条毛巾帮她洗澡,扶她上厕所,是的,甚至在她用过便盆后帮她擦屁股,擦掉血污、粪便、脓液、尿渍,都是些自家人不愿干的活儿,要么太脏,要么太私密,让萨洛米去做吧,花钱雇她,就是让她做这些事的,不是吗?妈死的时候,她就在床边陪着妈,不过大家似乎没看见她,明显是把她当作了隐形人。同样隐形的,还有她的感受。大家只会吩咐她,把这里打扫干净,把床单洗了。她则一一照做,她打扫卫生,她清洗床单。
可阿莫尔能透过窗户看见她,所以终究还是有人注意到她并非隐形人。与此同时,想起了一段直到此刻才明白过来的往事:就在两周前的某个下午,她还在同一个房间里,跟妈和爸待在一起。他们忘了我也在那儿,待在角落里。他们没看见我,对他们来说,我就像个黑人妇女。
(你能答应我吗,马尼?
紧紧抓着他,瘦骨嶙峋的手紧握不放,那情景,仿佛出自一部恐怖电影。
嗯,我会做到的。
因为我真心希望她能得到些什么。毕竟她付出了这么多。
我明白,他说。
答应我,你会做到的。把话说出口。
我答应你,爸声音哽咽地说道。)
这一幕依旧历历在目,她父母纠缠在一起,像耶稣和他母亲一样,仿佛打了一个可怕且悲伤的结,紧紧抱着彼此,哭个不停。说话声在别处,越飘越高,越飘越远,直到现在才传到她耳畔。可她终于意识到他们说的到底是谁了。当然。显而易见。毋庸置疑。
她正坐在她喜欢的地方,在岩石之间,在那棵被烧焦的树的树根旁。闪电落下来的那一次,我就坐在这里,结果我差点当场死掉。砰,白色的火焰从天而降。就像上帝把你当成了靶子,爸说,但他怎么会知道呢?事发时,他甚至都不在这里。主的愤怒如同复仇之火。可我跟那棵树不一样,我没被烧死。只烧伤了脚。
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才痊愈。脚底到现在还有些痛,而且少了一根小脚趾。此时她摸了摸脚趾处,用手指感受那道疤痕。总有一天,她大声说道。总有一天,我会。她想到一半,思绪却断了;于是,她总有一天会做的那件事没了下文,悬在了那里。
这时,有人正从山的另一边往上爬。一个人影越来越近,慢慢显出了面目,将年龄、性别、种族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到最后,一个黑人男孩映入她的眼帘,也是十三岁,穿着破旧的短裤和T恤,脚上则穿着破破烂烂的运动鞋。
汗水把衣服黏在身上了。用你的手指把衣服扯一扯。
你好,卢卡斯,她说。
你好,阿莫尔。
首先,需要用棍棒敲打地面。随后,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了一块岩石上。两人交谈起来并不拘束。他们不是头一回在这里见面。都还是孩子,不过很快就不是了。
我为你妈妈的事感到难过,他说。
她差点再次哭起来,但没有。他这么说没关系,毕竟卢卡斯的父亲也死了,死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座金矿上,当时他还很小。有什么东西将两人连在了一起。她快憋不住了,想把刚刚记起来的事情说给他听。
现在是你们的了,那栋房子,她说。
他看着她,不太明白。
我妈妈让我爸爸把它送给你妈妈。基督徒一向说话算话。
他低头望着山的另一边,他就住在那里,在那座歪歪扭扭的小屋里。隆巴德家的房子。大家都是这么叫的,尽管隆巴德老太太多年前就死了,后来,阿莫尔的爷爷为了阻止那家子印度人搬进来,便买下了它,并让萨洛米住了进去。有些名字会留传下来,有些则不然。
我们的房子?
马上就是你们的了。
他眨了眨眼,依然很困惑。那栋房子一直都是他的家。他出生在那里,睡在那里,这个白人女孩在说些什么?他觉得越来越没劲,便吐了口唾沫,站了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双腿已变得又长又壮,大腿上长出了粗硬的毛。她还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是股汗臭味。这一切给她一种新奇的感觉,或者说,是她之前从没留意过这一切;甚至在她意识到他在看她之前,她便已经很尴尬了。
怎么了?她蜷缩着身子,胳膊放在膝盖上,说道。
没什么。
他跳到她坐着的岩石旁,在她身边蹲下。他光着的腿离她的腿很近,她能感觉到温暖和刺痒,便把膝盖侧向一旁。
呃,她说。你得洗一洗了。
他迅速起身,跳回了之前坐着的那块岩石上。这时她觉得很难过,觉得不该赶他走,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捡起先前用过的棍棒,再次用它敲敲打打起来。
好吧,他说。
嗯。
他沿着来时上山的路走回山下,时而用棍棒挥砍白色的草尖,时而将它插入白蚁的巢穴。让世界知道他的存在。
她一直看着他,直到他从视野中消失,这时她觉得轻松了一些,因为那辆黑色的大轿车已经开走,笼罩在她心头的那团大黑云也已消散。接着她溜达到小山的另一边,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脚步,观察一块石头或一片树叶,朝自己家的房子,或是她觉得属于自己家的房子走去。等她从后门进来时,距离她出走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三分二十二秒。在此期间,开来了一辆车,开走了四辆,包括那辆长长的黑色轿车。电话响了十八次,门铃响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因为有人大老远地送来了一些花,它们的出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人们喝掉了二十二杯茶、六杯咖啡、三杯冷饮,以及六杯加了可乐的白兰地。楼下的三个抽水马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仗,总共冲了二十七次水,冲走了九点八升尿液、五点二升粪便、某个反胃的人吐出来的一肚子食物,以及五毫升精液。数字层出不穷,但数学有什么用呢?每个人的生命中,每样东西其实只有一个。
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虽说屋里的这一片很安静,可她还是听到了远处的说话声。她走上楼梯,来到二楼。沿过道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她得路过通往妈房间的那扇门,房里此刻空无一人。萨洛米洗寝具去了;尽管她知道没有发生的事情并未发生在这里,但她于情于理都得进去。
小女孩看着母亲的遗物。她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从门口走到床边要多少步,台灯的开关在哪里,地毯上的橙色旋涡图案(仿佛会引起头痛),等等,等等。她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以为看见妈的脸出现在了镜中,可等她直直地往镜子里一看,它却不见了。她反倒能闻到母亲的气息,或者说,能闻到一股复杂的气味,她把它与母亲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它却源自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涉及呕吐物、熏香、血液、药物、香水和某种隐秘的黑色音符,兴许是疾病本身的气味。由墙壁呼出,在空中盘旋。
她不在这里。
说话的是姐姐阿斯特丽德,她不知怎么发现了她,跟了过来。
他们把她带走了。
我知道。我看见了。
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已被拿走,光秃秃的床垫上沾着某种东西,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她俩看着那漆黑的轮廓,仿佛看着一幅地图,地图上是一块新大陆,既迷人,又令人恐惧。
她死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阿斯特丽德终于说道;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毕竟她说的不是实话。母亲死的时候,她并不在母亲身边。当时她待在马厩后面,正和迪安·德韦特聊着天,那男孩来自勒斯滕堡,有时会来农场帮忙打扫马厩。迪安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阿斯特丽德的母亲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开导她。他是个朴素、真诚的男孩,他的关心让她感到高兴;她最近很乐于接受男性投来的目光,这便是其中一例。所以说,蕾切尔·斯瓦特大限已至时,陪着她的只有她丈夫(也就是爸,亦称马尼),还有那个黑人女佣,她叫什么来着,萨洛米,很明显,她无足轻重。
我本该在那里。阿斯特丽德心想。可她却在和迪安调情,这确实只会让她更加内疚。她有种错觉,认为妹妹很了解她那些事。不止这件事,还有其他事。比方说,半小时前,她把吃过的午饭吐了出来,为了保持身材,她经常这么干。她很容易疑神疑鬼,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有时候,她怀疑自己的心思能被周围的人偷偷读懂,有时候,她又怀疑生活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表演,别人都是演员,只有她不是。阿斯特丽德很容易害怕。抛开别的不说,她害怕黑暗、贫穷、雷暴、变胖、地震、潮汐、鳄鱼、黑人、未来、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害怕不被爱。害怕一直都没有变化。
可现在,阿莫尔又哭了,因为阿斯特丽德说起那个词来,就好像真有其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并非如此,哪怕房子里满是不该出现的人,满是通常不会出现或通常不会同时出现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