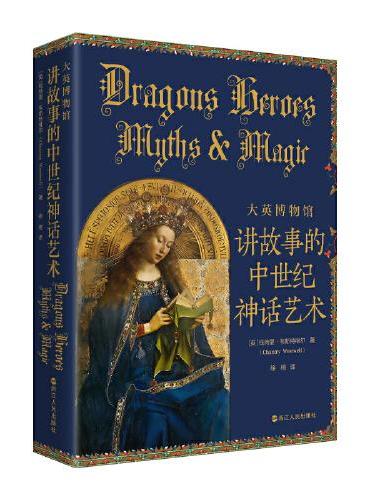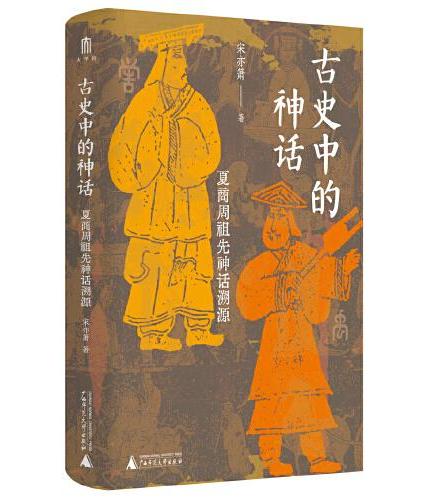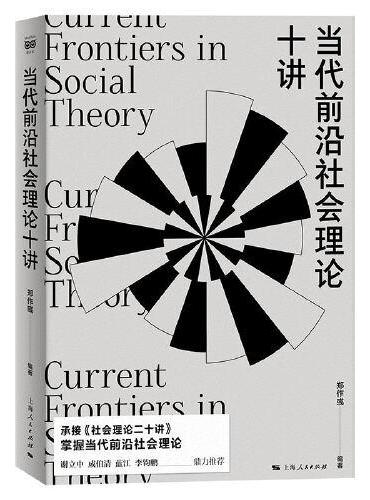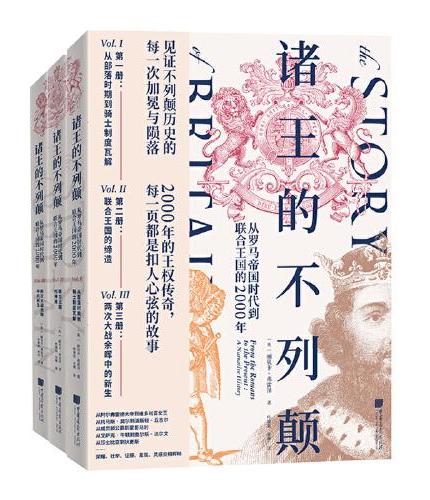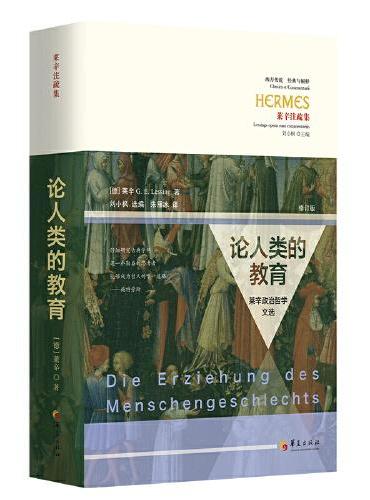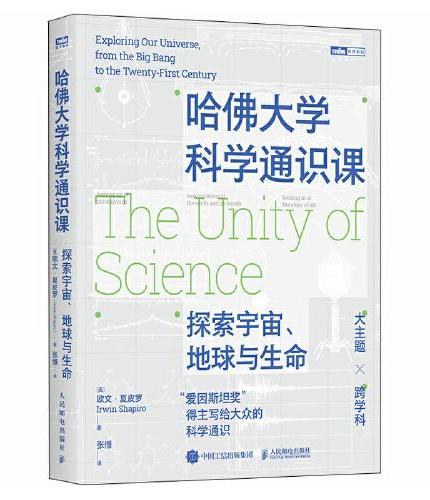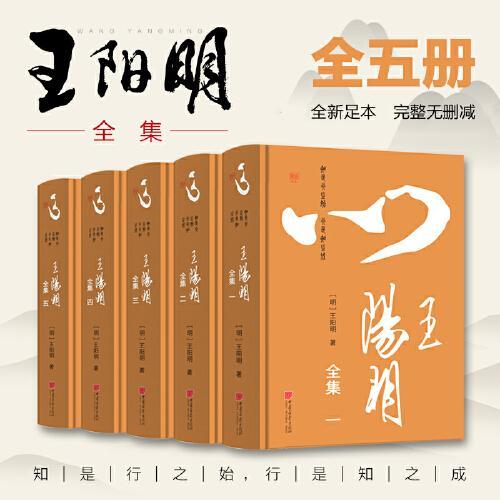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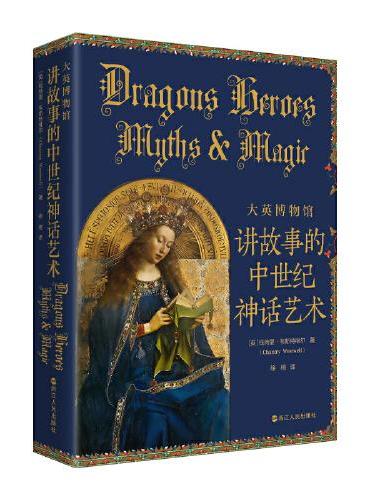
《
大英博物馆:讲故事的中世纪神话艺术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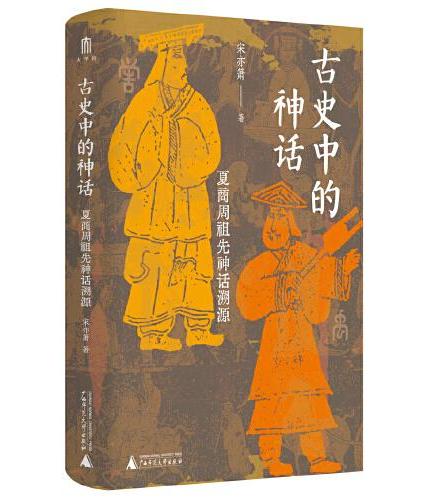
《
大学问·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一部三代造神指南,重构夏商周祖先神话)
》
售價:HK$
96.8

《
俗说矩阵——线性代数详解(Python+MATLAB)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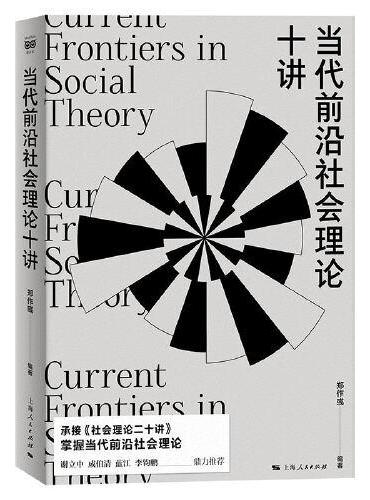
《
当代前沿社会理论十讲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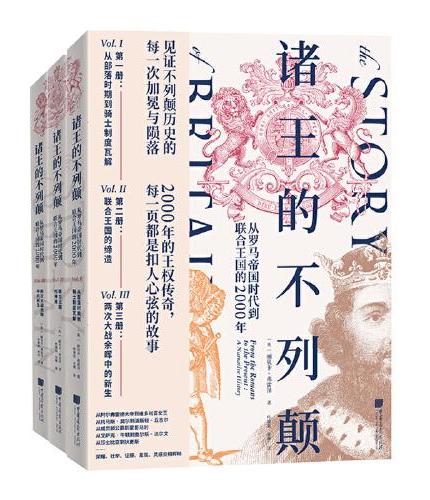
《
诸王的不列颠: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联合王国的2000年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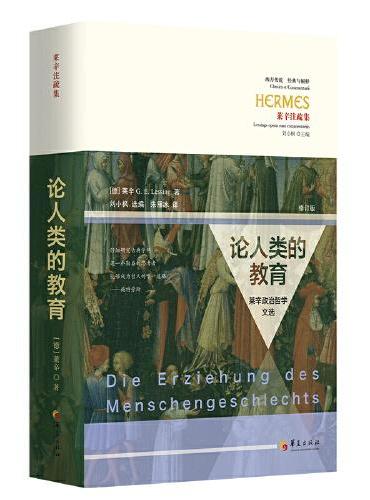
《
论人类的教育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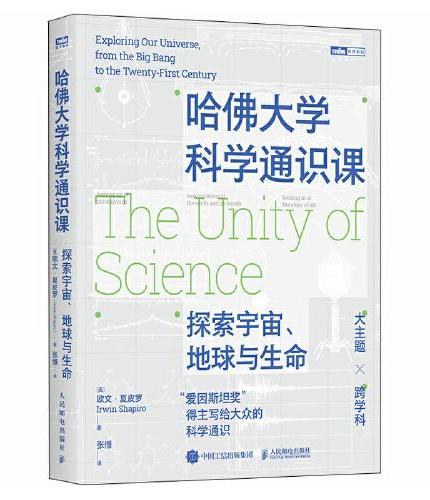
《
哈佛大学科学通识课:探索宇宙、地球与生命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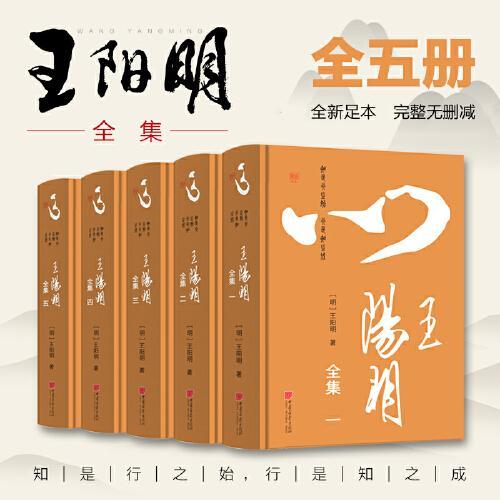
《
王阳明全集(套装5册)
》
售價:HK$
294.8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收录了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历次访谈中的精彩篇目,主题包括文学、教育、文化、传统、人生等方面。通过这些富含真知灼见和人生智慧的访谈,读者不难看到一个当代著名学者的精神坚守和大爱情怀。本书通过一篇篇精彩的访谈,展现了陈思和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辛勤耕耘、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丰硕成果以及他在治学过程中的珍贵经验,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当代学者对于学术、教育、人生的独到见解和担当意识。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搜集、整理、选编了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传播学科知识、学术心得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多篇访谈录,每一篇文字既是交心的谈话,也是长者的经验,包含这做人道理、做学问方法以及言说背后体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是青年人以及教育从业者的必读书。
|
| 關於作者: |
|
陈思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人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复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获上海市共青团颁发的“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和五四奖章、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BU跨世纪人才”称号以及霍英东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
|
| 目錄:
|
目 录
001 总 序
第一辑
002 巴金研究访谈录——答孙正萱
017 给知识以生命——答黄发有
034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史,力量在未来——答柯弄璋
050 久别的未曾失去的笔——答吴天舟
088 百年新文学 百年新发展——答郭瑾海
103 八个会议,一个时代——答周明全
136 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答舒晋瑜
第二辑
158 百年荣枯一夕话——答李瑞腾
165 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展望——答李安东
182 要有一颗敢于抗衡的心——答唐明生
197 有行有思,境界乃大——答颜敏
211 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答傅小平
第三辑
002 做同代人的批评家——答金理
024 学院批评在当下批评领域的意义和作用——答梁艳
040 评论家不食人间烟火 文坛会干净得多——答陈仓
第四辑
056 大学教育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岗位——答张新颖
071 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答李辉
095 从中学语文教材改革谈起——答刘旭
107 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答刘志荣
120 让自我超越自由与无用——答朱朋朋
第五辑
134 关于“火凤凰”,我还要说什么——答王文祺
143 在出版中贯穿人文精神——答金理、黄华远
153 继往开来——答姚克明
161 传承人文薪火——答黄发有
184 我与图书馆是很有些缘分的——答傅艺伟
198 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答柏琳
205 编后记 陈丙杰
|
| 內容試閱:
|
总 序
张安庆先生为团结出版社策划一套“边角料书系”,他来约稿,鼓励我编几种“边角料”为他的新的工作策划壮壮行色。我当然很乐意。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珍惜边角料的。我年轻的时候,任何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买衣服更是如此,所以,节省是上海人做人家的第一要义。那时妈妈买了一部缝纫机,学会自己动手做衣服,我则学会了裁剪。也没有什么名师指点,只是买一本裁剪指导之类的书,根据书上指导,依样画葫芦地量体裁衣,先是在旧报纸上琢磨裁剪,然后再把纸样按在布上,用一分钱买来的彩粉划划改改,大着胆子就剪下来了。这样“三脚猫”做出来的衣裤,居然还是能够穿上身的。但是就在自鸣得意之际,被一些内行看了,摇摇头说,这样裁剪太浪费了,平白糟蹋了许多布料呢。于是开始谨慎地学裁剪,果然,用心裁剪,只要位置稍微偏一点点,大裆处就可以省出一块布料——这就是边角料。有时候,几件衣裤套着裁剪,可以省出好多边角料,用来做鞋面,做口袋布,做假领子,这才是最见功夫的裁剪本领。
所以,边角料,本来就是整块布料的一部分,你不在意,它就不存在;你若在意,它还是能够发挥很好作用;若过分在意,把整块布料弄得零零碎碎,当然也是过于浪费,更是不行。一切都在于恰到好处,经济实惠。用上海话来说,学裁剪要学会“候分掐数”。弄文字的人,也应该学会处理边角料。写论文,创作小说,都是整块布料上裁剪出来的服装,除此而外,为了积累零星素材,积累点滴思想,作家的笔记、书信、日记、随笔……一切信手拈来的文字形式都属于边角料之类。在我的阅读中,遇到过好几本极为难得的“边角料”。第一本就是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所翻译的《契诃夫手记》,里面记载了许多作家的神来之笔,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二本是钱理群先生编的《删余集》,忘了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长长短短的文字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锈迹;还有第三本,王观泉先生编的《鲁迅与里维拉》,都是边边角角的剪报材料,竟编出了一本天下奇书。
接下来就要说到我自己提供的“边角料”了。2017年底广东人民出版社刚刚推出我的七卷本文集,所以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已经无法再结集出版了。计划中的好几种专著,也都无法顷刻间完成。但是边角料总还是有的,打开电脑,翻箱底似的寻找出来,大致分作四类的文章:第一类是我的演讲录,我在大约六七年前编过一本演讲录,也是在张安庆先生的操刀下编辑出版的,书名为《从鲁迅到巴金: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现在是在这本演讲录的基础上重新编过,篇目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二类是访谈录,一般发表在媒体上的访谈,除个别篇什,很少被收入我的编年文集,但是我有个习惯,凡公开发表的文字,我都是过目修改的,所以也算是比较负责的文字;第三类是书简,其实也不是普通书简,我以前写评论文章,有时候是当作读后感,直接与作家进行交流,后来觉得这种形式的评论比较自由,不那么正规,写起来更加随性,所以就有意识地尝试着写。那时朱光潜的《谈美书简》流行一时,我也很想出版一部书简体的评论集。当然这个梦想也没有实现,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成了“边角料”;第四类是杂感集,杂感的形式,是一百多年前《新青年》发明的,叫作随感录,当时涌现出两个杂感大家,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鲁迅。鲁迅编辑《而已集》的时候,依然把自己这一类短文称作杂感,后来鲁迅编自己的文集,把各类文章(也包括杂感)编在一起结集出版,称作杂文集。再后来人们把作为文体的杂感与作为编书体例的杂文集混为一谈,于是广义地称作“杂文”,而杂感作为一类文体的名称,反倒寿终正寝了。在鲁迅的著作里,杂感是他主要的写作形式,当然是整块的布料,而我,实在是偶尔为之,也很少收入文集,所以仍然是我的边角料了。
我还要说明的是,这四种“边角料”的编辑工作,我分别邀请我的学生刘安琪、胡读书、陈丙杰、刘天艺和陈昶来参与,他们帮我搜集、整理、编选、校对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是有意把这项繁琐的工作交给他们来做。在我看来,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学会做学术研究、写高头文章,同时还应该学会做具体的与学术有关的工作,譬如学会操办一次学术会议、完整编辑一本书、独立主讲一门专业课程,等等,知识分子从事的学术工作很具体,最忌讳的就是眼高手低,或者眼低手也低,什么丰功伟业都需要从点点滴滴开始做起。我希望通过这次编辑工作,学生们获得具体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从而提高学术服务的自觉。
是为序。
陈思和
2019年2月13日写于鱼焦了斋
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答李辉
一、心绪万端说高考
李辉(以下简称李):高考刚过,对于全国成千上万的家长和学生来说,每年都要经历这么一次“黑色的七月”。我还记得,两个月前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你曾这样说:早知道大学考试制度今天搞得那么可怕,还是不要恢复高考制度的好。你这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然我感觉这也许是一种激愤的表述。不过,在我们准备进行的一系列回顾20世纪的对话中,谈教育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教育总是有许多困惑,甚至存在误区,在中国,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这一两年来,陆续有一些谈教育的文章,但我感到并不充分,而且没有涉及到我所认为重要的一些问题。你的专业虽然是文学批评,但涉及面超越了文学领域,这几年侧重于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思考;另外,从你这些年的经历看,自1978年进大学起,你就没有离开过大学,可以说接触了大量的教育方面的现实情况,肯定会有许多感触。因此,我很想请你谈谈对20世纪教育的一些想法,包括它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与教育的关系,还有,你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教育应当怎样发展,等等。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对高考制度有这么严厉的批评?
陈思和(以下简称陈):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惠者,没有高考我们都进不了大学。但我觉得近年来的考试制度——包括高考、中考在内的各种考试,越来越成为一种人性异化和知识异化的现象,妨碍了青少年人性自由发展和知识的全面培养。从理论上讲,考试是一种社会规范,代表着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这就要求每个应试者服从社会规范,比方说,入学有入学考试,升级有升级考试,不管哪种考试,都是社会意志的体现。考试是要别人出题的,这种出题本身并不考虑应试者的特点,它只是要求应试者服从某种社会共同需要。我们的学问知识是相对独立的东西,可是在现实当中,这些知识又是被调动起来为社会服务的。推而论之,人的生命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权利,但是人的发展过程需要服从社会规范,按社会公众理想塑造成社会认可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与社会意志之间要通过许多考试来磨合——个人牺牲自己的自由,换来社会的承认,同时也换来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发展是以社会标准来衡量的。在学校里,在单位里,可能考试的方式不一样,但总的说来,都是为了不断获得社会的承认,获得更高的自由,为此不得不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牺牲自由。这是一个悖论。
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后转向西方式教育,再后来现代教育发展得越来越规范化,到现在考试制度更为严格。从发挥个人自由的角度看,这个代价是否太沉重了?另外,你是否在说,考试并不是要鼓励应试者把自己的最好水平体现出来、发挥出来?
陈:没有一种考试是这样的,恰恰反过来,比如学校里的政治考试,从中学就考,一直考到大学里还要考。但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培养学生的政治头脑和政治能力,学生也不能自由讨论政治问题,所有的话都是按现成的答案背出来,换来的只是一个及格分数。
李:我觉得政治考试出的题目从中学到大学都差不多,而且对青少年的知识形成也起不了太多作用。比如,据我所知,有的地方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题目,一个是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另一个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题目都应该是专家讨论的问题,中学生怎么讲得清楚。好像中学生们都精通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似的,实际上学生只能靠背教科书上的答案,然后再把答案交给老师。中学学过的一些知识,上大学后又重新学,完全是原地踏步走,对扩展人的思维空间,形成思维方式,并没有特别的帮助。
陈:这只是一个小问题。既然考试反映了一种社会需要,那么就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追究考试的根本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健康向上,真正重视人才,需要通过造就和培养人才来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那考试制度就应该反映出这种精神要求,譬如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就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那个时代,个人没有选择自己出路的可能性,你就是一颗螺丝钉,社会机器像一只巨大的手,个人的一切都被它控制。那时要改变命运,只有通过高考,才可以改变生存环境。对此我是有很深体会的。“文革”时,我在社会上混,后来把编制挂在一个街道图书馆,它是属于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我一直在卢湾区图书馆参与书评工作,它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我在那儿工作多年,区图书馆也希望我调过去,做了很多努力,但我就是调不过去,因为所有制不同——这些僵死的、非人的因素就可以置人于死地。那时个人想改变所有制,连参军都不行。从农村入伍的,复员后还得回农村,唯有高考可以改变这一切,尽管高考也是让你服从社会意志,但毕竟给了你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李:像我们这些幸运地在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人,命运的确是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否则,我们就不会认识,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谈这些问题。
陈:那时还有家庭成分、户口等限制,都把你规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动弹不得。恢复高考,是打破这种束缚的唯一希望,为发扬人的主观因素、改变命运提供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得感谢高考。
然而,在目前开放的社会形态下,高考对个人改变命运的积极意义减弱了。当然,农村青年读大学也可以留在城市里工作,但总的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多。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做生意、打工,也可以达到在城市工作的目的,户口现在已经不成为太大的问题,甚至出钱就能买到城市户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