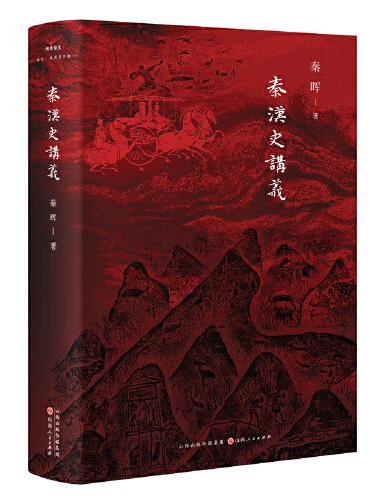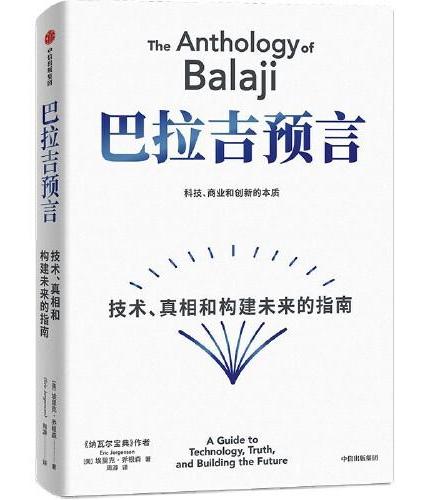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HK$
119.9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HK$
85.8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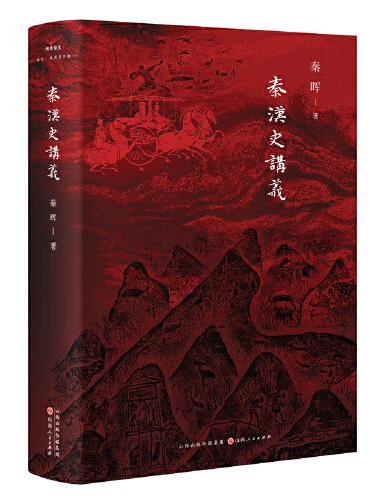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HK$
151.8

《
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售價:HK$
104.5

《
荷马:伊利亚特(英文)-西方人文经典影印21
》
售價:HK$
107.8

《
我的心理医生是只猫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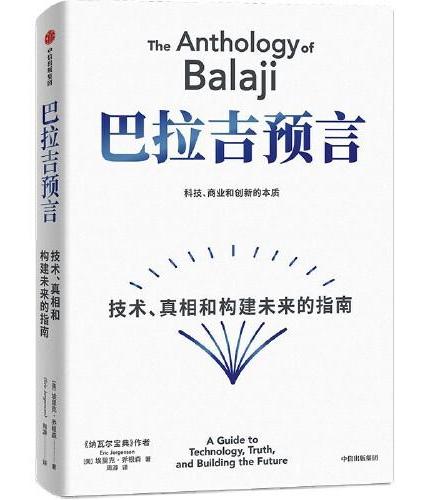
《
巴拉吉预言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伟大的小说家、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奠基人之一——果戈理小说戏剧代表作
★翻译家满涛译本
★喜剧《钦差大臣》中“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笑。“笑要比人们想的重要得多,深刻得多”。——果戈理
|
| 內容簡介: |
|
《果戈理小说戏剧选》共收入果戈理的四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涅瓦大街》《肖像》《外套》和一个剧本《钦差大臣》。
|
| 關於作者: |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小说家、剧作家。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主要作品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
译者:
满涛(1916—1978),原名张逸侯。江苏吴县人,生于北京。1935年入复旦大学就读,未毕业即东渡日本学习俄语,1936年赴美学化学。1938年初赴法学法文。同年回国。先后在时代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处工作。译作有契诃夫的《樱桃园》、《果戈理的《死魂灵》及中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等。
|
| 目錄:
|
目次
译本序
小说
塔拉斯·布尔巴
涅瓦大街
肖像
外套
戏剧
钦差大臣
|
| 內容試閱:
|
译本序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一八○九年四月一日诞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大索罗庆采镇。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富有的中等地主,颇有文才,曾用俄文写过诗,还用乌克兰文写过几部喜剧。
果戈理在一八一九年进了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读书,然后在一八二一年转入涅仁中学。这时候,俄国刚经历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人民的民族自觉心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又掀起了贵族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涅仁虽然较为偏僻,但是也不能不受到这一蓬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果戈理和许多同学一起争读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北极星》,热情地背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诗。他特别爱读普希金的诗,把普希金当作崇拜的对象。
果戈理从学生时代起,就显露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和同学们一起编辑手抄的刊物,有《文学彗星》等四五种之多。他把民间的警句、俗谚、歌谣以及历史文献等材料抄录在一本练习簿上,把它叫作“日用百科全书”。他写过诗、讽刺作品以及剧本《强盗》等。他又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从写剧本、画布景……到演戏,什么事都要干。他在这些演出中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类的喜剧角色。他在冯维辛的《纨绔少年》里出色地扮演了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据当时目击的人回忆说:“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曾经把普罗斯塔科娃的角色演得像十六岁的果戈理这样成功过。”
果戈理对陈腐的课程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对教自然法的别洛乌索夫以及其他几位进步的老师却怀着极大的尊敬。这些老师经常介绍学生们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果戈理对别洛乌索夫大为倾倒,把他称为“稀有人物”。
一八二七年,新任校长奉派到涅仁中学来“整顿学风”。当时有人控告别洛乌索夫等人在学生中间宣传“自由思想”,这样,就制造出了所谓“别洛乌索夫案件”。这案件拖延了很久,牵累了许多人,果戈理也是被传讯的学生之一。校长把别人交出的果戈理的笔记本作为物证,要他证明别洛乌索夫在上课时宣传“政治方面犯罪的议论”。果戈理承认笔记本是他的,但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上面抄的是一些法国启蒙学者的意见,这和别洛乌索夫没有关系,别洛乌索夫在上课时是按照规定的课本授课的。”但是,尽管别洛乌索夫等几位进步教师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在果戈理离开学校一年以后,他们还是成了倾轧、陷害的牺牲者,被驱逐出学校。
果戈理在这时候已经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问题。他对周围腐败的环境感到十分憎恶,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把涅仁的人们称作“俗物”,这些俗物“用世俗和猥琐自满的外壳扑灭了人的崇高使命”,而他所感到痛苦的是必须在这些人中间苟安偷生。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诉说自己沉痛、苦闷的心情,说他“好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漂泊在异乡”。
他决心要摆脱这种灰暗的奄奄无生气的生活,希望为祖国效劳。但是,他为祖国效劳的方法,他所设想的“人的崇高使命”,是非常模糊的。他只想到在司法界服务,以为这样就可以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进。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同年年底,一个初出茅庐的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就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丽幻想,出发到彼得堡去了。到彼得堡以后不久,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他带来的几封介绍信都没有能用上。他自费出版了一部题名为《汉斯·古谢加顿》的叙事诗,但结果遭到严厉的批评,他从书店里收回全部存书,把它们焚毁了。他甚至也尝试过投考演员,但是剧团的负责人是个伪古典派,要求演员必须装腔作势,果戈理的演剧才能当然不能被他所赏识。
一八二九年末,他终于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官俸微薄得可怜,他经常过着受冻、挨饿的生活。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道:“恐怕没有人在彼得堡生活得比我更俭朴了,……幸亏我已经有点习惯于寒冷,因此,能够穿着夏季薄外套挨过整整一冬。”
果戈理原来是为了追求理想才到彼得堡来的,哪知道在彼得堡接触到的仍旧是卑污的现实。但是,如果说他幼稚的幻想完全破灭,那么他梦寐以求的为祖国和人民谋福利的理想,却在现实环境中进一步受到了磨炼。在这一时期,他一边在美术学院的夜校学习绘画,一边更加被文学所吸引,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一八三一年二月,他辞去了小公务员的职务,开始完全把文学写作作为终生的事业。就在这时候,他又认识和接近了大诗人普希金,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巨大的影响。
一八三○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果戈理写作活动为旺盛的时期。他在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几乎写出了他全部重要的作品,计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卷,1831年;第二卷,1932年)、《密尔格拉得》(1835年)、《彼得堡故事》(1835年)、《钦差大臣》(1836年)以及《死魂灵》的部(1835—1842年)等。
果戈理的作品以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丑恶为内容,因而自然地引起封建农奴制度的热心维护者的攻击。另一方面,进步舆论界支持他,赞扬他,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他首先发现了果戈理作品所包含的革新意义,写了无数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保卫果戈理的倾向,阐述并发扬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摧枯拉朽地驳斥了反动文人们的种种邪论谬说。
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必然崩溃的过程,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斗争要求的,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复杂矛盾。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绝,但是,对社会发展的前途却茫无所知,更不知道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社会制度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他对自己作品中得出来的革命结论也感到害怕。他揭露了地主阶级和沙皇官吏的丑恶,但是他又把宗法制度的某些方面加以美化,主张倒退到已经消逝的古老宗法制度中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思想上的这种矛盾,初只是表露在他的某些作品当中(例如《肖像》《罗马》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化,消极的因素增加,先前作品中所表现的批判、揭露的力量就显著地削弱了。
他的一些斯拉夫派及其他保守、反动阵营的朋友,当他后期长时间居留国外时,利用他思想上的弱点,拼命包围他,隔绝他和俄国国内进步思想界的联系,挑拨离间。这更促进了他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危机。
果戈理动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时,正是他的思想危机开始逐渐发展的时期。他在第二部里描绘了一些地主阶级寄生虫的形象,如懒汉坚捷特尼科夫等,讽刺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的,大体上仍旧保持着部中的批判、揭露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地主阶级寄生虫的世界中寻找积极因素,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物,这些人物没有现实根据,破坏了艺术的真实,因而招致了他的创作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一八四七年一月,他出版了充满伪善说教的《与友人书信选》。在这本书里,他公开宣传斯拉夫派的反动主张,认为封建农奴制度是不可废除的,认为只要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教育就可以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刻博得了反动文人们的喝彩。他们高兴地看到,果戈理的灵魂“得救”了。他们包围果戈理使他脱离革命影响的罪恶计划终于收到了成效。连充当沙皇宪兵第三厅的特务、过去曾经大肆攻击果戈理的布尔加林,也假惺惺地引咎自责,说什么以前对果戈理的“批评”未免失之“过苛”了。
但是,当时俄国进步的舆论界对这本书是一致予以愤怒谴责的。别林斯基在一篇批评《与友人书信选》的文章里,指出果戈理落入反动文人们的陷阱,表示了万分的惋惜。一八四七年七月,别林斯基在德国萨尔茨堡养病时,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这就是后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好的作品之一”。别林斯基在这封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沙皇俄国的病根所在。他认为,当前重要、迫切的问题,就是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摆脱专制政体、正教、国粹主义,而不是像果戈理所说的那样,要到神秘主义、禁欲主义里面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的思想“危机”,充分反映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旧社会中找不到明确的出路,因而陷入的彷徨、苦闷的心情。他对《死魂灵》的第二部进行过长时期的反复修改,焦思苦虑地企图表现客观的真实,但是因为摆脱不掉世界观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终于还是写不出他自己所满意的作品。一八四五年他曾经把原稿焚毁,重新从头写起。一八五二年一月,完成了第二稿,在病逝前十天又把它焚毁了。这个第二部现在幸存的只有初的几章。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到耶路撒冷去作了一次身心交疲的宗教朝拜。同年五月,回到了俄国。此后,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病逝于莫斯科。
果戈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卓越,他的小说和戏剧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果戈理“在俄国创造了新的艺术,新的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果戈理是“俄国作家中伟大的一个”,他认为“世界上久已没有这样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人民,像果戈理对于俄国这样重要”。
普希金和果戈理是俄国文学中的双璧。普希金在诗歌方面所完成的任务,果戈理在散文方面把它完成了。普希金也写过许多篇小说,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在诗歌方面。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的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正像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创始人一样,果戈理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散文之父。
果戈理从初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就大胆地把普通人民写进作品里,这在当时的俄国实在是破天荒的。出现在他的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教堂差役、农村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们。作品里充满着纯朴的语言,丰富的幽默,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果戈理的作品,一开始就和主张铺张堆砌、喜好陈腔滥调的贵族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狄康卡近乡夜话》虽然也注意现实的描绘,但它更多偏重于浪漫主义的渲染。这以后,果戈理的观察、分析现实的力量更加成熟了;同时,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也迫使他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粗野平庸的方面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继承普希金的优良传统,发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加强了文学中的批判倾向。他不仅如普希金说的善于揭露“庸俗人的庸俗”,更重要的是,剖开封建农奴制现实的表皮,毫无顾惜地揭露它的庸俗、空虚、丑恶,赋予“缠住人生的可怕的、惊人的琐事的淤泥”以普遍意义,使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从而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
.......
“转过身来,儿子!你这副模样多可笑!你们穿的这也算是僧侣的袈裟?神学校里大伙儿都穿这种衣服吗?”老布尔巴用这几句话接待了他的两个儿子,他们曾在基辅神学校念书,现在回到父亲家里来了。
哥儿俩刚刚下了马。他们是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们还显得有点腼腆,正像刚出校门没有多久的神学校学生一样。他们结实的、强壮的脸上覆盖着还没有碰过剃刀的初生的柔毛。他们被父亲的这种接待弄得狼狈不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眼睛望着地上。
“站住,站住!让我好好儿看看你们,”他把他们拨弄着,继续说,“你们穿的褂子多么长呀!这也叫褂子!走遍世界,这样的褂子也找不到一件。你们哪一个跑两步试试!我看他会不会叫前襟绊住,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别笑,别笑,爹!”做哥哥的那一个终于开口了。
“你瞧你,好神气!为什么我不能笑?”
“就是不能嘛。你虽是我的爸爸,可是只要你敢笑,实话告诉你,我就揍你!”
“哎呀,居然有这样的儿子!怎么,你要打老子?……”塔拉斯·布尔巴惊悸之余,往后倒退了几步,说。
“是的,就是我的爸爸也不成。谁要是侮辱我,不管是谁,我都要对他不客气。”
“你要跟我怎么个打法?用拳头?”
“不管用什么都行。”
“好,就用拳头吧!”塔拉斯·布尔巴卷起了袖子说,“我倒要瞧瞧,你动起拳头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父亲和儿子,在长久离别之后没有欢叙,却互相动起拳头来了,重重地打在对方的肋骨上,腰眼儿上,胸口上,一会儿退后去,互相瞪着眼睛,一会儿又重新进攻。
“瞧呀,好心的人们:老头子发昏了!他简直疯啦!”他们的脸色苍白的、瘦弱的、善良的母亲喊道,她站在门槛边,还没有来得及拥抱她的亲爱的孩子们,“孩子们好容易才回家,有一年多没有看见他们了,可是他不知怎么想的,要跟儿子动起武来了!”
“他打得真不赖呀!”布尔巴住了手,说,“说真的,是不赖呀!”他稍微理理衣服,继续说,“用不着正式跟别人交手就可以知道他的本事了。他会成为一个好哥萨克的!欢迎你,儿子!我们来拥抱吧。”于是父亲和儿子接起吻来了。“好哇,儿子!往后你就得像刚才打我那样去打所有的人。别放过任何一个人!可是,不管怎么说,你这身打扮总是挺可笑的!为什么系着一根绳子?还有你,懒东西,为什么站在那儿,垂着一双手?”他转向年幼的一个说,“你怎么不打我啊,狗杂种?”
“亏你想得出!”母亲说,同时拥抱了一下小兄弟,“谁听说有儿子打老子的?你们闹得也够啦:孩子年纪还小,走了这么许多路,也累了……(这孩子有二十多岁,身材足有一俄丈高。)他现在需要睡个觉,吃点什么,可是你叫他打架!”
“哎,我看,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布尔巴说,“儿子,可别听你母亲的!她是个老娘儿们,她什么都不懂。你们需要的是什么爱抚?你们的爱抚是空旷的原野和一匹骏马:这就是你们的爱抚!瞧见这把马刀没有?这就是你们的母亲!别人塞进你们头脑里的那些东西,全是废料;神学校啦,所有那些书本啦,识字课本啦,哲学啦,这一切鬼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我唾弃这一切!……”说到这儿,布尔巴在自己的话里插进了一个这样的字眼,甚至是不便形诸笔墨的,“好这个星期我就把你们送到查波罗什去。那儿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那儿是你们的学校;只有在那儿,你们才能够得到知识。”
“那么他们一共只能在家里待一星期?”瘦弱的老母亲眼睛里噙着眼泪,凄楚地说,“可怜的孩子连玩一玩也没有工夫了,连认识认识他们出生的老家也没有工夫了,我也没有工夫把他们看个仔细了!”
“够了,吵得够了,老太婆!哥萨克生来不是为了跟老娘儿们打交道的。你想把他们两个都藏在裙子底下,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他们上面。去吧,去吧,把所有的东西尽快地都给我摆在桌上。我们不需要馒头、蜜姜饼、罂粟馅点心和别的甜品;给我们拿来一整只的公羊,给我们一只母羊,四十年的陈蜜酒!白酒要多些,不是那种加了许多花样的白酒,带葡萄干和各种各样玩意儿的,要那种纯粹的、冒泡沫的白酒,让它像疯狂一样地沸腾着,咻咻发响。”
布尔巴把两个儿子带到正房里,两个正在收拾房间的、戴着钱币编制的颈环的美丽侍女从那儿迅速地跑出去了。显然,她们是因为不喜欢饶恕人的少爷们突然来临而吃了一惊,再不然,就是想遵从她们女性的惯例:见了男人,大叫一声,慌张地跑开,事后用衣袖长久遮住羞得通红的脸蛋。正房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风尚陈设的,那个时代只有在歌谣和叙事民谣里还留下一些鲜明的痕迹,而在乌克兰,已经不再有长髯垂胸的盲老人,在多弦琴的静静的伴奏下,对围观的群众唱这些歌谣和叙事民谣了;正房是按照乌克兰因为宗教合并而开始爆发骚扰和杀伐的那个艰难战乱时代的风尚陈设的。一切地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涂着彩色的黏土。墙上挂着一些马刀、马鞭、捕鸟网、渔网和步枪,一只雕工精巧的角形火药匣,一副金光灿烂的马勒和镶有银片的绊马绳。正房里的窗户很小,嵌着圆圆的不透明的玻璃,这种窗户如今只有在旧式教堂里才会遇到,除非掀起那块活动玻璃,否则是什么都不能够望见的。窗和门的周围有红色的木框。墙犄角的架子上摆着许多坛、瓶、绿色和蓝色的长颈玻璃瓶、雕花的银杯、各地制造的镀金酒杯:威尼斯的、土耳其的、契尔克斯的,都是通过各种路径,经过三四个人的手,才到达布尔巴的正房里来的,这种情况在战乱的年代原是极普通的。屋子的四周摆着几张白桦树皮制的凳子;一张大桌子摆在正面的墙角里,圣像下面;还有一座具有后灶和凹凸部分的、盖着彩色斑斓的瓷砖的大炉子。这一切对于每年假期远道跋涉回家的这两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他们跋涉回家,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马,再说,习惯上也不允许学生骑马的缘故。他们只有一缕长长的额发旧时乌克兰人的一种头发式样,头顶剃光,留一丛头发在脑门上。,任何一个携带家伙的哥萨克都能揪住这缕额发,把他们痛殴一顿。这次因为他们毕业了,布尔巴才从马群里选了两匹年轻的种马送给他们乘骑。
布尔巴趁儿子们回家的机会,叫人去召集所有留在当地的中尉和全体联队长官;当其中的两位和他的老伙伴德米特罗·托符卡奇副官来到的时候,他立刻把两个儿子介绍给他们,说:“瞧呀,多么棒的小伙子!我马上就要送他们到谢奇去啦。”客人们祝贺了布尔巴和两个年轻人,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做得很对,对于年轻人说来,再没有比查波罗什的谢奇更好的学校了。
“来吧,弟兄们,大家都在桌子跟前坐下,爱坐哪儿就坐哪儿。来吧,儿子们!首先我们要喝白酒!”布尔巴这样说了,“老天爷保佑!欢迎你们,儿子们:你,奥斯达普,还有你,安德烈!老天爷保佑你们打起仗来永远胜利!要打败伊斯兰教徒,打败土耳其人,打败鞑靼人;波兰人要是胆敢反对我们的信仰,那么也要打败波兰人!来吧,把酒杯凑过来;怎么样?白酒好喝吗?拉丁话管白酒叫什么来着?儿子啊,拉丁人都是笨蛋,他们连世上有没有白酒还不知道哩。那个写拉丁诗的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没有念过多少书,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贺拉斯,对吗?”
“瞧,多聪明的爸爸!”大儿子奥斯达普心里想,“这老狗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还假装糊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