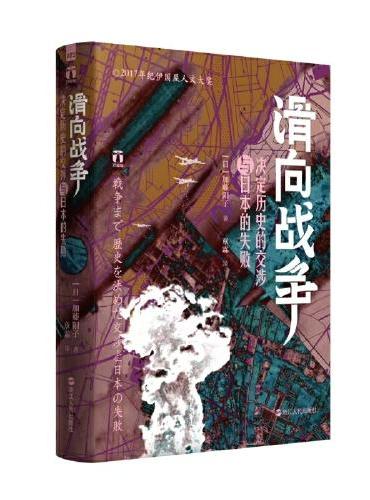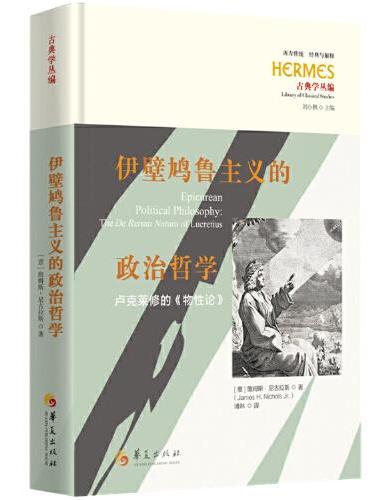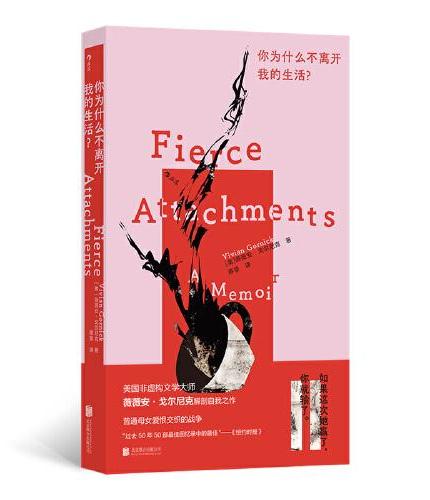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你可以有情绪,但别往心里去
》
售價:HK$
46.2

《
汴京客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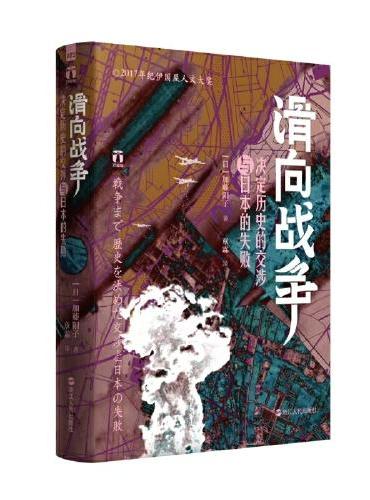
《
好望角·滑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
》
售價:HK$
107.8

《
八千里路云和月(白先勇新作!记述我的父亲母亲并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
售價:HK$
68.2

《
教师助手:巧用AI高效教学(给教师的66个DeepSeek实战技巧,AI助力备课、教学、练习、考试及测评)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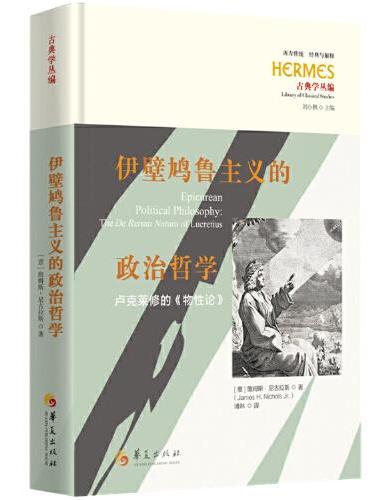
《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 :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
售價:HK$
68.2

《
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新经济结构
》
售價:HK$
1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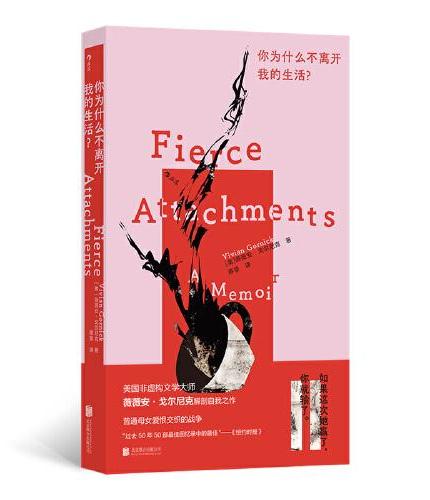
《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
售價:HK$
54.8
|
| 編輯推薦: |
1、横扫欧美文坛的孤独小说家麦卡勒斯的传奇之作
2、全新未删减全译本,收录麦卡勒斯七篇传奇之作,包括19岁时发表的处女作《神童》
3、特别收录作者12张珍贵照片,并附文字解读
4、译者李文俊译文精准、流畅,完美呈现麦卡勒斯作品的文学之美、孤独之美。
5、麦卡勒斯是20世纪美国极其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劳伦斯之后极有原创诗情的作家
6、《伤心咖啡馆之歌》是麦卡勒斯的代表作之一,六十多年来经久不衰
7、《纽约客》《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南大西洋公报》……全美主流媒体重磅推荐。
8、麦卡勒斯以她的“孤独”影响了世界上众多作家。
9、从钱钟书到苏童,从21次获诺奖提名的格雷厄姆·格林到心理学宗师荣格无一不为其笔下的“孤独”所痴迷。
10、根据《伤心咖啡馆之歌》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
|
| 內容簡介: |
《伤心咖啡馆之歌》收录了麦卡勒斯七篇传奇之作,包括19岁时发表的处女作《神童》,以及六篇麦卡勒斯发表于不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为著名。
这镇上曾有过一家咖啡馆
这是一座钉上木板的旧房子
它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这里曾摆过铺了桌布的桌子
电风扇前飘舞着彩色的纸袋
一到周六晚上更是热闹非凡
咖啡馆早就关闭了
可是咖啡馆里发生的故事谁都还记得……
|
| 關於作者: |
卡森·麦卡勒斯,横扫欧美文坛的孤独小说家,与杜拉斯齐名的“文艺教母”,海明威、福克纳之后,欧美文坛耀眼之星,被誉为继劳伦斯之后极有原创诗情的作家。34岁时出版《伤心咖啡馆之歌》备受好评。
主要作品:《心是孤独的猎手》《金色眼睛的映像》《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没有指针的钟》等。
|
| 目錄:
|
目 录
伤心咖啡馆之歌/ 001
神童/103
赛马骑师/131
席林斯基夫人与芬兰国王/143
旅居者/161
家庭困境/183
树·石·云/205
作者年表/223
|
| 內容試閱:
|
伤心咖啡馆之歌
[美]卡森·麦卡勒斯 著
李文俊 译
小镇本身是很沉闷的;镇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家棉纺厂、一些工人住的两间一幢的房子、几株桃树、一座有两扇彩色玻璃窗的教堂,还有一条几百码长、不成模样的大街。每逢星期六,周围农村的佃农进小镇来,闲聊天,做买卖,度过这一天。除了这一天,小镇是寂寞的、忧郁的,像是一处非常偏僻、与世隔绝的地方。近的火车站在社会城,“灵”和“白车”公司的长途汽车都走叉瀑公路,公路离这里有三英里。这儿的冬天短促而阴冷,夏日则是亮得耀眼,热得发烫。
倘若你在八月的一个下午在大街上溜达,你会觉得非常无聊。镇中心,全镇的一座建筑物上,所有的门窗都钉上了木板,房屋向右倾斜得那么厉害,仿佛随时都会坍塌。房子非常古老,它身上有一种古怪的、疯疯癫癫的气氛,很叫人捉摸不透是怎么回事。到后来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很久以前,前面门廊的右半边和墙的一部分是漆过的——可是并没有漆完,所以房子的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显得更暗、更脏一些。房子看上去完全荒废了。然而,在二楼上有一扇窗子并没有钉木板;有时候,在下午热得让人受不了的时分,会有一只手伸出来慢腾腾地打开百叶窗,会有一张脸探出来俯视小镇。那是一张在噩梦中才会见到的可怖的、模糊不清的脸——苍白、辨别不清是男还是女,脸上那两只灰色的斗鸡眼挨得那么近,好像是在长时间交换秘密和忧伤的眼光。那张脸在窗口停留一个钟点左右,百叶窗重新关上,整条大街又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了。在那样的八月下午,你下了班真是没什么可干的;你还不如走到叉瀑公路去听苦役队唱歌呢。
可是,这个镇上是有过一家咖啡馆的。这座钉上木板的旧房子,在方圆若干英里之内,也曾是颇不平常的。这里摆过桌子,桌子上铺了桌布,放着纸餐巾,电风扇前飘舞着彩色的纸带。一到星期六晚上,更是热闹非凡。咖啡馆的主人是爱密利亚·依文斯小姐。可是使这家店兴旺发达的却是一个名叫李蒙表哥的罗锅儿。另外,还有一个人在这段咖啡馆的故事里扮演了一个角色——他是爱密利亚小姐的前夫,这个可怕的人物在监狱里蹲了很久以后回到镇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又一走了之。咖啡馆早就关闭了,可是它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地方原先也并非一向就是咖啡馆。爱密利亚小姐从她父亲手里继承了这所房子,那时候,这里是一家主要经销饲料、鸟类以及谷物、鼻烟这样的土产的商店。爱密利亚小姐很有钱。除了这店铺,她在三英里外的沼泽地里还有一家酿酒厂,酿出来的酒在本县要算首屈一指了。她是个黑黑的高大女人,骨骼和肌肉长得都像个男人。她头发剪得很短,平平地往后梳,那张太阳晒黑的脸上有一种严峻、粗犷的神情。即使如此,她还能算一个好看的女子,倘若不是她稍稍有点斜眼的话。追她的人本来也不见得会少,可是爱密利亚小姐根本不把异性的爱放在心上,她是个生性孤僻的人。她的婚姻在县里是件奇闻——这次结婚既古怪,又让人提心吊胆,仅仅维持了十天,使全镇的人都莫名其妙,大吃一惊。除却这次结婚,爱密利亚一直是一个人过日子。她经常在沼泽地她的工棚里待上一整夜,穿着工裤和长筒雨靴,默默地看管蒸馏器底下的文火。
爱密利亚小姐靠了自己的一双手,日子过得挺兴旺。她做了大小香肠,拿到附近镇子上去卖。在晴朗的秋日,她碾轧芦粟做糖浆,她糖缸里做出来的糖浆发暗金色,喷鼻香。她只花了两个星期就在店后用砖盖起了一间厕所。她木匠活也很拿得起来。唯独与人,爱密利亚小姐不知怎样相处。人,除非是丧失了意志或者重病在身,否则你是不能把他们拿来在一夜之间变成有价值、可以赚钱的东西的。在爱密利亚小姐看来,人的用途就是从他们身上榨出钱来。在这方面她是成功的。她用庄稼和自己的不动产做抵押,借款买下一家锯木厂,银行里存款日渐增多——她成了方圆几英里内有钱的女人。她本来会像议员一样富有的,可是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特别热衷于打官司和诉讼。为了一点点屁大的事,她会卷入漫长而激烈的争讼里去。有人说,要是爱密利亚小姐在路上给石头绊一下,她也会本能地四下看看,仿佛在找可以对簿公堂的人。除了打官司之外,她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每一天都跟前一天差不多。只有那次为期十天的结婚算是一个例外。除却这件事,她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爱密利亚小姐三十岁的那个春天。
那是四月里一个温暖、安静的夜晚,时间将近午夜。天上是沼泽地鸢尾花的那种蓝色,月光清澈又明亮。那年春天,庄稼长势很好。过去几个星期里,棉纺厂一直在加夜班。小河下游那座方方的砖砌的工厂里亮着黄黄的灯光,传来织布机轻轻的无休止的营营声。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你听到远处越过黑黝黝的田野,传来一个去求爱的黑人慢悠悠的歌声,你会觉得蛮有意思。即使是安安静静地坐着,随便拨弄一把吉他,或是独自歇上一会儿,脑子里啥也不想,你也会觉得蛮有滋味。那天晚上,街上阒寂无人,不过爱密利亚小姐铺子的灯光却亮着,外面前廊上有五个人。其中之一是胖墩麦克非尔,这人是个工头,有一张紫糖脸和一双细气的、紫红色的手。坐在一级台阶上的是两个穿工裤的小伙子,那是芮内家那对双胞胎——哥儿俩都又高又瘦,动作迟缓,头发泛白,绿眼睛老是似醒非醒。另一个人是亨利·马西,一个羞怯、胆小的人,举止温和,有点神经质,他坐在一级台阶的边沿。爱密利亚小姐自己站着,靠在洞开的门的框上,她那双穿着大雨靴的脚交叉着,在耐心地解她捡来的一根绳子上的结。他们好久都没有开口说话了。
双胞胎里的一个一直在望着那条空荡荡的大路,他首先开口了。“我看见有一个东西在走过来。”他说。
“是一只走散的牛犊。”他兄弟说。
走过来的身影仍然太远,看不清楚。月亮给路边那溜开花的桃树投下了朦胧、扭曲的影子。在空中,花香、春草甜美的气息和近处礁湖散发出的暖洋洋、酸溜溜的气味,混杂在一起。
“不,那是谁家的小孩。”胖麦克非尔说。
爱密利亚默不作声地瞅着路上。她撂下绳子,用她那棕色的大骨节的手抚弄工裤的背带。她皱着眉头,一绺黑头发披落在脑门上。他们等待的时候,路上谁家的狗发狂般嘶哑地吠叫起来,直到有人从屋子里喊了几声,止住了它。直到那身影靠近,走进门廊附近的黄光圈,五个人才看清那是什么。
那是个陌生人,陌生人在这样的时辰徒步走进镇子,这可不是件寻常的事。再说,那人是个罗锅儿,顶多不过四英尺高,穿着一件只盖到膝头的破旧褴褛的外衣。他那双细细的罗圈腿似乎都难以支撑住他的大鸡胸和肩膀后面那只大驼峰。他脑袋也特別大,上面是一双深陷的蓝眼睛和一张薄薄的小嘴。他的脸既松软又显得很粗鲁——此刻,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扑满了尘土变得黄蜡蜡的,眼底下有浅紫色的阴影。他拎着一只用绳子捆起来的歪歪扭扭的旧提箱。
“晚上好。”那罗锅儿说,他上气不接下气。
爱密利亚小姐和前廊上那几个男人既不打招呼,也不开口。他们仅仅是瞅着他。
“我在找一位爱密利亚·依文斯小姐。”
爱密利亚小姐把头发从前额上抹回去,抬起下巴。“怎么回事?”
“因为她是我的亲戚。”罗锅儿回答。
双胞胎和胖墩麦克非尔抬起头来瞧着爱密利亚小姐。
“我就是,”她说,“你说‘亲戚’,指的是什么?”
“那是因为……”那罗锅儿开始说了。他显得忸怩不安,仿佛都快哭出来了。他把提箱搁在一级台阶上,手却没有从把手上松开。“我妈叫芬尼·杰苏泼,她老家就在奇霍。大约三十年前,她回出嫁的时候离开了奇霍。我记得她说起过,她有个叫玛莎的同父异母姐妹。今儿个在奇霍,人家告诉我那就是您的母亲。”
爱密利亚小姐听着,脑袋稍稍歪向一边。她一向是一个人吃星期天的晚餐,从来没有一大帮亲戚在她家里进进出出,她可算是六亲不认。她倒是有过一个姑奶奶,在奇霍开了家马车行,可是这老太太已经死了。除此以外,只有一个姨表姐妹住在二十英里外的一个镇上,可是此人与爱密利亚小姐关系不好,偶尔面对面碰上,彼此都要往路边啐一口痰。不止一次,有人想方设法要和爱密利亚小姐攀上些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然而都是枉费心机。
那罗锅儿背起一部又臭又长的家谱来,提到一些仿佛离题十万八千里的人名地名,都是前廊那些听众闻所未闻的。“这样一来,芬尼和玛莎·杰苏泼就成了同父异母姐妹。而我又是芬尼第三个丈夫的儿子。因此你和我就算是……”他弯下身去解提箱上的绳子。那两只手像鸟爪,在不住地颤抖。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破烂——破旧不堪的衣服和古里古怪的废物,有点像缝纫机的零件,或是什么同样毫无用处的东西。罗锅儿在里面掏了半天,找出来一张旧相片。“这是一张我妈妈和她的同父异母姐妹的合影。”
爱密利亚小姐没有开腔。她把下颚从这一侧移到那一侧。你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在想什么。胖墩麦克非尔接过相片,凑到灯光底下去瞧。相片上是两个两三岁的苍白、干瘪的小孩。两张脸仅仅是两个模糊不清的白团团,你说它是从哪家的相册上撕下来的都成。
胖墩麦克非尔把相片递了回去,没有表态。“你从哪儿来?”他问。
那罗锅儿的声音迟迟疑疑的。“我是在到处转悠呢。”
爱密利亚小姐仍然没有开口。她仅仅是靠在门边上,低下头去看看罗锅儿。亨利·马西神经质地眨巴着眼,两只手搓来搓去。接着他一声不吭地离开一级台阶,走了。他是个软心肠的人,小罗锅儿的处境很使他同情,因此他不想等在这儿亲眼看着爱密利亚小姐把新来的人从她的产业上赶出去,从镇上赶出去。小罗锅儿站着,提箱在一级台阶上敞着口;他吸了吸鼻子,他的嘴嗫动着。也许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了吧。也许他明白作为一个陌生人,提了一箱子破烂到镇上来和爱密利亚小姐攀亲戚是件多么不妙的事了吧。总之,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突然间号啕大哭起来。
一个素不相识的小罗锅儿半夜时分走到店前来,然后又坐下来哭,这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爱密利亚小姐把前额上那绺头发往后一抹,那几个男人不安地对看一眼。整个镇子一点声音也没有。
后,双胞胎里的一个说道:“他要不是真正的莫里斯·范因斯坦,那才怪哩。”
每个人都点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是一个含有特殊意义的说法。可是罗锅儿哭得更响了,因为他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莫里斯·范因斯坦是多年前住在镇上的一个人。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动作迅速、蹦蹦跳跳的小犹太人,他每天都吃发得很松的面包和鲑鱼罐头,你只要一说是他杀了基督,他就要哭。后来他碰到了一件倒霉的事,搬到社会城去了。可是自此以后,只要有人缺少男子气概,哭哭啼啼,人们就说他是莫里斯·范因斯坦。
“唔,他很苦恼。”矮胖子麦克非尔说,“这总有个什么原因。”
爱密利亚小姐迈了两下她那迟缓、笨拙的步子,跨过前廊,下了台阶,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端详那陌生人。她小心翼翼地伸出一根长长的、棕黄色的食指,去戳戳他背上的驼峰。罗锅儿仍然在哭,可是已经安静些了。夜晚很寂静,月亮的光辉依旧很柔和,很明澈——天气有点转凉。这时候,爱密利亚小姐做了一件稀罕的事;她从后裤兜掏出一只瓶子,用掌心把瓶盖拧开,递给罗锅儿让他喝。爱密利亚小姐是不轻易赊酒给人的,对她来说,即使请人白喝一滴酒也几乎是件史无前例的事。
“喝吧,”她说,“能让你开胃的。”
罗锅儿停止了啜泣,把嘴巴周围的泪水舔干净,照别人的吩咐做了。他喝完后,爱密利亚小姐慢慢地啜饮了一口,用这口酒暖暖她的嘴,漱漱口,然后吐掉。接着她也喝起酒来。双胞胎和工头有自己花钱买来的酒。
“这酒真醇。”胖墩麦克非尔说,“爱密利亚小姐,你酿酒还从来没酿坏过。”
那天晚上,他们喝酒(两大瓶威士忌),这件事很重要。否则,很难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没有这点酒,就压根儿不会有咖啡馆。爱密利亚小姐的酒确有特色。它很清冽,尝在舌头上味儿很冲,下了肚后劲又很大。但事情还不仅是这样。大家知道,用柠檬汁在白纸上写字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如果把纸拿到火上去烤一烤,就会显出棕色的字来,意思也就一清二楚了。请你设想威士忌是火,而写的字就是人们隐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这样,你就会明白爱密利亚小姐的酒意味着什么了。过去忽略了的事情,蛰伏在头脑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的想法,都突然被认识、被理解了。一个从来只想到纺纱机、饭盒、床,然后又是纺纱机的纺织工人——这样的一个人,说不定某个星期天喝了几杯酒,见到了沼泽地里的一朵百合花。也许他会把花捏在手里,细细观察这纤细的金黄色的酒杯形状的花朵,他心中没准突然会升起一种像痛楚一样刺人的甜美的感觉。一个织布工人也许会突然抬起头来,生平次看到一月午夜天空中那种寒冽、神奇的光辉,于是一种察觉自己何等渺小的深深的恐惧会突然使他的心脏暂时停止跳动。一个人喝了爱密利亚小姐的酒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也许会感到痛苦,也许是快乐得瘫痪了一般——可是这样的经验能显示出真理;他使自己的灵魂温暖起来,见到了隐藏在那里的信息。
他们一直喝到半夜过后,这时,月亮躲进了云堆,夜晚因此变得又冷又黑。那罗锅儿仍然坐在一级台阶上,身子可怜巴巴地朝前伛着,额头靠在膝盖上。爱密利亚小姐站着,两手插在裤兜里,一只脚支在第二级台阶上。她好久没有出声了。她那副表情在稍稍有点斜眼的人的脸上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在沉思的时候,脸上总是既显得非常聪明又显得非常疯狂。后,她说话了:“我不知道你名字叫什么。”
“我叫李蒙·威里斯。”那罗锅儿说。
“好,你进屋去吧。”她说,“炉子上还有些剩饭,你可以吃。”
爱密利亚一生中,撇开打算作弄人家、想敲人竹杠的那些回不算,请人吃饭的次数真是屈指可数。因此,前廊上那几个人都觉得不大对头。事后,他们互相嘀咕说,她那天下午准是在沼泽那边喝酒来着。总之,她离开了前廊,胖墩麦克非尔和双胞胎也动身回家了。她插上前门,向四周扫了一眼,看看她的货物是否都完好无缺。接着她走进厨房,那是在店铺的尽里头。罗锅儿尾随着她,拽着他那只手提箱,一面吸鼻子在嗅气味,一面用他脏外套的袖口擦鼻子。
“坐下,”爱密利亚小姐说,“我把饭菜热一热。”
他们那天晚上一起吃的那顿饭颇为丰富。爱密利亚小姐有钱,在吃喝上从不亏待自己。吃的东西里有炸子鸡(胸脯肉让罗锅儿挑到自己盘子里去了),有山药泥、肉卷拌青菜,还有淡金色的热甜薯。爱密利亚小姐吃得很慢,胃口好得像个庄稼人。她吃的时候双肘支撑在桌子上,头低俯在盘子上,双膝分得很开,脚抵在椅子的横档上。那罗锅儿呢,他狼吞虎咽,好像几个月都没闻到食物的香味了。吃饭时,一滴泪从他肮脏的脸颊上慢慢地滑下来——那只不过是刚才残余的一小滴眼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桌子上的灯擦得很干净,灯芯边上发出一圈蓝光,在厨房里投射出一片欢乐的光亮。爱密利亚小姐吃完晚餐,用一片松软的面包把盘子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自制的澄澈、喷香的糖浆浇在上面。罗锅儿也照办,不过他更讲究,居然还要换只干净的盘子。爱密利亚小姐吃完后,把椅子往后一翘,把右拳握紧,用左手去摸摸她右臂干净的蓝布衬衫下坚硬的肌肉——这已经成为她每顿饭后不自觉的习惯动作了。接着她从桌子上拿起灯,脑袋朝楼梯那边点点,示意罗锅儿跟她上楼。
店铺楼上有三间房间,爱密利亚小姐从生下来就住在这里——两间卧室,当中是一间大客厅。很少有人参观过这些房间,但是大家知道这里陈设很讲究,打扫得非常干净。可是如今爱密利亚小姐却把不知哪里钻出来的一个肮脏的小罗锅儿带上了楼。爱密利亚小姐每回跨两级,走得很慢,灯举得高高的。那罗锅儿在她身后挨得那么紧,摇曳的灯光在楼梯墙上投出来的他们俩的影子都并成扭曲的一大团了。不久,店面二楼上的窗子也跟全城一样,是一片漆黑了。
翌晨,天气晴朗,温暖的紫红朝霞里掺杂着几抹玫瑰色的光辉。小镇四郊的田野里,土畦是新翻耕过的。一大早,佃农们就在栽种墨绿色的烟草嫩苗。乡野的乌鸦贴紧地面飞翔,在田畴上投下了飞掠的蓝色阴影。在镇上,人们很早就提着饭盒去上班,纺织厂的窗户在太阳下闪烁出耀眼的金光。空气清新,桃树上花枝招展,像三月的云彩一样轻盈。
爱密利亚小姐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下楼来了。她在水泵那里冲了冲头,很快就开始干活了。小晌午时分,她给骡子备上鞍,骑了它去看看自己的地,地里种的是棉花,就在叉瀑公路附近。到中午时刻,不消说,每个人都听说了小罗锅儿半夜到店里来的事了。可是人们都还没有见到他。很快,天气变得十分闷热,天空是一片浓艳的、晌午时分的蔚蓝色。仍然谁也没看见这个陌生的客人露面。有几个人记得爱密利亚小姐的妈妈是有一个同父异母姐妹的——可是她到底是死了还是和一个烟草工人私奔了呢,这上头意见便有些分歧。至于那罗锅儿声称自己是爱密利亚小姐的亲戚,每个人都认为那是胡说八道。镇上的人都知道爱密利亚小姐的为人,认为她喂饱罗锅儿以后准已把他撵出家门。可是快到黄昏,天空重新泛白,工厂也下了班时,一个妇女声称她看到有一张奇形怪状的脸从店铺楼上房间的窗户里探出来。爱密利亚小姐自己一句话也没说。她在店里照顾了一阵,和一个农民为一张犁铧讨价还价了一个钟点,补了几只鸡笼。太阳快下山时,她锁上门,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这使全镇的人摸不着头脑,议论纷纷。
第三天,爱密利亚小姐没有开店营业,而是锁上了门待在屋子里,谁也不见。谣言就是从这一天起开始流传的——这谣言真可怕,全镇和四乡的人都给吓呆了。谣言先是从一个叫梅里·芮恩的织布工人那里传出来的。这是个说话没分量的人——脸色灰黄,行动蹒跚,嘴里连一颗牙都不剩了。他身上有三天发一次的疟疾,这就是说他三天就要发一次烧。所以,有两天他呆头呆脑、脾气乖戾,可是到了第三天,他就活跃起来了。有时候他会想出一些怪念头来,绝大部分都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在梅里·芮恩发烧的一天里,他突然转过身来说:
“我知道爱密利亚小姐干出啥事来了。她为了箱子里的东西谋杀了那个人。”
他是用很平静的声音、作为叙述事实那么讲的。一小时之内,这消息传遍了全镇。那一天,全镇在集体编缀一个可怕、阴森的故事。这里面,使心脏打战的一切细节应有尽有——一个罗锅儿,半夜沼泽地里埋尸,爱密利亚被拖过街头锒铛入狱,接下来又是一场财产的争夺战——人们讲这一切时,用的都是压低了的声音,每重复一遍就加上一些新的怪诞的细节。天下雨了,妇女们却忘了收衣服。有那么几个人,欠着爱密利亚小姐的债,他们甚至还穿了好衣服,仿佛在过节。人们在大街上围成一堆在讨论,并且观察着那家店。
要说全镇的人都参加了这次邪恶的庆祝活动,那也不尽然。有那么几个头脑清醒的人,他们推论说,既然爱密利亚小姐有的是钱,何至为了一点点破烂儿起意谋害一个流浪汉。镇上居然还有三个善良的人,他们不想见到这样一次犯罪行为,即使它能带来很大的兴趣与刺激;他们想到爱密利亚小姐身陷囹圄,在亚特兰大坐电椅,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乐趣。这些善良的人用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来看爱密利亚小姐。当一个像她那样各个方面都违拗常情的人,一个人干下的坏事多得都让人想不周全时——那么,就根本应当用特别的标准来衡量这样的人。他们记得爱密利亚小姐生下来就黑不溜秋,脸有点怪;她从小没娘,是她父亲,一个孤僻的人,把她拉扯大的;她年纪小小就蹿到六英尺两英寸高,这对一个姑娘家本身就是不自然的。何况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又是怪得不可理喻。要紧的是,他们记起了她那次古怪的婚姻,这是本镇有史以来没有道理的一件丑闻。
因此这些好人对她怀有一种近似怜悯的感情。当她出去干一件粗暴的事时,比如说闯到人家家里去把一架缝纫机拖出来抵欠她的债,或是让自己卷进一场官司里去——他们就会对她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这里面混杂着恼怒、可笑的痒痒的感觉以及深深的无名的悲哀。可是关于好人说这些也就够了,因为好人拢共只有三个。至于镇上其余的人,他们整个下午都在过节似的欢庆这桩想象出来的犯罪行为。
不知怎的,爱密利亚小姐本人对这一切好像一无所知。她一整天几乎都是在楼上度过的。等她下楼到店里来时,她安详地四处转了转,双手深深地插在工裤兜里,头低垂着,下巴颏都快插进衬衫领子里去了。没见到她身上哪儿有血迹。她常常停下来,仅仅是阴郁地瞅瞅地板上的裂缝,把一绺短发卷了卷,兀自嘟哝几句不知什么话。不过几乎整整一天,她都是在楼上度过的。
黑夜降临了。那天下午,雨水使空气变得很寒冷,因此夜晚就跟冬天一样,凄凉而又暗淡。天上没有星星,冰冷的蒙蒙细雨下起来了。从街上看,屋子里的灯光摇曳不定,使人发愁。起风了,然而不是从镇子边上沼泽地里刮来的,而是来自阴冷的松林。
镇上的钟打响了八下,仍然没什么动静。在谈论了一天骇人听闻的事以后,这个凄凉的夜晚给某些人带来了恐惧,他们待在家中紧靠着炉火。其他的人一群群凑在一起。有那么八九个人聚集在爱密利亚小姐店铺的廊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就光那么等着,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等的是什么。可事情就是这样:在严重的时刻,当某个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时,人们总是这样聚集在一起等候。过一阵子,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他们一起采取共同行动,并非出于深思熟虑,也没有受谁的意志支配,而是似乎他们的本能已汇合在一起,因此这一决定不属于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集体。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一个人会踌躇不决。至于这种联合行动的结果是洗劫、暴行还是犯罪,那就全看命运的安排了。现在,这群人就这样在爱密利亚小姐店前廊子里阴郁地等着,没人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可是内心里都明白自己必须等待,那个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
需要交代的是,店门是开着的。里面很明亮,显得很正常,左边是柜台,上面堆着猪肉、冰糖与烟叶。柜台里面是放着腌肉与杂粮的货架。店堂右侧基本上都放着农具一类的东西。店堂尽里面,靠左边,是一扇通向楼梯的门,这扇门开着。右面,是另一扇门,通向一个小套间,爱密利亚小姐管这叫她的办公室。这扇门也开着。那天晚上八点钟,可以看到爱密利亚小姐坐在她那张翻盖式书桌前,拿着钢笔和一些纸,在计算。
办公室里灯光明亮,让人见了高兴。爱密利亚小姐似乎没有注意廊子上的代表团。她周围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和往常一样。这个办公室在全县也是有名的房间,几乎令人肃然起敬。爱密利亚小姐就在这里处理一切事务。桌子上放着一台盖得严严实实的打字机,她会用,可是仅仅在打重要的文件时才用。抽屉里放着成千张纸,一点不夸张,全都按字母次序排列。办公室也是爱密利亚小姐接待病人的地方,她喜欢给人治病,也经常给人治病。整整两个架子上放满了各种药瓶与医疗用具。靠墙根放着一张给病人坐的长凳。她给病人缝伤口时用的是烧过的针,这样伤口才不至于化脓。治疗烧伤,她有一种让人凉快的糖浆。对于不能确诊的病痛,她也有各种各样亲自按秘方煎制的药。这些药吃下去对于通便非常灵验,可是不能给幼儿吃,因为吃了会抽风;对于幼儿,她特地配制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药,温和得多,也甜得多。是的,总的说来,大家都认为她是个好大夫。她那双手虽然很大,骨节凸出,却非常灵巧。她很能动脑筋,会使用成百种各不相同的治疗方法。逢到需要采用危险性不寻常的治疗方法时,她也决不手软。没有什么病是严重得她不愿治的,在这方面,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要是有个病人上门,说自己害的是妇女病,爱密利亚小姐就束手无策了。真的,只要人家一提这种病,她的脸就会因为羞愧而一点点发暗。她站在那儿,弯着颈子,下巴颏都压到了衬衫领子上,或是对搓着她那双雨靴,简直像个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的大孩子。可是在别的事情上,人们都相信她。医药费她分文不取,因此经常是病家盈门。
这天晚上,爱密利亚小姐用她的钢笔写了不少东西。可是即使如此,她也不可能永远察觉不到黑黑的廊子上有一帮人在等着,在观察她。她过一阵就抬起头来定睛看看他们。不过并没有对他们嚷叫,质问他们为什么像一群无聊的长舌妇,在她店门前瞎厮混。她脸上的神情骄傲而又严峻,她坐在办公室书桌前的时候总是这样的。过了一阵,他们的窥探似乎使她心烦了。她用一块红手帕擦了擦脸,站起身来,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对于廊子里的那群人,这个姿态宛若一个信号。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在阴冷、潮湿的黑夜里已经站了很久。他们等待了很长时间,就在这一刻,他们身上出现了行动的本能。在一瞬间,仿佛由一个意志操纵着似的,他们全都走进了店堂。在那一瞬间,八个人看上去非常相像——都穿着蓝色的工裤,大多数头发花白,每个人的脸色都很苍白,眼神也都是呆滞的、梦幻似的。他们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来,没人说得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楼梯顶上传来一个声音。他们抬头一看,都傻了眼啦。原来正是那个罗锅儿,在他们的臆想里已经被谋杀了的罗锅儿。而且,这人也和他们听说的完全不同——不是一个无依无靠、赖乞讨为生的可怜、肮脏的小饶舌鬼。实际上,他与这些人迄今为止所见过的任何一种人都不一样。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