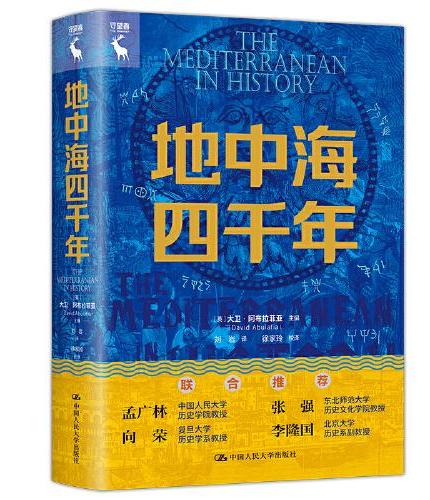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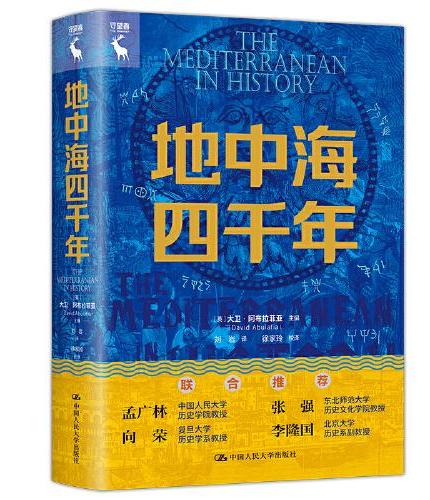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HK$
184.8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HK$
68.2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HK$
41.8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HK$
54.8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HK$
63.8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HK$
86.9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HK$
32.8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著名评论家、作家王尧的散文集,文章主要集中在《雨花》杂志连载。包括《“我的腿迈不出去”》《李先生的文言文》《那是初恋吗》《曾经的仪式》等篇目,主要为作者叙述当年求学过程中所遇到的老师、朋友、亲人,以及江南的风物人情、时局时代对个人的影响塑造等,在刻画记录往事的同时,充分呈现一代人成长的韧性与国家民族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扶持,带有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本书的关键词为“个人成长”“民间记忆”,既能唤起读者的时代记忆,对作者所走过的时代感同身受,又能感受当下。
|
| 關於作者: |
|
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2021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民谣》。
|
| 目錄:
|
那是初恋吗 1
琴声 13
有表姐的那年那月 23
奶奶和她的小镇 33
“我的腿迈不出去” 47
李先生的文言文 59
先生和学生 73
邂逅 83
气功叔叔 93
疼痛的记忆 103
我在未名河的北岸 113
脸谱 127
草鞋·蒲鞋·茅窝 137
能不能开门 143
二黄 149
田爷爷说三国 155
“神经病” 159
返回与逃离 165
熟悉与陌生 191
昔我往矣 213
融入与隔膜 233
后记 250
|
| 內容試閱:
|
奶奶和她的小镇
奶奶坐着花轿从女庙巷到两千米之外的爷爷家。我不知道奶奶当年是什么发型,在我的印象中,奶奶的头发从来都一丝不苟,梳着一个髻。奶奶出嫁一定是大排场,随她去爷爷家的还有一个丫鬟。我后来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想到我奶奶。大陆演员扮演大户人家的祖母无论神形常常不及台湾的一些演员,这可能与家庭背景有关。我在镇上读高中时,走过无数遍奶奶坐花轿的这条路,偶尔也有奶奶同辈的人喊住我说:你是闻二小姐的孙子?我是闻二小姐的孙子。在爷爷家那条巷子,有人会指着我说:这是二少爷的孙子。我爷爷排行老二。
我读初中时,奶奶的妈妈,我爸爸的外婆,我的婆太太还健在。我偶尔跟奶奶去镇上看她,她会从袖子里掏出一毛钱,让我肚子饿了去买烧饼。我一直记得婆太太的眼神,她没有奶奶的眼神那样自信,她的脸上留下了从繁华到衰败的痕迹。苍老的婆太太活到近九十岁,在我们有限的接触中,我从未听她说过闻家当年的境况。她不叫我的名字,见到我会说峥鸿的儿子来了。峥鸿是我爸爸的名字。如果我的舅爹、舅奶奶在家,我进门以后,依次恭敬地称婆太太、舅爹、舅奶奶。舅爹和舅奶奶都是老师,舅爹教中学语文,舅奶奶教小学余算。舅爹是我在青少年时期见到的读书多的人。舅爹知道我喜欢读书,但我们两人无法交流。舅爹背《古文观止》,我读小说,偷偷看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和《红旗谱》等。我在客厅站着,舅爹舅奶奶和我的谈话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
在婆太太家的大客厅里,我特别紧张,周遭所有的物件都散发着我在《苦菜花》《家》中读到的那些大户人家的气息。后来知道成语“如芒在背”,我就想到我在婆太太家客厅的感觉。其实,我非常尊敬我的舅爹和舅奶奶。我随奶奶出门后,奶奶会说:他们就是讲斯文。奶奶和她弟弟长得很像,关系可能一般,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姐弟亲近过。舅爹在一个大队小学教书时,我们家修房子,爸爸写了一封信让我去舅爹那里借钱。舅爹留我吃午餐,扁豆烧肉。饭后舅爹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回,没有提钱的事。我在路上急切地打开信封,信里有“入不敷出”四个字。我一直记着舅爹的午餐,在那样的日子里,舅爹留我吃午餐,而且有红烧肉,已经是深情厚谊了。多少年后,我路过那个村庄,想起秋天的那个中午,舅爹从危楼的楼梯送我下来的情景。我奶奶去世时,舅爹没有送我奶奶,他当时也重病在身,但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能够撑着病体和他的姐姐做后的告别。
婆太太家的这条巷子,原来叫女庙巷,后改称井巷,但奶奶习惯叫它女庙巷。一口古井居中,巷子两侧是粉墙黛瓦。井巷的房子似乎都特别高大宽敞,可以想象当年这条巷子的富贵景象。奶奶就是在巷子裹脚又放脚的,这位“闻记棉线店”的二小姐,把往昔繁华的生活和她在女庙里听来的故事都梳进她的发髻里。即使在潦倒的日子里,奶奶在乡下依旧保持着镇上大家闺秀的风采。我奶奶在她晚年经常向我讲述的我们那个大家族的故事早已离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远去,我们像听别人家的故事一样。在村上我家不大不小的天井里,总是放着两只荷花缸。奶奶说从前镇上老屋天井里的两只荷花缸比现在大多了,我爸爸的印象也是这样,祖辈给我诗性的记忆就是缸里的荷叶。
在奶奶的叙述中,我陆续知道闻家的历史和一些规矩:在镇上和县城有几家棉线店;三个舅爹都是读书人;中秋节的月饼从大到小放在盘子里;奶奶和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有空时就去书场听书(姨奶奶跟我说她很少去,奶奶去得多);家里人不到齐了,不好开饭;吃饭不能有声音,筷子只能伸到菜盘子靠近自己的这一边;吃好了要对长辈说慢慢吃,不能起身就走,起身时要说您坐稳了;早上起来要向长辈请安;做生意要老少无欺;亲友往来不能嫌贫爱富。这些历史和规矩后来都渗透在我家的日常生活中,我有一段时间比较习惯繁文缛节,与我们家族的传统有关。
爷爷家在两千米之外的那条巷子依水而建,很像我们熟悉的周庄,爷爷的家在这条巷子里,有好几进房子,比奶奶的娘家还要阔绰。爷爷的规矩和奶奶娘家是一样的,那是镇上大户人家通行的礼数。数百年来,这些规矩成为小镇文明的面貌之一。我的曾祖父也是经商的,开油店。我喊曾祖父老爹。我爸爸说,附近的几个镇都是吃老爹家的食油。我妈妈见过老爹,在我出生的第二年,老人家去世了。我一直没有问我的爸爸妈妈,老爹有没有见过我。我看到老爹的照片,一脸的严肃甚至刻板。但所有熟悉曾祖父的人都说到他的宽厚仁爱,曾祖父从来都答应顾客赊账,一直到他破产也没有收回欠债。我对祖屋的初印象非常阴冷,曾祖父去世后没有安葬,灵柩停放在家里。我从记事开始,就很怕去镇上的祖屋,进去后就要到停放祖父灵柩的屋子里磕头。磕好头了,再向曾祖母请安,我喊曾祖母“老太”。我看不出老太是爷爷的后妈,爷爷奶奶对她行礼如仪。那时粮食特别紧,新米出来后,我爸爸妈妈总是到镇上给老太送新米。
直到读初一后我才知道,我所见到的老太是我老爹的填房。那一年春节,我的几位姑奶奶都到我们家了,在她们的言谈中,我听到她们对老太的一些非议。我想应该没有女儿会这样议论妈妈,这才知道老太的身份。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从爷爷和几个姑奶奶的年龄,我应该能够算出他们和老太的关系。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对老太的尊敬,让我失去了判断。我的两个姑奶奶,和我的奶奶一样,头发一丝不苟,衣服整整齐齐。我觉得大姑奶奶特别像我的老爹,不苟言笑。二姑奶奶则端庄中带着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二姑奶奶家的圣堂村离我们十里路,我不常去。有次到圣堂,二姑奶奶看到我了,拉我去她家,用铁锅做鸡蛋饼,她用稻草烧火,慢慢把蛋饼烤脆。二姑奶奶说,你要好好念书,王家就靠你了。我的大爷一家在解放前就去了泰州,和我们这边几乎不往来。这边的两个姑奶奶几乎把我看成是中兴家族的希望。两年后的1975年,我初中升高中,突然要通过考试升学,考点就在圣堂村。中午在二姑奶奶家吃饭,我的表伯问我上午作文是什么题目,我告诉这位小学校长:《读书务农,无上光荣》。
婆太太家和老爹家的产业在解放战争期间破产。我的爷爷奶奶带着我爸爸和两个姑姑到了乡下,两个姑奶奶则在相邻的一个村子里。他们都成了难民,因此土改的时候都是好成分。从镇上到乡下,那几年一定是异常煎熬。我的大姑姑过继给了我的姨奶奶,她留在镇上,二姑姑出嫁回到镇上。小姑姑在乡下长大,成了和大寨大队铁姑娘一样的农村青年。这个农村真正改变了我们家族的一员就是小姑姑一人,终小姑姑也嫁到了镇上。这好像是命定的秩序,她们都回到了曾经的繁华梦中。但今非昔比,无论如何家道衰落了。她们都带着旧的记忆开始新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我的爷爷有专长,到乡村不久,他就被政府安排到另一个乡的粮管所,发挥他的专长了。我的奶奶差不多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爷爷那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村上,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则是到镇上和我的几个姑姑一起住。我会在假期中到爷爷那里住几天,爷爷非常严格,管理粮食仓库就像管理自己家的一样。粮仓里有成堆成堆的北方的山芋干,即使不煮熟也可以吃。爷爷看到我盯着山芋干的眼神,便说:你一块也不能拿。我回去时,奶奶总是送我到很远很远的路口,我走了很远回头时,奶奶还站在那里。我的易于伤感,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养成的。有一次,奶奶很生气,说她送我时头也不回就走了。我想了想,我是回头向奶奶致意的,但回头的次数可能比以前少了。我在长大,我消失在行走的人群中,奶奶的眼睛也老花了,她可能看不出我的背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