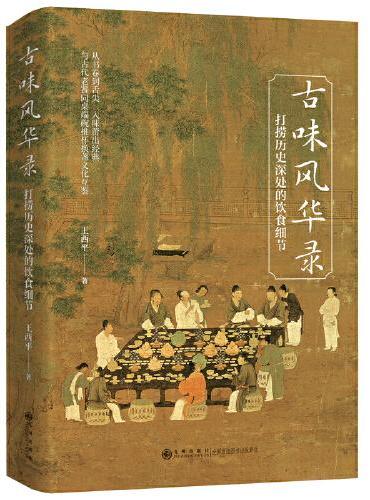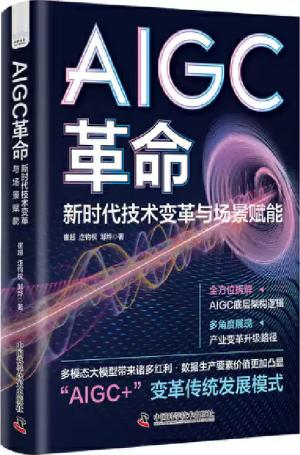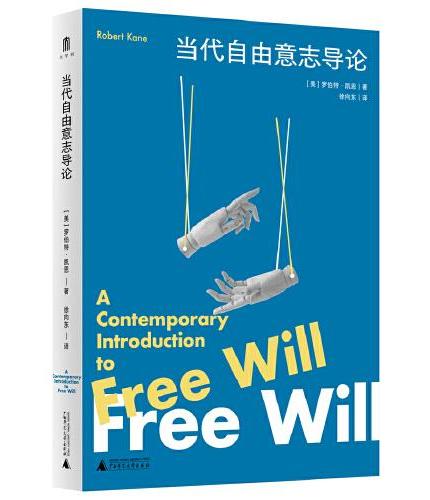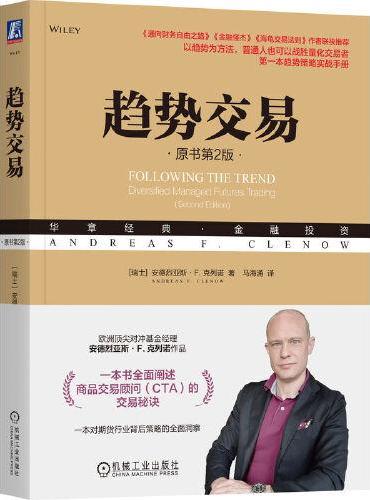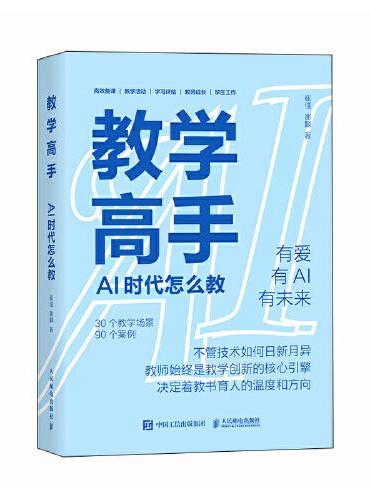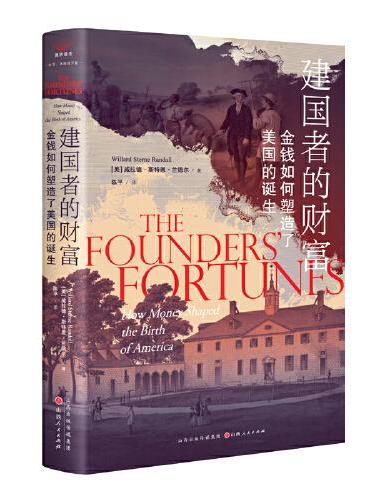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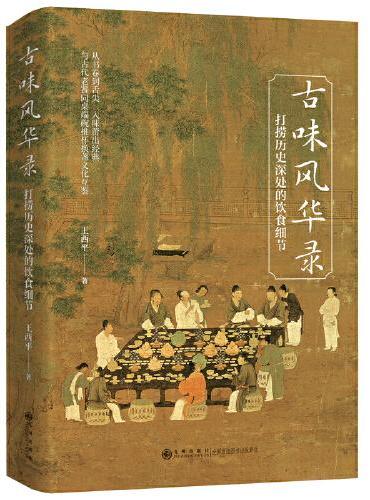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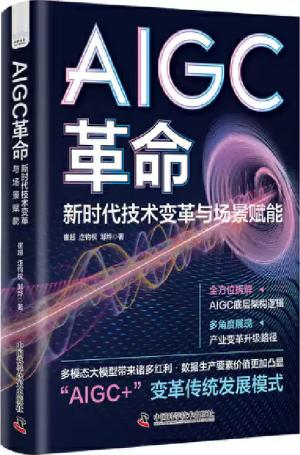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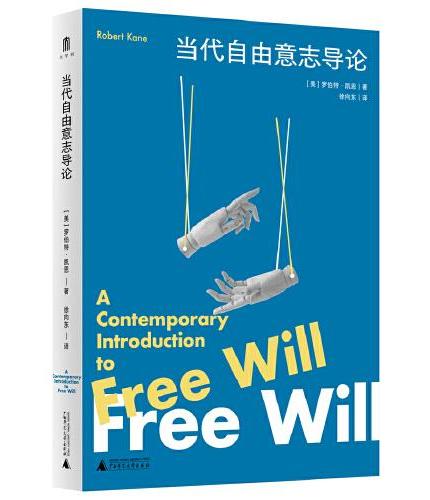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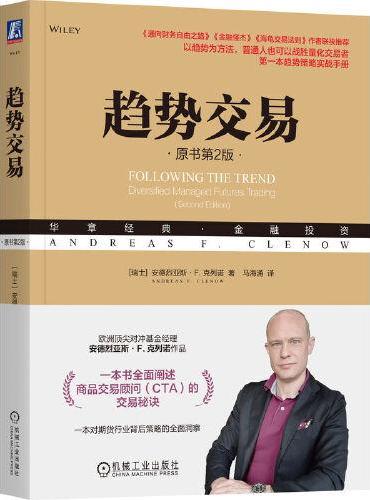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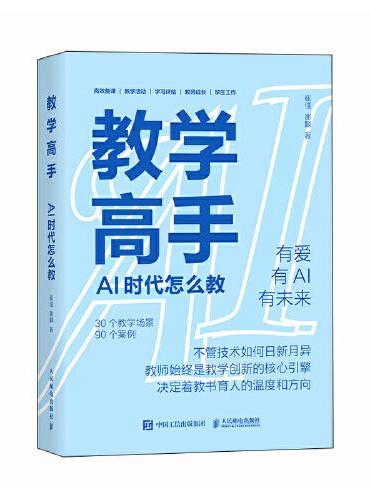
《
教学高手:AI 时代怎么教
》
售價:HK$
65.8

《
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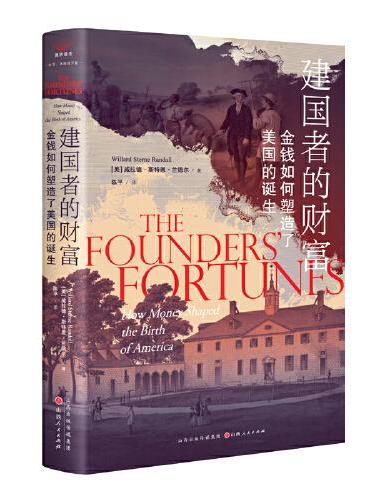
《
建国者的财富:金钱如何塑造了美国的诞生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关汉卿、王阳明、吴承恩、汤显祖……王国维,11个坐标型的文化名人,11种跌宕起伏的命运特写
※体量轻盈的文化名人小传、时空交错里精神和心灵的遥相呼应
|
| 內容簡介: |
群星璀璨的先秦诸子、独具风骨的魏晋名士、青春昂扬的唐代诗人、儒雅风流的宋代词人,元曲大家关汉卿,明清著名的思想家及文学家王阳明、袁枚、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王国维……
这套“品中国古代文人”书系以纵横的笔墨、现代的眼光书写从先秦至清代对中国文化及文学影响至深的文人或文人群体。以他们的生命历程为经,以他们的经典文学作品为纬,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小传记来勾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脉动。
作者将丰富的史实嵌入丰富而细节化的文学想象当中,融诗情、史识与深思于一炉,以独具特色和极大影响力的个体文人的生命演进,展现中华文化与文学的缤纷斑斓。
这本《元明清文化名人小传》以11个元明清时期的坐标型文人的人生历程和心灵轨迹,串起自元至明清数百年的文化史。他们拥有卓绝的才华,他们也曾迷茫彷徨,也曾在泥淖中眺望繁星,终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
| 關於作者: |
|
新宇 ,古典文学的爱好者。致力于将尘封的古诗词唤醒,向现代人展示古代诗文的生命力。
|
| 目錄:
|
元
关汉卿:绽放在俗世里的奇葩
一 世变 / 004
二 浪子 / 010
三 斗士 / 017
明
王阳明:知行合一
一 我本狂者 / 025
二 “五溺三变” / 027
三 龙场悟道 / 031
四 致良知说 / 036
吴承恩:神魔现实主义鼻祖
一 家世 / 041
二 迷途 / 042
三 游戏 / 044
四 幻想 / 048
汤显祖:戏剧“梦幻”大师
一 神童 / 052
二 狂奴 / 055
三 茧翁 / 058
四 巨匠 / 059
清
蒲松龄:于热场中作冷淡生活
一 科举:期许跃龙津 / 068
二 坐馆:游子心易酸 / 076
三 聊斋:集腋为裘,浮白载笔 / 083
纳兰性德:我是人间惆怅客
一 佳公子:人间富贵花 / 091
二 至情人:情在不能醒 / 096
三 金兰契:肝胆皆冰雪 / 103
四 饮水词:心事几人知 / 112
五 惆怅客:生活在别处 / 118
郑板桥:难得糊涂
一 另类少年 / 123
二 风流措大 / 128
三 入世诱惑 / 132
四 一官归去来 / 135
五 三绝诗书画 / 141
吴敬梓:儒林怪杰
一 家声科第从来美 / 147
二 从出嗣到移家 / 149
三 十年沉潜撰讽书 / 154
四 伟大也要有人懂 / 155
袁枚:人生贵在适意
一 抽离官场 / 161
二 经营随园 / 165
三 美文美色 / 168
四 美食美景 / 174
曹雪芹:繁华过后是苍凉
一 极贵极贱的身份 / 180
二 极盛极衰的家境 / 183
三 谋道:一个离经叛道者在世俗标准下的挣扎 / 187
四 谋食: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力 / 191
五 红楼是梦原非梦 / 197
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 哲学梦 / 204
二 文学梦 / 211
三 甲骨与敦煌“朴学”梦 / 215
四 梦碎 / 221
|
| 內容試閱:
|
王国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终其一生,王国维都处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当中。
22岁之前,他在家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在科举考试时弃时文帖括八股而不为,“不终场而归”,弃绝了传统的仕进之路。
30岁之前,他醉心于西方的哲学美学,深受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服膺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哲学,借哲学“探索宇宙人生之真理”。
30岁之后,他深感“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渐由哲学转入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人间词》《人间词话》是他寻求心灵之慰藉、灵魂之安顿的实践与理论的产物。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在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上又一次发生了转折。文学中寻求慰藉不可得,灵魂无法得到安顿,他转而埋头于古文字、古彝器、古史研究,陷入纯粹的考据之学中,于喧嚣的人世里寻求最纯粹的寄托。
与文学上超越时代相反,在政治上他却越来越趋于保守。他以清朝遗老自居,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他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格召见,并任“南书房行走”。当溥仪被逐出宫,他视为奇耻大辱,欲投河自尽而不得。在“君辱臣死”的心灵阴影笼罩下,他最终以自杀而“完节”。王国维之死因,众说纷纭。与他精神相通且为至友的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茫茫宇宙,唯有一死。王国维最终以“自沉”结束了他带有悲剧色彩的一生。
一 哲学梦
不羁少年
1877年,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双仁巷。这时离鸦片战争过去已30多年,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新旧思潮碰撞激荡,社会正处在暗流涌动的关口。
这一年,康有为20岁,罗振玉12岁,孙中山11岁,蔡元培10岁,章太炎8岁,梁启超5岁。龚自珍已去世36年,4年之后,鲁迅出生。
王氏家族在浙江海宁一带素有声望,只是传至王乃誉这一辈时,已日渐式微。至今,海宁仍有安化王祠——为纪念先祖王禀在靖康之难时,率太原军民奋力抗金而建,供王氏后人和海宁人祭奠。
在海宁,除了王氏祠外,双仁巷也有来历。它因颜杲卿和颜真卿得名,兄弟二人在安史之乱中忠勇报君,先后被叛军杀害。
在这块人文思想浓厚的土地上,秉承着传统文化的基因,王乃誉自然也对长子王国维寄予厚望。王乃誉早年为躲太平天国战乱曾流落至上海,在茶叶店、油漆店中讨生活,后返回家乡,继续做一点小生意,后又游幕溧阳,生活逐渐有了一些起色。
虽是一介幕僚,但他痴迷于书画、篆刻、古诗文,学养颇深。王国维7岁时,便被送到私塾学习,他是打定了主意让儿子走传统的科举仕进之路的。
后来王乃誉干脆辞掉了幕僚一职,在家“课子自娱”。只是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少年,“学既不进,不肯下问于人。而做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父亲的失望溢于言表,但失望归失望,11岁时,他还是送王国维到著名的秀才陈寿田处学习,学的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及八股时文。
就是这个在父亲眼中“毫无英锐不羁”的少年,却在读书上面,渐渐显示出自己的不羁来。15岁时,他以第21名的成绩,考取秀才。16岁时,见友人读《汉书》,心生喜悦,拿出小时积攒的压岁钱,从杭州购得前四史,开启了自己的读书生涯。他不喜欢《十三经注疏》,也不专事帖括,读书唯究经史大义。
1893年,王国维在父亲的催促下应乡试,“不终场而归”。1894年甲午海战中,大清帝国被一个弱小的国家击败,国人震惊,王国维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始知尚有新学者”。一时之间,救亡图存的思潮涌动。在这种动荡纷杂的局面下,传统的科考仕进之路,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走下去,到底还走不走得下去,都是未定之数。
1897年,他勉强又参加了第二次乡试,未中。看来,这个他本来就不甚有兴趣的科举之门,也不愿意为他敞开。传统仕进之路,应该弃绝了。
他决定离开家乡,去往一个视野更开阔、舞台更大的天地——上海,在那里谋生活。
初涉人世
1898年初,22岁的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馆作书记员。
《时务报》的主笔是当时大名鼎鼎、 主张变法求存的梁启超。去《时务报》,一是可与自己崇拜已久的梁启超共事,幸莫大焉;二来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毕竟此时的王国维已在家乡成婚。
但令王国维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他去前的几个月已辞去《时务报》职务,两人并未见面。梁启超受命主笔《时务报》,代表的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而《时务报》的大股东汪康年,则代表张之洞。两者在人事及其他利益方面,多有龌龊,最终以康门弟子相继离开收场。
到《时务报》后,王国维感觉失望了。所谓的书记,不过是一个打杂人员,干干抄写、校对、收发书信的杂活而已。而他本人个性内向,又不善交际言谈,在同僚中与他有交际的人,也没有几个。当唯一一个主动与他接触的欧榘甲也离开后,他在这家报馆也成了孤家寡人。
什么维新思想,什么救亡图存,在现实的生计面前,仿佛也渺小得不值一提。他也曾想过离开,但为了那许诺的每月20块银圆的薪金,他不得不留下来。毕竟当时1块银圆可以买40斤大米。
苦熬了二个月后,他只领到了12圆的薪金。在汪氏兄弟眼中,他办事能力不足,领12圆已是恩赐。为了生计,王国维只得将少年壮志埋在心中,每日工作之余,以读史来打发无聊的时日。
只到有一日,在上海东文学社的罗振玉去报馆找汪康年,没碰到,却对报馆里只顾埋头看书,对来人从不曾举目正视的年轻人有点好奇。当他看见王国维的《咏史》诗时,心中暗自称奇,当下便觉得这是一个胸中有天地、不可小视的人才。诗曰:“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就是这一首诗,拉开了他和罗振玉30多年的知遇之交。
罗振玉本是经史考据学专家,好金石古玩。但甲午海战后,他意识到中华上国已不复存在,便办《农学报》,以译介日本农业方面的书籍为职志。为培养翻译人才,他又与汪康年谋划,于1898年初成立东文学社。
自此,王国维与罗振玉结下不解之缘。
罗振玉先给他在东文学社派了一个闲差,每月30圆。随后因东文学社关闭,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仅数月因脚气病返国。但正是这段时间,他进入“独学时代”,大量接触并钻研西方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书籍。
用他自己的话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当时正发生“戊戌政变”,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和人生观念也在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中,社会、人生的种种问题,萦绕在这个将近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心中,他选择了用哲学来探究并解决他面临的一切疑问。
突破迷雾
留学日本,罗振玉的本意是让王国维物色一些日语翻译人才。
结果,翻译人才没有找到,他却找到了一大堆哲学书籍。一来是他认为,无论是什么变革,首先要改造人的思想,而改造思想,需要教育学,需要哲学。二来,其直接的原因则是,张之洞向朝廷上奏折,痛陈哲学无用,要让哲学从清政府正在创建的新式学堂中剔除。
王国维写了《哲学辨惑》一文,认为哲学集真善美于一体,无哲学便无教育。他的一番宏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王国维由此声名大振。
盛名之下,通州师范学堂向王国维发出邀请,其创建者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张謇。为这个科考之梦,张謇从16岁一直考到41岁。但中状元之后,他又毅然选择辞官下海,办教育、兴实业,对这样一个充满传奇性、敢于与旧我决裂、不断探索社会人生新出路的人,王国维心里是佩服的,这也是他选择来通州的原因。
在这里,他任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读叔本华之书后,进而上窥康德的学说。他希求在哲学中思索人生的本质,以慰心中的困惑和种种苦闷。他读到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好之”。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一方面高扬生命意志,顺应当时的时势思潮,一方面其“悲观主义人生观”甚合“性复忧郁”的王国维之个性。
浓厚的悲观色彩和悲剧精神,一直贯穿在王国维的文学观和人生观当中。哪怕正当盛年,他也以悲情打量着、探究着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悲观的因子,渗透在他过于年轻的肌体中,血肉中,思想中。来看看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人,写下的悲观句子:
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免襁褓,役物固有余。
人生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在他眼里,人只是寄寓在这个世界上,寄寓在一段形体内,人皆无法摆脱嗜欲的挟制,皆是物质或欲望的奴隶。生而为人,无法摆脱被羁束的宿命,那么,这样的人生与地狱又有何异?
在南通师范学堂,他做得并不如意。半年之后,他离职而去。
离职后,他受罗振玉之邀来到了苏州师范学校,同时任罗振玉主办的《教育世界》主编。这二三年间,他的心情是少有的晴朗,甚至发出“直欲奋六翮”的豪情之叹。这段时间,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第一个井喷期。
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等文,在译介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外,他的“非功利审美”文学思想也得到了集中呈现。对他而言,哲学也好,文学也好,无关功利,无关现实的补缀,它们在本质上都是超越于功利之上的独立存在,是建构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东西。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的思想也悄悄发生了转变。
二 文学梦
《人间词》
在苏州讲学期间,除了大力译介哲学,他又将西方哲学理论用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对《红楼梦》作出了新人耳目的独特评介,在后来的“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
除此之外,他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运用中国传统的词体,创作了大量的“人间词”。这时的转变是无意识、自然而然的。直到二年后,在《三十自序》中,他才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欲借哲学、教育学改造人心,改造人的思想,希求在救亡图新中取得一点点功效,这信仰看来已经产生了动摇。而他之转向文学,并不是追求文学的伦理和实用功能,而是借文学这种形式,以安放自己的情感和心灵。
文学无关功利,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形式。
对他而言,参与社会的改造,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凭借自己的学养,在不违逆自己个性的前提下,以文字为口舌,在这个世界上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
1906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奉调学部而返京,住罗家。接下来的两年间,先后发表了《人间词》甲乙两稿。他对自己的《人间词》颇为自负,“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关于《人间词》,黄霖先生的一段评价写得很好:
王国维《人间词》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陟黜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也就是说,王国维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力争第一义处”。王国维的《人间词》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他用一双充满忧郁、孤独、悲悯的眼睛审视着世界和人生。词中的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这种慨叹不是古人那种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词人王国维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洞识和艺术感觉。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 “人生”。“人间” “人生”作为诗人体验思索的对象进入诗人的视野。王国维曾以“人间”为室号,将他的词集称为“人间词”,将他的词话命名为“人间词话”,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人生叩问的哲学况味。
1906年,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病逝,王国维回家奔丧。
1907年,原配夫人莫氏病亡,王国维自京返乡奔丧。
接二连三的打击和无常,加之抑郁内向的个性和自己多病的身体,他在《人间词》中的悲观主义和人生叩问,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了。
《人间词话》
1908年,在罗振玉主办的《国粹学报》上,王国维又刊出了《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说”。如果说《人间词》是他在实践上向传统文学的回归,《人间词话》则是其《人间词》的理论升华,也是中国传统词话理论的升华。
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既是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也是东方与西方融合的开拓者。《人间词话》集中体现了他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思想特色。它既是中国传统词话的终结,也是中国现代词学的开启;既具有浓厚的东方思维特色,又闪耀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彩。“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人间词话》的核心是“境界论”,其整个理论建构都围绕着“境界”二字,理解了“境界”,其他很多论述都会迎刃而解。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还有著名的“三境界”说,这些无不成为词话理论中颇具新见而又带有母题性的研究话题。
继《人间词话》后,王国维又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这一点也是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在西方,戏曲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戏曲一直衰疲不振。他试图从戏曲史的角度,担当起戏剧振兴的责任。“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由此,他写出《宋元戏曲史》,郭沫若称此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王国维的天才。
天才有异于常人的感受和洞见,也有异于常人的痛苦。无论是将西方哲学与中国《红楼梦》相结合,提出《红楼梦》是真正的“悲剧”,还是《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他的感受和洞见,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
但天才往往都有自己的宿命,也有不可解的、不可知的莫名的痛苦。学术研究,对王国维而言,不仅仅是他天才的表现之一,也是他对抗痛苦的唯一慰藉。
终归是一个书生啊,在这个复杂和无常的人世间,过去令他倍感痛苦,现在也令他倍感迷惘,而未来他看不清楚,也看不到希望所在。他能做的只是,在学术和书本中求生活、求慰藉,求自己活着的价值和动力。
改良派也好,维新派也好,革命派也好,还有各种打着变革旗号的野心家,对他而言,都是一个个即将告别的身影。他看不到现实好转的迹象,也看不到未来之路在哪里。早年勃发的英气,还有为“新学”激荡而奋力研究的西方学说,对他而言,都是越来越遥远的梦境。
现实越是混乱,他越是往传统回溯,越是沉潜眷恋于过去的一切。
对他而言,过去纵然不好,但总还有一个统一的帝国在,有一个可以围绕着这个核心的中心人物在。
三 甲骨与敦煌“朴学”梦
如果说寄情于哲学,还有一线改造现实的初衷;寄情于文学,是寻求慰藉痛苦的转向。寄情于“朴学”,则已然是对现世的一种逃避。
1911年,王国维35岁。这一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革了大清皇帝的命。
对越来越眷恋过往的王国维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它革掉的不仅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命,也是王国维心中残存的恢复大中华文化的希望。这个革命让王国维感觉到了恐惧。
比他还恐惧的是罗振玉。罗振玉是朝廷的四品官,而且,此时他家里有大批古籍和龟甲兽骨。
已成为姻亲的王国维和罗振玉一筹莫展,此时早年在东文学社结识的日本友人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他们于11月中旬,携家带口前往日本。
1912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他写长诗《颐和园词》,写《隆裕太后挽歌辞》,咏叹清室的兴亡,祭奠一个逝去的旧王朝。在这曲曲挽歌中,他表达了一个“遗民”的忠愤与哀思。其实,他哀悼的到底是一个王朝的逝去,还是一种文化象征的颓逝?说不清。这一点,在他接下来的人生历程中,会渐渐清晰。
在日本一待就是5年。这5年之间,他越发感到在混乱的世变中,唯学问之道是最高尚的,也是最恒定的。自此后,他的治学兴趣又发生了一次转向。——专攻经史小学、金石器物之学。无关义理,无关情感,从纯粹的史料和文物中,寻绎考辨中华文明的脉络,今人称之为“朴学”。
在日本,他治学最大的成果和贡献,一为甲骨文,一为敦煌学。
他研究甲骨文,源于罗振玉带到日本的大量龟甲兽骨。这些藏品罕见而丰富,其中最珍贵的是发掘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
河南安阳的农民在地里劳作时,挖掘出一批龟甲和兽骨,他们将这些作为龙骨卖给了中药铺。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一次偶然中,发现这些叫“龙骨”的药材,非同一般,他以异于常人的敏感和卓识,斥资买下京城所有的“龙骨”,还派人去安阳收购。八国联军进京后,他死于乱中,其子将这些龙骨卖给父亲的好友刘鹗,罗振玉又是刘鹗的亲家。随罗振玉一起运去日本的龙骨成为他们研究的最可靠而原始的依据。
1917年,王国维将自己在日本期间的研究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一系列文章,将殷商从传说变成信史,展现在了国人面前。他这是在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正本清源,在为社会变革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个重大研究成果有关敦煌。
敦煌,有举世闻名的文化古迹,也有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要道,这里是中国、印度、希腊等文明交汇、激荡而后又被封存之地。只到清末,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从一道裂缝中发现了它。
他将洞内藏有绝世经书绢画的消息告诉了官府,官府的命令是“就地封存”,但在国力日渐衰弱之际,哪里封存得住?那些窥伺中华文物的野心家和强盗先后登场,比如伯希和、斯坦因。
在日本的第二年,法国汉学家根据斯坦因带回的文物,撰成考释请教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借此机会,研究考证了这批文物,最后写成《流沙坠简》。在《流沙坠简》中他们解开了诸多千古之谜,为近代研究西北古地奠定了基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玉门关究竟在何处。
布衣长辫
1916年,王国维回到了故国。
回来后他发现,一场革命后,除年号被废外,皇帝依然端坐在紫禁城,只是无法再发号施令。以前的巡抚改名叫督军,除了变了名称外,仿佛那些前清的老朋友,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只是不需要再去朝拜皇帝了。
在新旧的转换交战中,旧的摇摇欲坠,但没有完全死去;新的尚在孕育之中,但也不知路在何方。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他也曾是新学的追随者与实践者,但他更怕旧文化传统的断裂与破灭。他对旧皇室抱着极大的同情甚至眷恋,因为在他心中,至少他们还代表着旧的文化或文明传统。
所以当他听说张勋要复辟,要拥立溥仪复位时,他禁不住为张勋大唱赞歌。
只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人又能挡得住历史的洪流?复辟的闹剧只维持了短短12天,便宣告破灭。
这下,王国维更是心灰意冷了,除了将自己封闭在书房和书本中,他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做不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大,让他无所适从。
他留着长辫,以独立的姿态祭奠逝去的旧王朝,同时维持着他心中固守的信仰和道义。
罗振玉写信劝他说:“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至少,在学术的国度里,他可以自由自主,做一个独立于时代的人。
所以,当犹太人哈同聘请他任教仓圣明智大学时,他略做考虑,便同意了。毕竟在那里,他可以主编《学术丛编》,既可以潜心研究,又能全权负责,同时也可以凭借优厚的报酬解决生计问题。
只是热衷于附庸风雅、世俗功利的哈同终究惹烦了王国维,没做多久,他欲辞职,再度去日本。
正在此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王国维犹豫不决。
说起来,蔡元培和他都是浙江人,只是一个在海宁,一个在绍兴。蔡元培出生于世代经商的家庭,但也走上了传统科举仕进之路。和王国维没有考取秀才不同的是,蔡元培年仅24岁时便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王国维个性内向,对旧文化传统多有眷恋,且精力大部分都花在学问和书本上。但大他9岁的蔡元培则不同,他终身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很多时候都在做官,且以激进的方式投身于政治斗争中。
1913年,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职,1917任年北京大学校长。
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二者差别很大。王国维秉持改良主义,希望清廷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他反对辛亥革命,希望清政权能延续统治。蔡元培知道改良无望后,便组织光复会,转向彻底的革命,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也许,正是这点不同,让王国维心有芥蒂。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蔡元培心中,他对王国维的学术造诣是服膺的,早年王国维写的《红楼梦评论》便受到了他的关注。执掌北大后,他摒弃政治立场之囿,以开放的气度和胸襟,延揽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有声望的学人。王国维以其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声誉,自然也进入了他的视野。
北大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好去处,但它的“新文化”思潮,又让王国维颇为犹豫。
在蔡元培接连四次发出邀请后,王国维终于于1922年同意担任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人不在北大,且不接受北大的薪金。
四 梦碎
文学侍从
如果王国维的生命,终止于此,也是波澜不惊的一生了。
但就在1923年,47岁的王国维接受了逊帝溥仪的谕旨,任“南书房行走”,当了溥仪的老师。以秀才身份入宫当帝王师,对王国维来说是“二百年未有之恩遇”。
为什么偏偏是王国维?
因为他以布衣长辫,独立行走在新世界丛林之中,坚守着心中的旧传统和故国梦。
溥仪摆出一副“重振朝纲”的势头,王国维为他尽心尽力,做着一个注定要破灭、要被时代遗弃的旧梦。溥仪赏王国维“五品衔”后,罗振玉为他刻下“文学侍从”印章一枚;接着皇帝给了王国维更大的恩遇,允许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这是以往只有亲王、军机大臣才能享有的恩遇啊。王国维内心感激莫名,以更大的诚心为皇帝进献良言。
只是没过多久,冯玉祥率军赶溥仪出宫。王国维身为帝王师,誓与溥仪共生死,当溥仪逃至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后,他和罗振玉等相约投神武门御河,自杀殉国,但被家人死死拦住。
就在溥仪被驱逐出宫前,因内务府和载洵等私售宫中文物给日本,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现,痛斥其卖国行径,他们发表的宣言直指溥仪小朝廷。王国维对他们直斥御名的行径极为不满,宣布不再担任北大国学门的通讯导师,与北大就此决裂。
清华一梦
溥仪躲进天津租界后,王国维则于1925年,接受吴宓的聘任,进入清华园。
请王国维来清华,是胡适推荐的。胡适服膺于王国维的学术造诣。但他连续邀请了两次,王国维都没有同意。最后,胡适请溥仪劝王国维,随即溥仪下了一道诏书到王国维家中,王国维才同意奉诏进清华,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共同成为清华“四大导师”。
清华大学校长吴宓知道王国维的习性,他亲自带着聘书,到王国维家中,对王国维行起了旧式叩首大礼,王国维一时之间感动莫名。他以为对方是一个西装革履之人,却不料对方以这种特有的方式示诚。
就这样,他戴着瓜皮帽,拖着一根长辫,穿着布衣长袍,行走在清华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一次夫人在为他梳洗长辫时问他,别人都剪了,何不剪掉?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掉?”他的长辫,和他独有的风格,慢慢地为清华园所习惯和接受。
在清华园,他外表极冷,与年轻老师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除陈寅恪等少数几人之外,他几乎是独来独往的。有一次,清华大学为他办五十寿诞宴席,赵元任的太太因为惧怕王国维而坚决不与他同坐一桌。
他内心是极热的,他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吸引了大批热情的年轻学子。他对年轻学子提出“以学术为性命精神”的期待,对以赚钱谋官为动力的学术动机,深恶痛绝,但他深知以一己之力改变社会全体之好,殊为不易。
他的治学态度是极谦卑的。据说他上《尚书》课时,开场白是独特的。他颇为郑重地对学生说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半点虚假和矫饰,此种师风,也让人追慕不已。
遗世独立
1926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不幸病逝于上海。
丧事完毕后,儿媳罗孝纯随父亲罗振玉回到了上海家中。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然而他面临的不只是丧子之痛,还有挚友之绝。与他结交近三十年的罗振玉,亦亲亦友的罗振玉,因为这次女婿的去世和往年因小夫妻之事而积累的龌龊,也宣布和王国维断绝亲友之谊。人生之痛,莫过于此。
在学术和文化的领域内,王国维如鱼得水,高深的造诣、卓绝的新见,让人望尘莫及。在人情世故这个领域里,他却像一个痴子,处处碰壁,处处受到伤害。在社会的洪流中,他一直不愿被裹挟着前行,独立地坚守着旧文化的残梦,坚守着他心中的旧世界。
还有,时局也让人越来越不安。听说冯玉祥已率兵入关,张作霖欲退到关外自保,一场大变恐怕又要来临了。而梁启超也欲前往日本避祸。
除了治学外,他又能做什么?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让人看不清。又有哪一方净土,可让自己心无旁骛地做学问?所做的学问,于这个现实的世道,又有何裨益?
回首半生,从早年欲以哲学改造世界,到中年转向文学寻求慰藉,到晚年转向考据以避世,到现在在清华园中传播学问,可这个社会又哪里需要这些纯粹的学问呢?那个寄托着他的信仰的旧文化传统和君主已自身难保,前路何在?寄托何在?
一切因缘郁结于他心中,忧心如醉,如煎,他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自己的去路。
1927年6月,清华园又迎来了一年的毕业季。距端午节还有几天,即将毕业的学生忙着向老师王国维告别,晚上戴家祥和谢国桢到老师家中话别。谢国桢还带了两把折扇,请老师题字留赠。
6月2日,王国维如常吃完早餐,到清华院有条不紊地处理了一应琐务,还特意为谢国桢留下的两柄扇子题了字。其一题曰:“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惊回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这是他的绝笔,其中透露出万事皆空、生死一梦的幻灭感。
随后,他向他遇到的一位教授借了五元钞票,出了清华园后,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吸完一根烟后,11时左右,他跃身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他内衣口袋中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仿佛,他在人世上走了五十年,一直在求死。其悲哀绝望之感,深入骨髓。
一代文化巨人,以自沉从容地向这个人世诀别。他走的时候,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一切都静悄悄地,不惊动任何人。
对于王国维之死,有殉清、被逼债等各种说法,但任何一种拘泥于一人、一时、一事之说,都不足以涵盖他选择自沉的原因。对他而言,这只是他自由选择的告别方式而已。
他曾在《屈子之文学精神》中这样评价选择自沉于汨罗的伟大诗人屈原:“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即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
家国情怀与个人知遇之恩,是屈原“终不能易其志”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作王国维的夫子自道吗?
对于王国维之死,梁启超是这样说的:
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
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另一个文化巨人陈寅恪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限于王国维一人一身,而是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
纵观王国维的一生,从生到死,无不贯穿着这个思想。
生,不随大流;在滚滚而来的新文化潮流中持守旧文化的价值标准,以对抗新文化产生的种种流弊。 死,不苟且偷安。在这个人世,我来过,我活过,留下了不灭的印记,然后,我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