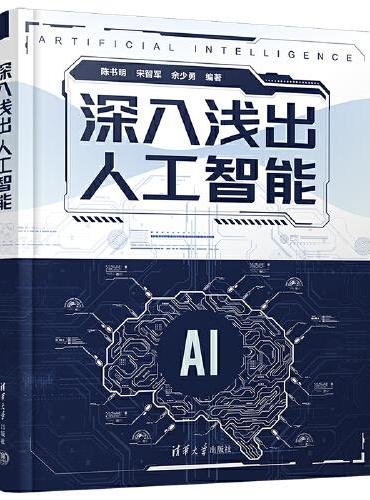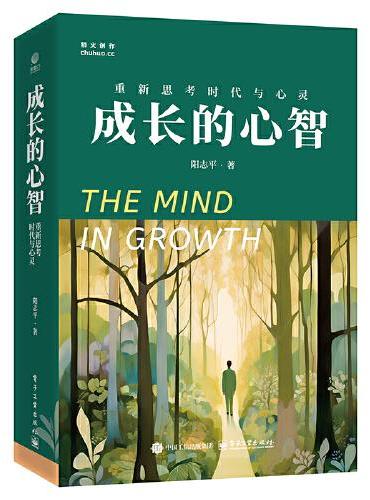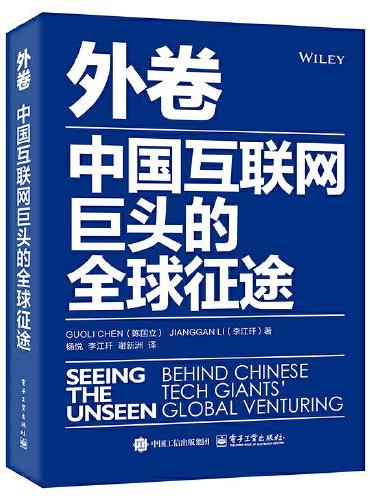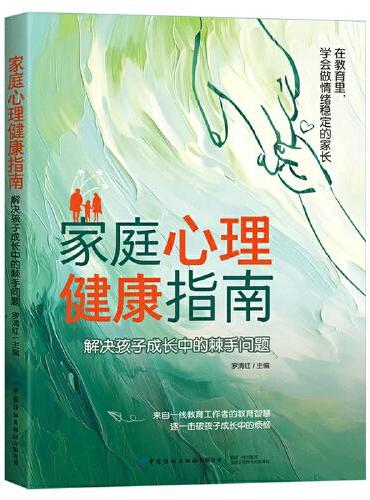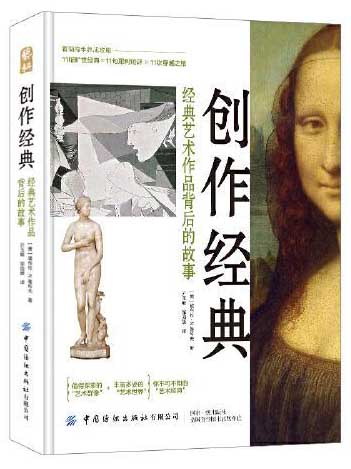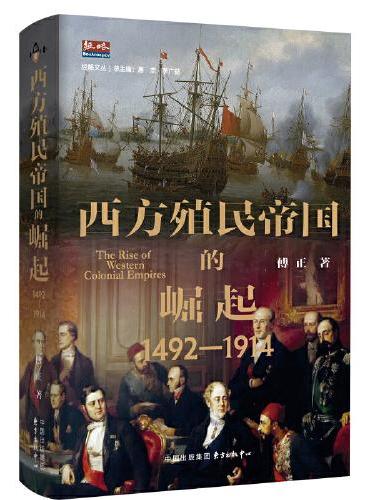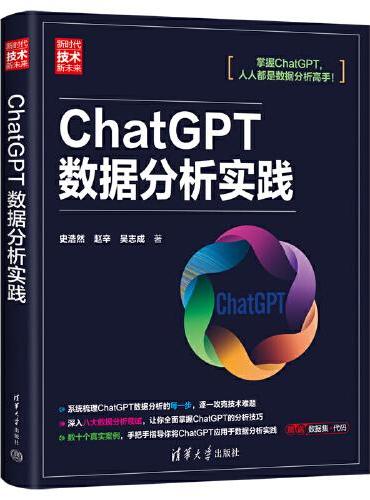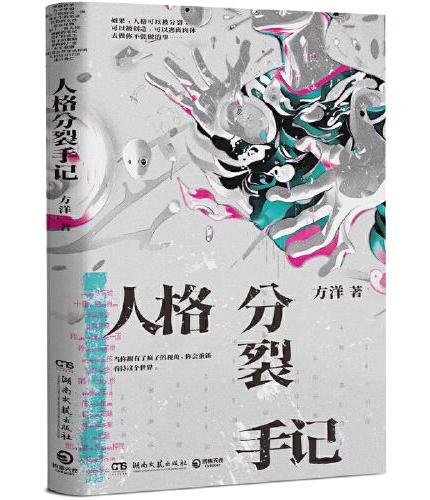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深入浅出人工智能
》 售價:HK$
75.9
《
成长的心智——重新思考时代与心灵
》 售價:HK$
96.8
《
外卷: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全球征途
》 售價:HK$
140.8
《
家庭心理健康指南:解决孩子成长中的棘手问题
》 售價:HK$
65.8
《
创作经典
》 售價:HK$
140.8
《
西方殖民帝国的崛起(1492 - 1914)
》 售價:HK$
96.8
《
ChatGPT数据分析实践
》 售價:HK$
108.9
《
人格分裂手记
》 售價:HK$
54.8
編輯推薦: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內容簡介: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關於作者: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廷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
目錄
章冬至1
內容試閱
章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