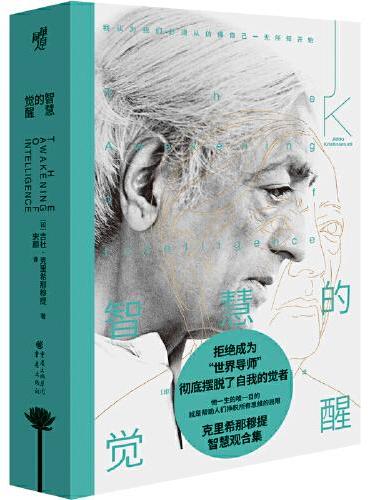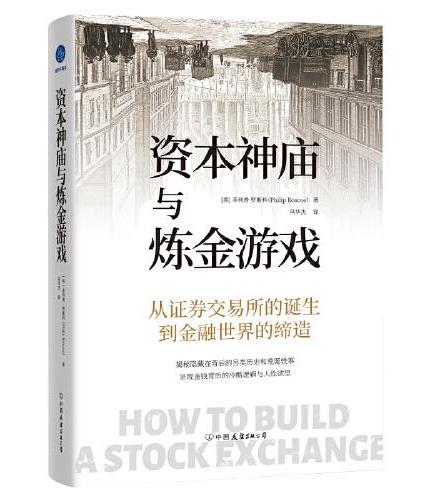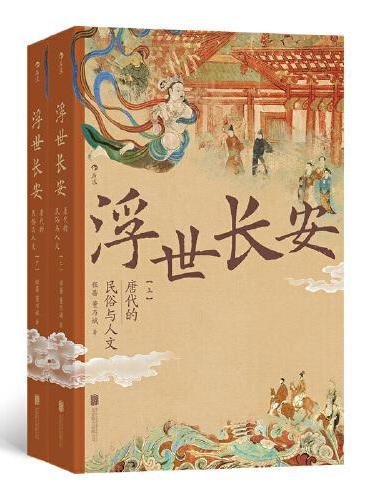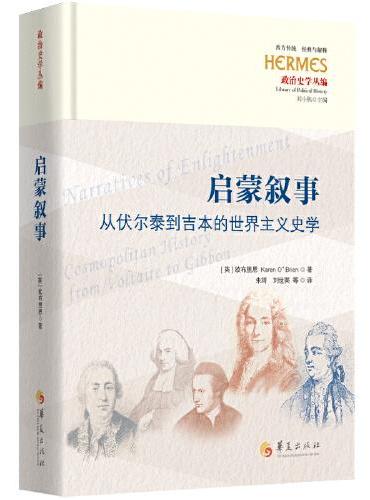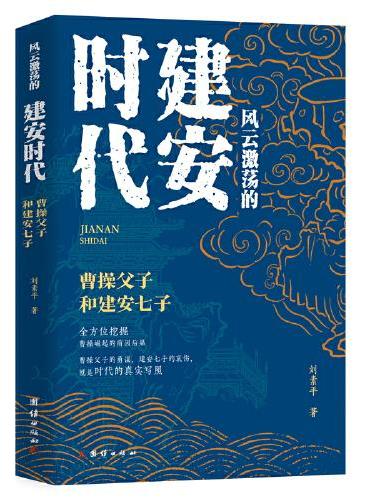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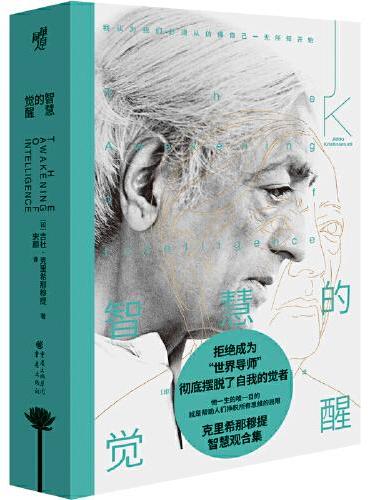
《
智慧的觉醒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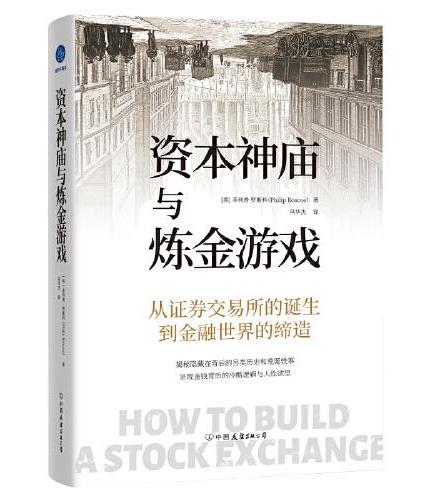
《
资本神庙与炼金游戏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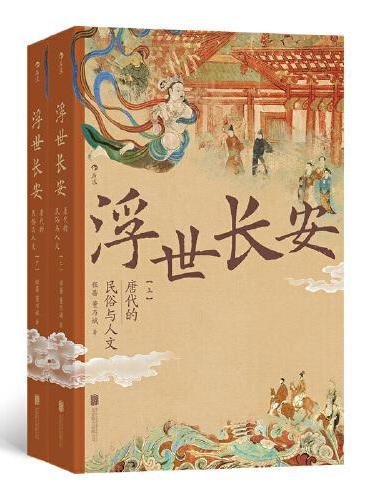
《
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
》
售價:HK$
140.8

《
怀忧终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
》
售價:HK$
53.9

《
生命合伙人Ⅲ:AI时代艺术思维引爆创造力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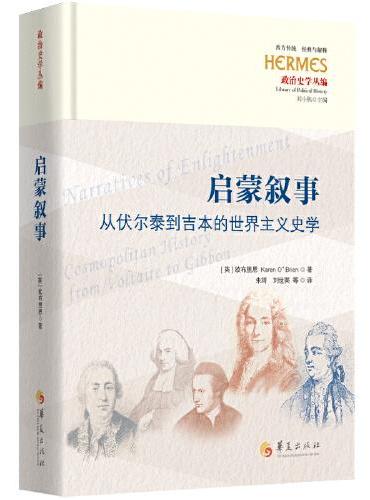
《
启蒙叙事: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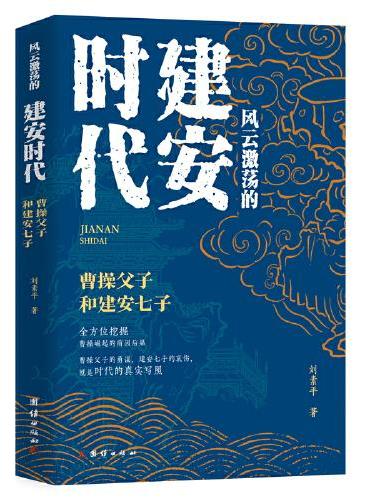
《
风云激荡的建安时代: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
》
售價:HK$
74.8

《
人生几何时:中国古代的才女与美女
》
售價:HK$
53.9
|
| 編輯推薦: |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一:
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大屠杀文化中的圣人让埃默里书写的一份超越问责与救赎的人性诊断。灾难过后,死亡营幸存者如何真正生还?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倾力推介。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二: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三:
埃默里说: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歪曲。
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
| 內容簡介: |
|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
| 關於作者: |
|
让埃默里(Jean Amry,19121978),原名汉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并在这座城市学习了文学和哲学。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埃默里在一家瑞士德国报社做记者谋生。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维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并因此广为人知。后又出版数本著作,包括他最著名的哲学论著《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1978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
| 目錄:
|
代序:理解他人的可能与不可能 杨小刚
1977年新版前言
1966年初版前言
精神的界限
酷刑
人需要多少故乡?
怨恨
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1977年新版前言
本书完稿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并不好过。只需要关注大赦国际的报道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之可怖堪比历史上最糟的那段时期,那段既实实在在又疯狂无比的时期。人们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希特勒死了反而获胜了。入侵、攻伐、酷刑,将人彻底消灭,事情够多了。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智利,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强制迁徙,苏联的矫正中心,巴西和阿根廷的谋杀令,某些自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拆穿了自己的谎言,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反思第三帝国受害者的非人处境还算什么?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者,至少要把我的文章重新修订一遍吧?
然而,在重读当年写下的东西时我发现,修订可能只是一个小伎俩,是为了时效性而付出的新闻式的代价。我不想修改这里说过的任何东西,只想略做补充。毫无疑问,无论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恐怖,那些事实都无法被消除。尽管出版了许多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非常用心,类似的著作还将继续出版,但对我来说那些事实仍然没有得到解释,很可能它们根本没法解释: 19331945年,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在一个具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工业生产力和举世无双的文化财富,也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里,发生了那些我所记录下的事情。
将一切归结为单一原因的解释一点不起作用,甚至十分可笑。说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的象征编码中包含的是自路德以来,经过克莱斯特( Kleist)和保守革命,直到海德格尔的德国精神史中已然存在的东西,说什么德意志的民族性格,这些都毫无意义。为了理解事实也不能就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说《凡尔赛和约》将整个民族逐入纳粹牢笼的经济危机,这都是幼稚的借口。 1929年之后,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失业人员,比如美国,但那里没有产生希特勒而产生了罗斯福。色当战役之后,法国也接受了不光彩的和平,也有查尔斯毛拉[1]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法国历史上令人瞩目的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对抗日益膨胀的军方势力、守卫共和国的人们。吉斯林、穆瑟特、德雷勒和莫斯利[2]都不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不是靠从一所可敬大学的校长到大城市贫民窟里每一个可怜的家伙都为他们欢呼来获得权力的。是啊,波茨坦集会[3]举行时,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在欢呼,全然不顾之前的选举结果。我就在那里。意气风发的年轻政治学家们不要向我讲述被他们的概念扭曲了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而言,他们的解释都显得格外荒谬。
历史写作只看到了个别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见第三帝国的德意志森林。如此一来,历史自身作为概念也变得不合适了,我想到的只有列维-施特劳斯(L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esauvage)中的一句话:在物理因果链中,一切历史事件最终都消解了,历史一词根本没有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对象。
一方面,在德国爆发的极端之恶实际上从未被解释清楚;另一方面,这种恶事实上就其全部的内在逻辑和让人诅咒的合理性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还原。尽管有智利、巴西,有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强制迁徙,尽管有苏加诺( Bung Sukarno)对上百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屠杀[4]和希腊军政府成员的暴行。正因此,我们依然面对一个阴暗的谜题。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像法国的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那样为了生存而进行血腥杀戮的革命。这发生在德国。它仿佛从母腹里直接生产出来,是一个反自然的产物。所有经济的解释,所有让人失望的单向度的解释,比如说,德国工业资本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赞助了希特勒,都没有告诉见证者任何东西,就像关于启蒙辩证法的精致思辨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东西。
所以十三年前,我没有致力于做什么解释,今天,同样的,我也唯有呈上我的证词。而且此刻就和以前一样,关乎我思考的不是第三帝国。我要考虑的,我有资格说的,是这个帝国的牺牲品。我不会给他们立纪念碑,成为牺牲品根本不是什么荣耀。我只想描述他们的处境,他们无法改变的处境。所以,我让 1966年首次出版的文字一如其旧。仅仅在《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一章中添加了一件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琐事,今天这个时刻需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当我写下这些文章时,一切已经结束,反犹主义在德国已不复存在,更准确地说,在反犹主义仍未灭绝的地方,它也不敢贸然出头。人们绝口不提犹太人的事情,或者用一种喋喋不休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us)来挽救自己。对诚实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种痛苦,而对不太诚实的受害者的存在不容忽视一个良好的机会,一个与德国人可悲的良知打好交道的机会。事过境迁,一种新旧混杂的反犹主义如今又厚颜无耻地探出头来,只不过尚未引起众怒。顺便一提的是,不仅在德国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均如此,鲜有例外,除了正直的荷兰,在此必须将其作为榜样明确提出来。受害者们死去了,这样很好,长期以来就如此,他们是多余的;刽子手们也一命呜呼,这样也好,符合生物死亡的规律。然而两个阵营里的新一代都在持续增长,在分别被出身和环境烙印的两方之间,又再次产生古老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确定,时间总有一天会弥合它。但弥合不可以是无心、无脑、大错特错的宽恕,这种宽恕如今已在加速成形。相反,既然这是一条道德鸿沟,就让它暂时保持裂开的状态,这也是新版的意义所在。
我关心的,是德国青年一代,是那些好学、慷慨、追求乌托邦的左翼青年,不要毫无防备地倒向他们的,也是我的敌人。这些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法西斯主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只是把没有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网格罩在现实上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迫切需要改善的现实虽然掩藏了诸多让人愤怒的不公,比如被称为《对极端分子公告》[5]的法案,但这个现实并非因此就是法西斯的。
联邦德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曾受到严厉的威胁,正如每一个民主制度国家经常遭遇的那样。这是它的风险,它的危险,它的荣耀。人们必须保持清醒,这一点没有谁比那些不得不亲眼看见德意志自由的崩溃的人更了解。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同样很了解,清醒不能在偏执狂式的状态中被葬送,这种状态不过助长了那些想要用粗壮的屠夫之手扼杀民主自由的人的气焰。而当德国年轻的左翼民主人士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一个半法西斯化的社会样本,而且一股脑儿地把所有被他们叫作形式化民主的国家在这之中首先是面临可怕危险的袖珍国家以色列都视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以相应的方式对待之,那么每一个经历了纳粹恐怖、同处这个时代的人就站在一个关口,在这里他有义务参与进去,无论他的参与会引起什么反应。当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那老一套可恶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时,那些既是政治犯也是犹太人的纳粹受害者我曾经和现在都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不能沉默。做犹太人的不可能变成了做犹太人的必然,准确地说,是做一个激烈抗争的犹太人。所以,但愿这本以极不自然的方式既过时又适合当下的书,不仅成为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和独一无二的纳粹是什么样子的见证,也成为对德国年轻人自我确定的呼吁。反犹主义具有一种深深植根于集体心理的基础结构,在层层分析后还可能还原至被压抑的宗教敏感和怨恨。它每时每刻都可以更新。当我得知,在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公告中,不仅犹太复国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理解这个政治概念)被当作世界的瘟疫而受诅咒,而且群情激昂的年轻反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一句有力的口号宣告了自己主张犹太人去死!我虽深深惊恐,但并不惊讶。
|
|